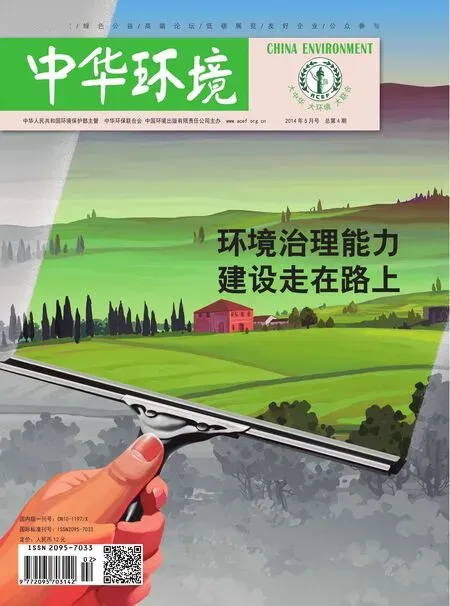理性參與是環保NGO的基本態度
竇麗麗 達爾問環境研究所理事
理性參與是環保NGO的基本態度
竇麗麗 達爾問環境研究所理事
最近幾年,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各地公眾成為這些事件的主角。這一方面說明了公眾環保意識的不斷提升,另一方面也說明,公眾的環保意識正在轉化成自發的環保行動。在關注這些群體性事件的同時,很多人也注意到,在這些事件中,幾乎沒有見到環保NGO的身影。在重大環保事件中的“缺位”,也讓環保NGO們受到了不少質疑。
事實上,這些對環保NGO的質疑多少有失公允。
首先,這些重大的環境突發事件對環保NGO的能力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從1991年中國第一家民間環保組織——盤錦黑嘴鷗保護協會成立至今,中國的民間環保事業已經走過了23個年頭。這23年里,涌現了不少活躍的民間環保組織,他們在提升公眾的環境意識、推動環境政策法律的改進以及推動一些重大環境事件的解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民間環保的力量依然非常弱小。很多環保組織依然無法注冊,只能以“環保志愿者小組”的形式開展活動;有的環保組織無奈選擇工商注冊;也有的環保組織明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活動,但卻只能在區縣一級的民政部門注冊,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民間環保組織工作的開展。另外,很大一部分的環保組織工作內容仍然以“開展環境教育、宣傳,提升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為主,沒有發展到參與環境治理的層面,也缺少參與環境治理的能力。
其次,即便是有參與能力的環保NGO,其在這些突發環境事件上的缺位也并非“主觀故意”。這些環境事件大都事發突然,發展迅速,結束的也很快。相關信息剛剛傳播開來,當地政府就已經做出表態。事件的熱度升得快降得也快。環保NGO甚至來不及做出反應,事情就已經結束了。而環保NGO要參與一個環境事件的解決,首先需要了解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然后才能決定是否參與以及如何參與其中,而這通常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最后,在有些環境事件中,環保NGO是有參與的,只是這種參與比不上“街頭散步”那么吸引眼球,得到的關注較少罷了。在2013年的昆明PX事件中,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就采取了信息公開、行政復議等方式參與其中。
2013年6月底,自然之友向環保部申請《中國石油云南1000萬噸/年煉油項目環境影響報告》及其批復。之后,環保部公開了該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的全本及其批復。自然之友發現,該環評報告缺少公眾參與部分,遂聯合多家環保組織向環保部遞交行政復議申請書,要求撤銷該批復;環保部以“申請人與該行政審批行為無利害關系”為由不予受理。同時,自然之友還向發改委申請公開“中國石油云南1000萬噸/年煉油項目核準文件,國家發改委報請國務院核準該項目的依據,建設單位提交的項目申請報告、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工程咨詢機構對項目申請報告、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的意見”。發改委回復稱“申請涉及第三方,需征求第三方意見,因此在15個工作日內不能答復”,此后便再無消息。
雖然自然之友的行動沒有產生直接的結果,但是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續的公眾行動。此后,安寧市連然街道的羅庭艷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環保部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關于中國石油云南1000萬噸/年煉油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的批復》(環審【2012】199號,以下簡稱199號批復)被受理;2014年4月19日,戶籍地在昆明主城區的鐘峪女士,鑒于向環保部申請行政復議未獲支持,又向國務院法制辦申請最終裁決,要求撤銷199號批復。

自然之友舉辦環保民間組織法律倡導行動分享會。 自然之友/供圖
應該說,昆明PX事件之所以較其他各地的群體性事件更為理性、有序,環保NGO的參與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
自然之友參與昆明PX事件秉持著這樣的理念:環境問題不能依靠沖突來解決,而應該遵循法治路徑,理性表達訴求。從自然之友對昆明PX事件的參與來看,環保NGO既是在回應著公眾對“NGO在重大環境事件中缺位”的質疑,同時也在尋求用一種理性、平和的方式參與重大環境事件的推動和解決。
事實上,中國環保NGO參與環境治理一直都堅持理性、合法的基本原則,相關的案例俯拾皆是:2005年,針對“圓明園湖底大面積鋪設防滲膜”一事,自然之友等多家民間環保組織呼吁圓明園管理處盡快委托具備資質的環評部門針對此事開展環境影響評價,并吁請環保部門針對環評報告書召開聽證會,最終促成了圓明園聽證會的召開;2007年,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聯合多家環保組織發起了綠色選擇倡議,并據此建立了綠色選擇聯盟的供應鏈管理體系,將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激發的動力,通過領先企業傳遞到龐大的全球供應鏈條,從而調動市場力量,推動環境保護進程;2009年,自然之友上海小組介入富國皮革污染事件,通過申請信息公開、現場調研等多種方式向富國皮革施加壓力,促使富國皮革不得不開始有所動作。而這些行動逐漸演化為社區居民、環保NGO與污染企業間的良性互動,促使事態向著有利于居民訴求得到正當申張、企業開始整治、生態環境有所改善的善治方向發展。2011年,針對云南曲靖鉻渣污染事件,自然之友聯合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發起了公益訴訟,這一案件成為首例由草根民間環保組織發起的環境公益訴訟;達爾問環境研究所自2009年成立以來,一直開展電磁環境科普工作,通過實地檢測,消除公眾對電磁輻射的擔憂和恐慌;綠色漢江自成立以來,在開展環境宣傳教育的同時,始終關注漢江兩岸的污染狀況,定期開展調研活動,并和當地政府、媒體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溝通與互動,推動了多起污染事件的解決。
近幾年,隨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后果逐漸顯現,對環保NGO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來越多的環保NGO不再滿足于將工作停留在開展環境宣教的層面,而是開始尋求更深層次的參與環境治理。這種深層參與包括推動具體的環境污染事件的解決,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參與重大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提出政策建議,影響環境決策,參與法律法規的制定與修訂,引導公眾遵循法律途徑解決環境問題等。所有這些參與都是以理性、合法為基本前提。
可以說,理性參與環境治理是環保NGO的基本態度,目前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斷提升環保NGO理性參與環境治理的能力。NGO業內一直有一些能力建設項目,比如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舉辦的環境信息公開培訓,自然之友舉辦的重金屬污染法律倡導工作坊,都是為了提升環境NGO參與環境治理的能力。除了自身的能力建設,環保NGO也需要更多法律、環境等專業人士的支持,更需要政府能夠給予環保NGO更多的參與空間和參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