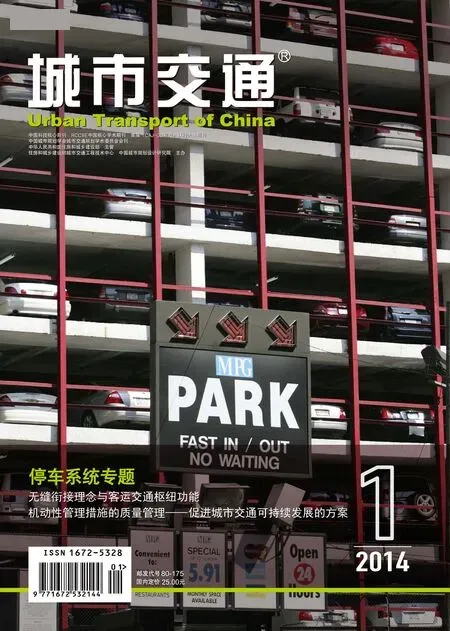無縫銜接理念與客運交通樞紐功能
(上海市城市綜合交通規劃研究所,上海200040)
1 客運交通樞紐與無縫銜接
客運交通樞紐是交通方式多元化和線路網絡化的產物,是多種交通方式實現分工協作和交通網絡達到一定規模后,無法滿足所有出行者直達的要求,為了提高網絡整體交通效率和可達性而形成的斷裂點。這些斷裂點不可避免地存在縫隙,造成乘客出行過程中的換乘損失,如換乘距離遠、換乘時間長、換乘條件差等,給乘客出行帶來不便。交通網絡越大、交通方式越多,斷裂點就會越多、縫隙就會越大。為了減少客運交通樞紐縫隙及其負面效果,無縫銜接逐漸成為共識。但何謂無縫銜接,社會各界卻存在不同的認識和看法。
以港鐵的同臺換乘為例,兩條線路換乘多采用兩線平行一段的設計,將常見的十字型換乘分解在兩個車站,每個車站均為上下島式站臺,站臺寬度即為換乘距離。這一無縫銜接的典型案例,卻引發越來越多的質疑之聲。很多人懷疑島式站臺的蓄流能力不足,無法應對緊急狀態下(節假日極端高峰客流、列車延誤引起的客流積聚等)的潛在風險,認為無縫銜接不表示也不能是零距離換乘,應從運營安全的角度,有意拉開距離,留出緩沖過渡區。可見,對于什么是“無縫”、怎樣做才能“無縫”,業內仍然存在分歧,在貌似共識的情形下各執一詞,看法甚至截然相反,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
在香港應用非常成功的同臺換乘,用到內地就會出現“水土不服”?實際上,同臺換乘是將兩條線路換乘4對方向的換乘量分散在2個車站、每個車站上下2個島式站臺上(見圖1),即每個島式站臺只承擔1對方向的換乘量,加上運營組織的協調,保證了運行安全,而且后期建設的軌道交通線路,也根據客流強度對站臺進行了加寬。同臺換乘可以保證安全,兩者并不是對立或沖突的關系。相比而言,十字型換乘的進出站客流和換乘客流相互交織,在樓梯口擁堵,反而容易引起踩踏事故。內地城市正逐漸引入和推廣同臺換乘的設計理念,如杭州市地鐵1號線與3號線換乘站(武林廣場站和西湖文化廣場站)、1號線與4號線換乘站(火車東站站和彭埠站),組成兩組“連續兩座同臺換乘車站”,能實現全部方向的同臺換乘;北京市地鐵6號線與8號線換乘站(南鑼鼓巷站)為上下島式站臺,4號線與9號線換乘站(國家圖書館站)為同平面雙島式站臺,能實現2對方向的同臺換乘。

圖1 港鐵太子站和旺角站Fig.1 MTR stations Prince Edward and Mong Kok

圖2 客運交通樞紐無縫銜接的目標Fig.2 The objective of seamless connection within passenger transport terminals
2 客運交通樞紐的功能
要理解無縫銜接在客運交通樞紐規劃設計中的權重,首先需要厘清其功能。客運交通樞紐是綜合交通網絡中客流中轉、集散的場所,具有中轉換乘、多式聯運功能;樞紐往往與場站結合在一起,具有運輸組織功能;樞紐對周邊土地開發、產業聚集具有帶動作用,樞紐地區不再是單一的交通空間,同時也承載了經濟服務的功能,是綜合的城市功能混合區。因此,客運交通樞紐的功能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換乘銜接功能,將各種交通方式、各條線路所承載的交通活動聯結成一個整體。2)運輸組織功能,包括車輛調度管理和停車服務等功能。3)引導開發功能[2],包括直接和間接的引導開發,前者指樞紐配套的商業開發,為乘客換乘過程提供游憩服務;后者指憑借樞紐的區位優勢,刺激土地開發,提高土地利用強度和利用效率,引導城市空間結構拓展。
換乘銜接功能是客運交通樞紐的首要功能,是立足之本。運輸組織功能放到客運交通樞紐中,只能是附屬功能,服從于換乘功能。引導開發功能是客運交通樞紐的派生功能,不能因開發而使換乘場地縮水。雖然客運交通樞紐建設的初衷,不僅在于提高交通方式及不同線路之間的銜接效率,也在于對周邊土地開發和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然而,過多強調宏觀層面的引導開發功能、強調客運交通樞紐地區的用地和產業規劃,對最基本、最核心的換乘功能重視不夠,導致換乘功能的薄弱,反過來會制約和削弱引導開發功能。正因如此,中國很多改擴建的客運交通樞紐,未能徹底解決樞紐地區交通混雜的面貌,帶動的也只是低檔次的商業發展。
3 無縫銜接的目標
無縫銜接是客運交通樞紐換乘銜接功能的核心理念,是實現樞紐整體功能的關鍵。無縫銜接的目標是換乘綜合成本系統最優,包括“距離、服務、時間、費用”4個方面,見圖2。
1)客運交通樞紐涵蓋的各種交通方式分屬不同的行業主管部門,為便于管理,往往相互分割,各自為政,自成系統,無形中擴大了樞紐的“縫”[3]。無縫銜接首先要減少“距離上的縫”,通過優化空間布局,縮短換乘距離。
2)相互分割也很容易造成露天的、長距離的通道換乘,嚴重降低換乘品質。無縫銜接要減少“服務上的縫”,換乘要在“同一個屋檐下”進行,免受露天日曬雨淋等惡劣條件的影響,而且換乘設施要有一定的服務水平,提高換乘過程的舒適性。
3)換乘時間的損失除了換乘距離消耗的行走時間和通道擁擠引起的附加延誤,主要是運行組織不協調造成的時間損失。無縫銜接要減少“時間上的縫”,所謂公交化運營、時刻表準點,其實都是為了減少時間損耗。
4)客運交通樞紐為調整和優化線網提供條件,犧牲網絡直達性來保障全網可達性,在降低運營成本的同時,增加了乘客的出行成本[4]。現有的換乘優惠實際上是換乘補償,是利用票價機制彌補換乘損失,換乘次數越多,補償力度應該越大。無縫銜接要減少“費用上的縫”,通過價格上的換乘優惠、換乘補償,彌補乘客損失的出行成本。
4 相關建議
針對4類客運交通樞紐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例,闡述如何利用無縫銜接理念增強樞紐換乘銜接功能。
1)對外綜合交通樞紐要銜接內外兩張網、優化內部換乘。
樞紐要達到一定的規模,對城市經濟的拉動效益才會顯現。為了實現空鐵聯運、擴大樞紐能級和輻射范圍,同時受中心城區土地資源緊張和土地成本昂貴的制約,中國很多城市將高鐵站和機場組合在一起,置于城市邊緣,滿足了空鐵聯運的運輸組織需要。對于空鐵競爭的線路,為乘客提供了更多的出行選擇;對于空鐵互補的線路,擴大了空港的腹地范圍。同時,也實現了引導開發功能,邊緣型樞紐憑借可達性和集聚效應,成為城市新的增長極,促進了城市多中心結構形態的形成[5]。
由于樞紐位于城市邊緣,中心城區方向集疏運距離遠、時耗長。發展快速軌道交通是消除空鐵兩端接駁交通瓶頸、滿足樞紐快速集疏運的關鍵舉措。在樞紐內部,由于涵蓋的交通方式多、空間尺度大、結構復雜,容易導致換乘距離過長、換乘流線復雜。控制樞紐合理的規模、內部布局緊湊、發展樞紐內部公共交通系統,都是比較常見的做法。已投入運營的樞紐,要優先保障換乘場地。以上海市虹橋樞紐磁懸浮站為例,由于種種原因,磁懸浮站一直處于擱置狀態,可以考慮引入西南(湖州、宣城方向)和北面(南通方向)的鐵路通道,以及浦東磁懸浮線路的延伸線或快速軌道交通線路,減小樞紐縫隙,縮短換乘距離,而不是開發商業,擴大樞紐縫隙。通過增強樞紐換乘功能,更好地實現引導開發功能,例如虹橋商務區的崛起、上海西部新城帶形成、上海中心城西擴和長三角城鎮群推進,都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2)軌道交通樞紐要優化軌道交通和公共汽車交通銜接的便捷性。
城市軌道交通與常規公交都擁有龐大的客運量和客運能力,兩者間銜接程度對城市公共交通網絡的運營效率起決定作用。中國很多城市在軌道交通與常規公交兩個網絡的融合問題上,圍繞軌道交通車站的常規公交接駁服務水平一般不理想。如在商業核心區,土地價值高,公交樞紐缺少用地保障,位置往往偏離客流中心,并與核心區內的軌道交通車站相距較遠,這種樞紐的換乘功能屈從于運輸組織功能,貌似是樞紐,實際上已經淪為純粹的公交停車場、首末站,將客流強行運輸到這里,無法滿足乘客實際的換乘需求。
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地鐵站,公共汽車直接開進地鐵車站的付費區。德國則規定地鐵出入口30 m范圍內布設公共汽車站。可見,縮短軌道交通與公共汽車交通的接駁距離,加強兩者無縫銜接,是提高軌道交通與常規公交兩個網絡融合水平的重要途徑。
3)常規公交樞紐要優化線網和車站布設。
常規公交樞紐的問題主要是線路集中布設在主干路、重復系數高,與此同時,次、支道路上線路少、線網密度低、可達性差。同一個車站集中的線路過多,表面上有利于換乘,實際上,為了滿足車輛進站停靠需求,站臺很長、車輛進站時排長隊,是導致高峰時段道路擁堵的因素之一。乘客換乘奔前跑后,乘車秩序混亂,安全隱患大。
道路網是公共汽車線路布設的基礎。結構合理的道路網,有利于本地交通流和過境交通流的組織和疏散,也有利于公交線網的布設。其次,公共汽車線路要分層、分級,既要有為中長距離出行服務的主要線路,實現“快速、高效”;也要有為短距離出行服務的次要線路,實現“方便、易達”。不同等級的公共汽車線路,宜布置在不同等級的道路上:交通性主干路可布置大站快線,生活性主干路可布置干線,次干路和支路布置普線。
4)停車換乘樞紐要創造條件,發揮P&R的比較優勢。
影響P&R停車場使用率的主要因素是周邊居住人口密度、軌道交通乘坐舒適度(位于首末站的效果最好)、換乘服務水平(換乘距離短、換乘條件好、有換乘優惠的效果最好)、目的地方向道路交通狀況、目的地停車位供應與收費情況[6]。
提高小汽車P&R停車場的吸引力,需要在距離、服務、時間、費用等方面,使“軌道交通+小汽車”組合出行優于小汽車出行。首先,P&R停車場與軌道交通車站要緊密銜接,縮短步行距離,優化步行環境;選址在軌道交通大小交路的首末站,既有用地保障,又能提供較好的乘坐舒適度;提高軌道交通運營速度,如采用快線形式,降低軌道交通出行時耗;最后,對停車費實行優惠減免,從而提高與小汽車交通的競爭力。
5 結語
客運交通樞紐的建設及樞紐地區的綜合開發,是發揮多種交通方式綜合效益、方便乘客出行的必然要求,也是發揮樞紐區位優勢、發展城市經濟、集約土地資源的必然趨勢。客運交通樞紐的發展趨向于交通方式綜合化、樞紐功能多元化,這就要求在樞紐的規劃、設計、運營中要理順三種功能的分層和相互關系,始終不渝地體現無縫銜接的理念,提高出行者在網絡中的易達性,并通過提升換乘功能增強客運交通樞紐的整體功能。
∶
[1]葉霞飛,譚復興.城市公交的換乘與接駁[J].城市軌道交通研究,1998,1(3):22-25.Ye Xiafei,Tan Fuxing.The Transfer and Lighter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J].Urban Mass Transit,1998,1(3)∶22-25.
[2]葉冬青.綜合交通樞紐規劃研究綜述與建議[J].現代城市研究,2010,25(7):7-12.YeDongqing.Integrated-Transport-Hub Planning∶Retrospect and Agenda[J].Modern Urban Research,2010,25(7)∶7-12.
[3]潘昭宇,孫明正,劉瑩,劉雪杰,余柳,白同舟.基于城市功能整合的“樞紐區域”研究[J].城市交通,2013,11(1):40-48.Pan Zhaoyu,Sun Mingzheng,Liu Ying,Liu Xuejie,Yu Liu,BaiTongzhou.Transit ExchangeTerminalBased on Integrated Functionality ofUrban Development[J].Urban Transport of China,2013,11(1)∶40-48.
[4]陳琛.城市公共交通換乘系統研究[D].南京:東南大學,2004.Chen Chen.Study on the Change System of Urban Public Passenger Transport.Nanjing∶Southeast University,2004.
[5]鄭德高,杜寶東.尋求節點交通價值與城市功能價值的平衡:探討國內外高鐵車站與機場等交通樞紐地區發展的理論與實踐[J].國際城市規劃,2007,22(1):76-80.Zheng Degao,Du Baodong.Looking for the Balance Between Transport Value of Node and Functional Value of City∶Discuss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irport Area and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Area[J].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07,22(1)∶76-80.
[6]上海城市綜合交通規劃研究所.上海市停車換乘P+R停車場運行情況評估[R].上海:上海城市綜合交通規劃研究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