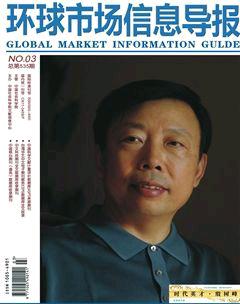政府行為對(duì)激發(fā)社會(huì)組織活力的影響及對(duì)策
關(guān)耀強(qiáng)
我國(guó)政府行為深刻影響著社會(huì)組織的壯大和健康發(fā)展,當(dāng)前,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中存在低效率與活力不足等各種問(wèn)題,與背后政府行為供給、行為反應(yīng)度、作用效果等有直接的關(guān)系。激發(fā)社會(huì)組織活力,促進(jìn)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政府可以選擇規(guī)范社會(huì)組織培育扶持機(jī)制、依法加強(qiáng)社會(huì)組織監(jiān)管、著力培育公民社會(huì)等行為對(duì)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指出,“要改進(jìn)社會(huì)治理方式,激發(fā)社會(huì)組織活力” [1]。政府與社會(huì)組織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的基礎(chǔ)并不是社會(huì)組織對(duì)政府的依附和歸順,也不是政府統(tǒng)管社會(huì)組織。相反,社會(huì)組織要保持自身的獨(dú)立性。在法律上兩者是平等的,是指導(dǎo)與被指導(dǎo)、扶持與被扶持且相互監(jiān)督的關(guān)系。因此,探究政府行為與社會(huì)組織關(guān)系及影響,對(duì)激發(fā)社會(huì)組織活力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政府行為影響社會(huì)組織活力關(guān)系分析
政府行為供給與社會(huì)組織需求關(guān)系分析。政府行為的干預(yù)大小,相對(duì)于社會(huì)組織而言,才具有實(shí)質(zhì)性的意義。也就是說(shuō),社會(huì)組織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一政府行為的作用程度。如圖1所示:
圖1政府行為供給與社會(huì)組織需求關(guān)系分析圖
社會(huì)組織的需求度,可以從0—100劃分為不同等級(jí),這些等級(jí)社會(huì)組織自身發(fā)展階段的影響面、周圍社會(huì)環(huán)境等因素所決定。處于較低等級(jí)上的社會(huì)組織需求屬于弱程度范圍,而處于較高等級(jí)上的社會(huì)組織需求則屬于強(qiáng)程度范圍。同樣,政府的行為供給度也從0—100劃分為不同的等級(jí),表現(xiàn)為弱行為供給度和強(qiáng)行為供給度。我們認(rèn)為針對(duì)強(qiáng)程度需求,政府強(qiáng)的行為供給也是一種供需平衡的表現(xiàn),可稱為強(qiáng)平衡。除此,如果針對(duì)弱程度的需求,政府作出強(qiáng)行為,而針對(duì)強(qiáng)程度需求,政府作出弱行為,則會(huì)出現(xiàn)行為干預(yù)過(guò)度或行為供給不足的問(wèn)題,此時(shí)都是政府行為和社會(huì)組織需求出現(xiàn)不平衡,不能滿足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需要,或阻礙了社會(huì)組織的發(fā)展。
政府行為反應(yīng)度與社會(huì)組織獨(dú)立性關(guān)系分析。政府的行為必然作用于社會(huì)組織的行為,無(wú)論是限制,還是放松,都意味著社會(huì)組織自我管理因?yàn)檎袨槎{(diào)整。那么,政府行為必然有一個(gè)相對(duì)應(yīng)的社會(huì)組織獨(dú)立性的狀態(tài)。如圖2所示:
圖2政府行為反應(yīng)度與社會(huì)組織獨(dú)立性關(guān)系分析
社會(huì)組織獨(dú)立性是一條自上而下的曲線,上面部分表述獨(dú)立性小,甚至零自由,越趨于下面,表述獨(dú)立性越大,直至絕對(duì)獨(dú)立。而社會(huì)組織獨(dú)立性為零,意味著政府的行為干預(yù)過(guò)度,即完全控制社會(huì)組織的自我產(chǎn)生、自我管理、自我決策和自我發(fā)展。該文原載于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獻(xiàn)信息中心主辦的《環(huán)球市場(chǎng)信息導(dǎo)報(bào)》雜志http://www.ems86.com總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轉(zhuǎn)載須注名來(lái)源而社會(huì)組織絕對(duì)獨(dú)立性,則意味著政府沒(méi)有行為或行為不足,自我管理活動(dòng)不受政府行為的影響,此時(shí)政府行為效果為零。
政府行為作用效果與社會(huì)組織活力關(guān)系分析。從政府作用行為產(chǎn)生的效果來(lái)看,有正面和負(fù)面之分,或者有效和無(wú)效的差別,這種效果又主要通過(guò)其行為作用的對(duì)象反應(yīng)出來(lái)。因此,社會(huì)組織面對(duì)政府行為的作用效果,一方面,會(huì)因政府行為供給的恰當(dāng)和充足,而獲得快速和健康的發(fā)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yàn)檎袨楣┙o不足、混亂和過(guò)度,而阻礙了其發(fā)展進(jìn)程,甚至造成負(fù)面作用阻礙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
如圖3所示:
社會(huì)組織的每一步發(fā)展都會(huì)受到制度環(huán)境的直接影響。適宜的制度環(huán)境能促進(jìn)其健康發(fā)展,而不合適的制度環(huán)境則會(huì)阻礙其發(fā)展。[2]激發(fā)社會(huì)組織活力,政府需要作出行為,但政府行為反應(yīng)的快慢、正確與否,結(jié)果均有所不同。不同的政府行為,直接的后果就是促進(jìn)社會(huì)組織的發(fā)展,或是阻礙社會(huì)組織的發(fā)展。
三、激發(fā)社會(huì)組織活力的政府行為對(duì)策
規(guī)范社會(huì)組織培育扶持機(jī)制。傳統(tǒng)的政府以社會(huì)控制為執(zhí)政理念,致使社會(huì)組織在與政府的交往和互動(dòng)中處于不利的不公平地位。進(jìn)一步規(guī)范社會(huì)組織培育扶持機(jī)制,這需要從以下幾點(diǎn)進(jìn)行努力:一是加快政府職能轉(zhuǎn)移,確立社會(huì)組織的法人主體地位,促進(jìn)社會(huì)組織依法自治并獨(dú)立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二是完善財(cái)稅支持政策,建立政府向社會(huì)組織購(gòu)買公共服務(wù)制度,將符合條件的社會(huì)組織納入政府產(chǎn)業(yè)扶持和社會(huì)事業(yè)發(fā)展扶持政策范圍。[3]三是保障社會(huì)組織合法權(quán)利,將符合條件的社會(huì)組織納入政府產(chǎn)業(yè)扶持和社會(huì)事業(yè)發(fā)展扶持政策范圍。
依法加強(qiáng)社會(huì)組織監(jiān)管。
社會(huì)公益和社會(huì)責(zé)任是社會(huì)組織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fù)著的使命,對(duì)社會(huì)組織的監(jiān)管應(yīng)將重點(diǎn)放在完善的社會(huì)問(wèn)責(zé)和評(píng)估制度上,并以此建立好“五道防線”,樹立社會(huì)組織良好的公信力。第一是政府的監(jiān)督;第二是獨(dú)立的第三方對(duì)社會(huì)組織分類評(píng)估;第三是社會(huì)組織自律與同行互律;第四是媒體與公眾的監(jiān)督與評(píng)估;第五是規(guī)范引導(dǎo)社會(huì)組織涉外活動(dòng)。通過(guò)加強(qiáng)對(duì)社會(huì)組織的監(jiān)管,提高其自身社會(huì)公信力和權(quán)威,最終達(dá)到改善政府對(duì)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中的行為選擇。
著力培育公民社會(huì)。近年來(lái),我國(guó)的社會(huì)組織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依然面臨著社會(huì)大眾普遍沒(méi)有完成從“人民”到“公民”身份的轉(zhuǎn)變的意識(shí)困局。而要想解決此問(wèn)題,最有效的途徑是培育和弘揚(yáng)民主意識(shí)的公民社會(huì)。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入手:第一,借助網(wǎng)絡(luò)推手,培育現(xiàn)代政治文化;第二,以法治精神構(gòu)建公民社會(huì)的理性規(guī)則秩序;第三,培育和壯大社會(huì)中間階層,促進(jìn)社會(huì)階層結(jié)構(gòu)“橄欖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