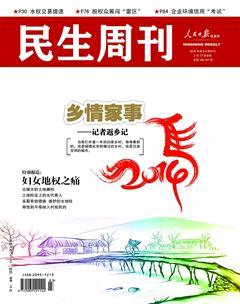老糝湯店與千尺高樓
劉偉鵬
我們找到的那個新建的店,又寬大大,四壁都是玻璃,里頭五光十色,一碗碗湯,成了流水線出來的產品。妻子說:“算了,我們回吧。”
和朋友聊天,聽說了一件事,說山東濟寧這個巴掌大的城市要建一座高樓,高超300米,要與北京、上海看齊。
建高樓的那塊地方我很熟,我妻子小時候就在那兒生活過。那兒有個賣糝湯的老店,每天天不亮,人們就排老長的隊,拿著鐵盆瓷碗過來打一份湯,再就著蔥香油餅,就是一份美味營養的早餐了。
前幾年有回我們經過那兒,妻子給我看,遠遠的一片白霧,那是湯鍋翻騰起來的水汽。骨頭、羊肉和麥仁配大料、蔥姜熬出來的汁水,香味穿過了整個青石板巷。
妻子去外地上學前,是那兒的主顧,經常捧著家里的搪瓷碗排在隊伍后面,店主一家都認識她。有回她帶我去,我倆喝完湯在店門口等車的時候,突然想起好像還沒付賬。轉身問老板,老板一家正笑盈盈看著我倆,說“好像是沒,不過沒事兒,下回再說”。其實我們都知道,“下回”還指不定是什么時候呢。
這里還有另一個故事。妻子的一幫同學們,每次回鄉,下了火車都要去這兒的另一家店去吃一碗羊雜面。他們中不止一人說起過,上小學時,每天上下學要經過那兒,有時水壺里忘了帶水,就去那家店里借一杯。后來老板干脆在門口設了一個水缸,里面泡了菊花水,供孩子們打取,十多年來一直如此。
后來他們一個個離鄉,去了各個地方,再回來,也會到那兒去看看。老板仍舊認識他們,一個個還叫得上名字,水缸也還擺在那兒。這個仁義老板后來果然做大了生意,擴了店面,開了分店,但仍留著這個地方。
這天早上,妻子突然早起,說要和我去那兒看看。我倆帶了飯盆,打車找了過去。車停在一片工地前,司機說“到了”。我倆心知是找不到了。工地上只剩幾間房子立在破磚爛瓦中間,幾臺挖掘機正張著牙口圍在四周。建筑工人又黑又瘦,行為堅韌可嘆,和他們攪拌的水泥黃沙一樣沒有生氣。
我說,我們換個地方吧,別的店也有的。妻子有點難過。
我們很少回到這里,以后回來的時間可能會更少,但我們還是希望它有點原來的樣子。建那么高的樓,有什么好呢?建得和別的地方都一樣,又有什么好呢?除了面子好看點兒,還能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我們都知道,真正底子足的,是不需要用多高的樓門來撐臉面的。
在有關這個城市的論壇里,也看得到大伙對這事的態度。有人說“不是樓高一丈,面子就大一倍”,“也不是經濟好不好,要看樓高不高”。城市建得一個樣子,建樓跟種樹一樣插得到處都是,這樣有什么好?城市如人,還是應該有它自己的樣子。
也有人對建高樓表示支持,說建高樓是沒辦法的選擇,因為人都到城市里來了,城市里的地兒不夠用,就只能往上走了。
這個說法聽上去似乎有點道理,可其實經不住推敲。城市里的人越來越多,似乎只能往天上走,但問題是高樓上的人一下來,城市馬上就開堵。頂上天的大樓看上去是為城市延伸了空間,而實際上它是以暫時避開的方式繞過了最根本的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解決不了城市病的本質,更不用說高樓防火、防風、防震等棘手的問題了。
妻子倒底沒有喝到美味的湯。我們找到的那個新建的店,又寬大大,四壁都是玻璃,里頭五光十色,做湯用的是全現代化的不銹鋼廚具,一碗碗湯,成了流水線出來的產品。妻子說:“算了,我們回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