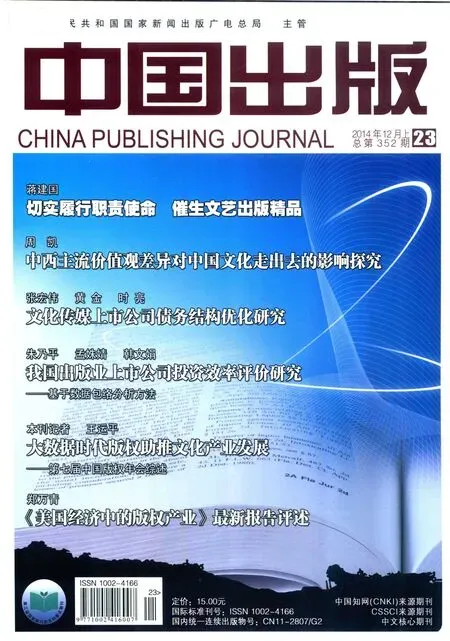實現具有文化記憶的創新*——當代書籍設計對中國傳統書籍設計的借鑒形式分析
文/秦 華
目前書籍的裝幀設計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支撐下,顯得快速而繁榮,但往往忽略了讀者的閱讀情境與感受。中國傳統書籍設計因其發展的歷程相對緩慢,會更多地保存對讀者的關注方式。從中國書籍發展的歷程看,傳統書籍設計經歷了編簡、卷軸裝、旋風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諸多樣式,盡管各種樣式的興衰都是其本身缺陷被克服的過程,但每一種完整的樣式都包含著材質與形式、功能與審美的結合,現在國內不少優秀的設計師已經關注到這點。在合理運用現代印刷技術和材料的情況下,我們能夠從中國傳統書籍設計中獲得更多的啟發。從現代書籍設計對中國傳統書籍設計的借鑒來看,一般分為三種形式:其一,對中國傳統書籍設計局部元素的挪用;其二,還原傳統式書籍形態;其三,從理解傳統閱讀體驗出發,創造出具有文化記憶恢復意義的設計。
一、對中國傳統書籍設計局部元素的挪用
傳統書籍的設計一般包含裝訂形式、版面設計、字體設計、插圖設計等元素。對中國傳統書籍設計樣式借鑒,一種原因是基于書中內容的傳統性質,書籍的主體設計是當代書籍樣式,但是會局部挪用傳統的元素,以體現書籍內容的傳統性。如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華傳世名著精華叢書》封面模仿線裝書樣式(印刷模仿,并非線裝),這種設計只為凸顯傳統內容特征,并不對書籍進行深入的設計,這是較為簡單的元素挪用(圖1)。再如黃山書社2011年出版的《徽州茶》一書(圖2)挪用的傳統元素較多,如線裝樣式、函套與書簽等,在封面設計上紅、黑、黃的基本色調總體上也能夠引起讀者對傳統文化信息的感受,但版面、字體、插圖設計為現代版式。這兩本書挪用的元素前者少,后者多,但在傳統元素挪用基礎上,還有對其他相關元素進行調整的空間。因為對傳統設計元素局部挪用,常常會與其他設計部分的不協調而導致設計的沖突,在借用傳統書籍設計元素之后,還需要對其他設計部分進行相應調整,才可能形成新的整體設計樣式,讓挪用元素變成設計中的有機部分。
比較優秀的例子如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城市文化叢書》(圖3),裝幀樣式采用了裸背裝。這種裝訂方式在挪用傳統書籍設計元素的時候較為常用,因為裸背裝在閱讀的時候,任何頁面都非常平整(尤其在設計畫冊時尤為適用)。這套叢書頁面版式上端采用了裝飾性的魚尾,書名模仿古代雕版的風格,由于整體的協調,讀者能夠感受到各種元素帶來的傳統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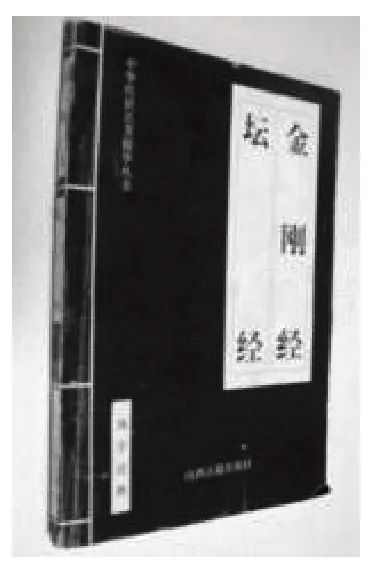
圖1 《中華傳世名著精華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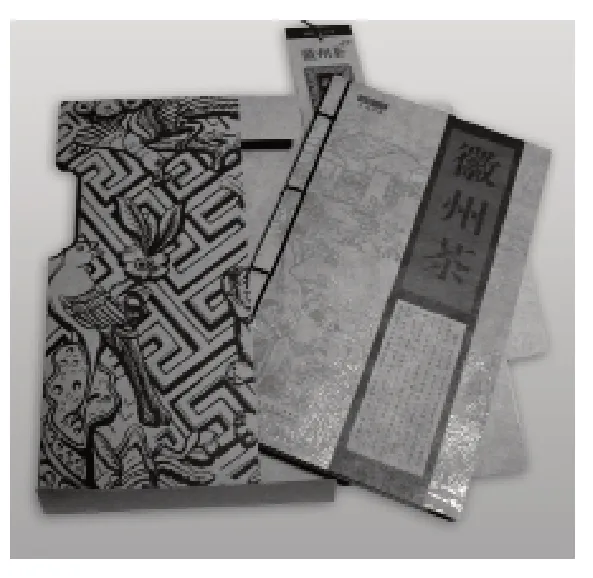
圖2 《徽州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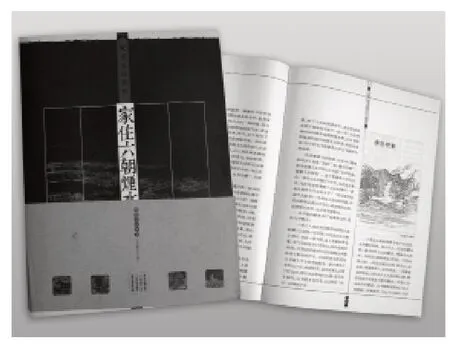
圖3 《城市文化叢書》
對傳統設計元素的挪用還有一種原因是書本內容的獨特性需要。如很多影印本圖書,書的整體樣式均為現代裝幀,但因為內容為影印,是對古籍原貌的再現,史料價值是其根本,故這里的傳統元素是由影印對象決定的。如中華書局2014年出版的《世界歷史年表》(圖4)為經折裝樣式,這種樣式非常符合歷史年表閱讀和比較的閱讀要求,設計者可謂是從閱讀需要上非常恰當地吸取了傳統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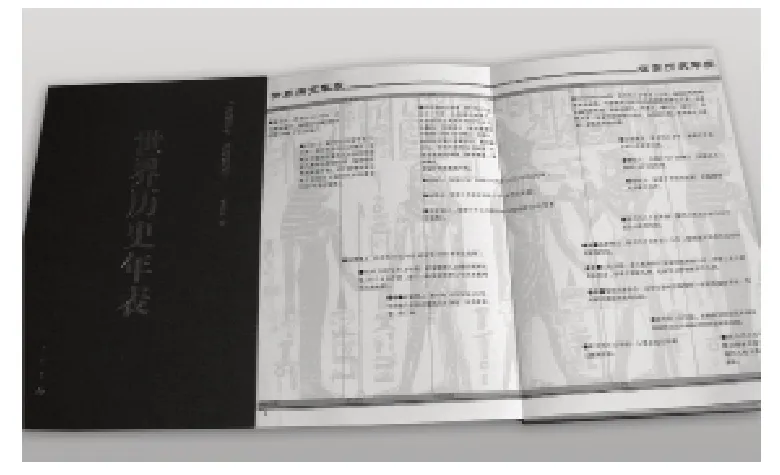
圖4 《世界歷史年表》
二、完整還原中國傳統書籍形態
還原傳統書籍形態的優點在于保存了傳統書籍的所有樣式,閱讀者可以非常完整地感受到中國傳統書籍設計閱讀體驗與設計特點,從書籍內容本身以及文化記憶的還原而言,具有很高的價值。這種價值不僅使讀者感受到傳統的閱讀意味,還可以讓讀者完成對傳統設計樣式的真實體驗,更具體地了解在這一傳統書籍樣式中包含的設計理念與具體展現。如中央檔案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毛澤東手書精選》(圖5)完全采用線裝書樣式,宣紙印刷,書根錄有書名、卷數,函套為布封紙卡,可謂是對傳統書籍設計的完整還原,我們在閱讀的時候能感受到濃厚的書卷氣息(但封面題字為電腦行書,略顯僵板)。

圖5 《毛澤東手書精選》
對傳統書籍設計再現的另外一種情況是出于設計者對樣式本身的鐘愛,如中國美術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藏書銘印記》(圖6)采用傳統蝴蝶裝樣式,盡管這種樣式因承載內容少,裝訂會出現白頁的問題,但讀者能充分感受到頁面天寬地闊的視覺審美。再如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逍遙游》(圖7),木質書盒,內置經折裝、線裝兩本設計樣式,其內部版式設計也按照傳統樣式,設計者在正文上使用了電腦里的字體,雖然讓書籍的歷史氣息略微減弱,但其整體設計樣式的還原,使得讀者在閱讀中把玩的意味已經完全實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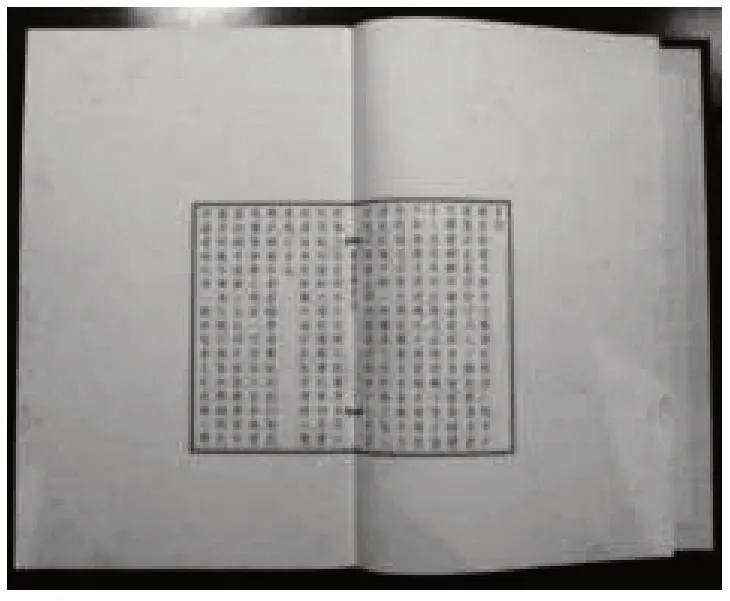
圖6 《藏書銘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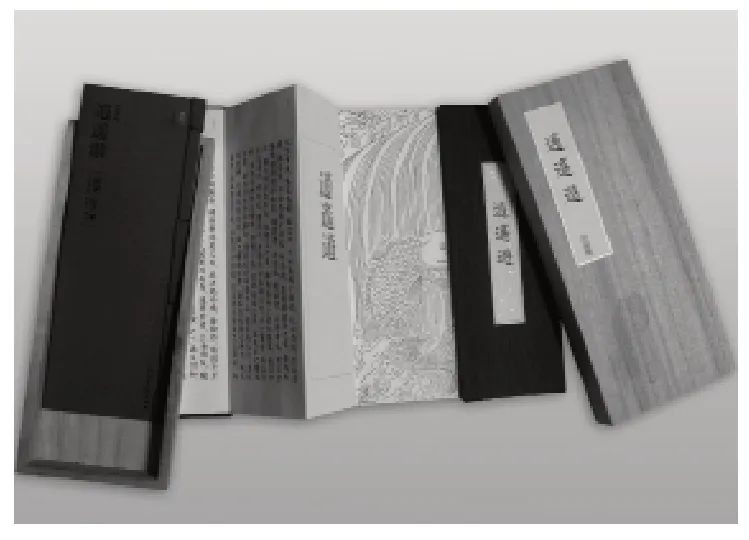
圖7 《逍遙游》
由于閱讀習慣的轉換,大多數現代讀者會不適應傳統的設計樣式,但傳統書籍設計中蘊含的設計審美、讀者意識都有著很好的留存,我們在閱讀還原設計傳統樣式的時候,是在了解書籍的歷史,體驗書籍設計的文化歷程。
三、理解傳統閱讀體驗,實現具有文化記憶的創新
時代發展與閱讀方式、形式的變化,導致純粹傳統書籍并不具有廣泛的讀者,對傳統書籍設計的更高要求的借鑒,應當是從讀者綜合體驗與需要出發,創造出符合閱讀時代性又具備文化記憶恢復的設計樣式。
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王國維手稿 人間詞話》(圖8),書函采用了線裝元素,這只是一種元素裝飾性的挪用,即引發了人們對傳統的聯想。打開函套,木質雕刻封面精美而有觸覺感,可見其文化意味;翻開封面,其內容為影印經折裝,具有很高的文本價值,同時,因為經折裝可以全卷打開,其手稿也得以完全展現。這本書對傳統書籍設計元素的挪用采用了實用與裝飾相結合的方式,給予讀者充分的閱讀享受體驗,完成了閱讀與審美的雙重需求,其設計是對傳統元素進行的分解重構。
再如中華書局2009年出版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叢書(圖9),書籍木函正面即是一幅木刻版畫,讀者從中獲得了閱讀之外的視覺與觸覺體驗;打開書函,其中有木刻印章一枚,這是木刻版畫真實的工具之一,讀者可以更直接地接觸木版年畫的實體。結合書中內容,讀者能夠從書本轉換到對木版年畫的直覺感受,書本和年畫的距離被拉近,閱讀和體驗完美結合。我們在閱讀傳統內容的同時真切地感受到,書籍設計者力求全面地復活書籍要傳達的視覺審美、閱讀體驗與文化記憶。

圖8 《王國維手稿 人間詞話》

圖9 《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叢書
四、對借鑒中國傳統書籍設計的反思
就信息內容的記錄而言,數字化形式逐漸成為主要的方式。但從另一面看,正如設計家原研哉所言:“正是數字媒體的發展,原來作為傳達圖文的最主要功能的紙張載體被解放出來,書,將成為書之本身,它將以獨立的藝術而存在。”當我們在翻閱一本書的時候,它脫離了僅僅是獲取信息內容的閱讀目的,同時也獲得一種直接的閱讀體驗。因此,當代的書籍設計就不能僅僅是滿足二維的設計,即書籍的保護與視覺美化——裝幀,而是需要從閱讀的時間、空間、裝幀等諸多方面進行考量。這也就意味著,書籍需要進行綜合的設計來滿足讀者的視覺與心理要求。正如呂敬人先生提出的從“裝幀”向“書籍設計”觀念的轉換:“書籍設計應該是一種立體的思維,是注入時間概念的塑造三維空間的書籍‘建筑’。其不僅要創造一本書籍的形態,還要通過設計讓讀者在參與閱讀的過程中與書產生互動作用,從書中得到整體感受和啟迪。”我們今天對中國傳統書籍設計中的任何一種借鑒,都需要意識到所選擇的是一種文化記憶的符號,這種符號曾經是如何在閱讀中實現其價值,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借鑒與駕馭傳統設計元素。
書籍閱讀本身作為一種文化,它將通過書的形式進行傳達。中國傳統書籍設計,是中國傳統文人另外的精神寄托樣式,在閱讀過程中,更多地類似于藝術把玩,以獲得更多的閱讀意趣。從文化的角度看,它包含人與信息交流過程中的情境,讓信息生活化、情義化,具有更多的“靈韻”意味與象征性。由于欣賞體驗本身具有的內在情感價值,人們在閱讀時,會形成對書籍本身的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在社會群體中,也暗含了一種優雅的生活態度。設計者如不能充分引發讀者視覺、觸覺的興奮感,讀者也就失去了閱讀書籍的情境體驗。
在中國傳統書籍發展的歷程中,任何一種樣式的出現都包含了內容、材質、閱讀方式與審美風格的統一性,也即任何一種樣式都包含著因書籍而延伸的閱讀文化記憶。當代書籍設計可以從中國傳統設計中去探究、學習傳統書籍設計的理路,將傳統文化內容通過具體的設計作品來表達,通過文化記憶信息的傳遞,實現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