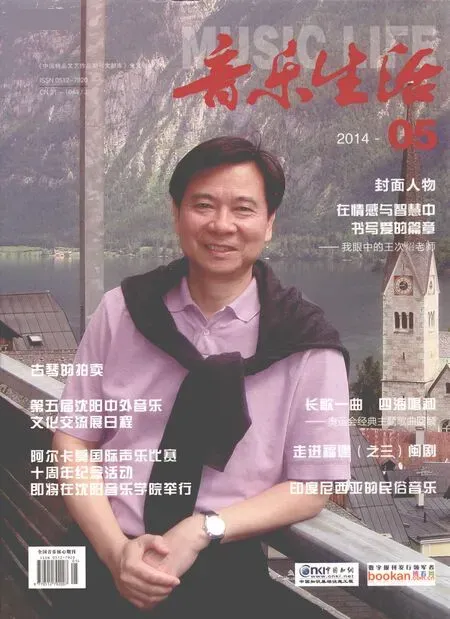關于斯克里亞賓《第二鋼琴奏鳴曲》“幻想”(op.19) 創作技法分析
文/劉旭娜
關于斯克里亞賓《第二鋼琴奏鳴曲》“幻想”(op.19) 創作技法分析
文/劉旭娜
本文通過對斯克里亞賓第二鋼琴奏鳴曲——“幻想”的分析來了解斯克里亞賓早期音樂創作中的音樂語言特點。從和聲語言來看,斯克里亞賓在早期仍然保持著傳統風格,但是由于他對二度的鐘愛,在和弦中不同的位置加入二度外音使得音響效果有別于傳統音樂。這正是斯克里亞賓突破傳統向他的神秘和弦邁進的第一步。
斯克里亞賓 鋼琴奏鳴曲 貫穿運用 創作技法 和聲語言
引言
這首奏鳴曲是斯克里亞賓創作走向成熟的標志。它包括兩個樂章,第一樂章1892年創作于意大利的熱那亞,而第二樂章直到1897年才在俄國的克里米亞完成。雖然寫作時間相隔5年之久,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兩個樂章間的緊密聯系。在這首作品中斯克里亞賓從肖邦的身影中走出來,充分表現出自己的個性。這時的斯克里亞賓沒有像他的老師和同時代作曲家那樣,多數都是走格林卡的道路致力于音樂的民族化。在他的身上較完整地保留著西方音樂的影響,使他成了西方古典、浪漫主義音樂傳統在俄羅斯的唯一繼承人,在思想感情的深度和各種表現手法方面都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樂曲的第一樂章為Andante(行板),但是作曲家卻把具體的速度標記為每分鐘60拍,已屬慢板。第二樂章是Presto(急板)。在主題材料的聯系方面這兩個樂章并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第一樂章像是提出問題,第二樂章給予回答,由此而使前后樂章有了一種“精神”上的聯系。另外在調性布局方面,也可以感受到兩者之間的微妙關系,第一樂章從#g小調開始,但再現部卻不同尋常地建立在 E大調之上,這種開放式的處理使第一樂章不中斷地進入第二樂章,而后者剛好是從#g小調開始。
1.主題—動機材料在全曲的貫穿運用
第一樂章的主部主題以同音反復的音型為特征,和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命運敲門聲”有著同樣的含意,是由三個樂句構成的開放式樂段結構(4+6+2),并且第一樂句和第三樂句運用了首尾模進的寫法,加強了對主題材料的深化。在副部第一主題中(13~22小節)仍然有“同音反復”材料的繼承與貫穿,仍然采用三連音的特有節奏型加以陳述。
在展開部中將“同音反復”動機材料作為展開的重點體現在各個階段。第一階段(58~61小節)對主部主題的材料進行展開,但其中鑲嵌有副部Ⅰ的織體材料。第二階段(62~74小節)為整個展開部材料最為豐富的部分,斯克里亞賓將主部、副部Ⅰ、副部Ⅱ的材料進行綜合展開。旋律是副部Ⅱ的主題材料,左手是同音反復的主部材料,并以這種形式陳述了五小節后,經過兩小節主部材料的連接后將副部Ⅰ的材料進行1+1的重復發展。正是這部分將各主題中的典型音調進行綜合展開,才使得樂曲更具有動力性。在第三階段(75~83小節)是將主部主題的“命運敲門聲”——同音反復的材料單獨進行分裂、模進的展開。可見這個主題所占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另外,在本樂章的最后兩小節再一次出現了“命運敲門聲”的主題并逐漸消失。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第一樂章就像在提出問題,同時等待在第二樂章給予回答。
在第二樂章中“命運敲門聲”依然貫穿始終,首先在第一部分的A段主題材料中除了保持著作者鐘愛的二度音程以附加音的方式出現外,同樣貫穿著用和弦外音細致打扮過的主題隱含著第一樂章的“命運敲門聲”。第一樂句的前四小節是2+2上方四度的模進結構,旋律是連續的三連音律動形態,配以急板的速度十分流暢。B段中右手延續了主題的三連音律動,同時左手加入了旋律性的線條。在第19小節左手出現了同音反復的“命運敲門聲”,這是對第一樂章材料的進一步發展,并且融入到第二樂章中。
2.和聲因素分析
在和聲方面,斯克里亞賓在全曲中十分偏愛在和弦中加入二度音程。他將二度音程以附加音的形式出現在各和弦中,因此,每一個和弦帶有一個二度附加音時和聲的功能勢必也就具有了復合性。在第一樂章的副部第一主題中二度音程的附加最為突出,幾乎每一個和弦都帶有這樣一個附加音,這種精細的處理給第二主題帶來一縷詩意。
此外,主部主題的第一樂句從T和弦出發結束在D和弦的第三轉位上,而第二樂句從ⅵ和弦開始形成了一種阻礙進行,并且第二樂句始終是以下屬和弦作為中心進行展開的。第三樂句同第一樂句構成五度模進,和聲同樣進入從屬和弦領域,結束在DD2 和弦上。同時這個和弦也正是副部一主題B大調的b5DDⅦ56和弦。 從而為副部Ⅰ主題主和弦的出現作了充分的準備。
第二樂章的第一部分在主題陳述時斯克里亞賓在第一樂句的和聲配置中主和弦始終沒有出現,是將屬功能組作為和弦的中心,從D和弦出發又結束在D和弦上,同樣第二樂句是上四度的模進,自然將主功能組作為和弦中心,從D/S出發結束在T和弦。這樣的和聲配置可以看出雖然第二樂章的調性同樣是#g小調,但是第二樂章的開始并沒有出現#g小調主和弦,因此#g小調的調性并不是十分的明朗、有一些在屬調上迂回的痕跡。
第二部分中的C段是由三個樂句構成的樂段。第一樂句結束在be小調的DDⅧ56和弦上,第二樂句結束在be小調的DD7和弦上;第三樂句是第一樂句的上方五度模進,因此將調號改寫為bb小調,并且將這一部分結束在bb小調的DDⅧ56和弦上。由此可以看出C段將重屬和弦作為各樂句的終止式加以強調,是對傳統和聲做了很大的突破。
3.調性布局方面的延承與突破
第一樂章的呈示部主調與副調是平行大小調的關系,仍然保持著傳統的調性布局關系。但在展開部中調性的變化則較為豐富,由副調B大調開始之后轉入遠關系d小調,在展開部的第三階段通過對“命運敲門聲”材料的集中展開使得調性的轉移也十分豐富,經歷了#g小調—G大調—E大調—#c小調—#D大調,最終以#D大調的主和弦進入再現前的屬準備階段。
在再現部則與對傳統奏鳴曲式的調式布局做了很大的突破,對主部主題只做了兩小節的再現,隨后就急促地進入副部。同時,副部第一、第二主題調性并沒有回歸主調,#g小調而是進入了E大調。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調性布局原因在于展開部中#g小調就有出現,特別在第四階段可以看作是主部主題的先現。這在古典奏鳴曲中是比較少見的(展開部出現主部調性),因此副部第一、第二主題的調性則轉入E大調再現。
第二樂章的第一部分調性與第一樂章的主調相同,但是在再現部分的結尾則將調性轉移到了#d小調結束第一部分,這種處理也不是傳統調性布局所常見的。之所以斯克里亞賓在這里將調性結束在#d小調上是因為第二部分的調性為be小調與其為等音調關系,如此的過渡使兩個部分在聽覺上更為自然而非遠關系調轉移的感覺。在第三部分(再現部分)時,調性則始終保持在#g小調并沒有再出現#d小調,因此可以看出第二樂章的調性布局具有一定的奏鳴性。
4.節奏音型的貫穿
主題中的“命運敲門聲”材料是采用三連音的特有節奏型加以陳述的,因此三連音的節奏音型已然成為全曲中始終貫穿出現的特有節奏。
第一樂章除了主部主題呈示外,副部I主題在織體寫法上采用了三連音音組節拍移位的手法。使原有的三拍子重拍移至到三個三連音音組的最后一個音符上,從而打破了原節拍的重音律動。副部Ⅱ主題是與主部主題對比最大的一部分,但節奏音型在采用八分三連音和十六分音符的流動旋律基礎上,左手又增加了一個以柱式和聲為主的聲部與主部形成對比。
第二樂章的第一部分主題隱含著第一樂章的“命運敲門聲”。節奏則同樣采用連續的三連音律動形態,配以急板的速度十分流暢。第二部分的主題也同樣貫穿八分三連音的律動形態。此外,在再現部分的最后是以華麗的三連音律動方式配以屬音的持續,最終用強有力的主和弦結束全曲。
結語
由于斯克里亞賓的第一和第二鋼琴奏鳴曲都屬于他的早期作品。在本人另一篇完成的《第一鋼琴奏鳴曲的分析》中對斯克里亞賓早期創作的特點已經有所總結。因此,在這篇論文中我只對斯克里亞賓創作進程中的新手法及新發現加以總結:
1.《第二鋼琴奏鳴曲》是斯克里亞賓創作走向成熟的標志,從這首作品開始他逐漸從肖邦的影響中走出來并開始樹立自己的音樂個性。在音樂表現手法及思想感情表述的深度等方面都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2.在主題陳述與展開的手法方面斯克里亞賓在這首作品中也在做著大膽的嘗試。兩個樂章之間并沒有直接的主題材料的聯系。但第一樂章像是提出問題,第二樂章給予回答,由此而使前后樂章有了一種“精神”上的聯系。而傳統作品中一般都由一個“種子”材料進行陳述而發展,各個樂章之間也都有著主題與材料之間的聯系。另外在調性上兩個樂章之間可看到微妙的聯系:第一樂章從#g小調開始,但在再現部別致地建立在E大調上,這種處理使得第一樂章不中斷地進入第二樂章,第二樂章剛好從#g小調開始。
3.在和聲方面,可以發現斯克里亞賓尤為偏愛二度音程的效果。他將二度音程以附加音的形式出現在和弦中,使得和聲的功能同樣具有復合性。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和弦的形成對斯克里亞賓日后獨創的“神秘和弦”開辟了先路。
4.斯克里亞賓在作品中所遵循的主題材料統一性原則正是延續著傳統寫作的技法。從主部主題奏出的“命運敲門聲”開始,這一核心材料在樂曲中得到了充分的貫穿與發展,尤其在展開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時在第二樂章中仍然隱含著這一核心材料的因素。
[1]羅忠镕著.現代音樂欣賞辭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王進著.20世紀和聲中的個性寫作風格與共性思維基礎[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3]姚恒璐.現代音樂分析方法教程[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
劉旭娜(1979-),沈陽音樂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