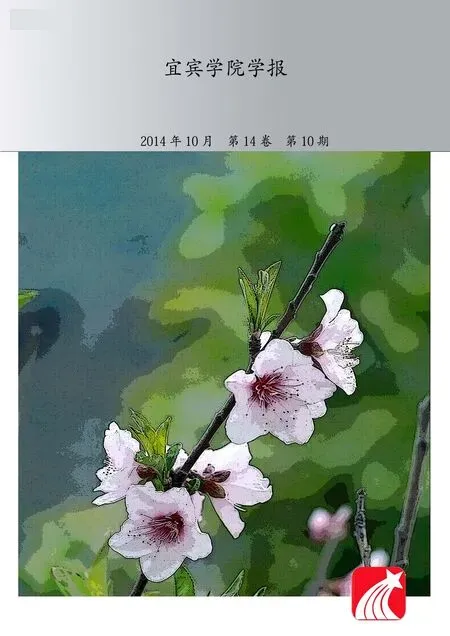冷靜批判下的浪漫書寫
——評葉彌長篇小說《美哉少年》
李姝錚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美哉少年》是葉彌創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這位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江蘇女作家,親身經歷了文革帶來的動蕩和不安,由富庶溫潤的江南名都蘇州輾轉流離到偏僻貧窮的蘇北農村。生活差異、文化差異、社會地位的差異都給當時年僅6歲的葉彌留下不可彌滅的印象。而這樣的經歷也深刻影響了葉彌的文學創作。葉彌在她數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寫出了多部的以文革為題材的小說作品,如《糧站的故事》《明月寺》《成長如蛻》《去吧,變成紫色》等。這些創作都得益于其少年時期的親身經歷,葉彌筆下的文革題材小說,都可以拿捏得當,厚重又不失飄逸,顯示出作品鮮明的藝術特色和較高的文學價值。《美哉少年》就是以文革為背景,展現少年在政治運動沖擊下的成長歷程。在葉彌的小說中,少年成長是一個重要的敘述視角和敘述主題,對這一主題的解讀不僅益于理解葉彌的小說創作,也益于通過評析特殊時期少年成長而獲得對現實的關照與反思。在《美哉少年》的創作中,作者采用冷靜客觀的旁觀視角、超越特定時空的人性思索,為讀者展現了文革對人性的異化和少年對理想精神家園的追求。浪漫的書寫方式使小說在嚴厲中不失溫情,表現出獨特的創作和審美風格。
一 旁觀視角下的冷靜批判
《美哉少年》講述的是文革背景下,遭遇生活顛覆,父權崩塌,喪失母愛后的十一歲少年李不安以反抗的姿態出走,追尋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園和精神歸屬的成長故事。[1]主人公在他的出走路程中經歷了欺騙、饑餓、偷盜等人性丑陋的一面,也在這一路程中學會了責任、感恩并最終成長。小說的時間跨度并不大,從李不安出走到回歸不過短短數月。而在這樣的時間跨度里,李不安從一個叛逆的、受到文革沖擊而異化了的孩子,通過在出走路上的所見所聞所做,逐漸成長為心智成熟,學會感恩,學會發現生活的美好的少年。作者的寫作重心并不在文革帶來的傷害,而是以一種理想浪漫的的方式,對青少年的理智與情感的成長展現出審美的關照,因此,小說的敘事動力也不僅僅來自對歷史的批判,也是來自人性的美好與特定時代發生沖突矛盾后,并最終由異化轉為回歸的歷程。葉彌的創作采用了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以旁觀的姿態最大化地給予小說敘述時間和空間上的自由,消除生理心理等因素對小說的影響,從而能夠靈活自然而又冷靜客觀地反映社會,完成現實書寫。小說中的李不安最初的形象正是當時社會大部分孩子的縮影,文革給他們的成長帶來了揮之不去的傷害,不安和恐懼始終伴隨著他們。雖然李不安的父母親一直努力維系著看似安穩體面的生活,卻無奈地被政治運動打破。父親李夢安因為被懷疑在縣城寫反動標語被捕入獄,母親朱雪琴性情軟弱,無法獨自承受動蕩社會和艱辛生活帶來的壓力,同時也為了打聽丈夫的情況,不得不委身于大隊書記孫二爺。而這一幕,恰巧被李不安親眼目睹。這個少年崩潰了,沒有人知道他這種隱秘的感受,也沒有人能明白他被擊垮到何種地步,他的“母親”沒有了,他賴以生活的最重要的內容突然消失無蹤。母愛的喪失,父親又因為知道了妻子與孫二爺的奸情而負氣出走,李不安的家庭終于崩塌。在這樣的崩塌之下,李不安學會了恨,他恨父親的自私絕情,恨母親的失貞軟弱,恨孫二爺仗勢欺人。在動蕩的政治背景下,單純的少年被扭曲異化,固執地走上一條出走之路。然而,受到政治運動影響而異化扭曲的人又何止李不安一個?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李不安的童年玩伴,同樣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小翠子家庭貧困無力上學,每天都要做繁重的家務,切藤喂豬洗衣服作晚飯,甚至沒有一點自己支配的時間,與李不安從“敵人”到朋友的張小明,十幾歲就開始代替母親作售票員工作。他的母親為了挽回在外面風流的父親,在張小明14歲的時候就給他定了親。作為村里小學校長的孫大舅讀過三年私塾,數學上只會加減法,不會乘除法。他畢生的目標和任務,就是把課文念得聽上去有點像普通話。“殺殺燕子五只槍。”他就這么念“颯爽英姿五尺槍。”人文缺失和政治運動的內外擠壓,讓這些孩子承擔起了孩子不該承擔的責任,又讓他們接受不到應有的教育。社會讓這些少年擁有了超越年齡階段的成熟和強烈的獨立性意識,然而卻沒有給他們提供接受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的教育,這使得本就自控能力不強的少年出現自相矛盾的行為,甚至畸形成長。文革給予整個中國社會的最大影響恐怕是對于孩子成長所造成了揮之不去的災難,并使他們始終游離與人類美好精神家園之外。[2]葉彌的小說表面往往不起波瀾,卻能夠在平靜的敘述之下,借助于形象精確的細節描寫,展現人物復雜矛盾的內心活動,透露出殘酷的真相,給讀者帶來深刻的思索。[3]如小說中李夢安到小學校長孫大舅家的情景:“長板凳放在孫大舅的屁股后面,兩碗茶一碗放在長板凳上,一碗端給李夢安。她(孫大舅的女人)說:‘李老師,坐。’李夢安聞聲坐到板凳上,又端著水認真地想了一想,離開板凳蹲到一邊去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動作,卻包含了巨大的信息。葉彌用這一坐一蹲的動作,形象地展現了文革時期受到批斗的知識分子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活動。在政治運動和階級斗爭面前,人生來擁有的平等權蕩然無存。這樣鮮活生動、充滿“即視感”的細節畫面,拉近了小說與讀者的距離,讓讀者更深入地走進小說的人物和故事。在小說中,面對文革對人性的摧殘和對少年成長的消極作用,作者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竭力地細致展現人物形象的真實生活,并對這種生活保持尊重,極少妄加指責評論。作者這種“作壁上觀”的寫作方式,使得小說所有的是非對錯都由讀者自行判斷,作者成了單純的敘述者和引路人,留給讀者更大的思索空間。《美哉少年》在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之下,將批判不動聲色地融于人物不經意間的言行與毫無造作的情景之中,盡可能保持了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人物心態,借助于人物自身的行為來還原歷史的真實。[2]
二 超越時空的理性思索
《美哉少年》雖然以文革時代為故事發生發展的背景,但與20世紀80年代的文革題材小說以反映文革本身為主題不同。《美哉少年》并不像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一般,把小說的思想主題、情節結構,甚至小說人物的命運都交由文革這一先行主題來決定,而是大大減少小說中文革內容的分量和地位,把文革作為小說敘事的背景,僅僅是小說主人公成長經歷的大環境。[4]在這樣的文本敘述方法下,文革的權威被淡化,甚至成了一種回憶,一種想象,一個故事的起因。這樣的寫作方式,給了小說更大的自由度,使得小說無論是思想內涵還是表現手法都更趨于多元化。在《美哉少年》中,文革成了李不安最初性格形成的外部環境,是李不安出走的主要因素。但在李不安的成長過程中,文革的因素被淡化了,具有更普遍性更廣泛的影響力和批判意義。如李不安在火車上遇到了叫做章四瓦的女人,這個女人看似像母親一樣關心著李不安,給他食物,給他“抓虱子”,卻借機猥褻了這個十一歲的少年,給李不安的身心成長帶來巨大傷害。在性意識還處于懵懵懂懂的年紀,李不安以一種被迫的姿態接受了“性啟蒙”,這樣的故事不僅關注了少年的身體成長,也對那些即將達到青春期的少年,在面對身體變化時產生的敏感、畏懼、好奇、自我防衛等情緒給予了關注。除了李不安,作者還塑造了人生導師一般的人物形象老刺猬。老刺猬年輕時有個顯達響亮的名字叫于光達,卻在三十歲時把名字改成了卑賤的名字:老刺猬。只有當人處在極端卑微絕望的境地時,才會覺得連響亮一點的名字都成了侮辱。老刺猬甚至后悔沒有給自己起一個更輕一點的綽號,當認定自己生來就卑賤時,才能在沒有尊嚴的環境中活下去。雖然輕賤自己,老刺猬卻分外愛惜紙墨。煤渣化在水里自制成“墨汁”還要時不時用筷子攪動它,不然水里盡是化不開的小煤渣,“寫在紙上面,對不起紙。”在老刺猬眼里,自己可以被社會輕賤鄙夷,但紙不可以,文化不可以,知識不可以。即便生活貧困不堪,他也要盡最大努力維護他心中的圣地。一個重視知識、尊重文化的人,卻要不斷輕賤自己,尊嚴成了生活的最大痛苦。小說沒有介紹老刺猬的生平,沒有人知道他曾經經歷過什么,只能從他曾經的“于光達”這樣的名字中看到父輩曾對他給予的厚望。在作者的描述中,讀者了解到這個人雖然自己都吃不飽穿不暖,卻愿意收養小瞎子平安,愿意收留流浪的不安,愿意省下自己的口糧接濟生活更加困苦的唐寡婦……老刺猬這個形象在《美哉少年》中是近乎完美的,也是矛盾的。他與自己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卻堅定地教導孩子們融入社會,他堅持教平安寫字,因為堅信“會寫字了就不會造反”。老刺猬在貧困卑賤中隱忍,卻對下一代充滿希望;他可以放棄尊嚴,卻絕不放棄道德;他忍受著社會的不公,卻始終懷抱感恩之心……這樣一個善良堅韌的人,為了滿足母親想吃魚的愿望,在初冬下河捕魚而得了感冒,無錢醫治死于肺炎。老刺猬的人生引起讀者的好奇與思索,這樣的思索就是作者的最終意圖。在葉彌冷靜的敘述中,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一個缺乏人性關懷的社會,人的尊嚴被踐踏,文化被輕賤,生活變得愚昧而麻木。這樣的批判,顯示出作者的思索已經跨越了時間和空間,以高屋建瓴的姿態表現出對人類社會中殘缺人性、病態文明的強烈控訴。
三 理想審美下的浪漫書寫
在閱讀《美哉少年》時,讀者不僅可以感受到作者不動聲色的批判,也可以感受浪漫的詩化書寫。李不安的遭遇,既是現實的,也是理想的。作者用一種浪漫的方式講述一個現實的故事。小說中隨處可見那些充滿愛意的畫面。如李不安在出走時與玩伴小翠子約定,在“春天,飄絮的時候”回來,和小翠子一起解救那些被頑皮孩子撈出來仍在土地上的小蝌蚪;李不安和與他年齡相仿的張小明,因為彼此的母親不和得緣故而結成“死敵”,卻在打了一架之后成了無話不談的“結拜兄弟”,張小明甚至冒著被父母責罵的危險給李不安偷了車票,促成了李不安的出走……孩子的這些童心并沒有被殘酷的社會所磨滅,而是以一種原諒的姿態,展現著人性美好的一面。除了這些充滿浪漫氣息的畫面,葉彌對整部小說的構造也具有浪漫的審美色彩。葉彌在小說中的創作思路非常清晰并且理想化,主人公經歷著“出場——遭遇成長困惑——出走——經歷社會磨礪——引路人指導——成熟”這樣一個大部分成長小說主人公都延續的一條道路。[5]在遇到老刺猬之后,不安的人生走上了一條向著真、善、美而去的光明之路。這是一條“單行道”,在這條路上作者有意忽略了成長期人性的自我矛盾,強化人物更自覺的道德行為,削弱成長過程的片面性與主觀性。這樣的設定,不能不說是充滿著浪漫與理想化。小說在批判的同時也帶有希望的積極樂觀情緒。這樣的成長小說充滿了浪漫化的理想色彩。在《美哉少年》中,除了人生導師老刺猬的循循善誘外,每一個人性的閃光點,幾乎都會出現一位起著“模范”作用的人物出現,通過言傳身授,帶給李不安美好的教育。如善良的王彪叔,明知李不安偷了他家的雞,卻為了維護李不安的尊嚴而沒有點破,讓李不安學會了知錯而改;總是來老刺猬家“蹭吃蹭喝”的唐寡婦,總是拿走老刺猬的一半口糧,給老刺猬納著永遠也納不好的鞋底,縫著永遠縫不好的棉衣。然而這個女人卻在動蕩的生活中獨立撫養四個孩子,其中有兩個是哥嫂和姐姐的孩子。唐寡婦的存在讓李不安學會包容與憐憫;老刺猬死后,不安承擔起照顧平安的任務。他要給平安做飯,督促平安練字,承擔起家庭的擔子。他不能丟下平安不管,平安讓他學會了責任……這樣的浪漫與理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說的現實批判意義,但也深刻表現出作者對生活,對少年的殷切希望,以一種母親般的姿態溫暖關照著他們。值得一提的是,葉彌并沒有在這樣的溫暖浪漫中迷失方向。與大多數成長小說最終以融入社會的和諧姿態作為結尾不同,《美哉少年》中李不安雖然人格得到了完善并最終回歸了家庭,但大的社會格局并未改變,除了小翠子的死亡,一切與李不安離開前別無兩樣:李不安仍然不愿上學,父親繼續看他的美女圖,母親仍在看她的菜譜,學生們還在學著“殺殺燕子五只槍”……這樣的回歸是無奈的,諷刺的,是對社會環境影響少年成長的深刻反思。
葉彌曾說“每個女人都是詩人”[6]。在葉彌的小說中詩思與詩的語言隨處可見。如小瞎子平安,看不見東西,卻堅信鎮長女兒月香送給他的糖紙“會化成水,就是化成太陽那樣的顏色。或者化成一道煙走了……煙也是太陽那樣的顏色”。這樣純真可愛的想象讓讀者憐惜之意油然而生。如李不安回家后去看小翠子的墳,作者這樣描寫:“解凍的土壤里有什么?有小翠子好看的頭發。小翠子又長又黑的頭發給嚴寒冰在土壤里,拉都拉不開來。現在解凍了,她從土里拉出她長長的黑發,不知對誰露出甜甜的微笑。”“螞蟻成群結隊地從草根里爬出來,蒼蠅棲在枯草的頂端,在風中愜意地飄蕩。第一只蝴蝶是不是早就從它的窩里爬出來,在太陽下面曬它麻木的翅膀?鵝和鴨子在沒有冰塊的河里歡快地嬉鬧……生命極端膨脹的地方,就是生命大量消亡的地方。”這樣充滿詩性的話語在葉彌的小說中隨處可見,這樣的浪漫話語讓原本充滿矛盾與批判的文章瞬間變得活潑明亮起來。舒緩的節奏、夢幻般的描寫、形象的比喻和擬人,顯示了葉彌深厚扎實的語言功底。這樣的詩性語言,也消弭了小說中劍拔弩張的對抗色彩,讓讀者在沉痛的反省與思索中又不失對未來的希望。
結語
葉彌對李不安成長歷程的描寫,表現了這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對青少年成長的關注與思考。在她冷靜的批判與浪漫的書寫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人性關懷。面對對蕩社會給人性所帶來的異化,葉彌毫不客氣地揭露并批判,但葉彌并未對這樣的人性失去希望,她渴望著每個少年都能夠在成長中學會真善美,而這樣的愿景,需要社會中的每一員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 張春紅.追尋成長的精神軌跡:從葉彌小說看其創作心態[J].山花,2012(7):123-124.
[2] 張蕙.理智與情感的審美關照:評葉彌小說《美哉少年》[J].棗莊師范專科學院學報,2004(6):28-30.
[3] 劉新鎖.生活像藏在棉花里的針:讀葉彌的《猛虎》[J].當代作家評論,2005(2):140-143.
[4] 余濤.另類的成長[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1:9.
[5] 易立君,劉彬.《看不見的人》:一部典型的成長小說[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7(7):43-45.
[6] 葉彌,姜廣平.我太想發出自己的聲音了[J].西湖,2008(6):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