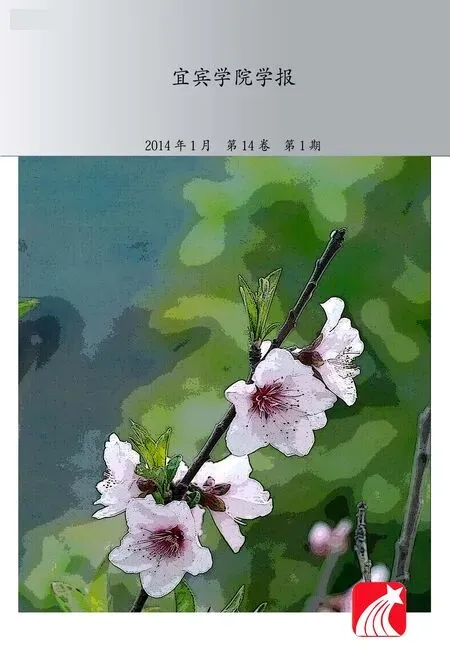語感與外語教學的界面
王月麗,楊國棟
(阜陽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就研究內容來看,語感研究與外語教學研究分屬不同的范疇和領域。但語言是語感的本體,也是外語教學的重要內容,語感研究與語言教學息息相關。從外語教學的視角看,人們對語感的認識伴隨著語言教學理念的更新由模糊逐步走向明晰,語感訴諸教學的行為也經歷了從盲目到自覺的深化過程。
20世紀60年代前,外語教學一直沿用科學主義的語言觀,固守“知識中心說”的大旗,語感被理解為人對語言的主觀感覺、知覺①,由此形成的認識是含混模糊的,語感基本被排除在語言教學范疇之外。20世紀70年代,功能意念主義理論使得交際教學法盛極一時,然而過度強調語言的交際功能,給語言戴上了“交際工具”的枷鎖,外語教學產生了一個無可逃遁的整體偏移和錯位。人們對語感在言語活動及語言教學中的重要性有所覺悟,但對其認知卻基本停留在“客觀存在、但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理解上②,語感付諸于語言教學的實踐是個別、盲目的。隨著建構主義外語教學論的逐漸流行,語感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了空前發展,曾一度引發了國內語文教學界的熱議。有些學者甚至在實踐教學中豎起了“語感中心說”的大旗。相比之下,國內外語界只有少數學者(如朱純、胡春洞等)對語感的形成和培養進行了零星闡述,也未引起很大的學術影響。進入21世紀以來的10年,語感研究有擴大之勢,系統研究(如王雪梅)和團隊研究(如湯富華團隊和梁儀團隊)及相關成果正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其研究范疇主要涉及語感的性質、地位、特征,語感與語言習得、學習的關系,語感的培養等問題,取得了不少可喜成就,語感培養也正逐步走入外語課堂,成為一些師生自覺的教學行為。然而,要真正打通語感與外語教學的嶺界,將語感研究理性睿智地應用到外語教學之中,首先還必須弄清楚以下問題:如何正確理解語感?將語感教學納入我國外語教學范疇的理據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可嘗試的實踐途徑?
一 語感的內涵
關于語感,雖然國內外研究者早有涉獵,但對其定義至今仍未達成一致見解。從研究視角看,對語感的界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把它看作心理現象;二是將其視為語言運用能力。前一種觀點的主張者主要以心理學理論為指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葉圣陶、邢公畹、呂叔湘、李海林、張普等人。如葉圣陶提出“語感就是對于語文的敏銳的感覺”[1]267。邢公畹認為語感是“某一語言的本地說者對這一語言的共同的感性認識”[2]。李海林、張普受喬姆斯基的語言習得機制——LAD學說——的影響,將語感歸屬于一種直覺。不管是“感覺”還是“直覺”,都側重從心理機制的角度揭示人類獲得、理解和生成語言的規律。堅持后一種觀點的研究者(如李珊林、韋志成等人)把語言看作一個社會符號系統。他們認為語言的運用是一種社會行為,語感就是個人運用語言的社會行為能力。以上兩種界定視角不同,觀點不一。把語感看作是心理現象,就是視語感為言語主體在言語活動中不斷感知、領悟和理解語言形式的主觀行為;視語感為社會現象,就是把語感看作以具體的言語形式和語境為感覺、知覺依據的客觀現象。作為語言及相關文化知識的心理內化,語感雖是無形的,但又是人的感覺、知覺可及的;作為一種社會的客觀存在,語感雖具化為生動的言語內容及語境,但又是人很難把握和掌控的。因此,語感是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客觀存在的社會心理現象。評判一個人語感的強弱,離開人的感覺、感知、語言知識的記憶與調取等心理活動是不可能的,但也必須看到言語內容及語境本身所發揮的引發作用。因為語感主體畢竟是以其所擁有的語言知識、客觀所觸及的言語材料及語境作為感覺、知覺的基礎和依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衡量一個人語感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人對語言形式與意義的掌握。
從制約言語主體掌控語言形式與意義的視角分析,語感與三個方面的因素相關:社會文化因素、認知心理因素和語言本體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從社會群體的角度制約語感,涉及宏觀的文化語境和微觀的情景語境。人們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其言行都要打上所賴以成長的文化背景的烙印③,直接影響他的言語行為及對對方言語行為的理解與解釋。根據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 情景語境是文化語境的實現途徑,是言語活動中支配語義選擇的因子。它不僅影響言語主體對話題、事件、參與者、交際媒介等的感悟和理解,也制約其對社會文化背景所決定的行為準則、道德觀念等的判斷。認知心理因素從個體的角度制約語感,涉及認知模式和心理思維。對個體而言,文化語境中的某些固定文化因素(如習俗、習慣、行為模式等)都會在個人頭腦中積淀,形成一定的動態或靜態知識結構(即特定的認知模式)影響個體語感的生成和運作。另外,言語活動勢必要受言語主體的心理活動、性格、情趣、心態等心理思維因素的制約。言語主體對語言文字的敏悟程度及自身的審美情趣與意念傾向都無形地作用其語感表現。語言本體因素從言語形式的角度制約語感,包括語言的形式和意義兩部分。語言是一個社會符號系統。建立在語言基體之上的語感自然離不開語言的語音、語義、語法等系統專業知識。總之,語感受言語主體所屬社會文化、認知心理和語言本體的制約,是言語主體的知識、認知和情感的有機融合。這三大因素是一個有機整體,共同作用于言語主體的語感行為,使其在漸進無形、無意識的狀態下形成和運作。
二 語感與外語教學
(一)外語教學實踐與教學目標
觀念是行動的先導,而我國外語教學實踐遠遠落后于教學理念。雖然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教學論已經成熟,但外語教學并沒有真正踐行“建構話語,重塑思想”的理念。就大學英語教學而論,目前盛行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一是語言知識教學,一是語言功能教學。前者奉行“知識中心說”,把語言作為一個知識體系來學習;后者奉行“語言工具說”,把語言作為一個行為體系來學習。[3]7現代外語教學的價值取向涉及外語教學的本質問題——外語教學目標。就英語教學而言,《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明確指出,大學英語教育要兼顧工具性和人文性, 其教學內容除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外, 還應該包括人文情感、人文素養和人文理想的培育。[4]簡言之,大學英語教學就是培養學習者的英語綜合運用能力和綜合人文素養。英語教學的奧秘就在“語用”和“人文素養”的豐富內涵中。語言的人文性決定了“語用”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使用”活動。在文化人類學和語言哲學的理論視野中,“語用”就是人的生命活動和精神活動,就是人的成長、發展本身,它塑造的是人的智慧。[3]7這種智慧來自于語言本身的符號特性,也可稱之為“符號智慧”。這種“符號智慧”區別于一般工具能力的地方正是“語感”。因為,語感不僅關照語言本體,還關照言語主體在社會文化情景中的內心體驗、成長和發展。無論是“語言知識教學”,還是“語言功能教學”都不能真正實現現代外語教學的雙重目標。
在教學實踐中,有意義的教學水平的提升應該通過關注學習的本質而非施加政治壓力來實現。現如今,一些高校的CET-4成績與學生的畢業、就業緊密相關,為適應這種強制性的評價方式,學生雖通過了CET-4或CET-6,但卻不具備真正的語用能力。學習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與測量的線性原理相左。學生的認知也包括對世界如何運作的內在建構的理解[5]110。如果外語教學去除了孕育語言生長的“枝枝葉葉”,無論通過何種方式來守護“語言樹干”,也不可能真正收獲枝繁葉茂的“棟才”。真正的大學外語教學不僅要學習者了解和掌握語言結構、語法知識、語言技巧和目的語文化,而且要關注學習者的內心世界,使學習者在知識建構過程中建立起自主學習能力、終身學習意識和對世間不同事物、不同文化的分析與認識能力,以逐步形成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在人生觀和世界觀方面得到多方位的塑造和升華。這種全方位的立體目標剛好與語感所關注的社會文化、認知心理和語言本體相契合,語感教學自然不失為外語教學走出困境的重要渠道。
(二)語感的普遍性、可習得性
語感是人聯系世界的通道, 是人與世界進行交流的最主要的途徑。馬克思認為,人不僅在思維中實現自己,同時也在感覺世界中實現自己。[6]79比之人的思維,人的感覺更有靈性。它不僅把思維的成果積淀在人的內蘊中,并且憑借其對現實敏銳的相通性,不斷吸納外界信息以滋潤自己,使之成為最具鮮活力的心理力量。[3]8對于語言活動而言,感覺比思維更具有現實可能性。第一,語言本身就是人感覺的產物。盡管“He is a machine”的邏輯意義、思維意義和語用意義存在巨大差異,但人們生成和理解這樣的言語表達卻毫不費力。第二,在言語活動中,“不假思索”的情況是普遍、大量和基本的。因此,外語教育實施語感教學,培養學習者的語感,教會他們認知世界的最基本方式責無旁貸。
有些研究者秉承生成語言學的觀點,認為語感是普遍語法的一部分,具有隱含性、不可習得性[7],而語言學家Bialystock認為,英語語感作為一種能力,是可以通過課堂教學、練習等培養的,且語感能力發展過程也是不斷變化的[8]。換言之,語感是可以習得的,也是動態發展的。王雪梅堅持語感并非只能在真實語境中無意識地形成,雖不能直接傳授,但課堂教學有助于學習者增強目的語語感。通過探索,王雪梅指出語感圖示在同化和順化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達到平衡,不斷循環發展;從原型理論來看語感圖示構成一個連續體,而從突顯觀視角來看語感圖示是輻射型的。[9]由此可見,語感的獲得過程符合人類認知的基本規律,實施語感教學,培養學習者的語感具有充分的認知心理學基礎。
(三)內隱學習和外顯學習
縱觀中外學習理論,大多以有意識的外顯學習(認知)為其邏輯基礎。[10]76然而,美國著名心理學家Reber研究發現學習系統中存在另一層次:內隱學習,即對學習過程缺乏明確意識卻學會了這種規則的學習活動[11]。作為一種學習模式, 內隱學習是有機體的一種適應技能, 它的存在和發展具有連續性,且其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作用得到了研究者的充分肯定。[10]77研究發現,內隱學習無需主體的有意識努力,能節約心理認知資源[12];在學習過程中,個體所接觸到的大量現象與知識不斷刺激語言的深層結構,不知不覺中儲存到長時記憶。它們不僅較之外顯知識持久、不易消退,而且當遇到類似情形時就會產生啟動效應[13]78,對類似行為產生促進作用。另外,內隱學習多是興趣使然,學習者沒有負擔和壓力,不會產生外語學習中常見的焦慮情緒。在輕松自如的狀態下,學習者能隨時隨地根據自身的經驗更加積極有效地去建構知識,完善自我認知,豐富自我情感世界。由此形成的知識、認知和情感的有機融合體及其形成過程的漸進無形、無意識性與語感內涵、形成和運作特征不謀而合。
長期以來,外語教學被批評為“費時低效”[14]26。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是多方位的,但忽視內隱學習的優勢,對學生認知能力過度開發的外顯認知教學難辭其咎。當下,大學英語教學中比較盛行的 “語言知識教學”和“語言功能教學”均以外顯學習理論為指導。前者過于重視語言結構、語法規則等冷峻、乏味的外顯知識講解,忽視了讓學生去體驗和感悟語言情境;后者過于強調語言的交際性,忽視甚至放棄了語法規則和語言知識,有意或無意夸大了內隱認知的作用。上述弊端的根源就在于割裂了內隱認知和外顯認知的辯證統一關系。外語教學要兼顧語言知識的掌握和交際能力的培養,促進學習者語感的生成和運作,可以將內隱學習與外顯學習相結合,充分發揮二者相輔相成的協同效應。
人對世界的語感把握在很大程度上訴諸于人的聽覺和視覺。對于身處漢語世界、缺失英語語境的學習者而言,獲得真實、豐富語境的最直接、便捷的方式無疑是廣泛而有選擇的聽力和閱讀。現代神經學的發展表明,充足真實的語言信息刺激會引起感覺、知覺、記憶、聯想、思維等復雜心理活動的“聚變”式綜合反應,這種非預期、突發式的心靈感應或者說“理性的直覺”就是語感。作為手、眼、腦等器官協調活動的過程,聽力和閱讀都是直接體悟語言的重要方式。因此,幫助學習者擴大視、聽覺通道的語言輸入,著眼于培養學生語感的外語教學勢必要改變以精讀為主的傳統教學模式,加強聽力和泛讀教學。根據美國語言學家克拉申(S. Krashen)提出的i+1輸入假設,語言習得是通過自動輸入并理解略高于現有能力水平的語言實現的[15]409。這種習得多借助于語境在潛意識或無意識中實現。因此,在教學中,語言輸入材料的選擇在宏觀上要遵循i+1的原則,同時協調微調輸入和粗調輸入的學時與比重。課堂教學注重微調輸入,課外以粗調輸入為主,讓學生多聽外語廣播、電視節目,多看外語原版電影,多讀外語原著,在潛移默化中加深學生對世界的認識,提高學生對語言作品的感知、審美和情感體驗能力。在學習方式上,可以積極實踐梁儀教授所倡導的“聽讀結合,堅持朗誦背誦”原則[16]14,有效地將視、聽通道與語言的符號、聲音聯系起來,將語言形式、意義和已有知識融會貫通,協同作用于大腦,產生一系列諸如感覺、知覺、思維、判斷和分析的心理反應,真正將理解了的語言材料變成一種感覺、習慣,在不知不覺中提高語言感悟能力。
結語
隨著我國外語教育、教學改革的推進,語感教學的重要地位正在逐步為越來越多的外語教育工作者所認識。語感是人與世界進行交流的基本途徑,受言語主體所屬社會文化、認知心理和語言本體三大因素的制約,是言語主體知識、認知和情感的有機融合。語感的獲得具有充分的認知心理基礎。實施語感教學是解決我國目前外語教學實踐與教學目標矛盾的重要渠道,而內隱認知的獨特優勢及其與外顯認知的辯證統一關系為其實施提供了實踐途徑。因此,實施語感教學,推動外語教育具有充分的認知理據,是必要、科學而切實可行的。
注釋:
①此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索緒爾、薩丕爾和喬姆斯基(詳見索緒爾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姚小平譯,商務印書館,1980:109;薩丕爾著《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85:16及《喬姆斯基語言哲學文選》,商務印書館,1992:1)。
② 此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Stern, H. H.、葉圣陶、邢公畹和呂叔湘(詳見《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5:18;《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267;《論“語感”》,載《語言研究》,1981(100);《學習語法與培養語感》,載《語文學習》, 1985(1) )。
③ 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把語境分成兩類:文化語境和情景語境。前者指說話人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文化背景;后者是言語行為發生時的具體情境。
參考文獻:
[1] 葉圣陶. 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
[2] 邢公畹. 論“語感”[J]. 語言研究, 1981(100): 15-19.
[3] 李海林. 為語文教育打開一扇窗戶——評王尚文的《語感論》[C]∥王尚文.語感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7.
[5] 竇坤, 桑元峰. 大學英語教學的實踐哲學[M].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
[6] 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 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7] 趙海波, 淳于永琦. 語感初探[J]. 外語學刊, 1995(5) : 47-50.
[8] Bialystock 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ing and using forms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2(3): 181-206.
[9] 王雪梅.英語語感的認知闡釋——內涵、心理機制及應用[J]. 外語教學, 2006(1): 6-13.
[10]高華偉. 內隱學習理論對大學英語教學的實踐意義[J]. 江蘇大學學報, 2006(3): 76-80.
[11]Reber A S. Implicit Learning of Artificial Grammars [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 Verbal Behavior, 1967(77): 317-327.
[12]張人. 內隱認知及其對英語語法教學的啟示[J]. 外語界, 2004(4): 43-47.
[13]杜建政. 內隱認知加工的探索[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4]蔡基剛. 大學英語教學: 回顧、反思與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15]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16]梁儀. 英語教學法研究[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