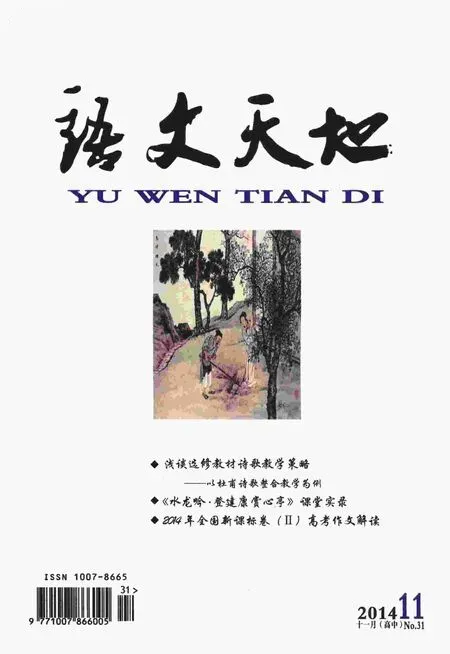淺析審美情感與文學創作的關系
2014-03-12 05:13:57劉曉敏
語文天地
2014年11期
劉曉敏 王 健
“豐富的情感是一切創作的源泉和動力”。沒有情感經驗準備而進入創作過程就等于無米之炊,毫不動情地走出創作過程就等于經歷了一場沒有意義的旅行。所以,沒有情感就無法順暢地走進創作過程,更不可能痛快淋漓地走出創作過程。本文將主要探討情感與文學創作主體的內在心理機制的深層關系。
一、童年經驗與文學創作的聯系
在我們的印象里,作家總是那種用靈魂的眼睛窺視生活的真諦,用一顆“赤子之心”真誠地對待生活的人。無數的事實證明:只有擁有真誠之心的作家,才能在歷史的風云中開拓屬于自己的藝術領地,使自己的作品成為一種不朽的存在。因此,對于作家來說,擁有一顆童心尤為關鍵。雖然藝術家會隨著人生實踐經驗的豐富而變得成熟,其內在心靈也會變得飽滿、充盈,但是藝術家始終脫離不開童年這一先在的意向結構對其創作的影響。
深深震撼作家心靈的體驗往往是一種痛苦的情感體驗。童年時期所遭受的苦難與不幸使作家引發痛苦、孤獨、抑郁等心理感受。為了轉移這些難以承受的心理痛苦,他們走上了創作道路。中外作家中有此種經歷的人不勝枚舉,表現尤為明顯的是中國的郁達夫和奧地利的卡夫卡。
郁達夫在幼年失去雙親,這一巨大的不幸給他帶來重大的精神打擊。長大后,婚姻的不幸、生活的不安定、經濟的窘迫、故國的哀思使他的這種憂郁氣質更加濃厚。種種郁積在心中的苦痛,就用這沾滿憂郁的文字流出筆端來。……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5期)2021-01-18 02:59:48
創作(2020年3期)2020-06-28 05:52:44
北極光(2019年12期)2020-01-18 06:22:10
小太陽畫報(2019年10期)2019-11-04 02:57:59
中國生殖健康(2018年5期)2018-11-06 07:15:40
讀友·少年文學(清雅版)(2018年3期)2018-09-10 06:04:54
讀者·校園版(2018年13期)2018-06-19 06:20:12
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 16:58:59
讀者(2016年7期)2016-03-11 12:14:36
爆笑show(2014年10期)2014-12-18 22:2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