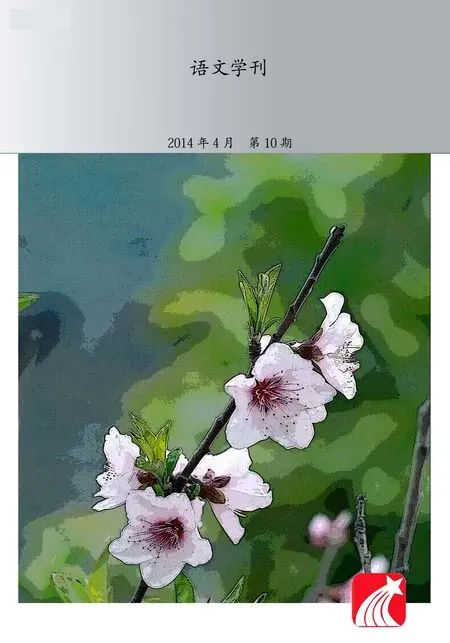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皮格馬利翁》中的語言危機和身份危機
○張春燕
(上海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34)
一、前言
蕭伯納的《皮格馬利翁》可分為兩部分的兩幕劇,每部分都是皮格馬利翁式的神話:第一部分賣花女被訓練成為一個上流社會的淑女;第二部分為從淑女到獨立女性的蛻變。初讀這部劇本,讀者會誤認為這是一部灰姑娘的故事:出租車是童話故事里的南瓜馬車,把戴著鴕鳥毛帽子、穿著粗布外衣的灰姑娘帶到了希金斯的實驗室。通過語言學教授希金斯對其六個月發音、講話方式和行為舉止的訓練,灰姑娘伊莉莎成為語音純正、談吐文雅、儀態端莊的淑女。
在蕭伯納的筆下,賣花女是無知的,她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差異,只是著眼于較為膚淺的外在品質,即高貴的談吐方式和優雅的禮儀風度,并沒有意識到金錢和物質是隱藏在華麗外表下的經濟基礎。顯然,皮格馬利翁式的神話在蕭伯納的筆下,被賦予了一定的社會意義,體現出了社會的不平等:上層階級的語言及生活方式被用作下層階級的“正面的”參照,實際上它們實施的是符號權力。社會學家認為權力不是存在于詞語或符號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們對詞語的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對說出這個語詞的人的信仰。六個月后,賣花女掌握了上流社會的高貴語言,卻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記了,就是想用以前的發音說話也已經做不到了。從某一層面上說,蛻變后的賣花女伊莉莎成為語言的奴隸,然而她并不是放棄反抗的權利而一味地妥協。相反的,她是在跟希金斯代表的父權制社會暗暗地進行著斗爭,這種意識源自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也是對擁有話語權力一方的積極反抗。正如福柯所說:“反抗與權力是共生的、同時存在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系,就會存在反抗的可能性。”[1]240
二、身份危機和語言危機
LyndaMugglestone認為,在社會語言學出現之前,蕭伯納似乎不僅意識到了口音和階級明顯的共同變異,而且也意識到了R.A.赫德森提出的“主觀的語言不平等”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2]373就是說,蕭伯納在創作這部劇本時,意識到了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是造成語言上的不平等的原因之一。第一幕出場時,賣花女說著一口流利的cockney accent:“Ow,eez ye-ooa san,is e? Wal,fewd dan y’de-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eed now bettern to spawla pore gel’s flahrzn than ran awy athahtpyin.Willye-oo pyme f’them?”(哦,他是您的孩子嗎?哼,您做媽媽的要是管教管教孩子,他也不能把人家的花給糟踏完了,就跑開也不給錢。您替他給錢吧?)這樣的語言確定了伊莉莎的身份:來自倫敦東區的下層賣花女。在希金斯眼中,伊莉莎只是一片“爛菜葉”:“一個說話口音那么難聽的女人,在哪兒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該活著。你該記得你是個有靈魂的,能說人話的人。”語言能夠反映說話者的身份,而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標記具有社會意義,它可以傳遞一定量的社會信息,比如說話者所屬的社會群體等,同時也阻礙了下層階級應有的機會與權利。
19世紀時,倫敦東區人不僅被視為社會上的低能者,他們的土音還成為上層社會的人們在語音學和語言學方面某一失誤的范例。賣花女正是來自這樣的階級,因為沒有標準的發音,甚至不能去商店里當售貨員。而相比之下,說著一口標準倫敦口音的希金斯教授屬于社會的上層階級,他利用語言控制著伊莉莎。蕭伯納并不是簡單地描寫了賣花女如何蛻變成一位上流社會的語音純正、談吐文雅、儀態端莊的淑女,而是一個賣花女在舍棄了自己的cockney accent,努力學習標準英語過程中面臨的身份危機。正如王成兵所說,“身份是指人類在社會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為軸心展開和運轉的對自我的確認,主要圍繞性別、年齡、階級、種族和國家等差異軸展開,而身份危機則是指自我身份感的喪失”,[3]18即自我價值感、自我意義感的喪失。
伊莉莎雖屬于社會中的下層階級,但是她善良且會替別人著想,有理想、有追求,這與來自上層階級的希金斯不同,他自私自利、對他人和周圍的事物極其冷漠。在與希金斯和辟克林朝夕相處的日子里,賣花女漸漸對他們兩個有了感情,一個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女孩子盡心地接受一項項的腦力勞動訓練,為了自己以后能到花店賣花,更重要的是由于她與希金斯和辟克林之間的情誼。然而希金斯只是把她當作一件實驗品,一個實現自己規訓權力的工具。賣花女伊莉莎的身份危機表現為個人語言感染力的喪失,正如她自己向希金斯抱怨的:“你同我說過的,要是一個小孩子到了外國,幾個星期他就能學會當地語言,自己的話就忘記了。我就是這樣一個小孩子,到了你們國家,把我自己的語言都忘了,現在只能講你們的話了。”福柯的權力理論認為,權力是一種力量關系:“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他們總是既處于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19世紀的西方文化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社會,女性的行為受諸多因素約束,并沒有自己獨立的生活空間,她們只能依附于男性。語言能力不僅代表著知識,同時也代表著權力和地位,它能夠標識上流社會的特權、優越感。希金斯教授就是這一觀點的忠實捍衛者,他認為:發音問題是階級和階級之間、靈魂和靈魂之間的鴻溝。在希金斯眼中,伊莉莎只是一片“爛菜葉”,而她的麗孫林區土音是讓她下半輩子仍然只能在貧民區里混的關鍵所在。作為一個造詣極深的語音學教授,希金斯期望用一些制度化的特殊方式,制造出一個能遵循規范去行動的馴服的伊莉莎。這種特殊的權力技術即是福柯提出的規訓權力。希金斯在當時的父權制社會中是具有話語權的,再加上他的職業,也是被社會認可肯定的。因此,對一個出身卑微的賣花女來講,希金斯對其具有絕對的約束權力:“不超過三個月,我便可以讓她出席外國大使的花園宴會,別人一定以為她是一位尊貴的夫人!或許我還可以為她找到一個去貴族家中當保姆或店員的差事,那樣的差事一般要求能說一口純正的英語。”六個月后,賣花女掌握了上流社會的高貴語言,卻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記了,她就是想用從前的發音說話也已經做不到了。從某一層面上說,蛻變后的賣花女伊莉莎成為語言的奴隸:“她真可憐,跟誰也不敢頂嘴了!為了要讓自己規規矩矩的,她的氣勢全沒了。”
三、獨立與自由的新女性的誕生
蕭伯納的劇作《皮革馬利翁》于1914年4月11日公演,其中扮演希金斯教授的Beerbohm Tree改編了原創劇本:最后賣花女伊莉莎與希金斯教授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為此,蕭伯納大發雷霆,便創作了《皮革馬利翁》的后序。在這篇散文性的后序中,蕭伯納強調的是最后賣花女自己開了一家花店,并沒有與希金斯教授結婚。對于蕭伯納的這篇后序,Nigel Alexander認為:“蕭伯納認為一個獨立的女性比一個蛻變的淑女要重要得多。讀者不應該只看到賣花女外表的蛻變,更要關注一個獨立、自由的靈魂的誕生。”[4]23
經過希金斯教授訓練,賣花女伊莉莎被塑造了一個新的社會身份,即一位上流社會的語音純正、談吐文雅、儀態端莊的淑女。當意識到自己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及自己面臨的語言危機、身份危機之后,這位淑女并不是一味地順從男性的思想,相反的,她是在跟希金斯代表的父權制社會暗暗地進行著斗爭。這種意識源自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也是對擁有話語權力一方的積極反抗。福柯認為“言說既是權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障礙和阻力,是它的反抗點及對立的戰略形成的出發點”,即一定的話語言說同時也會創造、加強或削弱、對抗權力。剛出場時的賣花女便突顯出了自己追求平等和獨立的意識:“咱是個十分正派的人,跟誰比都不差。”[5]68當聽到一個上流社會的男士對自己的貶低時,她堅定地聲稱自己和他有同樣的權利待在這個地方。
福柯強調說,一個話語也可以作為一連串的事件來理解。[6]39賣花女伊莉莎也通過一些行為事實體現自己的特殊話語。例如在第四幕舞會結束后,伊莉莎因不滿希金斯教授對自己的無視,扔了他的拖鞋。這雙拖鞋可以被視為伊莉莎決心與過去決裂的一個象征物,也是拒絕自己的灰姑娘式的圓滿結局,即嫁給一個王子。她希望希金斯教授能意識到她的存在,尊重她的感受,而不是只把她當作一個毫無感情和人格的賭注。當天晚上,她便離開了實驗室,這一舉動使伊莉莎的形象更豐富,她的離開也正是她努力追求平等以及獨立的意識體現。
四、結論
通過分析賣花女伊莉莎的語言危機及身份危機,讀者可以領略到蕭伯納對神話模式的顛覆,這部劇作《皮革馬利翁》并不是簡單描寫一個賣花女的浪漫故事,它是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劇作,揭露了資產階級的虛偽。在等級秩序充斥著整個時代的背景下,人們在想盡辦法擠進上流社會的同時,卻失去了最為珍貴的東西:自我。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告訴我們,在相互交錯的權力網中,每個人既可能成為被權力控制的對象,又可能同時成為實施權力的角色。通過描寫一個普通的下層階級賣花女的故事,蕭伯納告訴讀者要去努力追尋一個自我認識的靈魂。
[1]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M].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Mugglestone,Lynda.“Shaw,Subjective Inequality,an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Language in Pygmalion”[J].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ew Series,1993:373.
[3]王成兵.當代認同危機的人學解讀[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4]Bloom,Harold.ed.George Bernard Shaw’s Pygmalion[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23.
[5]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
[6]丹納赫·斯奇拉托·韋伯.理解福柯[M].劉瑾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