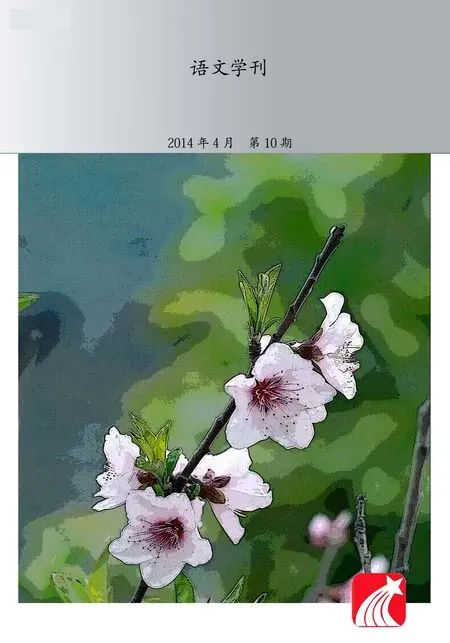三重人格:《西游記》人物形象的心理底蘊
○馬愛忠
(定西市岷縣岷州中學,甘肅 定西 748400)
古典名著《西游記》可謂家喻戶曉,該書“不僅在其離奇怪誕的情節,主要在于完整地塑造了一師三徒及神仙魔怪等眾多的典型形象”。[1]其中,豬八戒呆傻貪婪,沙僧憨厚老實,唐僧謹言慎行,孫悟空則融頑皮、精明和守職于一身。這“一師三徒”形象如此銘刻于人心,除了所謂“典型形象”,一定還存在心理深層的緣由。現用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理論對其剖析如下:
一、豬八戒——本我的化身
根據三重人格理論,“本我”“既無組織,也無統一的意志,僅僅有一種沖動為本能需要追求滿足”。[2]“它所有唯一的內容,據我們的觀點看來,就是力求發泄的本能沖動。”[4]豬八戒這個形象正是這種“既無組織,也無統一的意志”的“本我”的體現,其行動全由“本能沖動”左右、“為本能需要追求滿足”。貪吃是豬八戒的一大“本能”。《西游記》中寫到:“(豬八戒)一連就吃有十數碗……把一家子飯都吃得罄盡,還只是說才得半飽。”[4]除了貪吃,貪色是豬八戒的另一本性。該書中寫道:“你看那豬八戒,眼不轉睛,淫心紊亂,色膽縱橫,扭捏出悄語……那婦人與他揭了蓋頭道:‘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他們大家謙讓,不肯招你。’八戒道:‘娘啊,既是他們不肯招我啊,你招了我罷。’那婦人道:‘好女婿呀!這等沒大沒小的,連丈母娘也都要了!”[2]從中可知豬八戒是“本我”活生生的化身。人們或喜歡或討厭他,都是針對他身上存在的人類共有的赤裸裸的、被壓抑的“本我”。正如學者所言,“當我們在笑豬八戒的缺點時,卻在內心笑自己靈魂深處的隱私,笑世人的劣根性,笑人世間的弱點,從反思中獲得思想境界上的升華”。[6]
二、沙僧——自我的代表
《西游記》中沙僧穩重忠厚的性格完全符合弗洛伊德對“自我”的界定:“用一句通俗的話,我們可以說自我代表理性和審慎。”[4]“自我”的行動邏輯是現實原則,即“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響,滿足本能要求”。[3]沙僧總是能理性地分析“外界影響”,做出自己的判斷,力求按現實原則辦事,一舉一動都是理性和審慎的。比如該書有言:“沙僧放下擔子,攙著唐僧道:‘師父請起。’”[2]“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里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吃我一杖!’……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道:‘沙悟凈,你不保唐僧取經,卻來此何干?’沙僧作禮畢,道:‘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為引見引見。’……這沙僧倒身下拜。”[2]一個盡職盡責的沙僧形象躍然紙上。我們不得不敬佩其身上“自我”的理性色彩和現實原則。
弗洛伊德說:“自我有別于伊底之點尤其是在于自我有綜合其內容及統一其心理作用的那一趨向,而這則是伊底無能為力的。”[4]沙僧身上體現著這種“綜合其內容及統一其心理作用”的能力與追求團結、和諧的好品質。因此,說“沙和尚擁有了這些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6]其實針對的正是他身上的“理性”、“審慎”的“自我”體現。
三、唐僧——超我的模范
弗洛伊德對“超我”是這樣闡述的:“自我本可以其本身為客體,和其他客體無異,可加以觀察,批評,還可以做天曉得的其他種種活動。在這種情形之下,自我的這一部分可以監視另一部分。而且自我又可以分裂;分裂時至少暫時行駛它的許多機能。”[4]“我們既認為它是另一實體,便不得不給它以另一名稱,因此,我們乃稱自我的這一機能為‘超我’。”[7]“超我則已為最早的父母形象所鑄造。”[4]
“超我”在唐僧身上為何會如此根深蒂固呢?是自己不幸的身世、對佛的虔誠和唐王的殷殷期盼共同鑄就的。《西游記》中那段唐王排架關外、賜酒送別的描寫便可印證。這樣,唐王、佛祖及等待超度的眾生共同扮演了唐僧的“父母”形象,也就促成了“超我”在唐僧心里扎根。在取經途中,唐僧身上時時刻刻顯現著“超我”影子。比如“(唐僧)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于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遞于行者道:‘猴頭!執此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與你相見,我就墮了阿鼻地獄!’”[2]惡徒不除,難取真經的想法,正是這種以良心為核心的自我偵察機能即“超我”的外現,而對其用世俗的眼光苛求是不妥的。“西天路上他是一面旗幟,一塊凜然正氣的招牌,構成超我的核心。”[1]作為取經途中唯一的精神領袖,唐僧這一形象的價值與意義正在于此。
四、孫悟空——三重人格完美結合的典型
在《西游記》中,受到贊譽最多的莫過于孫悟空,他首先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者,其次,他又是一個武藝高強、變化多端、能戰勝各種兇魔惡妖的英雄人物。[1]這兩句話既是對孫悟空形象精辟的概括,同時也是對其身上“本我”、“自我”、“超我”的間接肯定。
對于孫悟空身上的“本我”,書中有言:“大圣卻拿了些百味八珍,佳肴異品,走入長廊里面,就著缸,挨著甕,放開量,痛飲一番。吃夠了多時,酕醄醉了。”[2]這種貪吃相,實與八戒無異。對于其身上的“自我”,《西游記》中亦有描述:“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爛板凳,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閑。容敘!容敘!’急辭別墜云。”[2]這段對話,反映出了孫悟空把握情感的理智與辦事的分寸,也正是“自我”的審慎與理性的顯現。對于其身上的“超我”,該書“前言”指出:“孫悟空是一個大膽的、富有斗爭精神的人物……取經途中,他面對各種妖魔,也是無所畏懼,總是敢打敢拼,或是上天入地,查問妖怪來歷,設法清除。”另外,他西天取經的信心與決心僅次于唐僧。“孫悟空在取經過程中,一方面為了保證取經的順利進行,不斷地使人格自我完善;另一方面通過斬妖除魔達到除害利民、‘普度眾生’的目的。”[8]這正好概括了孫悟空身上的“超我”特質。
綜上所述,《西游記》中的四個主要人物似乎與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論有一種對應關系,即豬八戒是“本我”的化身,沙僧是“自我”的代表,唐僧是“超我”的模范,而孫悟空則是三重人格完美結合的典型。這一結論的得出,有益于《西游記》研究向精神分析層面深入。
[1]孔仞非.西游記人物形象塑造的心理成因[J].明清小說研究,1997(3).
[2]吳承恩.西游記[M].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3]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華東師大出版社,2005.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M].商務印書館,2007.
[5]何峰.耐人尋味的異中之同與同中之異:《堂吉訶德》與《西游記》之比較[J].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6).
[6]王彬.西游記師徒四人形象及其現代意義[C].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7]馬躍.豬八戒形象的文化意蘊及理性思索[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6(4).
[8]紀倩倩.孫悟空形象塑造新論[J].濰坊學院學報,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