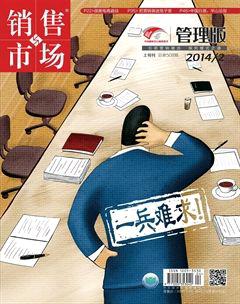人力困局帶來的“三把火”
楊鋼

人的問題和農民工回流問題,帶來的結果是——轉型升級不再是中國企業的選擇題,而是成為必選項。
德魯克在《下一個社會的管理》一書中曾經說過:“社會變化對于組織和管理者的成敗而言,可能比經濟事件還要重要!”當下中國社會能夠對中國企業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主要有人口變化以及歐美再工業化這兩大因素。在此,筆者就人口變化這個首要因素,來談談其對中國企業帶來的影響和改變。
人口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人口老齡化和農民工回流。
201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明顯出現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呈現負增長,這是一個根本性變化。由于這個變化,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勞動力投入都會受到一定影響,所以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預測,未來中國勞動人口比例會持續下降。然而,比起這一數據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醫療、教育資源的投入不足以及極高的房價,使得當前大多數大中城市的青年夫婦都不愿意生二胎,而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生二胎的夫婦,又受制于不符合“單獨”政策的局限。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的中國社會不僅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也進入了低生育率陷阱——而鄰國日本持續20多年的經濟低迷,首要原因就是人口老齡化和過低的生育率,這直接導致日本社會的平均年齡越來越高,而老齡人口的消費習慣更加保守,不像青年人那樣敢于消費而且是超前消費,這無疑會加劇經濟的疲軟。
農民工回流則始于2002—2003年首次出現的民工荒,其背景因素又可根據時間軸來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國務院于2005年取消了農業稅,使得農民的負擔有了明顯減輕,務農的積極性有了顯著提高。其次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的大批企業停工減產,導致農民工回流。再次是各地農地流轉政策的陸續出臺和陸續實施,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60條決定中的第11條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第20條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和第21條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力的相關利好政策,使得農村戶籍和有農地的農民可通過農地和農村戶籍身份實現“財產性收入”的增加,這又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外出務工的意愿。
在以上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農民工回流的趨勢將逐步擴大,由此產生的直接影響是勞動力的供應總量明顯減少,并且勞動力成本將會越來越高。因此,曾經長期依賴低價勞動力作為競爭優勢的中國企業,未來將會面臨生死大考。
人口老齡化與勞動人口的持續減少,對中國企業帶來的最突出影響是一線操作員工的招聘將越來越難,原本低廉的勞動力將不再低廉,由此將會給中國企業帶來三大變化:
1.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將被迫提高自動化程度,以減少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
在同等或相近的條件下,如果無法提升產品的價格,那么企業就一定會想方設法地降低成本以提高利潤率。其中,成本控制手段中最容易使用也經常被用到的就是減少對機械設備(尤其是自動化設備)的依賴,大量使用人力來替代機械設備。這種做法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前提下很有效,也幫助許多企業在初創期完成了原始積累。
事實上,不僅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常用這一手段,包括比亞迪、一汽轎車、豐田汽車在內的許多非勞動力密集型裝備制造企業,也曾經或正在通過人力來替代機械設備(例如用人工點焊取代激光焊接機器人)。而勞動力供給不足或當勞動力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將被迫提高自動化程度,例如改變生產工序和工藝、通過引進工業機器人來提高自動化程度,以減少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
典型的案例是國內知名的計算機外設品牌深圳雷柏,早在2007年就通過優化生產工序、增加工業機器人的數量來減少生產線上工人的總數。截至2012年年底,雷柏公司的員工總數已經從最多時的3000多人降至1000人左右,而工業機器人的數量也增加到70多臺。由此使得基層重復操作的產業工人數量銳減,而操作和維護機械設備(工業機器人)的技術工人數量遞增,而員工結構的改變,也顯著提升了深圳雷柏的技術實力和競爭優勢。
2.企業將積極改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提高薪酬福利水平,以提高對生產一線員工的吸引力和保留效果。
曾幾何時,在工廠里工作的產業工人們的工作環境和收入都飽受詬病,這種情況正在發生逆轉——珠三角、長三角和其他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里,一線生產工人的工作環境已經大幅改善,而一線生產工人的薪酬福利水平甚至已經超過了普通的辦公室白領。這一切,都是為了吸引和保留供給不足、招聘和保留難度越來越大的一線操作員工。
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加工制造業企業為例,當前一個普通的基層生產線操作工人,其平均月薪已經不低于4000元;而同一地區的應屆畢業生,尤其是坐辦公室的普通白領,其平均月薪也只有不到3500元,并且還有許多應屆生找不到工作,這與供不應求的一線操作工人相比形成了鮮明對比。
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應屆生的就業觀未發生大范圍改變的背景下,中國企業會更加重視對生產操作一線員工工作環境的改善,并提高他們的薪酬福利水平,以緩解招工難、留人難、流失率高的問題。
3.倒逼中國企業提高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向技術密集型和精密制造轉型與升級。
長期以來,中國制造都是低價低質的代名詞,盡管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聲音不絕于耳,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升級的說法也提了很長時間,并且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減稅和定向貸款支持等財政政策也從未停止過,但這些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解決方案從未真正改變中國企業長期處于低端制造和低質低價競爭環境的問題。反而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卻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低質低價低附加值的“三低”模式+日趨走高的人力成本=企業要么關張,要么向產業鏈的上下游擴張,或者向技術密集型和精密制造轉型與升級。因此,未來中國企業只能選擇從“三低”模式轉型升級為高質高價高附加值的“三高”模式,以此抵消勞動力不足和人力成本驟升的壓力。
更具意義的是,由人口老齡化和農民工回流引發的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招工難、留人難的問題,最終很可能成為促使中國企業實現轉型和升級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如果這樣的情況成為主流,那么中國制造也將真正迎來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新機遇,而由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也能夠從一句口號變為現實。這或許就是人口老齡化和農民工回流給中國企業帶來的意外驚喜!
如果說轉型升級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曾經是一個選擇的話,那么自2013年開始發生逆轉的人口問題和農民工回流問題,則讓轉型升級成為中國企業的必需。對于那些仍然故步自封的企業而言,這或許是個最壞的時代;而對于那些居安思危,早已開始謀劃和實施轉型升級的企業來說,這或許是個最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