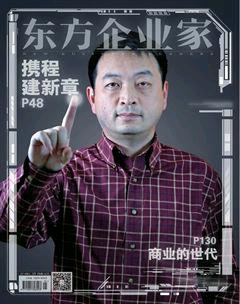職業(yè)的前途
現(xiàn)代化首先是人的現(xiàn)代化。歷史學(xué)家高家龍著作《大公司與關(guān)系網(wǎng)》記述1880-1937年六家中外大企業(yè)在華的組織變遷。當(dāng)時(shí)的外企和民企都努力將中國(guó)員工從中世紀(jì)的人身關(guān)系擺脫出來(lái)。美孚石油把員工派駐外地,內(nèi)外棉和申新建設(shè)的工人社區(qū),有后來(lái)計(jì)劃經(jīng)濟(jì)單位辦社會(huì)的雛形。
半個(gè)世紀(jì)之后,外企和民企重新登上歷史舞臺(tái),本書的邏輯也就重演。學(xué)者甘陽(yáng)著書《統(tǒng)三統(tǒng)》,試圖整合中國(guó)古典、革命和西化三個(gè)傳統(tǒng),他的理想在企業(yè)界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一部分。典型民企的組織文化,如果可以稱為組織文化,往往是中世紀(jì)的人身關(guān)系、類政治動(dòng)員和泰羅式科學(xué)管理隨機(jī)的拼湊。直到今天,幾代員工都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起步的。
但之所以稱為拼湊,三者本質(zhì)上是沖突的。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越來(lái)越難以為繼。柳傳志那一代人也許只能隱忍:“大環(huán)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環(huán)境。小環(huán)境還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適應(yīng)環(huán)境,等待改造的機(jī)會(huì)。”新一代有更多選擇,沒(méi)有耐心等待,而是拍屁股走人,換個(gè)環(huán)境。85后在職業(yè)生涯早期跳槽的頻率遠(yuǎn)高于前輩們。
中國(guó)制造長(zhǎng)期以低人工成本著稱,不僅僅是工資低,世界上還有很多窮苦的人民。而是中國(guó)工人可以在低廉的工資下嚴(yán)格執(zhí)行工作流程、紀(jì)律。可以說(shuō)從高家龍研究的那個(gè)時(shí)代到現(xiàn)在,對(duì)中世紀(jì)國(guó)民性的改造,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也就注定走向反面。
2010年就發(fā)生 “12連跳”的悲劇。這也是個(gè)世代問(wèn)題。年輕一代沒(méi)有吃過(guò)父輩的苦,見識(shí)過(guò)父輩沒(méi)有見識(shí)過(guò)的豐富多彩的生活,很多農(nóng)二代從小跟著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長(zhǎng)大,從來(lái)沒(méi)有種過(guò)地。機(jī)械操作就變地不可忍受。
低工資也已不能維持。從2000年代中期以來(lái),民工荒越演越烈,不只技術(shù)工人,普工也缺。民工荒的重要成因之一,中國(guó)已經(jīng)通過(guò)劉易斯拐點(diǎn)。這一概念用來(lái)分析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二元經(jīng)濟(jì),農(nóng)業(yè)部門的過(guò)剩勞動(dòng)力向工業(yè)部門輸送殆盡,用工成本即開始上升,標(biāo)志著向發(fā)達(dá)國(guó)家轉(zhuǎn)型。
網(wǎng)上有科學(xué)工作者轉(zhuǎn)述見聞:一個(gè)做實(shí)驗(yàn)的教授來(lái)實(shí)驗(yàn)室玩,對(duì)我說(shuō):我們的工作極端無(wú)聊,每天就是磨晶體,做電鏡……我問(wèn):那招個(gè)做手機(jī)貼膜的民工豈不是手藝更好?教授答:請(qǐng)不起啊,民工在北京一個(gè)月五六千,博士只要兩千多。
人工整體上漲,看起來(lái)對(duì)員工是好事。但企業(yè)付出更高的成本,能換來(lái)需要的價(jià)值嗎?傳統(tǒng)將員工分成藍(lán)領(lǐng)和白領(lǐng),這是大工業(yè)的分工,工業(yè)的原則是通過(guò)標(biāo)準(zhǔn)化獲得規(guī)模經(jīng)濟(jì)。早在1990年代,《哈佛商業(yè)評(píng)論》就注意到,已經(jīng)只有約1/3的成本直接來(lái)自制造,2/3則來(lái)自流轉(zhuǎn)成本,這是由于客戶需求的差異化造成的。
十幾年過(guò)去,這個(gè)比例進(jìn)一步拉大,同理C2C,在美國(guó)發(fā)生的早晚,越來(lái)越早,在中國(guó)也會(huì)發(fā)生。未來(lái)的員工分成少數(shù)的標(biāo)準(zhǔn)化工人和多數(shù)的差異化工人,解決方案專家。不幸的是,我們培養(yǎng)了太多標(biāo)準(zhǔn)化工人。大學(xué)生的簡(jiǎn)歷上都寫四六級(jí),Office熟練。文革前的學(xué)制甚至更合理一些,初中畢業(yè)之后,所謂兩條腿走路,上高中自費(fèi),上技校有很高的補(bǔ)貼。
如何轉(zhuǎn)型?公共教育改革來(lái)日方長(zhǎng),員工和企業(yè)的關(guān)系越來(lái)越不穩(wěn)定,也不能指望企業(yè)培訓(xùn)。小伙伴們可以靠自學(xué)嗎?在社會(huì)大學(xué)中接受再教育。
外企長(zhǎng)期是就業(yè)的優(yōu)先選擇,待遇優(yōu)厚,管理規(guī)范,又有面子,能實(shí)現(xiàn)人生價(jià)值。這種光環(huán)逐漸黯淡了。業(yè)務(wù)上受到本土企業(yè)的猛烈挑戰(zhàn)。歷任多家知名外企高管的杜家濱評(píng)價(jià):我在中國(guó)從來(lái)沒(méi)有覺(jué)得生意好做,即使開始好做,后來(lái)肯定也會(huì)變得難做,大家都進(jìn)來(lái)了。業(yè)界還有段子:美國(guó)人發(fā)明技術(shù),日本人精益求精,然后中國(guó)人學(xué)會(huì)了,于是大家都窮了。
外企職業(yè)生涯也早有“玻璃天花板”的說(shuō)法,盡管看不見,它就擋在那。2006年4月“史上最牛女秘書”向公眾暴露了外企管理的另一面。對(duì)這一事件有多種解讀,其中之一,由于歷史原因,外企形成一個(gè)來(lái)自大陸以外華人地區(qū)的中高級(jí)經(jīng)理階層,與本土經(jīng)理人群體存在矛盾,在這件事中以一種奇特的方式爆發(fā)。
外企的薪資優(yōu)勢(shì)在逐漸侵蝕。《世界是平的》曾風(fēng)行一時(shí)。而對(duì)于全球企業(yè)的普通員工,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向下傾斜的。2000年代初,外媒還在討論白領(lǐng)崗位從歐美向第三世界轉(zhuǎn)移,而到這一年代后期,在國(guó)內(nèi)外企派遣員工已很常見。壓縮成本還有一些“人性化”的方法,比如把員工從美國(guó)派回中國(guó),等他安家落戶,就降到local的水平。
國(guó)企卻已不是吳下阿蒙。如今基本退出競(jìng)爭(zhēng)性領(lǐng)域,收縮到資本密集和政策壁壘行業(yè),待遇優(yōu)厚,管理也大有長(zhǎng)進(jìn)。就業(yè)形勢(shì)嚴(yán)峻,于是相當(dāng)一部分85后流向國(guó)企及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與20多年前相反的方向。
1984年潘石屹分配到石油部管道局經(jīng)濟(jì)改革研究室。傳說(shuō)辦公室新分來(lái)一個(gè)女大學(xué)生,對(duì)發(fā)給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潘勸她湊活用,她十分認(rèn)真地說(shuō):“小潘,你知道嗎,這套桌椅可能會(huì)陪我一輩子的。”1987年潘石屹辭職,揣著80元南下。
現(xiàn)在國(guó)家有錢了,機(jī)關(guān)也不會(huì)再一套桌椅坐一輩子,但85后會(huì)有這樣坐一輩子的覺(jué)悟嗎?或者即使他們有覺(jué)悟,參考?xì)v史經(jīng)驗(yàn),就能坐得住嗎?我猜想,他們中的一部分有一天會(huì)逃回北上廣。其實(shí)北上廣的發(fā)展已經(jīng)到達(dá)某種極限,而因?yàn)楦哞F拓展,工業(yè)內(nèi)遷等動(dòng)力,很多二三線城市迸發(fā)生機(jī)。可能更多的人,經(jīng)過(guò)若干年積累,會(huì)選擇就近創(chuàng)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