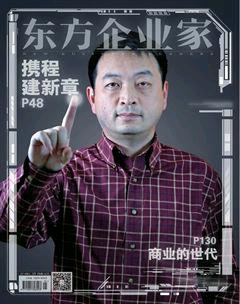相生相克
緬甸有個傳說,有一條惡龍,每年要求村莊獻祭少女,每年村里都會有個少年英雄去殺惡龍,但無人生還。又一個英雄出發時,有人悄悄尾隨。龍穴鋪滿金銀財寶,英雄用劍殺死惡龍,坐在尸身上,看著閃爍的珠寶,慢慢長出鱗片、尾巴和角,變成惡龍。
職場的代際競爭
如同幾代消費者一起入市,幾代人雖然先后參加工作,在1980年代初站在一個職業的起跑線上,相應代際競爭也比成熟的商業社會來地激烈地多。那些今天保持成功的企業都能處理好這方面的關系。
1995年柳傳志致信楊元慶:“在純粹的商品社會,企業的創業者們把事業做大以后,交下班去應該得到一份從物質到精神的回報;而在我們的社會中,由于機制的不同則不一定能保證這一點。這就使得老一輩的人把權力抓得牢牢的,寧可耽誤了事情也不愿意交班。我的責任就是平和地讓老同志交班,但要保證他們的利益。”
柳傳志2000年退居二線,交班給楊元慶(1964)和郭為(1963),也就是隔代相傳。西方商業有類似的例子,1981年GE董事長雷吉·瓊斯(1917)交班給韋爾奇(1935)。有董事提議先由另一名58歲的高管過渡。瓊斯認為如果這樣做,韋爾奇會走人。韋爾奇執政20年后,再傳于杰夫·伊梅爾特(1956)。
商業社會隔代相傳,由企業自行決策,各家錯開。而在中國,國企有嚴格的組織秩序,一般代代相傳,民企中家族企業按平均生育年齡,會跨兩到三代,非家族企業很多跨兩代,由于時代的劇變,都會呈現出宏觀周期。特別是50后成為小年。這在科技界更明顯,后者更需要青年時的漫長訓練。造成40-60后交接的運動。
再創業繼承
家族企業將上演一幕幕中國版的豪門恩怨。有統計稱,家族企業能傳兩代的不到20%,傳三代的不到5%。其實中國古人早有認識,君子之澤三世而斬。但也是出于中國文化,不能傳給兒女,我又為什么奮斗呢?
家族企業基于特殊的人身關系,而現代企業基于普遍的契約關系,經理人靠業績上位。人身關系難以傳承,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這也是家族企業引進經理人,甚至傳承給經理人大多以失敗告終的原因。在工業時代,企業競爭更多地取決于資本規模,遺產的繼承即確立企業的傳承,但今后越來越取決于企業家能力。根據達爾文的理論,用進廢退不能遺傳。歐美很多家族企業傳承辦理信托,在國內也略顯超前。
沒有絕對的事情。商業史上也有少數的案例,三世而斬,但企業沒有衰亡,而是從家族平穩轉入經理人,基業長青。追溯第二代,都成功再創業。例如IBM。這種傳承方式的邏輯在于,二代憑借人身關系上位,憑借再創業的業績證明自己的能力,也符合經理人的標準。通過這樣一種雙重角色過渡,第三代就能平穩交接給純粹的經理人。
傳承要及早布局,雷吉·瓊斯剛入主GE不久,就開始規劃。中國歷史上王朝繼承相對平穩的大多也是如此,宋高宗雖然臭名昭著,但傳給宗室子,退位后相安無事。如果有意于再創業繼承,就更要深謀遠慮。
再創業和繼承最好在同一領域,既有經濟上的協作效應,也能整合上一代的人身關系。中國企業盛行多元化,經常采取分封制,不同家族成員打理不同業務,也可以稱為再創業,但這種架構很難實現上述的轉變,更趨于爭奪資源。不過可以用來安撫繼承競爭的失敗者。
消費的代際互動
在商業社會,消費潮流的傳承顯然是順序的。而國內的代際差異更大,1980、90年代幾代人同時疊壓在一起。進入網絡時代,出現某種倒序。網絡的消費情境與傳統完全不同。起碼要會用電腦,老一代年輕時還沒有電腦,甚至沒有學過拼音,就被擋在外面。他們最終還是參與進來。蘋果普及觸屏人機界面,降低了技術門檻。再就是求助子女,網絡世代很多人都給父母當過代購。但老一代對網絡語境的影響始終是微乎其微的。
網絡世代之間,也出現一個倒序的案例。即時通訊長期涇渭分明:MSN的主流人群是白領,QQ是學生。當更低齡用戶群的應用更趨多元化,MSN卻因各種原因式微,即時通訊不可或缺,其用戶大批向QQ遷移。
新應用新概念層出不窮,更新越來越快。對當下的前沿,早期網絡世代也會不明覺厲。比如在90后中流行的彈幕視頻網站,用戶留言以字幕在視頻中動態呈現,稱作彈幕。源于日本的niconico,引入中國主要有AcFun和bilibili,簡稱A站B站。
從傳統觀眾的角度,彈幕對觀看是種干擾,不像傳統字幕位于屏幕下方,字數少,字幕會彈到屏幕各處,特別是高潮部分,用彈幕站的術語“前方高能”,整個屏幕都被彈幕覆蓋。傳統(其實沒有幾年,土豆網2005年創立)視頻網站早期為提升觀看體驗做了巨大的努力。彈幕站的興起,可能反映在這個瓶頸解決之后,體驗的重點轉向互動。
這種變化最終會傳到上游。在產品時代,員工和消費者之間的代際差異不太重要,經驗是重要的,資歷是必要的,員工在職業階梯上慢慢攀爬,特別是日本企業的年功制度。今后以客戶為中心,年輕人總是最活躍的消費群體,企業用人可能會出現比1980年代更傾斜的情況,后來居上,年輕的產品經理自己就是用戶。這會造成類似的員工代際沖突嗎?或者轉化為高頻的創業潮?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今天最尖銳的代際沖突,不在企業,而在家庭。我們不關注文化,只討論對下一代職業發展的影響。儒教將政治奠基于家庭倫理,沒有讓政治變得溫情,卻把家庭變成官僚機構。今天典型的中國傳統家庭,子女如同銷售,在父母的人際關系,所謂“中國式親戚”中如同上市公司的季報,必須不停地按時完成數字。
這樣的家庭教育下,不可能有任何職業生涯的概念。這意味著把整個職業生涯,正常人至少三十年,作為一個整體來規劃。為了整體最優,必然犧牲一些局部,這也是企業戰略的意義。但一旦不能按時完成數字,會給父母造成巨大的焦慮,放出巨大的壓力。大部分子女都不能抗拒這樣的壓力。
這種壓力通常會在兒女三十歲前后達到極大值。三十也是職業生涯關鍵的轉折點,面臨職業轉型或創業的抉擇。壓力主要來自買房、結婚和生育,都是大事,且持續影響后半生。而職業轉型和創業也需要承擔巨大的投入和風險。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兼顧。
職業女性受到的壓力尤其大。由于革命的作用,中國大陸女性在職業和創業中的表現,要比其它華人社區和毗鄰的日韓等國活躍地多,盡管也存在性別天花板、性騷擾等問題。約翰·沃洛諾夫在《日本浪費的人力》一書中用很大篇幅抨擊了該國職業女性的境遇。但這種活躍的職業角色和仍然保守的家庭角色,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沖突。
實際上在家庭生活的早期,望子成龍,女兒則被預期嫁人,背的銷售指標更低。這造成男性個體普遍兼具晚熟和早衰,而社會呈現某種陰盛陽衰。但從大約25歲甚至更早,就會開始受到中國式親戚逼婚的壓力。“剩男”同樣存在,但壓力相對小。早在網絡時代前,婚介所的資料就顯示,剩男是素質較低,剩女則是較高的一群,但只有剩女被污名化。這樣的無物之陣,加之女性在生育中的付出更多,對職業生涯的干擾更大。
不幸的是,在這種文化最喧囂日上的時候,也是中國的職業環境正發生劇變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