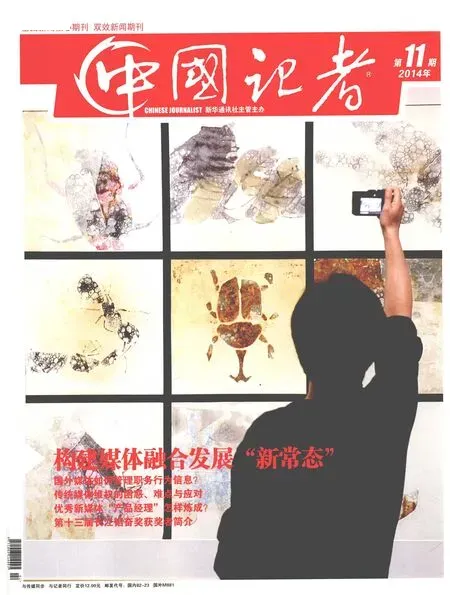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美國媒體自我審查的歷史與現實
□ 文/馬桂花
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美國媒體自我審查的歷史與現實
□ 文/馬桂花
在美國,賦予新聞自由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一直都是媒體追求自由報道的尚方寶劍。然而近年來,隨著美國政府對媒體泄密事件的密集調查以及法律對涉及國家安全信息實施監控的規定,媒體夾在新聞自由與保護美國公民、維護國家安全的愛國責任之間,地位十分尷尬。
國家安全 美國媒體 自我審查
立法維護國家安全
美國不少法律都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規定對發表機密信息的行為實施刑事處罰。《間諜法案》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臺,當時是為了打擊未經授權批準占有并泄露國防機密的行為。1942年,《芝加哥論壇報》在報道中暗示,軍方已破解日軍密碼。據報道,羅斯福總統曾一度威脅要“派海軍陸戰隊占領論壇報塔樓”,還差一點就起訴該報。之所以沒有起訴,也正是法律未能執行的主要原因——起訴只會導致更多的機密被泄露,進而讓敵人對最初披露內容的嚴重性產生警惕。
1950年《間諜法案》增加了一項補充規定,禁止發表有關“情報活動通訊”的機密信息。1982年《情報身份保護法案》規定,披露秘密特工身份為犯罪行為。當時,一位中央情報局站點負責人在其姓名被媒體公布后遭到謀殺。還有一項法律規定,若有理由相信泄密會傷害美國,則禁止披露有關原子能的機密。
一戰和二戰期間,為保護軍事機密,隨軍戰地記者的報道必須經過嚴格審查。1941年12月,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簽署行政命令,成立了“審查辦公室”負責審查國際通訊。審查不限于新聞報道,當時也有郵政審查。在后期的戰事中,戰地報道接受的審查程度不同,據稱,有的審查與其說是出于軍事考慮,不如說是政治原因。特別是在越戰和對格林納達的侵略中,更是如此。聯邦政府管理部門越戰中試圖阻止《紐約時報》刊登屬于高級機密的“五角大樓文件”,警告說根據1917年頒布的《間諜法案》,此舉將被視為叛國。最終《紐約時報》勝出。
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純屬軍方與媒體之間達成的默契。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為保護軍事機密,五角大樓對媒體報道地面戰加以限制。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期間,許多隨軍記者也面臨同樣問題,他們在報道中不得提及部隊的具體方位。戰地記者通常在獲許隨軍前必須簽協議,一旦違約則會受到懲罰或強迫調離,如此看來,隨軍報道對這些記者來說既是一種保護也是監控。
事實上,這些法律大多難以執行。迄今為止,美國還沒有什么媒體因發表機密內容而受到處罰。但針對政府官員和雇員泄密的指控則在不斷攀升。
“9·11”恐怖襲擊后的2001年10月,美國通過《愛國者法》,授權國家安全和司法部門對涉及專門化學武器或恐怖行為、計算機欺詐及濫用等行為實施電話、談話和電子通信監聽,并允許電子通信和遠程計算機服務商在某些緊急情況下,向政府部門提供用戶的電子通信,以便政府掌控涉及國家安全的第一手信息。
奧巴馬任總統前40年間,美國只有三個案件運用《間諜法案》起訴政府官員泄密。不過,奧巴馬當政后,當局對政府雇員向媒體泄露國家安全信息實施嚴打。2009年以來,當局已根據《間諜法案》起訴了6名政府雇員和2名承包商,其中包括2013年6月對國家安全局泄密者斯諾登的指控。
2010年,美國國務院分析師史蒂芬·金被控向福克斯新聞泄漏關于朝鮮的機密,該案目前還沒有定論。在2013年7月法院裁決中,一位聯邦法官表示,政府沒必要表明泄漏的信息有損國家安全,只要金自己知道后果并蓄意泄漏構成事實就行。《華盛頓郵報》2013年5月報道說,福克斯新聞記者詹姆斯·羅森在金案中受到調查。安全部門拿到了羅森的電話和電子郵件記錄,跟蹤到他在國務院的來去蹤跡。羅森沒遭到犯罪指控,但聯邦調查局調查人員寫到:有證據顯示他是“共謀者”。
為防止官員泄密,美國國防部已修訂“信息安全計劃”手冊,要求對全部門實施泄密事故報告系統,跟蹤未經批準的信息泄露,并責成負責情報的國防部副部長協同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部長一起監控所有“主要、全國性媒體”對未經批準的國防部機密信息的泄露情況。國防部還啟動一個自動安全事件報告系統及部內監控網絡、內部威脅計劃和未經許可泄露情報工作組。
《哈佛法律評論》2009年刊文稱:美國的確有一些法律規定,公布機密信息屬非法。但這些法律從未用于懲罰新聞記者,即使有的新聞報道看起來完全符合現有刑事處罰的范疇。對媒體而言,通行的模式是自我規范和自我審查。不少業內人士認為,這些法律未能執行本身意味著全國已就媒體自我規范達成了有力的共識。
媒體“自我審查”
的確,對于許多媒體,由于擔心利益沖突、訴訟甚至迫于商業、政治壓力等,選擇“自我審查”的做法由來已久。
1969年,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專員尼古拉斯·約翰遜在《電視指南》上發表文章說,在美國“審查制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同意一些電視網絡官員的看法,認為電視應受到審查,但對“誰來審查”有些異議,畢竟當時多數審查屬公司審查,而非政府審查。新聞業的這種自我審查因其隱蔽,很難取證。
1995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新聞節目“60分鐘”曾試圖就煙草公司故意掩蓋香煙的健康危害,追蹤這一在當年堪稱最大的新聞,但最后卻因擔心陷入煙草業的訴訟而放棄對告密者的采訪。此例美國重量級電視節目的“自我審查”令從事深度調查的記者十分寒心。《紐約時報》特別以《CBS的自我審查》為題就此事發表評論,稱CBS此舉是基于告密者曾與煙草公司簽訂的嚴守公司內部秘密的協議,如果訴訟成立,CBS將面臨大筆賠償。
《新聞周刊》專欄作者強納森·奧爾特曾表示:“在就業緊張的情況下,人們通常會避免讓自己或老板陷入麻煩。因此有的報道會放棄,雙關語被刪除。”“媒體準入項目”負責人安德魯·施瓦茨曼認為,此類自我審查并非誤報或虛假報道,而只是根本不報。記者為保住飯碗,編輯為維護公司利益,如此眾多小行為或不作為,最終積少成多,令媒體成為“公司友好型”。
“全球問題”網站創辦人阿努普·沙阿發表于2012年的《美國媒體》一文中稱:“在美國沒有正式的審查制度,但有一種被稱為‘市場審查’的制度,即主流媒體因不愿冒犯廣告商和媒體業主而不刊登某些報道。如此一來,媒體實際上在進行一種自我審查,對諸如企業行為等重要問題不予報道。”幾大新聞網的記者都有因政治原因自己的調查不會被播發的經歷。這表明,哪怕是最自由的媒體,公司影響仍會左右報道的內容。大費城分地區報業協會主席亨利·霍爾庫姆當記者40年,他認為,40年前報紙的使命十分清晰,但公司壓力逐漸讓其模糊。
文章援引美國媒體獨立監督組織——公正與準確報道(FAIR)的雅尼娜·杰克遜的話說,60%參加該機構調查的美國記者承認廣告商“使盡招數改動報道”。“有的廣告商槍斃一些稿件,推薦另一些報道。”她認為,對廣播新聞和紙媒新聞而言,公司和廣告商的影響可謂壓倒一切。一些地方廣播公司受大公司的鉗制,與其說是對公眾發揮“告知”作用,不如說是“娛樂”,公眾看這些電視新聞后會“更加無知”。
2000年4月,在皮尤調查中心和《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四成記者和媒體高管都承認自己進行自我審查,故意不碰一些更有新聞價值的報道,或為了所屬新聞機構的利益,在報道中盡量軟化語調和口吻。盡管在入行時大多都懷抱崇高的理想,但不少記者都盡量避免有爭議的報道,以免讓公司卷入與其他公司或政府機構之間的沖突。當然除了公司內部的自我審查,還有來自外力如廣告商等的壓力。
奧巴馬總統任職期間,對泄密行為實施嚴控,主要媒體對此都采取默認態度。美國記者兼律師格倫·格林沃爾德認為,太多記者將自己調至自我審查模式,從事“諂媚的新聞”。
一項針對記者的調查顯示,美國記者中偶爾未經許可使用機密商業或政府文件的比例由1992年的81.8%降至2013年的57.7%。約四成美國記者不會發表類似斯諾登泄漏的信息內容。
報業管理也不例外。2004年,《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里森和埃里克·利希特布勞發現了小布什政府未經授權的非法竊聽計劃,但報社將此稿壓了15個月,直至小布什再次當選。當局官員曾警告《紐約時報》高層,若登此文,就是幫恐怖分子的忙。報社只好接納。2006年,《洛杉磯時報》也向國家安全局讓步,將一篇有關美國政府監聽國人的報道扣下未發。
此外,越來越多的媒體在發表名人采訪報道前,需要讓他們審閱文章或圖片。有的名人的代理機構會對采訪客戶的記者十分挑剔,避免不利報道。
政府嚴打泄密,媒體帶著鐐銬跳舞
在媒體競爭極其激烈的今天,信息的準確與獨家已成為各大媒體競相追逐的目標。然而,隨著當局對政府雇員泄密實施密切跟蹤,嚴重依賴信息源的媒體人報道風險急劇增加。
《華盛頓郵報》前執行編輯萊昂納多·唐尼2013年10月刊文稱:《愛國者法》的通過令報道國家安全的記者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政府官員不愿與記者交談,擔心談話內容會隨時遭到監控。于是乎,記者與少有的信源盡量避免使用電話和電子郵件,只能偷偷見面交談。還有一些新聞機構甚至為受過加密訓練的記者設立單獨的電腦網絡和安全房間,躲開監控。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加密文件和涉密人數也日漸增多。著名律師詹姆斯·古德爾在《為新聞而戰》一書中稱,2010年,奧巴馬政府為770萬份文件加密,比前一年增加了44%。此外,美國還有480多萬政府雇員和承包商通過安全調查,可以進入安全保密設施,涉密概率明顯增加。
2012年,《紐約時報》、美聯社、《新聞周刊》等媒體刊發美國對伊朗實施網絡襲擊、由雙料間諜挫敗在也門的恐怖計劃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決定:減少各機構獲準向媒體通報情況的官員人數,公開情報信息必須得到參眾兩院情報委員會批準,并允許政府剝奪非法泄露機密信息的情報官員的退休金。
2013年5月,美國司法部在調查一起涉及中央情報局泄露事件時秘密截獲美聯社記者的電話記錄,并在一個刑事泄密案件中將目標鎖定福克斯新聞的一位記者。但最終,新聞記者沒有受到犯罪指控。但媒體認為,奧巴馬當局對泄密事件實施的強硬手段將對依賴政府機構內部線人的新聞調查造成嚴重影響。特別在當今數碼信息時代,當局不必逼迫記者交出信源,只需進行電子調查就能找到證據。
不僅獲得涉密信息難度增加,播發此類信息也絕非易事。對涉密信息的掌控與決斷已成為對媒體高層智慧的考驗。
2010年11月28日,《紐約時報》和一些歐洲媒體開始編發該報獲得的美國駐外使館發給華盛頓高級決策者的數千份電報。《紐約時報》在《告讀者信》中稱,刊登這些機密的外交文件是基于重要的公共利益,試圖讓公眾更好地了解美國外交的目標、成功、妥協和失意。盡管如此,《紐約時報》還是跟維基泄密和其他獲得這些機密文件的新聞機構私下溝通,對一些文件進行編輯處理,盡量統一行動。
關于如何選擇涉密信息,《紐約時報》稱:“刊登涉密信息對媒體而言絕非簡單的決定。編輯試圖在讓公眾了解信息價值與可能給國家利益帶來的潛在風險之間取得一種平衡。通常,如果公布秘密信息可能給信息源引來報復行為或者透露行動情報進而在戰爭中造成對敵方有利,我們就會選擇不刊發。我們刪去那些可能讓恐怖分子得到武器材料、損害正對敵對國家的情報搜集計劃或透露有可能被敵人利用的關于美國軍事能力的信息。但我們不太會因有可能引發外交沖突或讓官員尷尬而審查那些坦率的言論。”
2006年,蕾切爾·斯莫爾金在《美國新聞評論》10月/11月刊中,發表《憑判斷力做決定》一文,分析美國大報編輯如何定奪根據機密信息采寫的國家安全報道。在文章中,曾任《華盛頓郵報》執行編輯的萊昂納多·唐尼稱,刊登報道的兩難不僅限于國家安全方面的文章。媒體編輯會因各種原因不發或槍斃稿件:“火候未到,太長,不夠有趣,不夠準確等等。”在面臨邊界難定的國家安全問題時,媒體應盡可能多地了解全面信息。
《華爾街日報》執行編輯保羅·施泰戈爾說:“人們通常以為,只要我們認為有新聞價值,就會刊登從采訪中得到的信息。但事實上我們總會傾聽負責任的政府官員表示出的擔心,并會在就刊發做出最終決定前嚴肅權衡。”
《今日美國》編輯肯·保爾森表示:“新聞機構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監督,他們的使命是審查政府的所作所為,特別是當政府行為引起違憲的爭議時更是如此。但即便如此,你還是要對即將發表的內容進行仔細檢查,確定是否有什么內容會嚴重損害國家安全。”
戴著腳鐐跳舞已成為世界媒體的常態,當然,舞跳得如何取決于腳鐐的重量,選擇的舞蹈,甚至舞者的心態,任何變數都會讓結果大不相同。
(作者單位:新華社北美總分社)
編 輯 梁益暢 46266875@qq.com
本刊新聘特邀顧問四川日報報業集團總編輯、四川日報社總編輯陳嵐同志簡介
陳嵐,女,漢族,1972年11月出生,籍貫重慶,中共黨員,高級編輯。1995年四川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后進入四川日報社從事新聞采編工作。2004年起先后擔任四川日報社經濟新聞部副主任、編輯中心主任、時政新聞部主任、四川日報社總編輯助理、四川日報報業集團總編輯助理;2010年12月起任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黨委委員,四川日報社副總編輯;2014年3月起任四川日報報業集團總編輯、黨委副書記,四川日報社總編輯。
2009年被中宣部批準為全國宣傳文化系統第四批“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2012年,被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為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2008年,被四川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部批準為首批四川省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2011年,被批準為第九批四川省學術技術帶頭人后備人才。
陳嵐同志忠誠黨的新聞事業,講政治,顧大局,勇創新,重實干,在推進新聞創新、提升輿論引導能力、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等方面深入思考、積極實踐,參與編輯、采寫的多篇(組)新聞稿件和論文獲得國家和省級新聞獎。(四川日報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