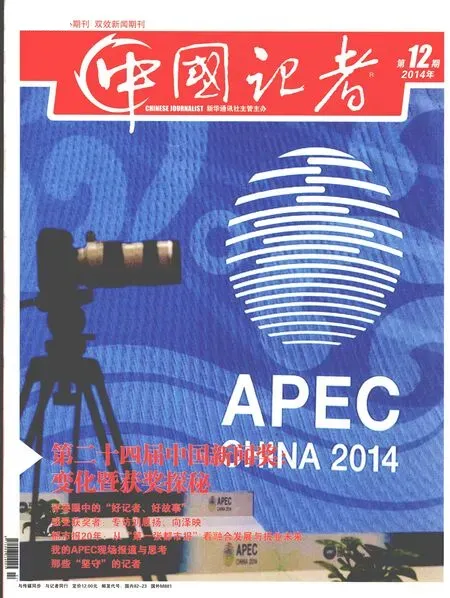成為范長江式記者需要什么特質
——《中國記者》專訪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向澤映
□ 文/本刊記者 梁益暢
成為范長江式記者需要什么特質
——《中國記者》專訪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向澤映
□ 文/本刊記者 梁益暢
長江韜奮獎是中國新聞界的最高職業榮譽,能夠在百萬新聞工作者中脫穎而出戴上這頂桂冠的新聞人,需要具備什么特質?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總裁向澤映,從一名歷史專業畢業的新聞“門外漢”,經過近30年不懈前行,終于成長為省級報業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并站上中國新聞界最高領獎臺,他身上體現出的特質,應該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國記者》近期專訪向澤映,聽他講述了如何從五個“萬里行”一路走來。
記者首先應是雜家:故事迷、背包族、收藏愛好者、文學青年……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相當于一個人成長的左右腳,缺一個都不行。這就是知行合一,對人的成才至關重要。——向澤映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四川廣漢綿水邊某小村莊,夏夜繁星下,曬壩上乘涼的人民公社生產隊社員扇著蒲扇,圍著一個講故事的人聽得津津有味,向澤映小時候總是搬條板凳坐在最前面。巴蜀地區有擺龍門陣的傳統,每個生產隊都有幾個此中高手,能將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引人入勝。所講無非《三國演義》《說唐》《水滸》《聊齋志異》等歷史演義或民間故事,但對生于1964年的向澤映而言,一個個精彩的故事,既豐富了知識,又拓展了想象力,而且深深體會到了故事的魅力。
“到重慶工作后,沙坪壩有個‘故事角’,文化館每個周末都會組織藝人講故事,還進行方言曲藝比賽,我經常去湊熱鬧,有時人太多,就干脆坐在地上。” “故事迷”向澤映說,愛聽故事的習慣一直沒丟。也許就是這種對故事的熱愛,無形中推動向澤映由一個歷史專業的大學生轉變為一個以寫故事為生的媒體人。
“今天的歷史是昨天的新聞,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向澤映說,他1981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學習,但對新聞一直有愛好,并且旁聽中文系、新聞專業的課程。當時川大歷史專業的教學,強調到曾經發生過歷史事件的地點采風、訪古,于是向澤映一到假期就和同學一道背上背包,足跡踏遍了眾多川內古跡。作為上世紀80年代初的“背包族”,向澤映說在這種田野考察中,他學會了做好新聞工作必備的調查研究這一基本功。
向澤映說,他從上學后,對歷史地理和文化相關的東西總是有股著迷的感覺。蜀中歷史文化名人李白、蘇東坡、楊升庵、李調元等的詩文、掌故,總覺得很有吸引力。年紀稍長,老師們鼓勵搜集四川方言、順口溜、民間笑話等,記了好些個筆記本。上大學及工作后,對歷史文化有了更深刻認識,開始搜集地方志、家譜和舊書。如今,家里的藏書已達幾萬冊。
這些積累,為進入新聞界的向澤映,提供了妙筆生花的能力,這從1987年他第一個“萬里行”報道的標題就可以看出來。《從“旱鴨子”到“龍王爺”》《知否?知否?吳家土瘠地瘦》《“包老頭”寶刀未老》《“綠林好漢”鬧荒山》《魚大王“家事”》……濃厚的說書演義色彩,為上世紀80年代末的重慶新聞界帶來一股清新活潑之風。
向澤映上大學時,正是文革后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熱情、創作欲望最旺盛的時期。他說那時盡管喜歡歷史學,但也偷偷跨專業聽外系的課,平時讀書也是多而雜,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甚至理科等方面的知識都大量涉獵,他還是川大學生社團綜合社的首任秘書長。文學青年在那時是比歌星還酷的群體,他從小對梅蘭竹菊、花鳥魚蟲的觀察有好奇心,中學就嘗試寫景狀物記人敘事,大三時開始搞文學創作。有一次居然獲得8元“巨額”稿費,引起歷史系主任伍宗華注意。伍宗華鼓勵他,“研究歷史不如去記錄歷史”,因此在向澤映畢業時推薦他到新聞單位工作。
1985年7月,向澤映跨入重慶日報社的大門,歷史學界也許少了一個專家,新聞界卻將多一位優秀的記者。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要做好“行走新聞”,不光要有廣博的知識,最關鍵是要有超人的勇氣,強壯的身體,堅毅的心理素質,尤其要有不畏艱難、不怕犧牲的素質。——向澤映
“行走新聞”又被稱作旅行報道,看似行走山野田間、江河湖畔,類似今日的“驢友”,有幾分浪漫色彩,其實不然。當愛好變成工作,往往并不全是美妙的體驗。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重慶不少地方都是窮山惡水、交通不便,治安也并不理想。1992年出版的《渝州萬里行》,是向澤映第一個“萬里行”報道和相關文章的集結,他在前言中寫道:“筆者在華鎣山區采訪,曾被毒蛇咬傷;為體驗長江漁民的生活,不慎翻船墜江;為預防野獸、山匪,曾幾度身帶獵槍、匕首,在當地民兵、獵人的‘武裝護送’下穿越原始森林、花壩草原……”
至于途中生病、找不到人家搭伙吃飯住宿的事,更是不時出現。1988年5月的一天,向澤映的“渝郊萬里行”尚未過半,正在吳家區采訪,因為天氣突變,將息不周,染上了重感冒和痢疾,頭昏腦漲,上吐下瀉。情急之下,他一次服了四五粒隨身攜帶的感冒清。結果情況更糟糕,全身開始長紅疙瘩,奇癢難忍。不得不連夜趕到區醫院,一次打了3針,病情才緩解。
這樣的挑戰,并不是每個記者都愿意接受,更不是每個記者都能勝任。1986年,《重慶日報》組織“貴州紀行”系列報道,那時的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條件很艱苦。工作才約一年的向澤映主動請纓,于是獲得了第一次出省采訪的任務,走遍了貴州每一個縣,行程近萬里,而且在《重慶日報》開了專欄,連發7篇通訊,引起較大反響。
2011年8月底,正是秋老虎發威的時候,時任《重慶日報》副總編的向澤映準備帶領一個由時政中心、區域中心、視覺中心記者參與的“走轉改”小分隊,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大型主題報道——千里走烏江。但是計劃途經的地區不是高山丘陵,就是峽谷湍流,加上氣候炎熱、路途遙遠,原來召集的記者有兩個因為種種原因不能成行。多路分頭行進,最后在烏江長江交匯處會師的計劃只能放棄。向澤映和時政中心記者程必忠不得不結伴前行,他們冒著大旱酷暑,行進在崎嶇的貴州高原、武陵山區,先后途經36個區縣,采訪了上百個貧困鄉鎮,行程四千八百多公里,刊發通訊報道30多篇,共6萬余字,拍攝了數千張有價值的新聞、資料圖片。
雖然成長會突飛猛進,為什么有的記者不愿跟著向澤映做“行走新聞”?因為確實是一件又苦又累,還很危險的工作。1996年,重慶直轄前夕代管三峽庫區涪萬黔三地。作為重慶日報社編委、總編室主任的向澤映帶隊巡回萬里訪峽江,走遍22個區縣的400多個鄉鎮,先后開辟“峽江浪潮”“峽江行”專欄,發表通訊30多篇。“我走了五次‘萬里行’,最難最險的就是這次。有幾次都差點車毀人亡。”向澤映說,“車溜坡、側滑多次遇到,而且途中有好幾次遭遇房子大的石頭砸在車前幾米的地方,想想也算是命大。”
可以說,向澤映的每次“行走新聞”采訪,都是險象環生。2007年10月,向澤映在離開重慶日報社到地方和廣電部門任職10年后,再次回到報社,任黨委委員、副總編輯。當年春節前后,中國南方多地遭遇重大凝凍災害,重慶南部的武陵山區也是重災區。當地是革命老區,也是少數民族聚居地,但山高坡陡,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基于這種原因,加上大雪封山,汽車容易打滑,而且已臨近春節,都想回家團圓,很多記者都有畏難情緒,不愿意參加救災報道。向澤映了解后,提出親自帶隊,以鼓舞士氣。途中,汽車好幾次因為打滑差點摔下懸崖,而且所有人都凍傷,長了凍瘡。不過,因為到了災區第一線,看到了最真實的災情,《武陵山剿雪記》一組報道非常鮮活,讀者反饋很好,中宣部提出了表揚。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向澤映當天就帶了3名記者一臺車往災區趕,第三天就到了重災區北川,是地方媒體中第一批到達的。“我們幾個人都是給家里留了話的,因為余震頻繁,塌方不斷。”向澤映說,前兩天只敢在車里休息,還不敢睡覺,怕余震太大。雖然報社的老車子不時“發脾氣”想罷工,向澤映還是帶著后續增援的六七十個記者四進災區,采訪了四川30多個重災縣市,刊發了數十篇現場報道及圖片。
為何要自找苦吃,還屢屢為之,好像上了癮。向澤映說,“行走新聞”跨度大,面對的對象不確定,人在旅途,常常身不由己,不可能完全準備,對記者的個性、品質要求非常高。所以每次“萬里行”報道,既是完成工作,也是對自身潛力極限的開掘,對個人素質提升幫助非常大,充滿了挑戰性,也充滿了新聞的樂趣。有苦有樂,苦中有樂,苦中求樂,向澤映認為這是每次都能堅持下來的重要原因。
記者要形成自己的風格:“五千”精神訪“五區”
每個人一開始都是模仿他人,然后逐漸獨立,形成自己的個性、風格,再就是別人模仿你,但這時不能停步,要通過學習交流繼續進步。——向澤映
作為一個非新聞科班出身的“門外漢”,向澤映是如何摸進門的?初入報社,向澤映主動要求分配到農村部,而沒有選擇時政、經濟等更風光的部門。但向澤映坦承,作為正牌大學生,在當時可謂天之驕子,對新聞工作有一種潛在的浪漫意識。向澤映覺得一開始總放不下身段兒,到一些單位采訪,會有意無意看怎么安排,對采訪條件也會有看法。雖然出身農家,對農村充滿感情,但到鄉村采訪,卻無法與農民打成一片。第一次獨自下鄉到石橋鄉紅巖村采訪,到了村辦公室外,轉了二三圈都不敢推門進去。
“對基層不熟悉,連著一兩次采訪都不成功,寫的稿子干巴巴的,既單調又膚淺。”向澤映說,為改變這種情況,他有意識往一些村社跑,摸索和村民交朋友的方法。后來有一次,向澤映被派去采訪永川一位被譽為“明白婆婆”的勞模。開始,他按套路想了解勞模的先進事跡,但婆婆并不熱情。相處久了一點,“明白婆婆”反而說起了當勞模之后的煩惱——有人說她的壞話,社會上的一些攤派也找上門來,她覺得壓力很大。向澤映說,這是他第一次了解到采訪對象真實的心理活動,挖到鮮活的新聞。
這篇《“明白婆婆”為何煩惱?》的通訊,沒有走傳統主旋律報道的路子,但角度反而顯得巧妙,而且真實、有針對性,被評為報社好稿。向澤映說,他還清楚地記得部門主任唐安良的鼓勵。唐主任要求他發揮從農村來的優勢,到田坎上多走動,要觀照現實,對歷史少用力,從實踐中摸索新聞的規律,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
不過,此時向澤映還只能算入了新聞的門,并不知道未來的路如何走。到1986年參加“貴州紀行”,從第一篇通訊出來,報社上下就覺得比較活。因為黨報過去假大空、程式化的報道多,而這組報道充滿現場鮮活的東西。向澤映說:“從那時發現,旅行報道比較適合我,符合我從小喜歡寄情山水、探險考察的愛好。” 但向澤映表示,對他觸動更大的,是當時《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徒步重走長征路,正好走到貴州境內。全國都很關注羅開富的創舉,經常有人跟著他一起走。
向澤映對此念念不忘,又想起讀書時看過范長江著作,知道他曾計劃在行走“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之前,來一個“環川行”,但未能實現。從貴州回報社后,向澤映在與領導交流時,提出想完成范長江未竟的理想。領導權衡后,認為“環川行”難度太大,條件不成熟,建議先“環渝行”。因為1983年重慶成為計劃單列市,并入永川地區8個縣,達到9區12縣的龐大規模,很多人對遠郊縣和邊遠鄉村不了解。
考慮到“貴州紀行”時,明顯感覺知識儲備、采訪功夫、身體心理方面都準備不足,向澤映在“環渝行”前進行了多項準備工作。他一頭扎進圖書館,拼命翻閱各種地方志、部門志、區劃志,跑了不少書店,廣泛搜獵有關書刊、地圖、畫冊。為鍛煉野外獨行的體能和膽識,1986年底向澤映利用回老家休假的時間,沿著古蜀道進行了一次跨越龍泉山脈的“演習”,用十來天時間徒步五六百里,橫穿廣漢、中江、三臺等7個縣市。單人單包,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有時找不到人家搭伙吃飯,只能就地取材挖兩個地里的生紅薯充饑。回到家時,兩只腳都打滿水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拄根拐杖,路人都以為是乞丐。
1987年3月1日,向澤映背上裝滿生活用品、文具、書籍、藥品等東西,重達十幾公斤的大包,拿著一把折疊傘,踏上了充滿未知的“萬里長征”。第一站是長江邊的永川縣朱沱區,當地解放前盛產沙金,建國后長期中斷,改革開放了,淘金能手們又有了用武之地,但仍面臨不少麻煩且苦于無解。向澤映據實反映了情況,《朱沱欣逢淘金熱》一文甫一刊登,就引起上至市領導下至普通讀者的關注。《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讀報后,專程趕到重慶,要求前去采訪淘金盛況。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重慶日報》顧問王文彬,在審閱文章后,特地修書一封以示鼓勵,并表示要約時間面談。各地讀者來信紛至沓來,有評論專欄文章的,有提供線索的,有表示愿同記者結為知交的。《重慶日報》領導評價說,這是真正到了基層,抓到了“活魚”,有突破,有創新,所以大家都關注。
整個“渝郊萬里行”,向澤映從1987年3月1日走到1988年10月,徒步穿越重慶所有21個區縣,800多個鄉鎮到了700多個,行程1.5萬里,寫了90多篇稿件。這些報道語言通俗、生動,富有鄉土氣息,受到讀者歡迎。也正是這一年多的“苦行”修煉,讓向澤映明白了“記者天生是行者,腳底板下出新聞”的道理,并堅信找到了自己的路子。
1989年夏,四川、重慶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向澤映第一時間深入川東平行嶺谷災區采訪,發表了“7·10”特大洪災紀實大型系列報道。之后,他又到20多個重災區縣巡回采訪,行程4800多公里,在《重慶日報》開辟“災區紀行”專欄,連續發表通訊28篇。包括此后1996年的“峽江萬里行”,2008年的汶川地震災區“萬里行”,2011年的“千里走烏江”(實際行程近萬里),五個“萬里行”磨礪了向澤映,也帶出了一支優秀的新聞隊伍。
1996年和向澤映一起走峽江時的羅成友,還只是一個跑區縣的普通記者,后來成長為《重慶日報》首席記者、“三農”問題專家,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2008年,和向澤映一起最早進入災區的三位記者之一秦勇,被國務院評為抗震救災先進個人。2011年和他結伴走烏江的程必忠,也已成長為《重慶日報》的部門中層干部。2007年全國記協、全國新聞戰線“三教辦”在重慶召開現場交流會,推廣重慶日報報業集團打造“田坎記者”“巷子記者”的經驗。向澤映的“行走新聞”實踐也引起業界、學界重視,并已移植進高校的課堂,成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的生動素材。
回顧近30年新聞工作經歷和五次“萬里行”,向澤映將自己創造性改造過的“行走新聞”和報道風格總結為“‘五千’精神訪‘五區’”。“五千”精神,即踏遍千山萬水,到邊遠艱苦地區抓“活魚”;走進千村萬寨,下基層,接地氣;融入千家萬戶,強調親民敬民,以民為師;歷經千辛萬苦,在深入調查中發現真相;排除千難萬險,在摸爬滾打中磨煉意志鍛煉成長。顯然,“五區”:即邊區、山區、庫區、災區、窮區。顯然,“五區”是很多記者不夠關注、不大熟悉或者不常到達的新聞富礦,只有真正具備“五千”精神的有心人,才能摸到開掘這個富礦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