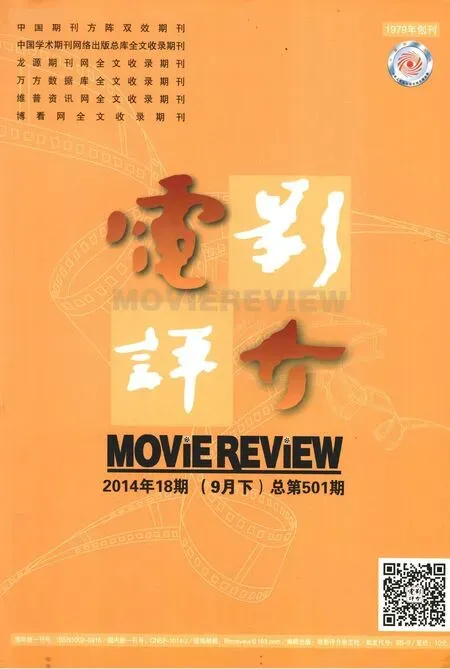符號與主體的角逐:評電影“Catch Me If You Can”
向一優
一、建立符號矩陣
2002年上映的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導演的影片“Catch Me If You Can”(中譯《逍遙法外》)影片講述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一名未滿十八歲的男孩弗蘭克偽造支票騙取巨額現金,假冒飛行員免費乘飛機遨游于多個大洲,成功假扮兒科醫生并與所在醫院護士布雷達相愛,憑借布雷達的律師父親的幫助通過律師從業資格考試成為助理律師,最終弗蘭克被FBI調查員喬·夏弗抓捕,由最年輕的頭號詐騙犯變為幫助聯邦調查局破獲支票造假案的權威人士。
本文試圖通過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分析片中人物及相關情節,繼而運用熱奈特敘事話語理論,透過敘事手段的有意而為看影片背后的權力爭奪,從而對影片進行文化解讀。[1]
因弗蘭克得以行騙的重要手段是偽造各種票據,而票據本身作為兌換憑證其實是一種符號,而行騙的主體設置為一個未成年男孩其實是在用孩童的主體性來沖擊現有符號構成的秩序,由此,我們得到秩序和主體性二元,并進而建立如下矩陣:

二、通過符號矩陣解讀片中人物
(一)弗蘭克之父
故事開頭,1963年弗蘭克的父親在高級商業俱樂部演講,講到兩個老鼠掉進一桶奶油里,一只放棄,被淹死了,而另一只拼命攪動,最終奶油被攪拌成黃油,第二只老鼠爬出來了,弗蘭克之父自稱是第二只老鼠。這其實是在肯定和宣揚只要努力拼搏就能在這個國家秩序中獲得成功。然而,僅過一年,這個國家秩序像游戲一樣輕易將弗蘭克的父親拋棄,他破產了,支票就像一副撲克牌,勞動與價值的一一對等關系被剝離開來,資本在這種符號之下游戲。由此,弗蘭克之父便成為這種游戲的犧牲品,他所踐行的自強不息的主體人格被這個符號秩序輕易戲耍、拋棄了。
(二)弗蘭克
窘迫之下,弗蘭克之父企圖從銀行騙取貸款,為此,他和弗蘭克來到銀行,在銀行門口他問弗蘭克,為什么楊基隊會贏?弗蘭克答道,因為他們有米基·曼托(該隊實力球員),其父說不對,因為他們的對手緊緊盯著楊基隊隊服上的條紋所以被楊基隊擊敗。其父雖貸款不成,但這個思想卻成為弗蘭克之后歷次成功詐騙、逃脫的重要法寶。父母離異后,弗蘭克難以忍受家庭破裂而離家出走,作為一個未成年男孩他要去替父親討回他們失去的一切,其實這只是導演向秩序重奪主體人格而設置的一個行動元,而此行動元設置為破產者的兒子,或許象征著一種希望,企圖用自由自在的孩子的天真來拯救、沖擊龐大而僵硬秩序對人的壓迫。而恰恰,弗蘭克屢次行騙成功,假能屢次混淆真,這不能不讓我們懷疑真的真實性,而這個“真”即國家秩序的所謂的真,它的真卻又一次次被構成它本身的符號所消解,弗蘭克假扮老師是利用身穿名牌中學制服,用空頭支票詐取現金是身穿飛行員的制服,第一次從FBI喬·夏弗手下逃脫是用錢包里無形的證件假扮美國情報局情報員,從邁阿密機場逃離美國是用空姐組成的美色符號陣容迷惑監控人員。
(三)喬·夏弗
作為這個符號秩序的忠實維護者,他對弗蘭克緊追不舍,然而他本身卻不是國家秩序的象征,他也只是這個秩序漏洞的修補匠,他不停地追逐案犯,自己卻也在這追逐中喪失著主體性,他每個圣誕都在辦公室度過,他破碎的家庭即是明證。然而同時他也在追逐中與弗蘭克惺惺相惜,追逐——這個運動的本身隱隱綻放著主體性光芒,他將弗蘭克從法國引渡回國,使其免于在法國被槍斃的危險,這當然有美國在世界各地保護他的人民的意識形態宣傳,但喬·夏弗同時也扮演了一個父親的角色,弗蘭克舉手投降向他退去時,既是弗蘭克的主體屈服,同時又摻雜著子向父、朋友向朋友回歸的情感皈依。從而在這個國家秩序統攝下符號對主體性剝離的現狀中,他與弗蘭克以彼此的追逐獲得一星半點的人性慰藉,這也是我認為中文譯為《貓鼠游戲》的可取之處,即肯定了不管是“貓”還是“鼠”的“智”的因素,并在此游戲的過程中消解秩序對人的主體性壓迫。
(四)布雷達之父
布雷達之父作為一個成功的律師基本可以代表這種國家意識形態,律師本身就是法律的維護者,給這樣的維護者配置一個恩愛的妻子,可愛的女兒,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這似乎是美國國家秩序的理想型態。然而這個秩序本身又存在理想性,比如,一旦破產他將淪為弗蘭克之父的境地——妻離子散;同時,他的這種美滿幸福也是建立在子女的痛苦之上的,是以父輩秩序對子輩主體的壓抑為代價的,布雷達在年紀不大的時候與和其父親一起打高爾夫球的男人懷孕然后被父母逐出家門。在此秩序下,導演努力維持一種家庭溫馨氣氛,這樣的氣氛來源于弗蘭克對布雷達的愛,他不在乎布雷達不是處女,卻對她的悲慘遭遇持同情態度,并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兩周內學習通過了律師從業資格考試成為助理律師,從而可能和布雷達結合。此處,似乎存在這種秩序與主體性調和的可能,比如在布雷達之父識破弗蘭克身份的時候,弗蘭克坦誠自己不是飛行員、不是醫生、不是法學院高材生,只是一個愛他女兒的孩子,這倒反而獲得布雷達之父的青睞,他對弗蘭克說道“沒有我們愛的女人,我們男人什么也不是”,這時他看重弗蘭克為愛而奮斗的朝氣,仿佛看到曾經的自己從一無所有開始拼搏而獲得現在的幸福。然而,這種愛又是要打折扣的,布雷達和弗蘭克并沒在影片中表現出多少情意,有的多是弗蘭克對布雷達的遭遇而生的同病相憐,以及布雷達對弗蘭克的感激之情,他們更多的是作為一對孩子在對秩序的反叛中結為了戰友,而不是從心靈上自然而然生發出愛意,雖不排除這種成分,但這種成分卻在與符號組成的秩序的抗爭中被稀釋了。
(五)謝麗爾
作為一個十七歲就登上著名雜志的模特,她一開始就被符號化了,符號意味著交換,交換因為權力介入從而將主體與價值分離,從而使主體淪為交換品,而符號成為異化力量,在她與弗蘭克的一夜情里,弗蘭克付費的手段是空頭支票,謝麗爾反倒給他找零四百美金,在此過程中,符號像刀片一樣將謝麗爾作為一個完整女人的主體性刮除了,她對身體的出讓甚至連符號都沒獲得,卻反被作為符號消費了。同時,再看影片中眾多女性無不被符號化,從而主體性淪落,空姐(因制服成為空姐)作為弗蘭克從飛機場蒙混過關的掩蓋,她們只是作為男性符號消費的客體而存在,甚至弗蘭克的母親在弗蘭克父親破產之后改嫁其實也只是淪為男人符號爭奪的錦標,那一絲殘存的夫妻之情、母子之情顯得稀薄。
由此,秩序由符號構成,而衣服上的條紋在支票和美色成為符號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催化作用,其實這就是話語權力,人因為衣服的條紋而被剝離了主體性,要么弗蘭克的父親成為國家機器運轉中秩序的犧牲品;要么謝麗爾的美色(其實這時的美色也成為了一種衣服條紋了,這與中國形容女人為衣裳暗合)作為商品被消費從而女人的主體性喪失;要么如弗蘭克和喬·夏弗對符號進行掙脫、追逐,而主體性在此追逐中也只是依稀閃現而已,人終究被符號游戲著,終究被符號構成的秩序壓抑著。
三、敘事話語層面的文化解讀
從敘事話語理論的敘事層面來看,敘事的開頭被放在一個名為“真真假假”的電視節目來展開,中間的敘事時間基本按照弗蘭克被引渡回國來進行,弗蘭克行騙的精彩片段被剪裁倒敘、插敘其中,影片結尾卻并沒回到開頭的電視節目而是以類似歷史評述的字幕結束:“弗蘭克成為世界著名的票據防偽專家。”這樣的敘述順序潛藏的其實就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由此將弗蘭克作為一個迷途知返的人物來塑造了,其反叛性、主體性被收編了,而中間的各種追逐游戲又恰好迎合觀眾興趣,體現的是一種大眾消費文化的印跡,而以電視節目展開敘事卻以歷史評述字幕結尾又隱隱透露出精英知識分子的思考。如果我們結合具體歷史語境來分析,這種思考便能更加明晰了,影片上映于2002年,而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美國,當時正是美國經濟虛假繁榮的黃金時期,那一套符號秩序正發揮著強大效應,但同時又已經顯露出秩序結構本身的弊端,由此可見影片敘事的真實性(文本的歷史性),而在21世紀導演此片顯然有對歷史作出回顧的意味,20世紀60年代又恰好是學界結構主義走向解構主義的時期,站在當今多元文化的歷史語境來看待此片,正是對符號與主體相互背離又不可欠缺的文化悖論的思考,或許主體間性和生態理論是其理論指向,當然這不在此電影表現范圍之內,只是這部電影參照歷史文化語境顯出的意義。
[1]趙炎秋.文學批評實踐教程(修訂版)[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7:104,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