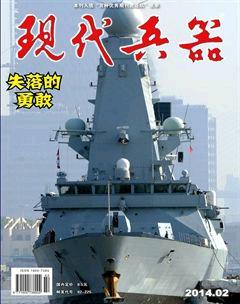大國對抗不可不知的秘密 美軍空海一體戰相關理論最新發展及評析(下)
竇超



盡管“離岸控制”戰略有很多優勢,但即使是哈梅斯也看到了其局限性。他認為:“在對任何與中國沖突有關戰略的可行性進行審查時,五角大樓必須對一系列可能的財政后果進行檢驗。尤其要注重長期沖突對全球財政形勢的影響,以及兩國維持沖突的財政能力。”他還認識到:“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意味著在制定與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行性戰略時,必須密切審查經濟問題……對‘離岸控制概念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在沒有中國金融和產品的情況下,全球經濟能以多快的速度圍繞著封鎖圈重建起來。”
在筆者看來,美國人高消費、低積累的生活方式是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這個中低端產品“世界工廠”提供的廉價消費品為支撐的。否則,以現在美國人普遍的消費方式和信用狀況是難以保持現有生活水平的。如果因為中美發生沖突,而沖突的原因卻又是與美國自身安全和經濟利益并非緊密相關的,那么美國人民是否能夠長期忍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困難,并支持這樣的沖突就大成疑問了。在可預見的未來,只要不出現戰略形勢重大逆轉或嚴重的戰略誤判,中國主動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可能性為零。即使出現上述情況,中國也極度缺乏破壞現有國際秩序體系的愿望。當然,必要的改變愿望是有的。畢竟諸如此類的沖突原因,不是珍珠港遭到偷襲或者是“9·11”事件的重演。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理論界在探討相關理論時基本避開了引發沖突的具體原因,只是籠統地假設是中國首先挑起沖突。
即使拋開這一點,單單是中國手中掌握的上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就足以遏止美國輕易對中國動武的念頭。只要中國揚言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將這些美國國債中的一小部分拋售出去,就足以讓美國經濟陷入崩潰的危險之中,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大概都不敢輕視這個問題。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如此之深,而且在諸多國際事務中保持著合作、協商的局面,這與當年的美蘇兩國是有本質區別的。筆者認為,很可能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哈梅斯才將自己提出的“離岸控制”戰略稱之為“針對不可能發生的沖突而提出的戰略”。盡管如此,美軍必然會吸收哈梅斯理論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觀點,并且有策略地運用到平時和戰時的行動中去。對于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
“海上戰”戰略
也許是同樣認識到了實施“空海一體戰”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美國海軍研究生院教授杰弗瑞·克萊恩和小韋恩·休斯共同提出了一個與“離岸控制”非常相似的新概念——“海上戰”戰略。這一戰略同樣要求剝奪中國在第一島鏈內的海洋使用權,并在遠海攔截中國商船。其著眼點同樣在于能讓美國逐步向中國施壓,不至于攻擊中國大陸,因此降低了沖突升級的可能性。“海上戰”戰略要求統籌利用美國常規空中力量、航母編隊和核潛艇,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國和盟國小型艦艇編隊,但更強調發揮美國優勢的水下部隊,即核潛艇部隊的力量,以及排水量約600噸、攜帶反艦導彈的小型艦艇編隊。這樣就可以抵消中國在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方面的“反進入”優勢。同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知道美國不會與中國全面開戰,而僅僅是在海上與中國對抗,與美國合作不會導致本土遭到中國攻擊,那么他們就會更愿意與美國合作。該戰略中可供美國決策層靈活采用的措施有:一是突然摧毀1艘中國的主要戰艦,以達到馬島戰爭中阿根廷“貝爾格拉諾將軍”號巡洋艦被擊沉那樣的震懾效果;二是跟蹤并擊毀中國出海活動的所有潛艇,但彈道導彈核潛艇除外;三是擊沉位于海上的中國水面艦艇;四是運用潛艇和無人潛航器在中國的一些或所有海軍基地及商業港口附近布雷;五是在劃定海上商業航運禁區后,擊沉闖入禁區的所有中國船只,同時保證中立國和友好國家進入東亞地區的航道暢通。
至于海上封鎖方面,該戰略的做法與“離岸控制”基本相同,只是更強調最初可能只是強行檢查,扣押如原油等這樣的貨物,之后再根據需要逐步升級到全面封鎖。“海上戰”戰略以此想要達到的目的是:“為雙方提供了冷靜下來的時間和進行談判的機會,以避免雙方沖突不斷升級,最終演化為長期的、對經濟產生致命打擊的全面戰爭,換句話說,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不過,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該戰略中提出利用前沿部署的美軍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及其兩棲艦船威脅中國控制的南海島嶼,尤其是那些“有爭議”的島嶼,甚至在必要時動用海軍陸戰隊奪控這些島嶼。“海上戰”戰略的提出者強調該戰略的基本原則是:除非中國做出“違反國際法”的宣示,否則美國海軍絕不主動采取行動。他們還宣稱,新戰略應該被公開,但這是一個維持和平的戰略,絕不是進攻性的宣示。
筆者認為,“海上戰”戰略除了存在與“離岸控制”戰略相似的缺陷外,還有一些相互矛盾或難以實施的地方。該戰略相對于“離岸控制”戰略而言,認為長期的沖突必然會對經濟產生致命打擊,進而可能升級為全面戰爭,而不像后者那樣認為可以采取措施將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控制在一定范圍以內。但是,“海上戰”戰略同樣要求對中國進行遠程封鎖,盡管是逐步升級后采取的措施,但這仍然會對經濟產生致命影響。在可供選擇的行動中,還提出對中國的部分或全部商業港口進行布雷。如果這一措施真的實施的話,那么海上貿易將基本中斷,進而對全球經濟產生致命影響。這是因為布雷不同于封鎖,后者可以適時選擇對部分船只放行,但什么船只面對水雷時恐怕都不可能自由航行了。
另一方面,該戰略提出利用海軍陸戰隊和兩棲艦船威脅甚至奪控中國在南海的島嶼。試問,既然你不想使沖突升級,那么你有什么理由奪控對手的領土?到目前為止,美國從未宣稱南海島嶼不是中國領土。那么你奪取了對手的領土,還希望沖突不要升級,恐怕就有點太一廂情愿了。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默認這種情況發生。島嶼有爭議是一回事,畢竟這些島嶼不是被別國從己方軍隊的手中奪走的,而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你要想通過作戰將島嶼從對方軍隊手中奪過來,那么沖突的升級也就無法避免了。
聯合作戰進入
前面提到的3個戰略概念有一個共同點,即在針對對手的“反進入/區域拒止”威脅時,主要運用海空力量解決問題而不投入大量地面部隊。眾所周知,美軍有四大軍種,其中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主體是由地面部隊組成的。大家也都知道,進入21世紀后美軍進行的幾次局部戰爭中,海空力量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地面部隊幾乎淪為海空力量的輔助力量,只是在戰后的維穩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情況對于歷史悠久并建立過赫赫功勞的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來說是難以接受的,而且及其不利于這兩個古老軍種爭奪日益有限的國防預算。而缺失了這兩個軍種,美軍的整體聯合作戰能力也會受到損失。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防部于2012年1月17日公布了《聯合作戰進入概念》(1.0版)文件,強調包括美國軍隊各個軍種在內的力量聯合克服“反進入/區域拒止”威脅的影響,實現作戰進入。隨后,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聯合提出了名為“實現并維持進入”的作戰概念,海軍陸戰隊又單獨提出了“單一海戰”的作戰概念,進一步強調本軍種如何實現作戰進入的問題。endprint
美軍認為作戰進入是指向戰區投送軍力,保持足夠的行動自由,完成任務的能力。作戰進入包含兩項不可分割的任務:第一項是作戰,即運用作戰力量遏制對手的“反進入/區域拒止”威脅,奪取主動;第二項是兵力和裝備、物資投送,目的是確保聯合部隊指揮官擁有所需的作戰力量。同時,作戰進入既包括將軍力投送到作戰區域,也包括保障投送的軍力在作戰區域內自由行動。與此相對應,美軍認為反進入是指那些防止敵軍進入作戰區域的行動和(通常為遠程的)能力,主要針對的是通過海上和空中進入的部隊,但目標也可以是支援他們的網空、太空部隊。區域拒止并非指阻止敵軍進入,而是指限制其在作戰區域內行動自由的(通常為近程的)能力。區域拒止能力針對所有領域的部隊,包括地面部隊。也就是說,聯合作戰進入中的作戰力量不僅包括海空力量,也包括陸軍和海軍陸戰隊這樣的地面部隊。《聯合作戰進入概念》(1.0版)所希望解決的就是這些作戰力量的作戰進入問題,這與“空海一體戰”、“離岸制衡”、“離岸控制”和“海上戰”概念中強調只使用海空力量有著根本不同。如美軍強調的所謂“強行進入”,就是指由陸軍或陸戰隊部隊為主發起的聯合登(著)陸行動,包括兩棲作戰、空降作戰和空中突擊作戰三種類型,目的是奪取敵縱深內的關鍵要點,為海空進入造勢。
《聯合作戰進入概念》(1.0版)文件中提出針對美國的“反進入/區域拒止”戰略將會包括以下關鍵共性要素:沖突前的長期塑造行動,包括信息行動,旨在增強地區影響力,建立地區“反進入/區域拒止”能力,孤立地區行為體,阻止美國創造方便美軍進入的政治條件;通過災難性襲擊或運用基于損耗、造成實質性傷亡的方式,使美國付出大大超過其所愿意承受的代價;創造盡量大的戰略戰役縱深,以便在縱深空間造成美軍人員傷亡,甚至在美軍的出發地或抵達港搞破壞,以阻止美軍部署;使用導彈、特種作戰部隊或非正規作戰部隊,甚至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擊美軍前沿基地;運用遠程能力(包括太空和網絡空間能力),攻擊美國的指揮控制和通信設施;在交通線的固定點或易受攻擊的咽喉部位,打擊美軍的后勤分發系統,或者通過網絡攻擊破壞美軍的后勤指揮控制系統;結合使用反進入和區域拒止能力,以爭取局部空中、海上優勢以及陸上機動自由。
針對這些“反進入/區域拒止”戰略的關鍵共性要素,美軍又提出了聯合作戰進入的一般性原則,或者說是面臨抵抗時實現作戰進入的方式:基于更廣泛的任務需求實施作戰進入,同時規劃后續行動,減小作戰進入的挑戰;提前做好戰區準備,使作戰進入更加容易;考慮多種基地使用方案;在多條獨立戰線同時部署與作戰,把握主動權;利用一個或多個領域優勢,摧毀敵在其他領域的反進入/區域拒止能力;破壞敵偵察監視行動,同時保護己方行動;創造局部領域的安全區或優勢通道,突破防御系統,并保持完成任務所需的優勢;實施戰略機動,直接打擊關鍵作戰目標;打擊敵反進入/區域拒止縱深防御體系,不要從外圍突破防御體系;充分利用欺騙行動、秘密行動和模糊行動,爭取出其不意,加大敵打擊的難度;打擊敵太空和網空力量,同時保護己方太空及網空資產。
通過以上顯得有些啰嗦的羅列,我們可以看出,相對于“空海一體戰”主要運用海空力量而言,“聯合作戰進入”概念更為強調跨領域一體化聯合,將包括海空力量在內的海、陸、空、天、網五個領域的作戰力量全部包括進來。其要求這些力量不是簡單地疊加其作戰能力,而是形成優勢互補、能力有機結合產生綜合效能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果。這種跨領域聯合不僅包括美軍部隊,而且包括了可供使用的非軍方力量和資產。如在該文件提出的指揮控制能力中包括“根據一個通用數據庫創建可共享、用戶定義的作戰視圖,以使人了解多個領域(包括友軍、敵軍和中立方的態勢)的態勢感知能力”,以及“整合跨域行動,包括更低層級的行動,并完全融合太空和網絡空間行動的能力”。這就要求美軍各軍種、部隊要將自身獲得的偵察數據共享,才能具備了解多個領域的態勢感知能力,跨域行動的整合不僅要在高層次進行,而且要包括更低層級的行動,并將太空和網空行動能力包括進來,也就是聯合作戰向低層次或者說戰術層次發展的趨勢,以及更廣泛地利用太空和網空作戰效能;在情報能力和火力打擊能力中,強調及時準確融合跨域全源情報的能力和利用跨領域情報實施探測、縱深打擊以遲滯、破壞或摧毀敵方系統的能力;在機動能力中,強調在網絡空間“機動”進入敵方數字網絡的能力;在保障能力方面,強調能夠快速靈活地建立非標準保障機制,如使用商業供應商及設施,以及能夠實施計劃、管理和整合承包商的保障能力,這就將商業系統也包括進美軍的保障體系,更不要說那些和美軍簽訂合同的承包商了;在國際交流能力方面,要求能夠獲得基地使用權、航行權和飛越領空權,能為區域伙伴提供軍事援助等。這樣一來,美軍在理想的情況下就可以將軍方、承包商、商業系統以及可能的盟友的力量完全聯合起來,用于對抗敵方的“反進入/區域拒止”戰略,形成“跨領域協同增效”的效果。
也就是說,美軍將利用其各軍種的聯合作戰、與盟友的聯軍作戰(指不同國家間軍隊的聯合作戰)以及整合非軍方力量以達成聯合作戰進入的目的。筆者認為,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更高層次上的聯合作戰,只不過其目的是為了解決戰爭進程的一部分——作戰進入問題罷了。不過,如果我們提高一下認識的高度,那么這種思路也就不會僅僅局限于解決聯合作戰進入問題,而是美軍在下一次戰爭中必然要運用的聯合作戰方式問題了。此外,《聯合作戰進入概念》(1.0版)文件中將威脅的關注重點由“空海一體戰”中明確指出的特定國家(中國、伊朗)轉向特定的領域和技術,并未直接指明針對哪幾個國家,因此更具有宏觀性和靈活性。
總體來看,上述情況無疑是美軍在理想的情況下,或者可以說是在極端理想的情況下才能獲得的能力,現實情況往往并不如此。《聯合作戰進入概念》(1.0版)文件中對此也有清醒地認識。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聯合作戰所面臨的困難之外,該文件還指出:“本概念要求在敵方反進入/區域拒止武器對我造成重大損失前,依賴縱深和精確打擊對其進行壓制,但這在概念所涉及的期限內可能還無法實現”,也就是說在可預想的期限內,美軍無法在遭到敵方打擊造成重大損失前對其進行壓制,這意味著美軍在該期限內將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在后勤方面可能無法達到本概念的要求”,這就涉及到前面提到的美軍現有后勤保障能力不足的問題;“在國防預算緊縮時期,本概念在經濟上可能難以支撐”,這一方面前文已經涉及不再贅述;“目前的國家政策可能不支持作戰需求”,這可能表明了目前美國政府無意與中國這樣的大國進行正面對抗。當然,這實際上是取決于中國自身實力發展的程度以及以和平方式融入現有國際政治體系的意愿。endprint
實現并維持進入
正如“反進入”和“區域拒止”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樣,由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共同提出的“實現并維持進入”概念(提出該概念的正式文件為2012年3月出版的《實現并維持進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跨軍種概念》)與原有的“空海一體戰”概念也是不同的。前者主要針對敵方的“區域拒止”威脅,主要由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聯合作戰實施,后者則主要是針對敵方的“反進入”威脅,主要由海軍和空軍聯合作戰實施。兩者都可以被視作“聯合作戰進入”概念的子概念。美軍認為,敵軍在運用“區域拒止”能力時可能采取的戰術包括:將復雜的武器系統隱藏于人口密度較大的沿海城市;放棄并癱瘓機場與港口;與美軍爭奪空中與海上優勢等。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么美軍將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為主,通過人力情報和沿海機動與陸地力量,并結合其他聯合部隊,消除美軍在空中、海上、網空和太空領域遇到的“區域拒止”威脅。這就要求海軍陸戰隊和陸軍通過進入敵方領域,定位并擊毀其“區域拒止”武器系統,為聯合行動提供作戰進入的條件。概括起來,就是登陸、打擊、搶占和投送4種能力。“登陸”強調通過多個位置分散、地形嚴峻、不同尋常的突防點和著陸區,進行兵力的同步投送并維持機動部隊開進,繞開敵防御系統和天然障礙物;“打擊”強調在陸、海、空、網等領域定位、捕獲、壓制和摧毀敵威脅上述領域的能力,形成“跨領域協同增效”,打擊敵防空與反導、反艦、制導火箭、火炮、迫擊炮和導彈等武器系統以及機動部隊;“搶占”強調占領關鍵地區,使敵難以進入,為后續部隊的進入創造條件;“投送”強調快速投送后續部隊,盡量減少部隊接收、集結、前出和整合環節,并減少對當地基礎設施的依賴。
該概念還提出了以下輔助作戰思想:運用海洋這一機動空間;整合特種作戰部隊和常規部隊;從中間整備基地開始作戰;實施機載諸兵種聯合作戰力量的垂直機動;進入偏遠地區并實施作戰;降低部隊的脆弱性;爭奪信息主動權。具體做法包括,海軍陸戰隊空地特遣部隊實施“由艦到岸”機動,在偏遠條件下實現進入,陸軍空降或空中突擊部隊實施強行進入,占領機場和港口,為后續部隊進入創造條件。整體來看,“實現并維持進入”概念實際上是在“空海一體戰”壓制住敵方“反進入”威脅后,以登陸或空降方式在敵方海岸奪占一個地區,作為后續部隊進入的依托。
在筆者看來,這個作戰概念似乎與美軍提出“空海一體戰”概念的初衷背道而馳,至少在面對中國時更是如此。正是因為投入大量地面部隊占領敵方領土,最后有可能造成曠日持久和遭受大量人員傷亡的局面,美軍才拋出以運用海空力量為主的“空海一體戰”概念。而“實現并維持進入”概念卻需要投入相當數量的地面部隊才能夠達到目的,這明顯有違于今天美軍高層的作戰思路。2011年2月25日,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西點軍校講話時提到:第一,無論在亞洲、波斯灣還是其他地方,在最可能發生的高端沖突中,美軍將主要動用海空軍參戰;第二,今后任何一名國防部長,如果建議總統再次向亞洲、中東或非洲派遣規模龐大的的美軍地面部隊,他就應該像麥克阿瑟將軍曾經精辟地指出的那樣——“檢查一下自己的腦子是否正常”。
盡管延續了《聯合作戰進入概念》(1.0版)中將威脅的關注重點轉向特定的領域和技術的特點,“實現并維持進入”概念也并未指出是針對什么特定的國家,但中國很可能仍然是該概念的“目標”。如果按照該概念的思路,美軍在克服中國“反進入”威脅后,就需要將相當數量的地面部隊投入到中國沿海地區并奪占一個地區。而面對擅長陸戰并擁有85萬陸軍機動作戰部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這一數量并不包括大量的邊海防和守備部隊等作戰部隊),這種行動到底能有多大勝算呢?一旦美軍地面部隊與中國陸軍的整體力量(包括現役部隊和預備役部隊,當然還可能有大量的武警部隊和民兵,而且這支陸軍部隊已經開始擁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裝備)纏斗在一起,大量的人員傷亡和物資裝備損失就根本無法避免。這樣的前景怕是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都不敢面對的。因此,筆者認為,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聯合提出的這一概念,在具體操作時并不具有很強的現實可行性,陸軍和陸戰隊的初衷有可能是弄一個抬高自己軍種地位和爭取預算的“幌子”,至少有這樣的用意在里面。當然,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地廣人稀、陸上作戰能力有限的對手,這一概念還是有一定的用武之地。
單一海戰
就在“實現并維持進入”概念提出僅5個月后,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埃利斯小組”就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報告——《美國兩棲部隊:美國海上力量不可或缺的要素》。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海軍陸戰隊針對“反進入/區域拒止”威脅開發的“單一海戰”概念。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表明其未來關注的重點將是亞太地區,而這一地區的很大一部分爭端屬于海洋爭端,這就給了海上力量一個發展的新機會。而目前因為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的拖累,美國海軍陸戰隊和陸軍幾乎已經從一支為應對高強度正規戰爭的正規力量,變成了一支以反恐和維穩任務為主的軍隊(如果說的不太中聽一點,差不多要變成一支“保安部隊”了)。海軍陸戰隊認為,他們正好利用“重返亞太”的機會,讓自身重新回歸到進行兩棲作戰的傳統上來。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通過的《國防預算的優先項目和選擇》明確提出,“給予空中和海上力量更多的重視”。因此,海軍陸戰隊并不滿足于和陸軍一起搞“實現并維持進入”概念,因為搞不好會把自己也和陸軍一樣成了“純種”地面部隊,而與“海上力量”沾不上邊了。而且,美國海軍陸戰隊雖然是獨立軍種,但卻在行政管理上與海軍一樣隸屬于海軍部,說起與海軍聯合作戰來更具有天然的優勢。沿著這個思路,“單一海戰”概念把陸戰隊和海軍的聯合作戰作為核心內容也就不足奇了。
“單一海戰”概念所要打造的作戰力量實際上就是陸戰隊和海軍的一體化力量,這將能夠勝任海軍的所有任務。一般來說,美國海軍的任務是控制海洋(有時還需要從海上發起對陸攻擊),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任務是從海上向沿海地區投送作戰力量,即進行兩棲作戰,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登陸作戰。因此,“單一海戰”概念中提出的海軍陸戰隊與海軍的聯合,可以理解為海上控制力量和海上投送力量的結合。而該概念提出的目標則是將兩種力量進行內聚式結合,以實施更為緊密的聯合作戰,并為聯合部隊指揮官提供一種在多領域遂行軍事行動的能力。endprint
從歷史傳統上來說,美國海軍陸戰隊與海軍結合的方式主要是“兩棲戒備大隊”,即海軍的兩棲艦艇負責運輸海軍陸戰隊的“空地特遣部隊”。其中,登陸艦和運輸艦運送陸戰隊的地面兵力,兩棲攻擊艦則運送AV-8B短距/垂直起降戰斗機和各類直升機、MV-22偏轉翼機等。任務分工是海軍負責運輸和部分對岸火力支援任務,陸戰隊則負責登陸作戰。但美軍認為,這種結合方式存在著不少缺陷,導致雙方都有作戰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后來,美軍開始在“兩棲戒備大隊”基礎上編入驅逐艦、護衛艦和掃雷艦等艦只,有時甚至將整個航母大隊也編進來,成為“遠征打擊大隊”。這種編組形式在具有強大投送能力的基礎上,還具有超強的打擊和防護能力。如果“遠征打擊大隊”在狹窄海域活動時,有可能受到岸上的反艦導彈和集群小艇的威脅(這實際上就是在暗指伊朗),這時陸戰隊就可以登艦阻止小艇的攻擊,甚至可以強行登岸將反艦導彈摧毀。在2012年初舉行的“勇敢美洲鱷”兩棲作戰演習中,“遠征打擊大隊”不僅出現在演習中,而且陸戰隊的一個小分隊還從兩棲艦艇出發,空中機動160海里攻擊了一個目標,展現了“單一海戰”概念中陸戰隊與海軍進一步緊密結合的優勢。
“單一海戰”概念中提出的陸戰隊與海軍進一步結合的愿景,同樣得益于此的美國海軍應該也是非常歡迎的。然而,要想進一步結合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是“單一海戰”概念回避了在進行進一步結合時,海軍和陸戰隊誰處于主導地位的問題,這說明兩個軍種對于這一問題存在著認識分歧。從一般的歷史經驗來看,在航渡階段海軍處于主導地位,包括海軍陸戰隊在內的登陸部隊要服從海軍的指揮,而當登陸部隊上陸并建立起火力支援體系和指揮控制體系之后,登陸部隊指揮官就會接過指揮權。“單一海戰”概念從海軍陸戰隊的行動出發,意圖從行動籌劃階段就要全程參與進來,實際上有爭奪主導權的意思,高傲的美國海軍無疑是不可能輕易接受這一觀點的。再就是“單一海戰”概念與“空海一體戰”可能會出現爭奪預算的情況。雖說美國海軍部同時管著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兩個軍種,但海軍部爭取回來的預算是不可能平均分配的,必然有所側重。在這種情況下,海軍陸戰隊要想多分一杯羹肯定要受到海軍的反對。雖然“單一海戰”概念強調不會和“空海一體戰”產生爭奪海軍資源的矛盾,海軍可以用其余的力量來進行“空海一體戰”。但問題是,在整個美國政府和美國軍隊都“沒有余糧”的情況下,美國海軍一方面要進行“空海一體戰”,另一方面還要滿足“單一海戰”的需求,資源是否夠用就成了大問題。
正如筆者在《揮向中國的大棒》一文中提到的那樣:我方斗爭準備的基點仍然是“練好內功”,即集中精力發展自身的實力,這才是在將來的斗爭中取得主動的根本,脫離了這一點,其他只能是“空中樓閣”。從這一角度出發,不管美軍提出什么針對我們的概念或理論,其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并不在美國人手中,而是在我們自己手中。古今中外數千年來大國崛起與衰落的事實已經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是無論修建再高再堅固長城或者維持百萬乃至千萬大軍,都不是牢不可破的,真正能夠維護國家和民族安定發展的唯有尊重自由與人權的民主制度、公平正義的法制保障以及團結一心的民眾認同感!
(編輯/一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