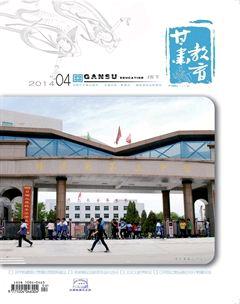政策的價值
陳富祥
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為人們熟知,而有關扁鵲的另一個故事也很有意思。《鹖冠子·世賢十六》篇中,引述了一段扁鵲與魏文王的對話。大意是這樣的,魏文王問扁鵲:“你們兄弟三人哪位醫術最好?”扁鵲說:“長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镵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閑而名出聞于諸侯。”
這段寓言式的對話,深刻地道出了人的奇怪而又真實的心理,就像蔡桓公一樣,對小病——不管是身體疾病還是社會問題總是諱疾忌醫,等到病入骨髓時,才四處亂求醫,而像扁鵲長兄那樣的人從來不受人重視。
以“小升初”亂象為例,其問題由來已久。前不久教育部出臺“小升初”新政,規范“以權擇校”、“以錢擇校”等教育腐敗和教育不公平亂象,限制愈演愈烈的擇校問題。
但這種補救式的政策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擇校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資源不均衡,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擇校等亂象就無法解決,“新政”或許能暫時剎住一些歪風邪氣,但時間一長它還會變個花樣、換個名頭出現。
另外,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驚呼“新政”送給房產商一個新年大禮包,學區房得到了政策的意外收獲。有人認為,這是升級版的變相“以錢擇校”。理性地看,“新政”面臨著更加復雜、更加難以預料的阻力,最終可能像之前出臺的“小學就近入學”、“劃分片區”等政策一樣成為一紙空文。
更為重要的是,以中國之大,教育問題之復雜,具體的應急性政策并不能真正解決紛繁復雜的問題。而且,此次“小升初”新政在很大程度來說只是針對城市學校來言的。教育部有關負責人也指出,由于大城市優質教育資源分布尚不均衡,引發了擇校熱等較為嚴重的問題。顯然,農村地區由于教育資源不均衡所引發的擇校問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那是否說明農村地區的擇校問題不嚴重呢?
實際上,農村地區擇校問題不亞于城市,只不過表現形式以及擇校方式不同于城市學校而已。當前,城鎮學校學生數激增,而大量農村學校學生數不斷減少,不少偏遠山區學校成為空殼學校,便是最好的例證。當然這里有人口結構改變以及進城務工人員等因素。但是,進入城鎮學校的學生并非全是務工人員隨遷子女,他們進城讀書只為享受到城鎮學校較為優質的教育資源而已。近年來城鎮出現的大量“陪讀族”就足以說明問題。
農村學生進城讀書難道不是擇校行為嗎?其家庭為此付出的額外代價不值得關注嗎?比如,陪讀人員每月的吃住行等費用對農村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顯然,這從另一層面引發了新的教育不公,作為政策最應保護的弱勢群體——無法進城讀書的學生,又一次在優質資源的爭奪中輸在了卡位戰中。
政策的核心價值是公平與公正,保護弱勢群體應該是最基本的價值標準。
因此,教育政策要像扁鵲的兄長那樣前瞻性地研判“病情”,而不是出現了具體的“病癥”后,趕緊制定一項政策予以限制和規范。有道是一只手捂不住十只跳蚤,捂住了這個,跳了那個。“救火式政策”只能讓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疲于奔命,無所適從。也就是說,如果將政策定位為權宜之計,定位于手段和策略性行為,必將帶來政策價值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何種教育政策,還要重視實施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單靠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的力量是無法實現政策所預期的效果,要利用政策的力量引導和調動學校的積極性,給予學校辦學的自主權,激活學校自身發展的活力,讓實施主體具有抵制各種違規和腐敗問題的“免疫力”。
在即將到來的深化教育改革中,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教育均衡發展是縮小各種差距、促進社會公平、解決民生問題的需要和基礎。各級教育部門的決策者要登高望遠,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的富有理想的教育政策,“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 發揮政策的規范功能,體現政策的引導功能和調節功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推動教育公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