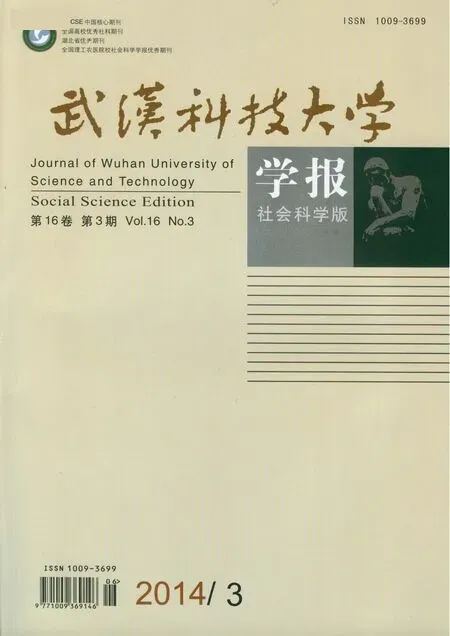論馬克思資本視域下的時間觀
沈 廣 明
(中共韶關市委黨校 黨建教研室,廣東 韶關 512026)
一、時間:勞動的延展歷程
在西方哲學史上,“時間”概念存在著自然時間、心靈時間等多重解讀。亞里士多德的時間觀是自然時間觀,認為時間是通過運動體現的,是運動的數和量,對后世的牛頓物理學及機械唯物主義影響深遠。奧古斯丁把時間理解為心靈的伸展,開啟了心靈時間的詮釋向度,并在貝克萊、康德哲學中得到深化。自然時間和心靈時間在物理學、心理學等學科領域中都有其解釋力,但在詮釋人類歷史問題上卻捉襟見肘。黑格爾的確關注到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時間性”,但他把歷史時間解釋為虛幻的絕對精神和主觀的自我意識之間的輪回歷程,實質上仍舊屬于心靈時間,他的貢獻在于激發了強烈的歷史感。馬克思正是在歷史感的感召下,進入唯物主義歷史哲學中思考歷史的“時間性”,與以往形而上學家們從本體論或認識論視角出發去討論時間概念不同,馬克思從社會歷史觀的層面來詮釋時間、揭示時間內涵。
馬克思的“時間”是創造人類歷史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把“勞動”理解為“人”改造“物”的對象性活動,正是在“勞動”中,抽象的“人”、“物”才在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中成為現實的“人”和“物”,亦即以“物”化了的“人”和“人”化了的“物”客觀存在著。抽象的“物”實質上是物理學研究中由自然時間所測度的“物質”,抽象的“人”同樣就是心理學或者精神現象學中由心靈時間所描述的“意識”,它們都脫離了人的物質生產生活。所以,現實的時間,就是在勞動中生成的延展人類歷史進程的勞動時間。馬克思這樣闡釋了生產勞動和歷史的勾連:“歷史不是作為‘產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告終的,而是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1]92時間就是人的物質生產生活的歷程,可見,馬克思的“時間”是創造著人類歷史的勞動時間。
針對馬克思的時間概念,古爾德(C·Gould)說:“勞動是時間的起源——既是人類時間意識的起源,又是對時間進行客觀測量的起源。”[2]勞動對時間的測量值就是勞動改造自然對象的持續過程,也就是勞動時間。在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中,勞動時間是以自然界的運動軌跡來計量的,如四季更替、莊稼的生長周期,等等,由于自然物的運動過程不受人的活動的干預,所以,勞動時間往往由自然時間來界定,具有穩定性和固定性。隨著傳統習俗社會為工商業活動所瓦解,人們在貨幣的運轉下逐漸將關注點和興趣點從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轉向它們在交換中所生成的“價值”,并在貨幣脫域性的驅動下人為地去縮短或延長勞動時間,從“時間差”中尋求價值的增殖,從而發現了“時間”能夠翻轉為“財富”的秘密。進而,人在貨幣拜物教的支配下,不再把自然界的運動軌跡作為時間的參照系,而開始用財富的數量值來測度勞動時間,把勞動時間納入到心理欲望的參照系中,勞動時間則體現為心靈時間。隨著貨幣通過對“人”的通約,逐漸轉化為組織“人”去改造“物”的資本,自然界運動秩序、人的心靈世界的波動等都在資本增殖性的統治下由理性化的科技、管理、金融等所重新編程和塑造。隨之,資本清除掉自然時間與心靈時間的現實有效性,將之替換為資本的增殖時間,獲得了對勞動時間的測量權、分割權和支配權。毋庸置疑,在資本統治的時代,推動歷史進程的勞動時間被資本截流了,資本通過對“時間”流逝秩序的不同組合,制造一幕一幕的歷史事件和故事,滿足和實現它的增殖目的性,進而,勞動時間被資本建構為“必要勞動—剩余勞動—自由勞動”的時間圖型。
二、時間的碎片化與資本的切割性
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社會關系中,工人的時間結構是由必要勞動時間、剩余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三者的比例關系建立的。與勞動時間不同,自由時間是工人在生產勞動時間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主要表現為休息、打理日常生活的時間以及從事社交活動、藝術創作、運動和游玩等時間。在自由時間范圍之內,工人以自身的充分發展和完善為目的。剩余勞動時間實質上也是工人的自由時間,但被資本強制性地轉化為剩余勞動時間,成為資本家的自由時間,招致了時間的異化。
必要勞動時間是工人生產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間。“我們已經知道,工人在勞動過程的一段時間內,只是生產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只是生產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但是“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3]242-243,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就是必要勞動時間,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就是必要勞動。概而言之,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工人為了能夠生存和勞動而生產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間。
在資本的增殖系統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不斷地被縮短。在小農經濟的社會中,農奴的勞動時間在自然界的安排下,與均勻流逝的自然時間和諧地吻合,所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在資本的安置下,生產力本身的伸展性卻能夠消解必要勞動時間原有的固定界點,使必要勞動時間具有趨于被“縮短”的取向。首先,科學技術對自然時間的解構與重構,使工人的生產勞動更符合人的生理結構、更順手、更便捷和更高效,從而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自然世界的事物都有自身的運動節奏和周期,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了均勻流逝的自然時間,如地球的公轉和自轉,生物體的“生物鐘”的調整和協調,等等。科學能夠對自然世界的運動時間做出公式化把握和實驗性測量,技術則能夠人為對自然事物的運動周期、節律進行壓縮式和延伸式的干預、重置甚至摧毀。在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關系中,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不是中性的,而是受資本增殖性所支配和服務的工具。馬克思說:“資本作為無止境地追求發財致富的欲望,力圖無止境地提高勞動生產力并且使之成為現實。但是另一方面,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提高……都是資本的生產力的提高,而且,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種提高只有就它是資本的生產力來說,才是勞動的生產力。”[4]305在他看來,資本的增殖性逼促、驅動勞動生產力的進步,強化對自然物質材料的改造,從而派生出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通過科學技術對自然物的改變來達到解構和重構自然時間的目的。資本用它所截獲的重構的時間來消滅空間,突出“速度”效應,并將“速度”投置到工廠的生產勞動流程中。其次,系統化管理通過對心靈時間的擠壓與釋放,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人的心理世界在外部事物的刺激作用下,生成感知、記憶、想象、推理等逐層深入的意識流,具有持續的時間綿延性。系統化的管理能夠在工人的勞動時間內壓縮或延伸工人的意識流,強迫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釋放心靈的能量,使工人在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繃緊神經投入到生產勞動中,用繁重的工作量來填塞漫長的工作日,提高勞動生產率。可見,科學技術和科學化管理通過對自然時間和心靈時間的改造,延長了工人的勞動時間。在便捷、高效的流水式生產線運轉下,工人在很短時間內就可生產出必需的生活資料,從而極大地“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
必要勞動時間的存在意義在于創造剩余勞動時間。“勞動過程的第二段時間,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并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我把工作日的這部分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把這段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剩余勞動。”[3]243概括而言,剩余勞動時間就是被資本無償攫取、由資本家自由支配的時間。剩余勞動時間是被資本的代表者——資本家所壟斷了的自由時間,它是資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義,“資本的規律是創造剩余勞動,即可以自由支配時間”[4]377。正是基于此,資本才將“人”商品化、異化。資本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勞動時間,就必然要盡最大可能地去“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并且產生了將必要勞動時間“縮短”為“零”的“狂想”。以此為目的,資本踐行了兩種路徑:一是最大限度強化勞動力生產強度,“通過強制地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其自然界限的辦法;通過把婦女和兒童納入勞動人口的辦法”[4]377;二是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發明類似于“永動機”的先進機器,建立“無人化工廠”,用自然力徹底代替勞動力。資本家試圖通過這兩條路徑獲得剩余勞動時間,將那些不是出于自愿的勞動轉嫁給工人,從而將別人的時間納入到自己的自由支配時間中。這在客觀上產生了可能消解必要勞動時間的效應,為消除異化勞動時間和回歸自由勞動時間創造了可能性。
三、時間的自由回歸與超越資本
馬克思的基本旨趣就在于剔除資本對時間的測度權和分割權,消除異化狀態,以自愿性的勞動分工替代自然形成的勞動分工,使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完全同一起來,構造真正屬于“人”的“自由勞動時間”,讓時間回歸自由。
剩余勞動時間通過消解必要勞動時間,轉換為自由勞動時間,資本無限度地實現價值增殖的活動也產生了否定資本、超越資本的力量。首先,在資本增殖系統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所預示的“異化”現象,“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5]。而異化勞動一方面導致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另一方面驅動工人階級訴諸暴力革命的手段將私人資本轉換為全社會的資本、將資本家私人占有的剩余價值轉換為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取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293,建立公有制制度,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社會。公有制的根本使命就在于將為資本家所單方強占的剩余勞動價值進行全社會重新分配,將被動的雇傭勞動轉為主動的自由勞動,從而彌合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的界限,形成自由勞動時間。其次,在資本增殖性的驅動下,科學的進步逐漸把體力勞動的工人置換為腦力勞動的工人,衍生出高度發達的生產力,而“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志,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6]。根據上述兩方面,在資本驅動下,當剩余勞動時間在最大限度地擠壓必要勞動時間而導致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公有制的經濟制度相結合時,那么剩余勞動時間就消解了必要勞動時間,消除了勞動時間的異化特質。
異化勞動時間嬗變為自由勞動時間,標示著人類歷史進程從必然王國跨入到自由王國。馬克思的“必然王國”既表現為人的棲居于世受物質生產生活的自然必然性所限制,也表現為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所限制。一方面,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1]79只要人類歷史存在,物質生產活動就是人無法擺脫的必然的客觀條件。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人的勞動受自然必然性所支配,人的勞動時間也由自然時間所界定。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發達生產力解除了自然對人的桎梏,以致能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7]927,自然時間對人失去了必然有效性。另一方面,必然王國還體現為以資本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統治,“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7]920,正是在這樣的生產關系中,資本的增殖時間取得了對勞動時間的占有權,從而一部分人竊取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時間,形成了異化勞動時間。但工人階級以革命的、改良的手段顛覆了資本的統治地位,消除了奴役性的生產關系,實現了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在同一勞動者身上的完全統一。據此,人們對自然的、生產關系的必然性的超越,從異化勞動時間嬗變為自由勞動時間,人類歷史進程也從必然王國跨入自由王國。
在自由王國中,自由勞動時間是以人的“自由個性”[4]108為基本特征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是這樣描述“自由個性”的勞動時間的:“隨著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1]85這一著名的隱喻蘊含著以下兩方面的內容:其一,資本的增殖時間失去了對勞動時間的裁定權與度量權,勞動時間不再是被劫持的、被任意剪短與扯長的資本品,而是還原到人的生命流逝歷程中,回歸到人的存在本身。在此階段,勞動時間在表面上仍然是由自然世界的自然時間與人的心靈時間所界定:人在勞動中所生成的一連串、一系列的事件終究逃不出日出、日落的自然時間規則的安排,同時它們也受它們在人的心靈世界所造成的認知、情感體驗的綿延時間的規制,所謂快樂的時光總感覺很短,痛苦感則相對漫長。但在深層次上,人在勞動中所發現和創造的科學技術、人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已經能夠按照人的目的性去干預自然時間和心靈時間,設定和裝置滿足人的“自由個性”的時間程序,從而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任何束縛,實現了人的自由。其二,人超越了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的界限。人的勞動擺脫了任何外在強制性的束縛,完全由勞動者自己自由支配、自由安排,打破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自然界限,人們在體力勞動、腦力勞動、藝術、文化、政治生活及社會交往等各方面都可盡情地施展自己的稟賦和才華,人自身的生命能量的絕對和充分發揮成為人自身的目的。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稱“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空間”[8]。因為資本已經被顛覆與超越,不再存在著侵占工人精神生活和肉體生活的剩余勞動時間。由此可見,在個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形態中,人的“自由個性”體現為勞動時間的自由支配、自由設定和自由享用。
綜上所述,勞動時間是人的物質生產活動所伸展開的時間。在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關系中,資本獲得了對勞動時間的截流權,通過對必要勞動時間與剩余勞動時間的劃界,攫取剩余價值,實現價值的無限度增殖。然而剩余勞動時間必定是異化的勞動時間,是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另一部分人自由時間的產物。所以馬克思設定超越了資本、消解了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界限的自由勞動時間概念,鑿通了通往自由王國的時間隧道。
[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Gould C. Marx’s social ontology: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i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ality[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78:41.
[3]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1.
[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3.
[7]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