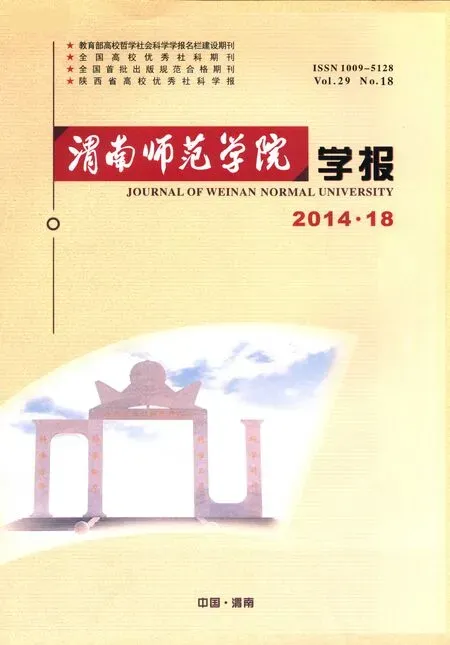對傳統審美形式的創造性化用
——賈平凹小說藝術技巧論
程 華
(商洛學院語言文化傳播學院,陜西商洛 726000)
對傳統審美形式的創造性化用
——賈平凹小說藝術技巧論
程 華
(商洛學院語言文化傳播學院,陜西商洛 726000)
賈平凹具有自覺的藝術意識,除了在藝術審美觀念上有自己獨特的認知外,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具有為實現此種審美認知所使用的獨特的藝術表達方式和藝術技巧。賈平凹小說的藝術技巧觀集中體現在他對傳統藝術形式的創造性化用中。賈平凹對傳統文學理論中虛與實的理解,小說與說話關系的理解,以及從民間和古語中尋找好的語言等進行創造性改造和發展,就是從文學表現的技巧上對中國傳統審美元素的創新和突破,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表達現代人的思想和情緒。
賈平凹;意象;結構;語言
文學是具有一定規則和方法的技藝,寫作過程不是自然表現的過程,而是精心構思的過程,文學形式和技巧的成熟,意味著文學創作風格自成一派。賈平凹在小說創作中能夠獨步文壇,與他在創作實踐中對形式的探索是分不開的。賈平凹注重借助中國傳統的審美表現形式,表現現代中國人的思想和情緒。賈平凹在接受記者的訪談時指出,“西方文學的境界可借鑒,因為追求境界是大多數作家共通的,但是形式不能借鑒,像水墨畫和油畫,京劇和話劇,體現了東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如果形式是借鑒來的就雷同于翻譯式的語言,喪失了民族性,雖說穿過云層都是陽光,但云層各有不同。”[1]231在賈平凹的意識里,要改變和發展傳統的文學表現形式,創造出具有中國作派的小說形式。賈平凹對傳統文學中虛與實的理解,小說與說話的關系,以及從民間和古語中尋找好的語言等進行創造性的改造和發展,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表達現代人的思想和情緒。
一、對傳統意象的創造性使用
1.將意象從傳統的感發功能升華到具有普遍的象征功能
“時下的文學作品中,時髦著潛意識的描繪,方法多是意識流,以一種虛的東西寫實的東西,《太白山記》反其道而行,它是以實寫虛,將人的意識用實體寫出,它的好處不但變化詭秘,更產生一種人之復雜的真實。”[2]272在這里,賈平凹提出“以實寫虛”的新觀念。所謂“以實寫虛”就是以象寫意,而以往的“以虛寫實”則是以意寫意;以意寫意通過心理或意識的真實揭示生活的真實;而賈平凹企圖借助生活中的客觀物象解釋他對生活的理解。這個象就是我們在意象論中論述的“象”。言不能盡意,而“圣人立象”卻可以盡意。立象的目的是為了見意。從藝術思維的角度而言,承接的是中國傳統的意象思維。傳統的意象論從觀物取象到立象見意,強調的是作者的感悟能力。中國是詩詞大國,王國維評價好的詩詞是有境界的,有境界就是要情景交融,情為意,是虛的,景為象,是實的。好的詩歌就是要虛實相融,要借象生意,強調作者的興發感動能力。賈平凹鐘情于意象論,不僅強調作者的感悟能力,而且要使意象具有象征和隱喻的功能。黑格爾認為,“象征所要使人意識到的不應是它本身那樣一個具體的個別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義。”[3]11賈平凹長篇小說中的題名,作為意象,就具有豐富深刻的象征意義。“浮躁”是20世紀80年代集體無意識的表現,“廢都”是20世紀90年代文化沒落者的精神映像,“秦腔”是傳統農耕文化衰落的象征[4],“高興”則是對當今時代人們普遍追求個體生存價值的一種精神想象。如果說,傳統意象重在興發感動,那么,賈平凹熟練使用意象,使得意象具有普遍的象征功能。
2.擴大意象在小說創作中的表現功能
賈平凹對傳統的意象論有創造性的超越,這種超越還體現在如何將意象思維運用到小說創作中。詩歌中的意象主要是物象,在賈平凹早期作品中,細節意象只具有點化作用,而無情節貫通作用。小說講究的是結構上的整體貫通。賈平凹想要尋找一種與小說文體一致的意象,《土門》的寫作在“虛實相間”中,明顯看出作者在意象營構中的刻意追求,實的部分沒能寫得更精彩,而“虛”的部分又顯現不足。《懷念狼》在“以實寫虛”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作者在寫作之前已有了明確的寫作宗旨:“局部的意象已不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將情節處理成意象。如果說,以前小說企圖在一棵樹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來造型,那么,現在我一定是一棵樹就是一棵樹,它的水分通過脈絡傳遞到每一枝干每一葉片,讓樹整體的本身賦形。面對著要寫的人與事,以物觀物,使萬物的本質得到具現”[2]272。因此,我們能看到,作者圓滿的用“具體的物事”,即在尋找狼——捕殺狼——懷念狼的過程中,將意象直接變成情節,這是依小說文體而對意象的創造性化用。
3.對意象的超越,還表現在對虛與實的處理上
賈平凹一再強調,他所創造的意象世界、虛構世界是要通過原生態的生活流來表達的。賈平凹的關鍵點是要達到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結合。在對兩者的結合上,賈平凹是有哲學依據的:“物象作為客觀事物而存在著,存在的本質意義是以它們的有用性顯現的,而它們的有用性正是由它們空無的空間來決定的,存在成為無的形象,無成為存在的根據。但是,當寫作以整體作為意象而處理時,則需要用具體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動的規律,順利或困難都要過下去,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鮮活。如此越寫得實,越生活化,越是虛,越具有意象。以實寫虛,體無證有,這正是我的興趣。”[2]272在這里,賈平凹理論上完成了他的整體意象論,那就是通過生活流的實存之象來傳達他對生活的形上之思。現在新寫實強調生活的原生態,整體上消解了作品本應有的價值和意義,只是力求通過生活流達到對生活的平面化的再現。而在賈平凹這里,他要通過原生態生活的流動,凸現作家的某種精神指向。就如同賈平凹所言:“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盡量原生態地寫出生活的流動,越實越好,但整體上卻極力去張揚我的意象。”[5]494現實的形而下的生活世界是他的象的層面,生活之上的形上之思則是他極力表現的意。這樣,意象不僅是表現手法,也是結構手法。不論在《廢都》《秦腔》,還是《古爐》《帶燈》中,我們在這種密實的流年似的生活流敘述中,找不到絕對的意念,獨立的意義,而是在似生活的、混沌的,多元的話語結構的背后,看到了小說多層次的、流動的意識形態,那是超越于形下生活的形上之思。謝友順認為,當代作家在寫作過程中始終在兩種極端之間搖擺,要么極端的寫精神抽象,要么極端的寫生活現實,匱乏的是將寫物質和寫抽象相平衡相綜合的能力。而賈平凹在寫實中,恰恰兼顧了物質與抽象的平衡,這就是賈平凹“以實寫虛”的魅力,而這正是賈平凹對傳統意象論的現代性突破。
二、“說話體”的小說結構
賈平凹將“小說”與“說話”聯系起來,明確表明自己對中國古典小說傳統的超越與反撥。賈平凹在《白夜》后記中闡明了他的說話理念,傳統說書人的說話方式重在“嘩眾取寵、插科打渾、渲染氣氛、制造懸念、善于煽情”[6]317,全視角的講述又類似領導干部式的“慢條斯理、拿腔捏調”[6]317。這兩種說話方式都存在敘述者橫亙在故事與故事接受者之間,都強調敘事者的態度對敘事文本的硬性切入。改變說話的方式,就是創造新的文體結構,如何拉近敘述者、接受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做到敘述的自然、隨意,是賈平凹孜孜以求的。
在不斷進行小說結構的嘗試中,賈平凹認為,如何達到在敘述生活故事的時候,如同生活本身在展示,這就要求在寫作中寓“技巧”于“故事”和“生活”之中。“給家人和親朋好友說話,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只是真。而在這平平常常只是真的說話的晚上,我們可以說得很久,開始的時候或許在說米面,天亮之前說話該結束了,或許已說到了二爺的那個氈帽。過后一想,怎么從米面就說到了二爺的氈帽?這其中是怎樣過渡和轉換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過來的呀!禪是不能說出的,說出的都已不是禪了。小說讓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6]318賈平凹在這里闡明的是“說話”體的文體觀念,其實是從“怎樣說”和“說什么”兩方面完成他的敘事結構。“怎樣說”,賈平凹強調聊天式結構,力戒敘述者觀念的硬性切入,追求敘述技巧的非表演性,達到讓人“看不出在做”的痕跡。“說什么”是指小說的敘述內容,賈平凹小說中的事不是傳統的有完整情節的故事。他強調的是那些生活中的“細微之事”,他認為:“如果看到了獲得了生活中那些能表現某人某物某景的形象而細微的東西,這也就是抓住了細節,文學靠的是細節,而素材的積累,說到底是細節的積累。”[5]447
賈平凹對小說世界的營造是出于一種重建小說世界的完整性的考慮。賈平凹在“說”的方式上要求與生活盡可能的靠近,使小說像生活本身一樣讓讀者看不到做的痕跡,在“說”的內容上又要求小說盡可能細微地袒露生活的真相,十分看重生活的日常性、瑣碎性、原生態。如果我們回到我們民族小說傳統的審美藝術領域,我們又會發現這種審美追求恰恰是我們民族的東西。自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的文學理論顛覆了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和漢語體系,小說家學西方的文論觀念,注重以刻畫典型人物,強化敘事結構的完整性為特點的焦點敘事,忽視的恰恰是對日常生活的細膩描摹。賈平凹的寫作,放大了日常生活的內容,這種更接近生活本質的敘述其實聯結的是中國文學以《金瓶梅》和《紅樓夢》為代表的生活敘事傳統。但同時又是在古典小說敘事基礎上文體探索的成果。
三、現代背景下語言功能的轉變
1.好的語言是冶煉出來的
賈平凹自開始創作小說,就非常注重語言的運用,而且有非常自覺的語言觀。在早期他就強調“語言是作品的眉眼”[5]442,賈平凹認為:“金在沙中,浪淘盡,方顯金的本色;點石如果能成金,那也僅僅只是鉆進了河蚌體內,久年摩擦、浸蝕而成的一顆珍珠,如果以為是現實里發生過的,就從此有了生活氣息,以為是有人曾說過的,就有了地方色彩,那流氓潑婦就該是語言大師了?藝術,首先是美好;美好是冶煉出來的。”[5]444關于語言是怎樣“冶煉”的,他談了三點看法:首先,好的語言要充分的表現情趣,“月有情而憐愛,竹蓄氣而清爽”,語言中有情操的內涵。在之后的創作中,他致力于追求有情趣的語言。王一川曾經評價賈平凹語言最重要的特征是白描化語言,白描是中國畫技之一,魯迅對白描有總結: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賈平凹在語言的白描化追求上,與魯迅先生如出一轍,他同樣反對浮華雕飾的語言,強調語言的單純樸素。“騙子靠裝腔作勢混事,花里胡哨是浪子的形象。文學是真情實感的藝術,這里沒有做作,沒有扭捏:是酒,就表現它的醇香;是茶,就表現它的清爽;即便是水吧,也只能去表現它的無色無味。”[5]443這種語言觀,從他最初的成名小說《滿月兒》到近期的《高興》,白描化的語言一直是為批評者們所稱道的。早期白描化語言清麗雋永,至后來,其語言愈加富有質感且生動鮮活。其次,他認為要和諧的搭配虛詞,其實是講語言的節奏感。他說:“為著情緒,選擇自己的旋律,旋律的形成,而達到表現情緒的目的,正是朱自清散文情長意美,正是孫犁小說神清韻遠的緣由。”[5]443作家的語言風格其實就體現在語言的節奏感上。和諧的搭配虛詞,使語感鏗鏘有致。筆者認為,虛詞的使用,會使運筆有疾徐,聲調有抑揚,節奏有張弛感,語感自然充滿韌勁和質感。第三,他認為要多用新鮮準確的動詞。“生動,生動,活的才能動,動了方能活”,動詞能使句子充滿動感,狀物記人猶在眼前一般,給人栩栩如生之感。他認為古今中外,“錘句鍛字,都在動詞”[5]444,好的動詞,不僅能夠狀物逼真,形象凸顯,而且可引發讀者產生文學性想象。動詞運用得好能夠增強作品的詩性特征。
2.恢復和起用語言的本意
文學語言要具有詩意,如何從現在的日常語言中尋找詩意,有的作家提出從古詩詞語中尋找,有的作家提出從翻譯語中尋找。賈平凹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還得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母語是與生命直接相關聯的東西,每種語言的產生,都與這個民族的生存環境、哲學、文學有關系,語言有很深的文化內涵。漢語文學原來是古漢語,時代發展變化,文學語言也要發展。白話文的寫作從五四到現在有百年時間,白話文沒有古漢語凝練,但用古漢語寫作又有一種迂腐感和陳舊感,這就需要對舊的語言進行超越,給予古語以新意。
賈平凹非常看重語言的本意。漢語本身就具有詩性,具有豐富的文化蘊涵,能夠直接傳達文化的感性與智性內容。“漢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義,象象并置,萬物寓于其間”,“漢字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幅抽象畫,它比現實簡單,經過提煉,但仍保持現實對象的感性質地,與其所處的境況,及它與它物的關系。因此,當漢字傳遞知識信息時,它所傳達的并非一個抽象概念,如拼音文字那樣。它所傳達的是關于認知對象的感性、智性的全面信息”[7]。對于中國漢語的這種詩性特征,賈平凹也有認識,“現在許多名詞,追究原意是十分豐富的,但在人們的意識里它卻失去了原意,就得還原本來面目,使用它,賦予新意,語言也就活了。……運用一些司空見慣的詞,新意就出來了。”[8]他非常看重漢語語言的本意,正因此,從一開始創作,他就十分注重從民間學,從古語中學,“向古人學,學習他們遣詞造句的精巧處,向民間學,留神老百姓口中的生動的口語”[8]。賈平凹認為,陜西民間土語相當多,語言是上古語言遺落下來的,十分傳神,筆錄下來,充滿古雅之氣,他早期作品非常注重古語在作品中的運用,其文學語言的重要特征就是古拙、質樸,這在《廢都》之前的創作中表現尤為突出,而且引起了批評家的高度認可。
3.提倡在現代背景下小說語言功能的轉變
賈平凹認為隨著西方文學的全面介紹,西方文學中語言的各種表現手法也為中國的作家們推崇效法和學習。傳統小說多寫人生、命運,現代小說多寫的是人性、生命,語言的功能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傳統小說中的語言更多是描述性的,現代小說的語言則更多在于敘述;傳統小說的語言要求描述得生動逼真,現代語言卻要求直達精神。他舉了一個例子:“在中國戲曲上,唱段是抒發心理感情的,即言之不盡而詠之,對白則是敘述的,承上啟下交待故事。中國戲曲上的這種辦法被中國傳統小說采用,對話在小說中的功能當然也能起到塑造人物之效,但更多的還是情節過渡轉化,或營造氛圍。一般作品中的對話僅是交待,優秀作品則多營造渲染氣氛,為塑造人物性格服務。現代小說則改變了,將對話完全地變為營造渲染氣氛和書寫心理活動……對話成了現代小說展示作家水平高低的舞臺。可以看出,現代小說中的對話就是對話,直抵精神。如一座水泥建筑上的窗戶,在這里,潛意識得到顯露。”[8]賈平凹認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對話中充分地把潛意識顯示出來,從而擴張、豐富著人的精神世界。現代小說中對話功能的改變可能只是現代小說語言表現的一種探索,一種為了使語言更好地傳達現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式。不僅是賈平凹,余華和王安憶等一批現代作家,都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踐豐富著現代文學語言,語言的功能的改變是文學創造性的表現。
[1]孫見喜.制造地震,賈平凹前傳:第二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2]賈平凹.懷念狼·后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3][德]黑格爾.美學:第二卷[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4]程華,李榮博.秦腔聲里知興衰——論賈平凹作品中秦腔和文化的映照關系[J].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2,(11):44-48.
[5]賈平凹.平凹散文[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
[6]賈平凹.白夜后記[M].廣州:廣州出版社,2007.
[7]鄭敏.語言觀念必須革新——重新認識漢語的審美與詩意價值[J].文學評論,1996,(4):72-80.
[8]賈平凹.關于語言——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講壇上的講演[J].當代作家評論,2002,(6):4-8.
【責任編輯馬 俊】
The Application of Creativity in TraditionalWays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n Jia Pingwa’s Novels
CHENG Hua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China)
Jia Pingwa possesses consciously artistic awareness,besides his unique cognition in the art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he author has the only art expressing ways and art skills to realize this cognition of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while he is writing. The viewpoints of art skills in Jia Pingwa’s novels embody his application of creativity in traditionalways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His understanding to the virtuality and reality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ies,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s and speaking,and even searching forwonderful languages in order to creatively reconstructand develop from folk languages and old languages.That is to say,he innovates andmakes breakthrough to China’s traditionalelements ofaesthetic appreciation from the literary expressing skills.His purpose of doing so is to better expressmodern people’s thought and feelings.
Jia Pingwa;images;structure;language
I206
A
1009-5128(2014)18-0072-04
2014-07-15
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項目:賈平凹莫言創作風格比較論(13JK0288)
程華(1975—),女,陜西韓城人,商洛學院語言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文學碩士,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