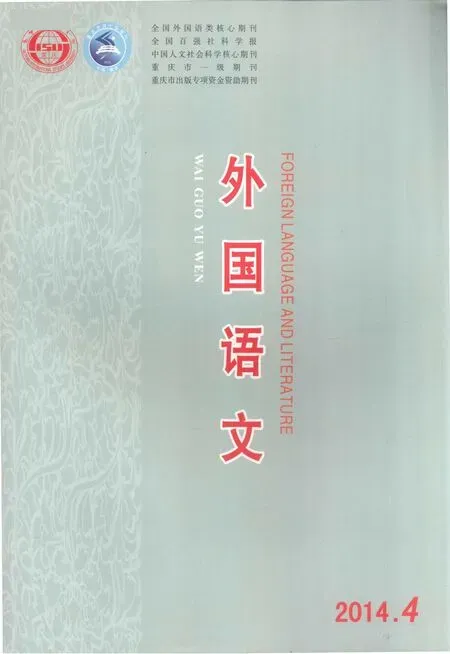翻譯史研究的一部新力作——《中國英詩漢譯史論——1937年以前部分》評介
易 經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1.引言
近年來,國內學者日益重視翻譯史的探討,相關研究所涉維度更多,對問題的洞悉更深刻。相關的代表成果有: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1984)和《中國翻譯通史》(2006),孫致禮的《1949-1966:我國英美文學翻譯概論》(1996),方華文的《20世紀中國翻譯史》(2005),王克非的《翻譯文化史論》(1997),李偉的《中國近代翻譯史》(2005),李亞舒、黎難秋的《中國科學翻譯史》(2000),黎難秋的《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1993)和《中國科學翻譯史料》(1996),陳玉剛的《中國翻譯文學史稿》(1989),郭延禮的《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1998),熱扎克·買提尼牙孜的《西域翻譯史》(1994),陳世明的《新疆現代翻譯史》(1999),陳福康的《中國譯學理論史稿》(1992)和《中國譯學史》(2011),臧克倫的《中國翻譯史話》(1991),謝天振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穆雷的《通天塔的建設者——當代中國中青年翻譯家研究》(1997)以及查明建的《中國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2007),等等。
筆者在自己的博士論文(2009)中曾討論了翻譯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翻譯實踐史、翻譯理論史和翻譯專題史是構成翻譯史學的三個主要分支。翻譯實踐史和翻譯理論史研究方面涉及中國翻譯史、世界翻譯史和區域翻譯史,而就研究對象的時間跨度上來講,這些方面都存在通史和斷代史研究。專題史分支的已有研究則主要包括如下方面:譯家研究、譯作研究、學科翻譯史、翻譯史與文化、翻譯機構發展史、翻譯教學發展史等。在翻譯史學的所有分支中,學科翻譯史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學科翻譯史即不同文本體裁的翻譯史,如文學翻譯史、科學翻譯史和宗教翻譯史。文學翻譯史可以更加細化為小說翻譯史、詩歌翻譯史、散文翻譯史、戲劇翻譯史等,科學翻譯史則大致可以分為人文社科翻譯史和自然科學翻譯史。
我們看到,上面列舉的那些翻譯史研究成果都是以這些分支中的某一個或幾個為視角,有的探討翻譯實踐史,有的討論翻譯理論史(當然實踐史和理論史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有的研究特定文體翻譯史,有的關注特定地域的翻譯史,還有的以特定時期的翻譯家為專題研究對象。這些成果大多涉及文學翻譯及詩歌翻譯,不少還專門討論文學翻譯史。但是,專門研究漢譯英詩的成果可說是罕見的。在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翻譯詩歌一直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中國的近現代翻譯史上,詩歌的翻譯也是一個重要的領域。詩歌是主要的文學體裁之一,對其翻譯發展歷程的考究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翻譯史研究分支而存在。翻譯史研究發展到今天,對文學翻譯史開展更為全面、更加細化的研究顯然成了一種必然趨勢。不過實際情況卻令人遺憾,雖然翻譯史學及文學翻譯史的研究有著長足發展,但是鮮有學者對中國的詩歌翻譯史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更不用說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詩歌翻譯史》的誕生了。
可喜的是,一部“詩歌翻譯史”專論的誕生讓這種局面有了改觀。這部專論便是張旭教授于2011年9月最新出版的著作《中國英詩漢譯史論——1937年以前部分》。該書是張旭繼出版《視界融合——朱湘譯詩新探》(2008)和《跨越邊界——從比較文學到翻譯研究》(2010)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在該書中并非構擬整部“詩歌翻譯史”,而是選取了英語詩歌(涉及作者并非局限于英美國家詩歌作者,也包括經由英語進入漢語主體詩學圈內的弱小民族國家詩歌作者)在1937年以前的漢譯發展歷程作為研究對象。這一研究可以說是填補了翻譯學界在該領域的空白。
2.內容概覽
英詩漢譯的歷史始于清末。近兩百年的時間雖說不是很長,但必須承認,要梳理這段歷史的脈絡、概括其全貌、探究其內在規律乃至發掘英語詩歌與中國民族詩歌的關系確是一項龐大而繁雜的工程。我們看到,作者張旭十分清晰地廓清了1937年之前中國的英詩漢譯脈絡,合理而嚴謹地對這一時期的英詩漢譯進行了階段劃分。從該書的結構和各章內容概述便可見一斑。
全書由13部分構成,包括緒論、主體10章、結語和后記。緒論部分概要地描述了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英詩漢譯史,將這段歷史分為四個異質的階段:清末到“五四”時期;1919年到1937年;抗戰時期;抗戰勝利到1949年。之后,作者分析了英詩漢譯對中國新詩發展的影響。緒論的后半部分交代了該項研究的背景及發展趨勢、研究的目的與范圍和研究意義。
主體部分的第1到第5章討論中國近代(即上述清末到“五四”時期)的英詩漢譯問題。第1章從整體上按照時間脈絡(分為文化外求時期、文化碰撞時期和文化動蕩時期)對近代英詩漢譯的發展史進行了描繪。第2章討論近代在華傳教士的英語宗教詩歌漢譯活動,對這類翻譯活動進行了詳盡地介紹,考察了傳教士在這類翻譯活動中的詩藝追求,分析了他們的翻譯決策。第3章從意識形態角度描述并考察當時英詩漢譯活動的贊助人、選材和翻譯策略的取舍等問題。第4章分析中國的佛經翻譯傳統對近代英詩漢譯的影響,回顧了早期的白話體譯詩。第5章選取了早期英詩漢譯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譯者進行考查研究,他們是蘇曼殊、陸志韋和劉半農。作者不但全面地描述了這幾位譯者的英詩漢譯活動,摘取典型譯例進行分析,還精辟地總結了他們的翻譯宗旨、翻譯策略及技巧、對英詩漢譯活動乃至中國本土詩歌創作的影響。
主體部分第6到第10章涉及中國現代早期(即1919年到1937年)的英詩漢譯。第6章以寫史、論史的方式全面而有重點地介紹了“五四”時期的白話譯詩運動、莎士比亞及黑人詩歌早期漢譯情況、英詩漢譯專刊的翻譯活動、現代派英語詩歌漢譯的萌芽及印度和古波斯等弱勢民族國家英詩的漢譯情況。第7章和第8章討論的實際上是同一主題——早期英詩漢譯的散體化現象。第7章闡述的是胡適、朱自清和鄭振鐸三位詩人兼翻譯家的譯詩實踐。第8章則著重討論創造社三位重要成員——成仿吾、郁達夫和郭沫若——的譯詩實踐。這兩章在概括這些譯者的譯詩實踐和開展典型譯例分析的基礎上,客觀深入地剖析了這些譯家的譯詩理念、翻譯策略和他們的譯詩活動的深遠影響。更為可貴地是,對于譯家們的翻譯理念形成的背景和影響翻譯策略擇取的內外在因素這兩章都有較為深刻的揭示。第9章考察新月派成員以新格律體翻譯英詩的實踐活動,集中描述分析了聞一多、徐志摩和朱湘三位新格律派詩人兼翻譯家的詩歌翻譯原則、策略及對譯詩新格律的探索、實踐和追求。主體部分最后一章主要研究白話文學語境中“學衡派”翻譯英詩的文言體傾向,對吳宓和吳芳吉等人翻譯英詩的藝術追求進行了全面而中肯地評析。該章還從歷史文化語境角度闡釋了“學衡派”詩歌翻譯觀形成的深層原因。結語是全書觀點的總結。
皮姆(Anthony Pym),(1998:ix-x)曾指出:“翻譯史知識的核心對象不應該是翻譯文本本身,也不是翻譯文本的上下文體系或者其語言特征。翻譯史知識的核心對象應該是譯者,因為只有人才具備適應于社會因果關系的責任……翻譯史應該圍繞譯者工作和生活地的社會環境建立。”該書主體部分的內容設置便基本貫徹了這一思想。可以說,全書的宏觀框架結構系統而縝密。各部分、各章節之間有機聯系,邏輯嚴明。以如此寬廣的視野對英詩漢譯如此多的方面展開研究,在國內外都可以說是首次。
3.全書特色
《中國英詩漢譯史論——1937年以前部分》一書特色鮮明。這部著作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史書,除了具備翻譯詩歌斷代批評史的特點,它還是一部學術研究專著。著者搜羅了大量珍貴的一手史料,按照史學研究體例編排。作者對這些史料進行了有理有據的系統分析和研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書與前人對相同時期的翻譯文學史表述有很大不同。這一點從上述內容概覽便可感知。在體例安排、內容取舍、觀點評價等方面,作者都注重對翻譯詩歌史的重點部分提出研究心得,探討不同時期的翻譯詩歌對主體國民族文學發展的貢獻,研究翻譯文學史上帶有規律性的問題。概括而言,全書有如下主要特色:
3.1 研究的理論基礎堅實,研究方法新穎得當
作者以廣博而獨到的眼光,吸收運用現代最新的翻譯理論和相關學科理論(描寫譯學、多元系統論、文化翻譯論、比較文學、社會學、闡釋學、接受美學)。可以說,描寫譯學倡導的描寫研究方法是整個研究一以貫之的方法。
不過,作者的論說并不停留在簡單描述層面。皮姆就曾批評霍爾姆斯(James Holmes)在“翻譯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描述翻譯研究的結構時對翻譯史研究的模糊定位。皮姆(Pym,1998:1-2)發問道:“霍爾姆斯的譯學結構圖是否意味著歷史僅僅是對史實對象的描述?像‘翻譯批評’這樣的非描述性領域是否就與歷史無關?是否‘理論研究’根本就存在于歷史之外?”皮姆(Pym,1998:2)接著說:“不管霍爾姆斯總結出那些關乎翻譯史的范疇的原因是什么,讓人感到詫異的是,無論是其描述分支下還是理論分支下,翻譯史領域都是片段化的,零碎的。”皮姆(Pym,1998:5)指出:“通常而言,翻譯史至少可以細分為三個領域:翻譯史實、翻譯史批評和翻譯史解釋。”
我們看到,張旭教授在運用描寫方法的基礎上,以多元系統理論為觀照,對早期的中國英詩漢譯活動做歷史重構和系統描述。同時,他以意識形態和詩學觀為主要視角,考究英詩漢譯的歷史文本。通過分析翻譯過程中操縱不同翻譯家的種種因素以及翻譯家對于當時翻譯規范的影響,透徹地評析并揭示了這背后的意識形態和詩學體系構建的訴求。最為可貴的是,作者站在多元系統論和文化翻譯觀的立場上,從中外文學關系的角度考察了歷史上翻譯詩歌所散發的文化力量,令人信服地解析了翻譯詩歌在民族文學體系重建過程中擁有的特殊地位和發揮的重要作用。作者將對英詩漢譯史的描述、批評和解析有機融合了起來。很明顯,他在全書研究中就1937年以前的英詩漢譯史較為全面地回答了皮姆對其翻譯史三領域的具體描述中涉及的這樣幾類問題:第一類,譯者是誰?翻譯了什么?如何翻譯的?在哪里翻譯的?什么時候翻譯的?為誰翻譯的以及有何影響?第二類,對不同譯本或翻譯行為推動或阻礙發展的情況進行評估;第三類,在當時當地,那些翻譯史實為什么會發生以及是如何產生變化的?(Pym,1998:5-6)這種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價值判斷的論述,另一方面其總結的規律和提出的觀點也頗具說服力。
在描寫研究的方法論基石上,作者把寫史和論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具體的論述中合理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正如作者(2011:12)所說的:“在論述的過程中,還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借鑒闡釋學的有關原理,通過對譯者與譯者、譯本與譯本、原作語言與目標語言、異域文化與目標與文化的比較和闡釋,揭示異質,彰顯特征,描繪出不同時期的英詩翻譯特征;同時還借鑒比較文學領域中影響研究和接受美學中接受研究的方法,運用資料統計方法調查不同時期的譯詩流傳和接受情況,從而弄清英語詩歌是如何通過翻譯的途徑進入主體文學體系,進而影響中國的詩歌創作的。”
3.2 史料十分翔實
許多史料均為作者首次整理發掘,為他人研究中國英詩漢譯提供了便利。比如說該書第2章集中研究了近代在華傳教士用中文翻譯英語宗教詩歌的情況。對在華傳教士的翻譯活動開展研究,本書作者并非第一人。但凡討論中國明、清之后的翻譯史,這一內容都是不可忽略的。從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向中國輸入科技文本到近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從事的翻譯活動,都在中國翻譯史、科技史、宗教史、文學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不少研究者都關注過這一課題。作者并沒有泛泛而談地介紹近代西方傳教士的翻譯活動,而是聚焦于他們對英語宗教詩歌的翻譯。可以說,這樣的視角在已有的對西方傳教士翻譯活動的研究中是獨樹一幟的。在這一章中,作者概括了西方圣詩傳播到中國的四個時期,即唐代、元代、明末清初和近代。前三個階段的圣詩漢譯所依據的源語為拉丁文,所以這一章重點關注的是近代即清末英語圣詩開始大規模介紹到中國的時期。張旭首次以表格的形式全景式地展現了這一階段英語圣詩漢譯的主要譯者、譯作、譯者所屬教派和國家、出版地和時間等信息。在接下來的部分,作者從意識形態、詩學、語言形式和意韻內涵等方面集中探討了在華傳教士圣詩漢譯的詩藝追求和翻譯策略。作者(2011:78)指出:“近代早期來華傳教士在翻譯西洋宗教性題材的詩歌作品時,一則由于針對的接受者主要是下層信眾,再則由于眾譯家的漢語文言修養仍然有限,只能譯成淺文理的白話體或采用方言形式,疑惑采取文白兩種語體并存的方式,不過其譯詩都適合于吟唱……它們對于后來漢語文學中白話替代文言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另則它們的譯詩還能與音樂聯系起來,這些自然在近代時期對主體詩學體系產生過巨大的沖擊,或是為其自身體系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可資參照的因素。”作者發掘到在華傳教士圣詩漢譯活動對于中國文學白話文普及的促進作用以及對許多漢譯圣詩的音樂性的細致分析都是發人所未發,別具一格。
還譬如說,該書第10章對“白話文學語境中‘學衡派’英詩漢譯活動的考察”就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在這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學衡派’多是作為負面形象出現的,也就是常被當作文化守陳者角色來對待,并備受時人的批評和攻訐”。作者并沒有人云亦云地對“學衡派”進行批判,而是敏銳地把握到了這一學派在外國文藝作品翻譯領域所做的工作,他(2011:370)說:“當年‘學衡派’成員在積極地開展文學創作的同時,努力從事著外國文藝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工作,這其中包括對英語詩歌的譯介,而且都使用了文言體形式。”對于“學衡派”的翻譯活動,作者沒有簡單地給出“落后”、“保守”或“守陳”的論斷,他力圖揭示“學衡派”的總體文藝追求之宗旨,解釋該派之所以以文言體為翻譯的主要形式的原因。在具體研究中,作者首先對“學衡派”成員的譯詩活動進行了概括性描述。作者以表格的形式,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歸列了從1922年1月到1930年3月期間“學衡派”主要譯者在該派翻譯活動主要陣地《學衡》雜志上發表的漢譯英詩。這可以說是基本史料的歸納。作者寫史卻并不簡單羅列史實,而是史、論結合,深入剖析,尋找內部規律。在接下來的論述中,作者分析了“學衡派”的總體翻譯特色、譯者的背景(包括譯者的年齡層次、地域分布和教育背景)、目標語的選擇和詩學追求。通過這些分析,作者(2011:377)的如下結論也就顯得十分令人信服了:“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中正’的學術態度,這種浪漫主義的詩學觀,還有所受到的新人文主義思想的熏陶,使得‘學衡派’成員在翻譯中能著意于‘融化新知’并在詩藝上精益求精。這樣就誕生了中國現代時期非常特殊的一批翻譯詩歌,而且從中又能讓人獲得獨特的審美享受。”
我們看到,正是由于史料詳實,論據客觀,作者探究問題得出的結論都是十分公允的。這反映了作者在研究中重調查、重考證而絕不依賴主觀感覺或印象的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作者的結論也是開放性的,他說:“至于這些譯詩對于后來中國白話新詩的誕生是否有過影響,尤其是有那么一大批白話詩人早年都在教會學校接受過西式教育,而且早期由傳教士翻譯的一批西洋圣詩又成了他們日間吟頌的必備科目,他們后來創作風格的形成是否與早年吟頌過的那些圣詩有著某種淵源,這些仍然值得進行深入系統的挖掘和研究。”(張旭,2011:78)作者不但給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還極具啟發性的對如何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這對于其他研究者而言,顯然是很有參考意義的。而這一“開放性”特點正是接下來要談到的。
3.3 觀點開放而不武斷,體系嚴謹而不封閉
由于本書整個研究都是建立在翔實的史料、科學的方法論和客觀合理的分析之上,這使得作者的觀點或結論乃至全書的整個體系都具備很大的開放性和啟迪性。他人可以沿著作者開辟的道路或者通過借鑒作者對相關課題進一步研究的思考展開更多有價值的探索工作。如對詩歌的建筑美和中國建筑傳統乃至中國傳統的“人本”及“天圓地方”思想之間的聯系的認識就大可作更多文章。
在第9章,作者通過對大量的翻譯實例考察,詳細討論了早期新月派成員翻譯英詩的實踐活動。在該章第一節中,作者集中回顧了聞一多的英詩漢譯活動,并著重從“音樂美”和“建筑美”兩個方面中英對照式地分析了聞一多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譯詩。作者尤其關注聞一多在譯詩“建筑美”追求中所做的創格舉措。在對聞一多和饒孟侃二人合譯英國詩人霍斯曼(A.E.Housman)所作《山花》的分析中,作者(2011:320)指出:“早期新格律派翻譯家在迻譯西洋律詩時,除了效仿原詩采取分行分節的排列方式外,盡量發揮漢語方塊字的形體優勢,努力使譯詩各行形體排列整齊,從而取得‘均齊’的建筑效果。”作者認識到,聞一多的譯詩同原詩在形式上是具備極大不同的,這正體現了譯者的“創作”詩學主張。作者分析了譯者之所以采取這種形式的譯詩的原因,即聞、饒二人在對原詩進行重寫的過程中更多地考慮到主體文學圈內讀者的閱讀習慣。譯者對詩歌形式進行的調整是要使譯詩在各方面都更加接近自己所標舉的新格律體詩歌的主張。作者(2011:322)分析說:“譯詩首先給人的是‘建筑美’。四四方方的排列形式,給人的視覺以整齊勻稱的感覺。譯者之所以會將這樣的詩歌處理成四方形的詩節,主要是參照了主體詩學的規范。”
在這樣的分析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將詩歌的“建筑美”同中國建筑藝術的傳統聯系了起來,即在主旨上講究天人合一,在基調上強調和諧,在工藝上師法自然,在風格上追求含蓄,在審美特點上近乎于繪畫,在設計的起始點上又重在線條。更為可貴地是,作者討論了中國建筑藝術傳統背后的哲學和美學思想根源,他(2011:323-324)說:“這些無一不與中國傳統的陰陽哲學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就是那種‘守中’的觀念相聯系……陰陽二氣相互消長會造成變化,這樣就與中國哲學中‘易’的概念聯系起來……表現在建筑領域,就是歷來的能工巧匠在追求中正和諧的同時,也普遍追求造型上的‘靈、活、巧、變’……由此派生出‘變中求齊’的美學思想……以此理念來考察聞一多的譯詩,我們發現他更多地是在貫徹‘變中求齊’的美學思想,從而在追求譯詩‘音樂美’的同時,體現‘建筑美’的效果。”
這樣的分析細致入微,絲絲入扣。作者選取微觀實例分析和宏觀社會文化和哲學思想的雙重視角,使我們讀者在整體把握聞一多譯詩的大體狀況的基礎上,通過作者對代表性譯例的詳盡解析,深刻認識那些譯詩誕生的背景及內在原因。作者的這些探討性研究也是發人深醒的。關于詩歌的建筑美、關于詩歌建筑美同真實建筑的建筑美之間的關系、關于詩歌建筑美或真實建筑美背后的社會文化、社會傳統、哲學思想、美學理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詩歌翻譯中種種相應的問題都值得我們進行更多的深入研究。
4.結語
皮姆(Pym,1998:6)曾指出:“翻譯史實和翻譯史批評主要關注具體的事實和文本。翻譯史解釋則必須關注這些資料的因果關系,尤其是通過權力關系表現出來的那些因果關系;正是在這一領域中,譯者表現為具備一定影響力的社會活動者。”《中國英詩漢譯史論——1937年以前部分》的研究無疑很好地注意到了這些方面。通過閱讀這部著作,相信讀者能對1937年以前的中國英詩漢譯史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對這段歷史中出現的種種英詩漢譯的現象有著更為深刻的微觀(具體事實和翻譯文本)和宏觀(相關翻譯現象產生的原因及社會背景、譯者的社會角色、翻譯行為的影響)把握,同時也會對翻譯史研究的套路和方法有著更為深入的領悟。讀者也可以就自己所感興趣的課題,借鑒本書作者的研究方法、思路和觀點,開展自己的研究。
總而言之,《中國英詩漢譯史論——1937年以前部分》開了英詩漢譯史專題研究的先河,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讀的著作。該書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成果。由于書中的開創性研究,這一成果被鑒定為“優秀”等級。其所具有的開拓意義,使其成為我國翻譯史研究領域十分重要的一部著作。我們期待中國英詩漢譯史1937年以后部分的研究成果盡早問世。
[1]Holmes,Ja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C]//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Rodopi,1988:67-80.
[2]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3]Pym,Anthony.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8.
[4]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B Publishing company,1995.
[5]馬祖毅.中國翻譯通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6]張旭.跨越邊界——從比較文學到翻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7]張旭.中國英詩漢譯史論——1937年以前部分[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