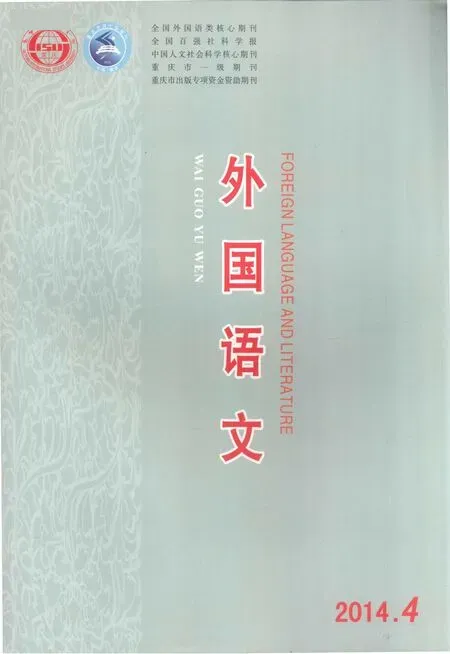語言與心智——塞爾與喬姆斯基的語言思想辨析
謝國平 王和玉
(1.廣東財經大學 外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320;2.廣東工業大學 外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1.引言
20世紀的西方哲學經歷了從“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最后到“心智哲學”的轉向歷程。分析哲學與語言哲學側重研究語言本體,而心智哲學側重研究人腦和心智。顯然,哲學關注的核心從邏輯轉向語言,最后轉向語言的使用主體。
在語言哲學向心智哲學轉向的過程中,塞爾和喬姆斯基都強調對語言使用者的關注和重視。他們的心智語言觀為后來的語用學、句法學和認知語言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塞爾結合心智哲學、語言哲學和社會哲學的研究成果,建構了聯系心智、語言和世界的“意向性理論”,促進了心智哲學、語用學和認知語言學的發展。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倡導內在語言觀和普遍語法,首次提出內在于人類心智的“語言機制”和“語言天賦說”,試圖揭示語言的本質和語言習得問題。在語言和心智問題的哲學思考上,塞爾和喬姆斯基有很多類似觀點,但由于研究目標不同,兩者在具體路徑和研究重心上也存在差異。本文擬對兩者語言思想進行梳理,比較異同。
2.塞爾與喬姆斯基的心智語言觀
2.1 塞爾的語言思想和心智哲學
塞爾的語言哲學思想可粗略分為兩個階段。初期,塞爾發展了奧斯汀(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后期,塞爾將語言與心智結合,完善了其心智哲學思想。
首先,塞爾將“言語行為理論”普遍化和規范化,并明確其規則系統和分析框架;其次,塞爾在言語行為與現實世界之間建立了關系。他(Searle,1983:10)提出“適應方向理論”:信念具有從心智到世界的適應方向;愿望具有從世界到心智的適應方向;每一個心智行為都反映了心智與世界的某種關系。顯然,塞爾已經開始關注和分析心智和語言活動的關系。
后期的塞爾關注言語行為的目的性,認為各種言語活動均與人類的意向性相關。“意向性”理論將人的心智因素納入語言分析中,突破了以往對理想語言分析的框架,主張言語行為受心智活動支配;這意味著塞爾的研究重心從語言哲學到心智哲學的轉移。在塞爾看來,語言哲學是心智哲學的一個分支;言語行為表征事態的能力是具有生物基礎的心智能力的延伸;心智能力通過人的行為和感知將生物體與世界聯系起來;不是心智依賴語言,而是語言依賴心智。據此,塞爾的語言思想完成了從“語言本體”到“人類心智”視角的轉變。
與奧斯汀不同,塞爾深受生成語法思想的影響(顧曰國,1994b)。20世紀80年代后,塞爾將心智哲學引入言語行為理論,認為言語行為的本質最終要到大腦的意向機制里尋找答案。塞爾(1984)指出行為結構同時具有生理要素和心理要素,后者驅動前者;大腦的心理意向活動是言語行為的最終原因。塞爾對“腦體二元說”進行了批判,認為人類的心理現象和大腦所進行的思維活動是基于大腦生理機制的自然特性,語言交際必須以大腦的心理活動為基礎。塞爾的心智哲學是言語行為理論的基礎(顧曰國,1994a),他對意識、心靈、語言、社會現實所做的全面闡述標志其心智哲學思想日臻成熟。
2.2 喬姆斯基的心智語言觀
喬姆斯基(Chomsky,1975;1980)多次強調結合語言與心靈的研究。語言是心靈的鏡子,心理的真實性即理論的真實性。在腦科學和神經科學未能為心智現象提供合理解釋時,語言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洞察心靈本質。只有承認語言與心智的緊密相關性,才能解釋語言的創造性,才能解釋大腦局部受傷時引發的語言障礙,也才能解釋為何使用語言時PET掃描能發現人腦局部區域的血流量增加(蔡曙山,2006)。喬姆斯基主張語言是具體的自然客體,實在地存在于心智/大腦中;語言是語言官能所呈現的狀態,是心智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表現于大腦的神經機制之中。語言知識的本質在于人類心智中具有一套語言認知系統,表現為一些運算機制和原則體系。這一系統可以解釋人類語言的創造性。在喬姆斯基看來,語言研究就是對人類心智和大腦的研究。基于生物學、神經科學和遺傳學的研究成果,喬姆斯基等區分了廣義語言機能(FLB)與狹義語言機能(FLN);前者指所有涉及語言運算的機制,可能與其他領域或物種的某些機制重合;后者指人類語言獨有的運算機制所體現的“唯遞歸性”(Hauser,et al.,2002;Fitch,et al.,2005)。盡管在語言進化的問題上,學界在“唯遞歸性假說”和“適應性假說”之間仍莫衷一是(Pinker&Jackendoff,2005),生成句法發展的趨勢顯然是正與生物學和進化科學的研究日益融合。
3.相同的哲學思想和方法論
3.1 心智和語言研究的本體論地位
傳統心理主義認為心理現象是客觀的存在,但是關于“實在”的定義一直將具有主觀性的心理現象排除在外。問題在于:如何將心理狀態的主觀性納入關于現實世界的客觀性概念中?
塞爾(2006:17)指出:“如果科學是指我們關于世界的客觀性和系統的真理之集合,那么主觀性的存在就像其他事實一樣,也是一種客觀科學的事實”[11]17;“如果主觀性事實與某個科學的定義相悖,我們得放棄定義而不是事實”。塞爾區分了認識論意義上的主客觀和本體論上的主客觀。如果一個陳述的真依賴于觀察者的態度和情感,該陳述在認識上是主觀的;反之,在認識上是客觀的。而本體論意義則涉及世界上各種類型的實體存在方式的地位。“山峰和冰川具有客觀的存在方式,因為它們的存在方式并不依賴于主體的經驗。但疼痛、癢覺、欲望以及思想、情感則具有主觀的存在方式,因為它們只是由于某個人類或動物主體的體驗才存在。”(塞爾,2006:44)
區分認識論與本體論兩種意義上的主客觀之后,意識具有主觀存在方式的事實,并不妨礙我們具有客觀的意識科學。科學在認識上應該是客觀的,科學家試圖發現獨立于任何人的情感、態度或先入之見的真理;這種認識上的客觀性并不排斥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本體論的主觀性。(塞爾,2006:45-46)
喬姆斯基認為,人類心智中存在著由生物遺傳系統決定的認知系統;喬姆斯基把這些認知系統稱為心智器官。心智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所有心智活動都是大腦所呈現的某種狀態和功能。語言是一種心智活動和表現,其物質基礎存在于大腦。將語言作為自然世界的真實客體進行研究是生成句法的語言哲學基礎。“心智其實是由器官組成的一個系統,根據遺傳規則組織而成;遺傳規則詳細地規定了它們的功能、結構及發展過程;正如視覺系統一樣,這些基本原則的實現依賴于與環境的相互作用。”(Chomsky,1977:80-82)在這些認知系統中,構成人類語言知識的語言機能是其中一個子系統。生成語法研究就是對語言機能的狀態和功能進行抽象刻畫;是在抽象層面上研究物質世界的性質,唯有如此才能對語言等心靈現象建構解釋性理論,洞察語言知識和語言官能等自然現象的本質。
總之,塞爾和喬姆斯基對心智和語言賦予了客觀存在的本體論地位;這樣為將之納入自然科學研究奠定了哲學和認識論基礎。
3.2 對二元論的徹底清算
哲學界一直存在“唯物”與“唯心”的區分,某一觀點非此即彼;唯物論可能包含合理因素,但唯心論絕對錯誤;處于兩者之間的二元論也一定有問題(徐烈炯,2008:218)。哲學思想一旦觸及心智,就被歸入唯心論或二元論,塞爾的心智哲學與喬姆斯基的心智語言觀也不例外。
塞爾(Searle,1992:1)批判了心靈哲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唯物論和二元論傳統。唯物論和二元論犯了同樣的錯誤:實體要么是“物的”,要么是“心的”。基于唯物論和二元論的這一共性,塞爾將二者歸并到所謂的“概念二元論”之中。“唯物論也是某種形式的二元論……唯物論是二元論最美的花朵”(Searle,1992:25)。
從語言的創造性出發,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知識是一種心理現象。正如光、電、和其他有機事物一樣,自然界也存在心理方面的事物。對于身心關系,喬姆斯基主張心靈的特征是大腦有機結構的結果。從牛頓推翻唯物論和機械論之后,人們對待物質與精神的問題有了顛覆性改變;二元實體區分所基于的那種物質根本不存在,關于思維本質及其與大腦關系問題的傳統觀念也應該隨著科學的發展而更新。正如喬姆斯基所言,“物質應受到我們更多的尊敬,因為它朝著精神的屬性更近了一步”(Chomsky,2002:113)。可見,物質與心智水火不容的觀點已不復存在。
喬姆斯基批判奎因(Quine)的“自然化認識論”對存在心智現象的否認。奎因認為脖子以上的問題不宜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這實際上是一種方法上的二元論。喬姆斯基提倡在思維模式上徹底擯棄二元論,特別是方法論上的二元論,因為這種二元論比“傳統的形而上學二元論危害更大”(Chomsky,2000:112)。
總之,“唯物”與“唯心”的對立是基于對于“物質”的清晰定義之上的。“物質”概念和術語只有在機械哲學的范圍內討論才有意義。機械哲學被顛覆后,對心物進行二元區分的理論前提已不復存在,對心智和語言的研究不宜再套以任何唯心的標簽。塞爾和喬姆斯基都對傳統哲學的“二元論”進行了徹底清算。
3.3 方法論上的自然主義
自從機械哲學的物質理論坍塌以來,學界產生了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觀點:宇宙是一個整體,其中所有客體都能進行科學研究。自然主義蘊含著方法上的一元論,即采用像研究自然物體一樣的方法研究語言和思維。
塞爾提出了一種“生物學的自然主義”的心智理論:心智是自然的一部分,對精神現象存在的解釋方式是生物學的。具體而言,這種生物學的自然主義認為:“全部心理現象,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視覺或聽覺的,不論是痛覺、癢覺或思想,以至我們全部的心理活動,都由腦中進行的過程產生”(Searle,1984:10)。生成語法采納的也正是這種自然主義的觀點。喬姆斯基認為:既然物質的概念無法確定,身心問題從此消解。從科學的角度看,“物質”的概念是開放和發展的。只有對“物質”進行確切定義后才能斷定某些現象是否超出了其界限(Chomsky,2000:84)。換言之,喬姆斯基認為對于心智與語言的研究沒有本質區別,研究心智同樣可以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如此,科學與哲學的目標不再是調和物理世界和心靈之間的矛盾,而是認可其共性,并在生物學和腦科學中去理解和解釋這種共性。任何填平心物之間鴻溝的努力毫無意義,因為這條鴻溝根本就不存在。塞爾和喬姆斯基共同的智慧在于用自然主義規避了心智和語言的區分問題,走出了心物二分的尷尬傳統。
3.4 對還原論的擯棄
唯物論者堅持意識必須還原為物質實在;若否認意識的不可還原性,就是拋棄整個科學世界觀。意識的不可還原性是二元論者強有力的證據。塞爾認為,即便賦予心靈以本體論的地位,卻并不一定要選擇二元論。傳統意義上的“還原”并不意味著一定消除主觀性。在唯物論與二元論的分歧上,意識的不可還原性不足以成為將其排除出局一個決定性因素。一些內在心智現象雖然客觀存在,有生理基礎,由大腦運作引起,在大腦結構中實現,但不能還原為其他物質,也不能以重新定義的方式化解。
還原論者將包括語言在內的心智活動還原為大腦的神經網絡、電流活動和物理化學反應和規律。但這明顯站不住腳,因為生命過程、語言、意識活動除了必需的物理、化學基礎外,還受制于其自身的活動規律。喬姆斯基也對還原論持否定態度。在他看來,心智活動不能等同于腦神經活動,對語言和心智的研究也不能完全還原為對大腦神經網絡的研究,語言機能及其運算表現不能還原為有關物質和生物的運動和表現。
受制于腦科學與神經科學研究的局限,對于心智與大腦的關系,目前還存在著認識方面的空白,這也正是喬姆斯基為何頻頻使用“心智/大腦”這種表達的緣由。我們還無法知曉“心智”與“大腦”這兩個表達之間的斜線究竟意味著什么(吳剛,2006:11)。當語言機能運算生成一個內在表達式,我們不知道其物質表現究竟如何;我們談論語言機能的遺傳基因,但不知道這些基因到底是什么。
可見,塞爾與喬姆斯基都堅決地擯棄了心智研究中流行的還原論,追求的是心智哲學與生物科學等自然科學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的統一。此路徑將語言、心智研究和腦研究統一在共同的理論原則之下,將其納入自然科學的總體研究之中。
4.不同的研究目標與重心
4.1 關于意義
意義的產生和理解是當今語言哲學和語言學研究的首要問題。維特根斯坦的一個重要語言觀就是:意義即使用。通過把語言和日常使用相聯系,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就由靜態的映射關系轉向了動態的糾纏關系。雖然塞爾的語言思想也沿襲了日常語言學派的精神,但其研究的是意義的產生而不是語言的理解(張紹杰,2001)。在塞爾看來,意義派生于心智的意向性;同一言語行為表現兩個不同層面的意向性,即表述的意圖(intention to represent)和交際的意圖(intention to communicate)。塞爾尤其關注前者,這樣將研究重心引向了心智,這是塞爾與其他語用學家的區別。
生成語法從來就沒有忽略對語義問題的研究(吳剛,2006:90)。喬姆斯基認為:諸如論元結構等傳統的語義概念,動詞間不同的語義關系,量化詞或代詞和先行語之間的語義關系,似乎無關于語言外部的因素,可以在語言內部得以解釋。但要確定和解釋關于詞語和句法結構的完全意義,不能光依賴語言內部系統;語言的意義還受制于語言與客體世界的關系。一方面,塞爾與喬姆斯基的意義觀不約而同地顛覆了自弗萊格(Frege)以來將意義與真值相聯系的哲學傳統;拓寬了意義研究的維度,即意義的關系與外在客觀世界無關,而是心智表征的體現。另一方面,塞爾的研究目標仍定位在哲學層面,關注的仍然是表述者的意圖所產生的意義。盡管引入了人的心智因素,對意義的考察和分析仍然是塞爾的重心。塞爾主張任何意義都是主觀的建構,是主客觀相結合的產物。但在喬姆斯基的生成句法中,很多語義問題被擱置,探討的重點是語言機能所體現的運算程序和原則體系。喬姆斯基認為目前無法考察所有的心智和意義問題,因此將研究目標鎖定在語言上,試圖通過語言研究洞察心智。
4.2 社會現實與心理現實
塞爾試圖通過對語言、意義和意向性關系的闡釋,證明言語行為能力是源于心智的內在能力。因此,其理論目標是解釋說話人言語行為能力的機制,而不是解釋說話人和聽話人使用語言的交際能力,這一點與喬姆斯基的理論目標有殊途同歸之妙(張紹杰,2001)。
但塞爾同時又認為語言基本上是社會現象;社會現實就是人們所思考的問題,所思就是如何進行交談,如何建立聯系的問題;人類社會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語言本身構成社會事實的一部分。在承認語言的意義來自心智的意向性的前提下,塞爾強調社會規約和使用慣例在言語行為中的作用。如此,塞爾的語言思想表現出與索緒爾的相似性。
與此相區別,喬姆斯基對語言和心智賦予了全新理解,語言不再是產生和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與思想同構;語言本身就是心智的一部分,語言研究就是心智研究。在喬姆斯基看來,語言就是內在于心智的一套原則與運算系統。從人類的語感和語言習得的角度看,這種潛在機制具有心理現實性。研究心智意義上的語言,得回避任何經驗主義和行為主義對語言所進行的外在主義的描寫和分析。社會規約和使用慣例由于變動不居,難以控制,不符合內在主義的語言研究觀。
4.3 心智哲學與語言科學
心智哲學不再將語言活動看成哲學直接的研究對象,而是通過言語活動這個窗口,洞察人類語言背后的心智活動。心智哲學的終極目標是解密意向和心智。從這個意義上看,塞爾不是語言學家,雖然其思想和言語行為理論被語言學界所接受和應用;因其對心智和意識本質的認識和關注,塞爾更宜被稱為心智哲學家。
喬姆斯基雖然從哲學的高度審視語言,將語言視為心智的一部分,但其核心工作仍為解密語言,通過語言探索心智,并最終為腦神經科學提供基礎。語言研究能幫助我們洞窺心智,但絕不是心智的模型(Smith,2004:47)。喬姆斯基對人類理解力的可及問題與無法觸及的神秘做了區分,無意將所有的心智問題納入研究視野。關于意向性,因其關涉心智如何處理外部世界的特質,也許永遠在人類的理解力之外,屬于難解之謎,不是目前的研究能探討的問題(Smith,2004:163)。
塞爾(2006:4)一再強調其形而上學的立場:“世界完全獨立于我們的心靈而存在,在我們進化的天賦范圍之內,我們能夠達到對于世界本性的理解。”
但對于喬姆斯基,“心智”只是描述世界的不同方面,不具有形而上的內涵。喬姆斯基不贊成在哲學與科學之間做出明確劃分。正是這一劃分使得“心智”的概念長期被排除在自然科學研究之外。
5.結語
不管是塞爾的心智哲學,還是喬姆斯基的生成句法,一個關鍵的理論前提是心智現象的本體論地位。這種思路符合托馬斯·庫恩對科學革命的描述。自笛卡爾以來的“二元論”傳統是“常規科學”范式;心身問題的困境乃“科學危機”;解決“危機”的方法在于轉換“范式”。對塞爾和喬姆斯基而言,就是徹底擺脫傳統哲學中唯物與唯心的糾纏,用自然主義的方法論將語言和心智重新納入科學研究的陣營。
但語言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解決心智問題?語言與社會的聯系有多緊密?對意義的追問是不是哲學研究永恒的主題?關注語言意味著更多地關注社會現實還是心理現實?意義與語言的研究在什么情況下必須融合和分離?這些問題是塞爾與喬姆斯基哲學觀和語言觀的困惑和分歧所在;也是將來的哲學與語言學研究必須解答的問題。
[1]Chomsky,N.Reflections on Language[M].New York:Pantheon,1975:4.
[2]Chomsky,N.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M].New York:North Holland,1977:80-82.
[3] Chomsky,N.Rules and Representation[M].Oxford:Blackwell,1980:191.
[4]Chomsky,N.The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M].Cambridge:CUP,2000.
[5]Chomsky,N.On Nature and Language[M].Cambridge:CUP,2002.
[6]Fitch,W.T.,Hauser,M.D.& N.Chomsky,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Faculty:Clarif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J].Cognition,2005(97):179-210.
[7]Hauser,M.D.,Chomsky,N.& W.T.Fitch,The Faculty of Language:What is It,who has It,and How does It Evolve?[J].Science,2002,(298):1569-1579.
[8] Pinker,S.& R.Jackendoff.The Faculty of Language:What’s Special about It?[J].Cognition,2005(95):211-225.
[9] Searle,J.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London:CUP,1983.
[10]Searle,J.Minds,Brains and Science[M].Cambridge:HUP,1984.
[11]Searle,J.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M].Cambridge:MIT Press,1992.
[12]Smith,N.Chomsky:Ideas and Ideals(2nded.)[M].London:CUP,2004.
[13]蔡曙山.沒有喬姆斯基,世界會怎樣[J].社會科學論壇,2006(6):5-15.
[14]顧曰國.John Searle的言語行為理論與心智科學[J].國外語言學,1994a(2):1-8.
[15]顧曰國.John Searle的言語行為理論:評判與借鑒[J].國外語言學,1994b(3):10-16.
[16]吳剛.生成語法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17]徐烈炯.中國語言學在十字路口[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218.
[18]約翰·塞爾.心靈、語言和社會[M].李步樓,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19]張紹杰.表述和意義:言語行為研究(導讀)[C]//J.Searle.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