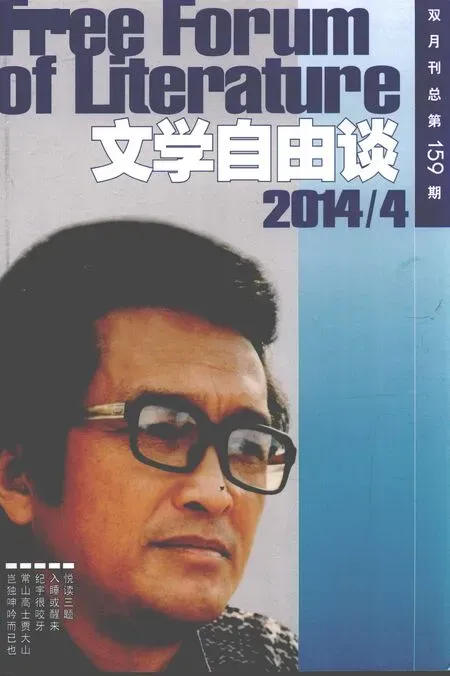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文/陳歆耕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文/陳歆耕
2014年6月2日,是《文學報·新批評》創刊三周年紀念日。而這一天,恰好是偉大詩人屈原的紀念日端午節。這樣一個看似偶然的巧合,似乎寓意著一種來自幾千年前歷史深處的呼喚——這呼喚聲中有傷時感世憂國憂民的胸襟,有讓天下遍植香草的情懷,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著……
此刻,我久久地凝視著新一期《新批評》的版面。從第一期到最新一期,內容期期更新,但每期封面下方的一排中外批評大家的如雕塑般的頭像始終未變:劉勰、魯迅、茅盾、別林斯基……但沒有屈原,因為屈原是偉大的詩人,不是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這不要緊,不影響我們在繼續前行的旅程中,向這位偉大的詩人致敬!
因為,偉大的詩人和偉大的批評家,他們無論曾是盟友還是“敵人”,都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者!
立場與平臺
當有些人看到《新批評》“光鮮”的一面時,又有幾人了解它曾經歷的艱辛?三年風雨路,足足可以寫成一部書。
我曾對參與《新批評》編審的韓石山先生半開玩笑地說過一句話:“等我離開現職崗位了,準備寫一部叫《“新批評”備忘錄》的書。”說是這么說,這部書我會不會去寫,我也不知道。因為要全面真實地呈現《新批評》走過的旅程,必然要涉及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現象。從“向善”的角度考量,有些“真話”是不能全講的。我非常理解季羨林先生那句名言“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的難言之隱。
在這里,我只能有限度地介紹一些情況,談一點純屬個人的感受和思考。
眾所周知,2013年初曾有人通過微博,用非常尖刻的詞語質疑批評家李建軍的一篇文章。
有媒體采訪我,問我對李建軍文章的看法。我回答:“《新批評》的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那是批評家在細讀文本后自己做出的藝術判斷。”最初刊發報道的《新京報》算較準確地傳遞了我的觀點,標題是《“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但很多媒體在轉述這篇報道時,略去了標題中的“文章”二字,把我要表達的觀點就完全弄擰了。說《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肯定沒有什么不當。因為《新批評》上刊發的文章各種聲音都有,對某一部作品,評論者持有完全對立的意見也是常態,那么《文學報》該站在誰的立場上呢?或誰有資格對不同意見的評論做一錘定音的裁判呢?
因此我認為,《新批評》只是提供了一個“百家爭鳴”的平臺,只要在文學藝術的框架內,各路“神仙”都可以登臺發表一己之見,公公婆婆各說各話也無妨。一己之見,很難說都是真知灼見。但如果說“《新批評》不代表文學報立場”是有問題的,《新批評》當然有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最初在征稿啟事中反復申明的“三提倡三反對”:“倡導真實、真誠和自由、銳利的誠意批評,反對謾罵式的人身攻擊;倡導‘靶標’精準、精到的及物批評,反對不及物的泛泛而論;倡導輕松、幽默、透徹的個性批評,反對故作高深、艱澀難懂的‘學院體’。”后來,編輯部又將之概括為六個字:“真誠、善意、銳利。”漢字就是如此精妙,略去兩個字,就會產生嚴重的誤讀。
《文學報》為何要創辦《新批評》,又為何要持有這樣的辦刊宗旨和立場?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是三言兩語能夠道清的。在它誕生之前,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在批評文藝評論生態出現的嚴重“污染”和惡化。但如何改變惡化的文藝評論生態,也幾乎沒有人拿出可踐行的方案。當有人提出要加強文藝評論時,他自己恐怕也不完全清楚,需要加強什么樣的文藝批評。從數量看,全國有為數眾多的文藝理論評論刊物,報紙也在刊登各類文藝評論的文章和類似文藝評論的文化報道。但人們又感到真正的文藝評論非常稀缺,文藝評論到底在哪里出現了問題?單從數量看,中國并不缺少文藝評論,缺少的是真正敢講真話的純粹的文藝批評。
編輯部曾就《新批評》的辦刊宗旨和定位,分別在上海、南京、北京召開專家座談會,問計于一些專業人士。實際上也就是尋找《新批評》的“靶標”在哪里?如要匡正文藝批評的時弊,當然首先要弄清楚文藝批評的“病灶”在哪里?經過考察和梳理,我們覺得“癥結”有三:一是“胡吹亂捧”。受人情面子、“紅包”等因素影響,只說好話,不說問題,甚至把“丑小鴨”吹成“白天鵝”,“和事佬”的身影頻頻出現在各類作品研討會上;二是抽象否定、具體肯定,成為很多批評家的批評策略。他們在談宏觀文學現狀時,對普遍存在的問題義憤填膺,而一談到某人某部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則完全轉換成另一套話語,幾乎全是肉麻的溢美之詞;三是大量毫無章法,只從個人好惡出發、缺少專業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評論”充斥網絡。正因如此,文藝批評已經毫無公信力可言。聽起來“眾聲喧嘩”,但滿耳皆“垃圾噪音”。
說了這些,質疑《新批評》的先生該明白了吧?所謂“三提倡、三反對”,所謂“真誠、善意、銳利”,都不是一拍腦袋就“靈光乍現”出來的。
痙攣與陣痛
雖然《新批評》創刊初期就有明確的定位和宗旨,但在具體的辦刊實踐中仍然不斷經歷痙攣和陣痛。這樣一種“陣痛”,至今仍在延續……
一切問題都可落實到一個實在而具體的問題上來——即符合《新批評》定位的稿件從何而來?在普遍害怕得罪人的情境下,有哪些批評家能夠成為《新批評》的作者隊伍?
當時,我們就想,目前活躍在文學界的大多批評家,大概很難成為我們的主要作者,因為他們中很多人都跟作家 “稱兄道弟”,“廝混”得很熟,怎么可能抹開面子“開火”呢?在南京、北京,編輯部邀請一些高校的教授和博士生研究生幫助策劃選題,我們寄望于那些對文壇還很陌生的年輕人能夠沖鋒陷陣,打破沉悶的僵局。這一想法,果然是有效的。《新批評》第一期三篇批評賈平凹《古爐》的文章,有兩篇出自在讀博士研究生之手。不斷地發現和挖掘新人,則是編輯部所有人都有的強烈意識。后來獲《新批評》優秀評論新人獎的唐小林,是從四川到深圳打工的農民,但長期愛好文學寫作。編輯從郵箱自發來稿中發現了這個作者,于是主動聯系他,請他改稿。后來唐小林頻頻在《新批評》亮相,成為文學界有影響的“打工評論家”。編輯部幾乎每天都在用雷達掃描儀,搜尋各類媒體上適合給《新批評》撰稿的作者,一旦發現,立即“收編”。文壇圈內人經常納悶,看到《新批評》上一篇妙文,但對作者名字卻很陌生,于是好奇者便向編輯部打聽,某文作者是“何方神圣”?
“陣痛”還表現在編輯部高水準文藝評論人才的稀缺。一個專業的有共同理念的優秀編輯團隊,是創辦好一份專刊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文學報》的采編隊伍非常優秀,他們都是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但為了節約人力成本,編輯部人手少而工作量大,為了保證每期16版正刊正常出報就已經疲累不堪,如再增加隔周8個版的《新批評》,顯然具有難以承受之重。
吸納外才,則是當時不得不采取的唯一之道。最初,我曾經動員剛退休的《文匯報》筆會主編、評論家劉緒源先生來加盟我們的團隊。但緒源先生正忙于與李澤厚搞對話,平日學術活動又很多,無暇來參與這類為他人作嫁衣的編務。至于儒雅敦厚的緒源先生,是否有擔心得罪人的忌憚,就不得而知了。但緒源先生的一大功勞是向我推薦了同樣也已退休的“山西刀客”、評論家韓石山先生。韓先生開始是一口回絕的,因他以為要承擔選題策劃和組稿的任務,覺得工作量太大太辛苦,難以承受;后來我說,主要是請他對稿件進行專業上的審讀把關,他這才應允。
韓先生的加盟,對《新批評》保持較高的專業水準,以及盡量避免犯一些低級差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此前,我與韓先生只有一面之交,但我們與韓先生的合作非常愉快,他深厚的學養和過人的識見,每每使我獲益匪淺。有些重要稿件,常常是我先發給他看,聽了他的意見后我們再進入編輯流程。令我尤為感佩的是,韓先生的嚴謹和敬業精神。他在2012年8月,因突發心臟病兩次住院,在病中還在堅持給我們審稿。無論病前還是病后,他除了用電子郵件回復意見,有時還用精致的毛筆小楷把審稿意見寫成書面信函寄來。除了韓先生,后又有余之先生、編輯部內部人員等陸續加盟,才形成了現在的編輯陣容。
編輯部人員對批評理念的不同認知以及帶來的碰撞,也曾是纏繞我們前行的“陣痛”因素。諸如有人擔心,批評了那些“名家”,會不會影響報社未來的發展?(擔心不無道理,但事實證明,報社發展不但不受影響,而且進入了更良性的發展軌道。)有人認為批評(指出問題)是“破壞”,我們還是多做點建設性的工作?(一位理論期刊主編也曾當我面談類似觀點,我立即回應:批評即建設。我們指出一部作品文本存在的問題,是為了引起寫作者的注意和改進,這是“破壞”還是建設?)而外界的各種議論和被批評者的情緒反彈,也難免要牽制辦刊人員的心態。面對這一切,如何保持清醒自覺的追求和定力,時時在檢驗我這個當主編的基本判斷力。因批評一位名家而激起強烈反彈,有人背后譏刺我為“瘋子”。我將此在電話中告知《文學自由談》主編任芙康,他哈哈一笑:“恭喜你!我干這活兒幾十年,才被人稱為‘傻子’,你剛干幾年卻已經晉級到‘瘋子’了!”
這個世界大概也不能全部由“聰明人”組成,也需要幾個“傻子”和“瘋子”,這個世界才完整。
老鳳與新雛
辦刊三年,要說個人有什么最直接的感受和收獲?那么,最主要的,我感覺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導師的門下,完成了學位的提升。因為三年中,專刊所有文章我都認真仔細閱讀過,由于職業性需要,有的文章而且不止讀一遍。這些文章均出自當下中國最前沿銳利的優秀批評家之手,他們中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學養深厚文字老辣的學人,有的是80后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他們刊登在專刊上的文章,盡管風格各異,但有一點肯定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的文章,多是掙脫了人情的商業的羈絆,在仔細閱讀文本后作出的自己的獨立評判,是尊崇自己藝術感覺,從內心發出的鏗鏘有力的批評之聲。
陳沖的幽默俏皮、李建軍的縝密深刻、王彬彬的犀利嚴謹、郜元寶的綿里藏針、肖鷹的迅捷奮勇、吳亮的騰挪跳躍、韓石山的刻骨辛辣……都已經成為《新批評》靚麗的風景,拜讀他們的文章,如同在影院接連看好萊塢大片,欲罷不能。當職業性閱讀,變成快樂之旅時,就成了一種享受。
他們是“真的猛士”,是“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我是他們忠實的讀者和“粉絲”。
河北老作家陳沖先生,可以視作批評界的老馬和黑馬,“正統”的學院派評論人士,一般不太接納他的批評風格。用他的評論方式寫博士論文,十有八九是難以通過評審關的。有人說他的文字太繞,但這個曾受過高等數學專業訓練的作家兼批評家,如果他在表述時出現了“繞”,一定有它“繞”的理由,在他“繞”的背面是有嚴格的邏輯鏈條支撐的。還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嚴肅的話題,到了他的筆下,他都能輕松地讓你饒有興味地讀下去。本刊在出刊兩期后,曾在北京開了一個征求意見座談會。他在電話中,對我們那個座談會很不以為然,潛臺詞是你們自己大概沒有弄明白怎么辦《新批評》吧?我就說:“《新批評》該怎么辦?請你發表高論。”時隔不久,他發來兩萬字的長文《我想要的“新批評”》,從批評的本質談到當下批評的沉疴,然后又以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為例,說明什么樣的批評才是好的批評。文章雖長,卻輕松好讀,因此一次性占了《新批評》四個整版。在第三屆《新批評》頒獎臺上,陳沖先生又以妙文《你從“這邊”看到了什么“風景”》第二次折桂。
李建軍是唯一連續三屆獲得 《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的批評家,獲獎作品分別是《〈蛙〉寫的什么?寫得如何?》、《猶如淚珠射來顫抖的光芒》、《為顧彬先生辯誣》。《新批評》評獎有一個基本規則,對待處在同等水平線的好文章,優先考慮未獲獎者,優先考慮年輕作者,以讓更多的人獲得激勵。但《新批評》愿意重復獎勵某位批評家,一定是評論本身成了該年度無法繞過去的重頭文章。我注意到,李建軍的批評文章在《新批評》刊發后,迄今尚未有人正面作出過有力的回應和反駁。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學理性的推論和判斷,讓每一個字都砸在實處,如同板上釘釘,要撼動它不是那么容易。
王彬彬的批評文章給人感覺數量不多,但他只要有文章出手,肯定是重量級的,每每總是成為學界熱議關注的話題。與大多數學院派的評論不同,他的文章不僅犀利深刻、學識廣博,而且清晰有力。
郜元寶先生性情溫和,他的文風也頗有謙謙君子之風。但讀他的批評文章在如沐春風的同時,也可感覺到他的識見如同老中醫的那根針,緩緩地扎入肌膚,在你尚未感覺疼痛時,針尖已經抵達穴位的最要害處。那篇曾獲《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的《中國作家才能的濫用和誤用》,對作家才能本質的評說分析實在精妙,令人拍案。
肖膺先生是寫文化批評的快槍手。每有文化熱點出現,他的文章幾乎同步到達編輯部。他依托深厚的專業學養寫時評,因此面對同一話題,他總比大多作者高出一籌。由于快,他的文章從發到編輯部到正式刊出,總是在不停地修訂和補充之中。只有編輯才知,從最初的稿件到最后的定稿,肖先生經過了多少次打磨。
獲益——不僅僅來自于拜讀他們的妙文高論,還有通過各種渠道、方式的信息交流……
求真與向善
當一種辦刊理念付諸實踐時,常常因我們的專業水準不夠,理念與實際操作會發生“摩擦”,使得實際效果偏離理念的軌道,是經常發生的現象。比如專刊倡導的“真誠、善意、銳利”的辦刊理念,但落實到某篇文章中,如何具體地體現出來?編輯部常常為此困惑和苦惱。所謂“好處說好、差處說差”的公允、客觀的批評,具體到某篇文章中,好差應該各占多少比重?誰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可以用來衡估所有文章的尺度?“銳利”地指出問題的批評,常常被人誤解為是不懷好意的,更遑論被理解為“善意”。
在專刊三年刊發的文章中,除了個別署筆名的文章,不排除有隱藏在背后的難以言說的個人動機,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并無哪位批評者因個人間有私仇而泄恨,故意與被批評者為“敵”。他們的文章是真誠的,他們的出發點也是善意的。我理解,指出問題的批評,是從更高層面釋放“善意”,所謂“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韓小蕙女士在《新批評》兩周年的研討會上說過一句話,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在生活中,批評往往只有在親人間才會發生。因而批評其實也是明亮的陽光。”而那種出于各種個人目的而發出的諛詞,聽起來順耳舒暢,其實卻是一種 “偽善”。
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情世故的因子,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多是說好話、泛泛而論的歷史。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全面梳理中國文學審美基本原理的理論經典著作,但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批評著作。金圣嘆是一位直接面對文本的天才的批評大家,但他也是以正面肯定為主的,至于腰斬《水滸》,也不涉及人情世故問題。施耐庵不會從棺材里爬出來,與他對“罵”,或打一場筆墨官司。到了現代魯迅、李長之這里,批評的“火藥味”才開始濃起來。但他們的這種批評精神幾乎難以為續。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一直未能形成,“捧殺”與“棒殺”幾成常態。因此,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學繼“五四”新文化運動后,需要繼續啟蒙,而中國的文藝批評更需要啟蒙。回到常識,回到文學本身,回到真正的文藝批評,需要文學界、知識界同心協力。《新批評》在這方面,只是做了一點嘗試。建立一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來澆水培土。
毋庸諱言,《新批評》確實是批評了一大批當代文學名家,這是因為名家、大家的作品具有示范、引領的作用,他們的優點會被放大,他們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也更易被效仿,當然也就更具有批評的價值和意義。在《新批評》創刊初期,南京大學一位教授問我:“你們在上海,敢發批評王安憶作品的文章嗎?”他大概沒有想到,他的話音剛落,《新批評》第三期就刊發了兩篇談王安憶新作《天香》得失的文章。且不論文章所論是否精當,見仁見智,都很正常。我們也根本不會預設立場,引導批評家故意挑某位作家作品的刺。我們從來都充分尊重批評家自己的獨立判斷。其實,批評王安憶的作品,還有另一層意義在,《文學報》并不因為在上海出版,就對上海的作家尤其是名家網開一面。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只要公開出版發行,就得接受專業的和非專業的各類讀者的評說和檢驗。沒有什么藝術的創造者,可以在這方面享受“豁免權”。如果有一天,《新批評》刊發了批評鐵凝主席創作的新作,那也是一個正常的批評行為。沒有真正的批評,要催化文藝創作的繁榮該從何談起?批評從來就如陽光、空氣和水,伴隨著整個藝術創造的過程。
可以不夸張地說,在建立一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方面,《新批評》的點點滴滴努力,已經產生一定的效應。
鮮花與板磚
風雨和陽光,鮮花與板磚,始終伴隨著我們前進的腳步。
我想,這完全是一個正常的現象。《新批評》本來就是逆水行舟,與惡化的文藝批評生態為“敵”的。如果它受到所有人眾口一詞的贊譽,反倒是有悖常理的。我們不能寄希望于“羊”給“狼”唱贊歌。如果我這里詳細記錄《新批評》受到的關注和褒獎,要用很長的篇幅。也有“自我表揚”之嫌,就如同在自傳中大談自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會令人生厭。關心《新批評》的讀者和專業人士,不難從各類媒體上搜索到對《新批評》評價,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斷。這里,我只想說說我親歷的兩件小事:一是2013年底,我在北京現代文學館參加一個研討會,會間,坐在我身邊的白燁先生告訴我,魯迅文學院執行副院長白描跟他要了我的電話,說是要跟我聯系,他說他有篇文章大概也只有《文學報·新批評》能發得出,想把文章發我。聽了這話,我心中是怦然一動的。一份媒體能夠得到作者如此信任,作為媒體人還有什么獎賞比這更珍貴?雖然白描先生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貫耳,但此前我們卻從未謀面,也沒有相互的聯系方式。隔了兩天,白描先生把他的那篇擲地有聲的文章發給了我,不久該文刊于《新批評》頭條,題為《要有肚量聽真話——我看文學陜軍再出發》。這篇文章全票通過,獲得第三屆“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第二件事是,2013年夏我到西安,聽陳忠實先生親口對我說,他唯一一份自費訂閱的報紙就是《文學報》,而訂《文學報》就是因為喜歡看《新批評》上的那些文章。而這一細節,在第三屆《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獲得者李建軍的“獲獎感言”中,再次得到證實。說明陳忠實先生不止對一個人說起過他對《新批評》的喜愛……
《新批評》在風雨兼程中已經成長為一棵樹,雖然它還不怎么粗壯,它的年輪才剛剛三圈,但從它的生命力看,相信它還將繼續生長。在籌備它三周年的紀念活動時,我想起蘇東坡詞《定風波》中的兩句,錄此與《文學報》編輯部同仁共勉:“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在這里,我要衷心感恩、感謝一切給予它呵護、包容、扶助的各方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