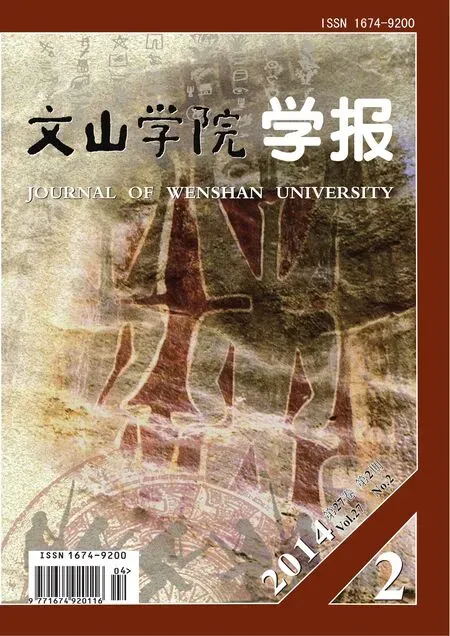淺談富寧土戲丑角形象的藝術特征
農尚春
( 文山州壯劇團,云南 富寧 663400 )
云南壯劇屬于多聲腔少數民族劇種,有富寧土戲、廣南沙戲、文山樂西土戲等三個分支。由于三個分支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以及受外地劇種影響的程度不一而導致了作為少數民族劇種的藝術要素形成了既有共性也存在明顯差異的藝術形態。就拿角色行當來說,據《云南壯劇史》載:“云南壯劇的行當里面,既有富寧土戲、廣南東路沙戲比較細致的劃分,也有廣南北路沙戲、文山樂西土戲比較簡略的劃分”[1]441;“富寧土戲和廣南東路沙戲的行當分為生、旦、凈、丑四類” ;“丑行有老丑、小丑、白鼻丑”[2]245-247。
富寧土戲在其漫長的孕育、形成、傳承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具有鮮明壯族特點的少數民族戲曲劇種。在富寧土戲的生、旦、凈、丑角色行當中,同樣也閃耀著少數民族戲曲的鮮明色彩,其中丑角形象最具特點。
一、用三種語言插科打諢,盡顯云南壯劇特點
富寧與廣西的百色、那坡、西林、田林緊緊相連,南宋后就是云南通往廣西和內地的交通要道。頻繁的經濟往來促進了民族文化藝術的不斷交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藝術形態、多元的文化在此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和融合。廣戲和彩調戲在富寧壯族地區的演出中也深刻地影響著富寧土戲,因此,演廣戲和彩調戲也把廣話和漢話傳到富寧壯族地區;富寧土戲藝人也把自己喜歡的廣戲和彩調戲表演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壯劇藝術中。同時,在觀看演出的觀眾中既有壯族,又有漢族和其他民族,為了滿足不同民族觀眾的要求,讓不同民族的觀眾都能喜歡看、看得懂,這就要求戲班的演員們在演出中既說壯話,也說漢話,還要說廣話。因此,在土戲班演出的同一劇目中同時使用壯話、漢話、廣話就是自然的了,這就形成了富寧土戲的語言程式。富寧土戲在演出中的漢話(云南壯劇中也稱為“官話”)主要用在演員的定場詩、道白和七字句、十字句唱詞的演唱上;壯話主要用在道白和五字句唱詞的演唱上;廣話則主要用在小丑道白、數板時的插科打諢、逗趣取樂上,以活躍舞臺氣氛和渲染小丑形象,使小丑形象的民族藝術特征更加鮮明和突出。[3]
分布在富寧縣剝隘鎮、那能鄉、者桑鄉和谷拉鄉的〔依嗬嗨〕戲班、〔哎依呀〕戲班、〔乖嗨咧〕戲班在演出同一劇目時同時使用漢話、壯話、廣話來塑造人物形象,這種表現形式在這些地區的土戲演出中屢見不鮮,如1985年6月30日富寧縣標村〔依嗬嗨〕土戲班演出的《賣花嫁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賣花嫁女》是〔依嗬嗨〕土戲班常演不衰的代表性劇目,劇中的何老三是個丑角。故事說的是何老三爹娘早亡,以賣花和賣蘇杭雜貨為生。一天他挑著貨擔上街賣花,正值李門王氏要嫁女,即將出嫁的女兒秀英見何老三到門前賣貨賣花,雙方講價還價,互相逗趣,何老三見秀英貌美活潑,有意對秀英表示慷慨大方,要秀英猜物,猜對一樣送一樣,結果秀英全部猜對了,何老三無奈只好把所有的貨物和花都送給秀英。事后被秀英媽發現,認為何老三上門調情,便痛打何老三一頓,何老三被痛打一頓而逃走,鬧得錢物兩空。劇中秀英和媽媽的對白用壯話,何老三唱【浪里白一】時,前后唱段用漢話唱“出(呀那個)得(吔)門(那個)來,往前走(羅羅羅不嚕那斯嗬了嗨呀嗬嗨依熱喲斯那斯嗬了嗨熱)”,緊接數板:(漢話)莫打就莫打鑼,我在臺上把話說,(廣話)前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漢話)今年古怪也不為多,我在臺上又把話說,(廣話)牛上樹馬生角,耗鼠踩斷牛欄桿,燈草打爛熬酒鍋,(漢話)今年古怪也不為多,我在臺上又把話說,(廣話)落雨紛紛火燒嶺,風吹石頭滾上坡。(漢話)今年古怪也不為多,我在臺上又把話說,(廣話)男人找老公,女人找老婆,找個老婆三十多,生個兒子七十多,各位朋友你不相信,你看他的胡須就滿耳朵(接唱收板,漢話)你看他的胡須滿(呀)滿耳朵(吔那斯嗬了嗨)你看他的胡須滿(呀)滿耳朵(吔那斯嗬了嗨呀嗬嗨嗬嗨依熱喲斯那斯嗬了嗨熱)[4]202。快板多為借古諷今或顛倒事物等幽默風趣的詞句,引得觀眾捧腹大笑。短短的前后唱段和中間插入的快板就用漢話和廣話交替演唱,渲染了何老三快活風趣、詼諧幽默的丑角形象,受到觀眾的歡迎,劇場效果十分熱鬧。再如那能鄉那勒(依嗬嗨戲班)演出的《打漁家》中,勤吃、懶做兩個丑角的對白也是用壯話、漢話和廣話互相交替一問一答,幽默風趣,成功地塑造了富寧土戲的丑角形象,突出了富寧土戲丑角鮮明的民族劇種特征。
二、獨特有趣的唱腔突出云南壯劇的風格
富寧土戲丑角的唱腔是獨特的,主要表現在唱腔的旋律和唱腔的襯詞上。
丑角唱腔的旋律與丑角的性格特征和人物情緒是緊密聯系的。富寧土戲的丑角在劇中起到活躍舞臺氣氛、吸引觀眾觀看、調節舞臺節奏的作用,因此丑角的性格是活潑開朗、詼諧幽默的,除了插科打諢等語言表演形態以外,其唱腔也迎合了丑角的性格特征,其旋律變化不多,起伏不大,似說似唱,字多腔少,一字一音,如《賣花嫁女》中何老三的唱段,《打漁家》中勤吃、懶做的唱段,《花園結義》中冬瓜三的唱段以及專業劇團演出的《憨憨戲主》中憨憨的唱段,《換酒牛》中阿壽的唱段和《彩虹》中大管家的唱段都突出了丑角形象的性格特征。除此而外,丑角唱段中運用的大量襯詞也很好地塑造了富寧土戲的丑角形象。仍以《賣花嫁女》中丑角何老三的唱段為例。何老三唱【浪里白一】時,唱腔前段“出(呀那個)得(吔)門(那個)來,往前走(羅羅羅不嚕那斯嗬了嗨呀嗬嗨依熱喲斯那斯嗬了嗨熱”和唱腔后段“你看他的胡須滿(呀)滿耳朵(吔那斯嗬了嗨)你看他的胡須滿(呀)滿耳朵(吔那斯嗬了嗨呀嗬嗨嗬嗨依熱喲斯那斯嗬了嗨熱”,前后唱段中很少的正詞卻添加了字間填充性襯詞和襯段型收腔性襯詞等大量的襯詞,配上夸張的動作和滑稽的表演,使得富寧土戲丑角的藝術特征和少數民族戲曲的藝術個性更加鮮明。
三、勾勒出壯劇丑角的審美取向
中國戲曲的臉譜有一定的規律和方法,而不是隨意涂抹而成的。講究章法而有規律地將點、線、色、形組成裝飾性的圖案造型,產生了戲曲臉譜的各種各樣的格式與規則,形成了一定的程式。丑角臉譜的特點是人物臉面中心一塊白,形狀有豆腐塊、桃形、棗花型、腰子型和菊花型等,而富寧土戲丑角的化妝臉譜則顯得隨意和樸實。一般的畫法,兩道眉毛尾向下彎垂,眼睛畫成斜眼或三角眼,歪嘴,嘴角一邊高一邊低,在左臉腮或右臉腮上點一顆黑痣或畫上一撮毛。而臉面中心的一塊白則不會有意地畫成豆腐塊或其他形狀,只是很隨意地將白粉撲上以形成與生、旦化妝的區別。看似隨意樸實的丑角臉譜,經過演員唱、念、做、打的滑稽幽默的表演,折射出壯族人民對土戲角色形象美丑善惡的審美取向。
四、簡約樸素的服飾和道具蘊含富寧土戲的少數民族劇種特征
中國戲曲服飾名目繁多,由于色彩、紋樣和質料的不同以及穿戴時的不同搭配而使不同角色行當的服飾變化多端、豐富多彩,富有藝術表現力[5]496。少數民族劇種的服飾除了與其他劇種服飾具有共性特征和一定的程式外,還顯示出少數民族劇種服飾的艷麗色彩和個性特點。據《云南壯劇史》載:“早期的富寧土戲和廣南沙戲演出,不專門縫制衣服,演員穿戴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服飾就演出了。僅只是手里拿著扇子、兵器等類道具,腰上系一條紅布帶,以示區別”[1]476。富寧土戲發展到逐漸趨于成熟的時段,演出服飾已有很大變化,或用自織的土白布縫制,或購買現成的各種服飾,顯得更加豐富多樣、富麗堂皇。即便如此,丑角的服飾卻仍然保留著土戲初始階段的特點:頭包壯族頭帕,身穿壯族藍色或黑色的生活便裝,腰間系一條紅色布帶,腳穿壯族青年喜愛的千層毛邊底布鞋,沒有鮮艷的色彩,也沒有那些眼花繚亂的繽紛飾品裝飾,手拿折扇或棕葉扇就上場表演了。與其他成熟劇種丑角服飾相比較就顯得更加簡約和樸素,乍一看顯得有點寒酸和粗糙。但這種簡約樸素的丑角服飾卻突出了富寧土戲的原生性、草根性和人民性,蘊含了云南壯劇的少數民族劇種特征。丑角的道具也只是普通的扇子、手巾、一枝樹葉或肩挎繡花掛包,顯得特別簡約和樸素。
五、幽默夸張的滑稽表演渲染富寧土戲的丑角形象
成熟的戲曲劇種,不同角色行當有比較嚴謹的表演程式,“相對地說,丑的表演程式不像其他行當那樣嚴謹,但有自己的風格和規范,如屈膝、蹲襠、踮腳、聳肩等都是丑的基本動作”[5]40。相比之下,富寧土戲丑角的表演雖然也有屈膝、蹲襠、踮腳、聳肩等基本動作,但沒有形成比較嚴謹的表演程式而比較靈活自由。《云南壯劇史》曾對富寧土戲丑角的表演有如下描述:“老丑如《大鬧三門街》中的萬事通,《文武妹賣馬蹄》中的周大喜等,出場多走矮步,定場時左手掌橫于胸前,右手藏扇于身后,到臺口撤扇亮相,退兩步轉身入座,雙手從下面畫圈,以示輕狂。小丑如《賣花嫁女》中的何老三,《二下南唐》中的馬牌等,出場時夾著雙脖走小八字步,邊搖扇邊全身左右搖晃;亮相時右腳尖點地成虛步,右手食指直指臉上黑痣,以示其丑相。白鼻丑如《九連杯》中的王二,《張古董借妻》中的張古董等,鼻梁上畫白烏龜,眉毛下彎的臉譜,做戲時常用扇子遮臉,或扇子在臉上時起時落,逗人發笑”[1]452。
在民間土戲班的演出中,還有一些丑角的表演也十分幽默和夸張,如那能鄉那勒〔依嗬嗨〕土戲班在2007年4月13日演出的《打漁家》中的勤吃、懶做兩個小丑,表演時一人拿竹制篾帽,一人拿毛巾,兩人在對白和對唱中,運用彎腰、屈膝、扭脖子、聳肩、擠眉弄眼,咧嘴吐舌等夸張的動作來表演。幽默的廣話、漢話對白和對唱時詼諧的襯段型收腔性襯詞加上這些夸張的形體動作引得臺下觀眾捧腹大笑。
在專業劇團的演出中,表現不同人物形象的丑角表演也十分夸張。文山州壯劇團根據壯族民間故事“卜荷的故事”(漢意:窮苦人的故事)改編了一批壯劇。卜荷的故事就像維吾爾族的阿凡提故事一樣,幽默、機智、聰明、勇敢地與土司和財主老爺斗智斗勇,挖苦和諷刺了土司老爺,大長貧苦人的志氣。這些小丑是勞苦大眾代言人的正面人物形象,這類小丑給壯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文山州壯劇團在20世紀60年代演出的小壯劇《換酒牛》中的阿壽,他機智、勇敢、幽默、風趣地與土財主斗智斗勇,用一頭跛腳牛換來財主的大牯牛。劇中阿壽的表演也十分夸張,引得觀眾陣陣掌聲。同樣是根據卜荷的故事改編的《野鴨湖》中的卜荷、本世紀初演出的《憨憨戲主》的憨憨等等,這些小丑夸張的表演輕松活潑、風趣幽默,讓觀眾在捧腹大笑中得到精神愉悅的同時,受到鼓舞和啟發,令人深思。
文山州壯劇團演出的劇目中還有一類表現靈魂丑惡、欺壓人民、道德敗壞的反面人物的小丑。例如20世紀60年代演出的《螺螄姑娘》中的布斗和1989年創作演出的五場壯劇《彩虹》中的大管家就是這類小丑的典型代表。
《彩虹》是根據流傳在壯族地區的敘事長詩《幽騷》改編而成,講述一對壯族青年為反抗土司的壓迫逃到遠方成為夫妻,因思念母親返鄉后又慘遭土司迫害,受盡酷刑、寧死不屈,被土司焚為灰燼,最后在狂風暴雨中化為彩虹,成為理想與吉祥象征的故事。劇中主人公朵比年輕貌美、堅韌剛強,與同伴沐郎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在一次壯鄉隆重的傳統節日瓏端街上被荒淫無恥、風流成性的土司看中并被土司用號字黑綢號下,要強娶朵比為妻。土司的大管家仗勢欺人、狐假虎威,在土司面前阿諛奉承、點頭哈腰,一副十足的奴才相,而對善良美麗的朵比和壯鄉人民則手段殘忍、無惡不作。《彩虹》中,土司和朵比是男女主角,大管家是配角,但要演好大管家確實不易,既要體現他卑躬屈膝的奴才形象,又不能喧賓奪主。在表演中,除了展示“屈膝、蹲襠、踮腳、聳肩”等基本動作的共性特征以外,還要表現壯族的舞蹈風格。如在第三場“娶親”中,朵比因被土司號中,七天后就要被娶到土司府當土司娘娘了。第七天,大管家率領一群家丁和侍女帶上豐厚的彩禮到朵比家迎娶朵比,此時有一段“娶親”的舞蹈,由大管家領舞,眾家丁和侍女群舞。舞蹈充分表現了丑角的舞蹈特點,既有“屈膝、蹲襠、踮腳、聳肩”的丑角基本動作,還有大管家和眾家丁左右腳隨音樂節奏向左、右側伸縮;大管家手拿扇子邊唱邊模仿烏龜伸縮脖子;模仿青蛙前撲后仰,配合著扇子上下升降左右移動而遮臉伸頭、擠眉弄眼、手捻左腮一撮毛等等夸張滑稽的舞蹈動作,渲染了身為大管家的丑角形象,反襯了土司和大管家的荒淫無恥、橫行霸道的丑惡靈魂。
富寧土戲的丑角形象也正因為具有三種語言插科打諢、獨特有趣的唱腔、樸實隨意的化妝臉譜、簡約樸素的服飾和道具、幽默夸張的滑稽表演等藝術特征而更加具有少數民族劇種特色,使舞臺上的丑角形象更加獨特鮮活,獨樹一幟,受到壯族人民的喜愛和稱贊。
[1]黎方,何樸清.云南壯劇史[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2]何樸清.云南壯劇志[G].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5.
[3]許六軍.富寧土戲〔依嗬嗨〕腔調的曲調類型及其程式——云南壯劇音樂初探之十二[J].文山學院學報,2013(1):7-9.
[4]梁宇明,許六軍.富寧壯劇音樂[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
[5]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戲曲 曲藝》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 曲藝[Z].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