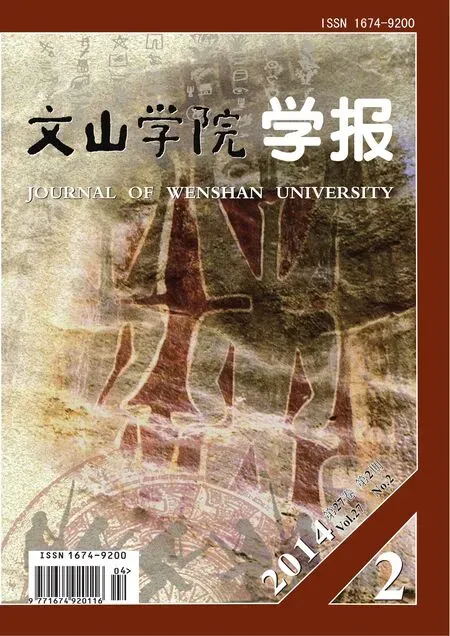論教育理性的消解及其功能的變異
王光斌
(文山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文山 663000)
人具有獸性、人性、神性,這三個層面決定了人是最復雜的生命體。獸性即人的動物性本能,是人源自動物界而與生俱來的屬性;人性即通過后天教育而養成的人文屬性,是它使人脫離動物而成為人;神性是在人性基礎上升華而成的最為高貴的特性,人的偉大或神圣皆緣于這一精神品質。“人與一般動物的區別在于人是精神性存在,有意識和自我意識。失去這種精神性,失去對自我的認識,也就失去了人的特異性,使人降格而與一般動物無異。”[1]人的成長過程就是控制獸性,保持人性,追求神性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完成程度決定了人的高貴程度。而這一切主要是通過教育來實現的。因為是教育使人獲得理性,這一理性的控制功能造就了人的高貴的精神性。教育理性主要包括科學理性、人文理性和審美理性。教育理性一旦被消解,其功能發生變異或者喪失,就預示著人的精神危機的到來,人類就會處于非理性的存在狀態。
一、教育的理性及其功能
人生之旅,永遠在修行的路上。修行的過程就是不斷獲得理性并堅守理性的過程。理性使人具有正確判斷真、善、美的能力,對理性的堅守使人自覺追求真、善、美,進而成為精神性的存在,成為真理性、道德性、詩意性的人。這個至關重要的理性作為一種判斷能力和意志力,它的獲得途徑就是教育,因此可以稱之為教育的理性。教育理性的功能就是控制,它規范人們成長的方向和目標。善惡是人與生俱來的,沒有后天的教育所帶來的理性力量的控制,惡根就會生長壯大,開出“惡之花”。請看生活中嬰幼兒的表現:其母親抱別的小朋友,他會以哭鬧的方式來表示抗議,他天生以為其母親屬于他自己,只能抱他,不能抱別人。有時這個抗議表現得更為極端強烈,他甚至會抓掐對方、毆打對方,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幾個幼兒在一起玩,經常發生矛盾,多半是因為爭搶玩具。而爭搶的原因并非玩具不夠多,而是“先天”認為小伙伴正在玩的玩具是最好的,他也要玩那個玩具。2013年美國的一個電視節目中,就美國如何償還所欠中國的巨額債務時,一個美國孩子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把中國人都殺光”。上述無忌童言和行為如果沒有后天的及時管教(教育),這種天生的自私就會越來越明顯。正如民間諺語所言:“小時偷針,大來偷金”,沒有教育的理性力量的引導和控制,人就會向“惡”的方向發展。常言道“利器在手,惡念自生”,沒有理性的人是很可怕的。德國人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南京大屠殺,是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導致集體喪失理性之后人性之惡帶來的瘋狂。相反,嬰幼兒同樣天生具有善根,如惻隱之心:他會盡心照顧他的小寵物,會搬來小凳子給奶奶坐,會纏著媽媽要錢送給街頭的流浪漢,會為灰姑娘的故事流淚。這些善行得到肯定和鼓勵,自然就會發揚光大。所以教育的功能就是通過教育理性來抑制人的惡根的生長,促進人的善根的壯大,使人成其為人。在教育所培養的理性中,具體有三種理性最為重要:科學理性、人文理性和審美理性。
教育要傳承關于自然的經驗知識(科學),使人認識事物,把握事物發展規律,概言之就是求真,培養人的科學理性。科學理性使人掌握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這個自然當然也包括人自己,“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科學理性是教育實現控制功能的前提之一。人具備科學理性,就能實現人的本質力量,最大限度避免人的生存悲劇。人類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始終伴隨著與大自然的博弈,博弈的基本目標就是生存,高級目標就是發展——確立人的主體性和主宰地位。而人參與博弈的資本就是科學理性。沒有科學理性,人類就喪失了參與萬物競爭并最終勝出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獲得就靠教育:經驗的傳承,技能的獲得,思維的訓練。因此,教育理性必須包含科學理性,無論是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教育邏輯,概莫能外。教育還要傳承關于人自身的經驗知識(人文),使人認識自己,把握人自身的發展規律,說白了就是求善,培養關于人的人文理性。教育傳承人文,培養人的人文素養,健全人性,提升人格,以教化自然人成為社會人,追求人生的價值,盡力避免人的價值悲劇——人可以賦予與人發生關系的一切事物以價值意義——避免人無意義的生死循環,抵制世間“祛魅”給人帶來的虛空感,保持人生存發展和革新創造的原動力。人文精神使人生有了價值意義,否則人生就是虛空的生老病死過程,與動物無異。因此人生是修行,死亡是“畢業典禮”。“畢業評語”是大不相同的: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或偉大,或平庸;或懷念,或遺忘。這些評價是基于精神層面的,是人文的價值判斷。所以人文理性的功能就是規定人向上提升的方向,避免人向下墮落,規定人創造價值,避免虛空。人的欲求就是創造價值,價值就是滿足人的欲求,否則就無價值。當然,欲求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目的就是塑造完整完美的自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人的一切行為的背后,都有利益作為驅動。這是千真萬確的,否則人就失去創造的動力,而利益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所以人文理性要解決的人生問題就是:超越苦難命運,混亂生活,無序人生的虛空的異化生存,建構有價值的充實的常態生活,避免異化生活帶來的負面價值。人類追求美妙而浪漫的愛情,就是對動物物種繁衍行為的超越。人類不再是一男一女隨意在一起的動物,而是要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尋覓自己的另一半。性愛升華為情愛,必然是具有人文理性的人才能做到。教育更要傳承人的審美經驗和知識,培養人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即求美,培養人的審美理性。“人直接需要美,因此審美因素滲透到他的整個生活中,人不僅按照物質必然性,而且也按照美的規律進行創造。”[2]151生活事實正是如此,吃穿住行都遵循美的規律。飲食不僅要求營養搭配科學合理,還要講究色香味俱全;穿衣不只求避寒遮羞,還要色調搭配,款式適合,穿出氣質和美感;住房不只是要求遮風擋雨,還要求舒適有品位;生活運動中不但要求秩序之美,還要追求凌亂中的自由自在。審美活動就是要創造最大限度剔除各種限制的自由舒適的空間(現實的和藝術的),讓人處于自由舒適狀態,形成完美人格。換言之就是超越人的現實生活困境。現實中常見的生活困境就是人的異化:人們的行為,往往偏離事物(包括自己)的本質,走向人的對立面,使人自己成為非我的存在,非常的存在,不獨立不自由的存在,成為非我力量的奴隸。即馬克思說的:人的本質力量成為人的反對力量。[3]22借助網絡語言來表述就如房奴、車奴、手機控、電腦控。所以審美理性的作用就是幫助人擺脫在現實生活中被“控”的不自由狀態,達到詩意的棲居。
總之,教育是有控制功能的,理論上講是教育使人具有理性,通俗來說就是教育使人具有教養和能力。教育的控制功能是通過科學理性、人文理性、審美理性實現的。科學理性的缺失,人就喪失對真理的判斷力,就會在謬誤中受難;人文理性的缺失,人就失去對道義和愛的感受力,只能在仇恨與爭斗中生存;審美理性的缺失,人就沒有了對自由和美的感受力,就做不到詩意的棲居。
二、教育理性的消解
理性的力量很重要,但卻不是萬能的,事實是人的任何一種能力都是有限的。教育作為人類的自覺活動,其理性也同樣如此,并且還會不斷被消解。當人類非理性的力量超過理性的力量時,理性的消解就發生了。法西斯主義就曾經消解了德國人的理性,把最富于理性的日耳曼民族推進戰爭軌道;美國9·11事件就是非理性的恐怖主義的典型事例。教育理性的消解,主要表現為真理性被偽理性替代,價值理性被實用理性所遮蔽。
先說偽理性對真理性的替代。請看下面事例:文藝復興時期,伽利略因害怕挨揍而在與羅馬教廷的斗爭中妥協了,其學生為他沒有成為堅持真理的英雄而指責他,為他惋惜,并感嘆“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但他說:“需要英雄的國家才不幸。”[4]這是一個偽理性試圖取代真理性的故事。顯然,伽利略更具有真理判斷力。因為妥協還是堅持只是一種態度,對真理無損,真理依然存在,不會改變——日心說仍然有其合理性,地球照樣還是圓的,而不會變成方的。其實這是一個關于理性的嚴肅問題:盛產英雄,推崇榜樣的民族是缺失理性的民族,只有愚民才崇尚榜樣和英雄,而這正是專制和暴君產生的土壤。創造英雄和樹立榜樣的行為本身就是愚民政策的體現。因為其邏輯前提是不希望民眾獨立思想,不需要民眾具有判斷力(理性),只要照著榜樣和英雄去做就行了。一個右派的妥協是這樣的:“白紙黑字,這話當然是我說的,但是對與錯,就等待歷史評判吧。”這就是理性的智慧,智慧的理性,在妥協中表現出巨大的勇氣和力量。再看美國控槍法案的荒唐:因為校園槍擊案頻發,2012年美國政府向國會提出了控槍法案。當然這個法案因涉嫌違憲而沒有獲得通過,但其實還有一個理由,即槍擊案頻發就控槍沒有道理,因為用槍的是人,顯然不能把人用槍的手都砍了,把指揮手用槍的人的腦袋都割了。上述事例都是理性對非理性的勝利,但現實中同樣有不少非理性消解理性的事例,造成許多非理性的存在。1950年代末的大躍進、共產風、浮夸風就是非理性的歷史存在。想用三五年就“超英趕美”,想一夜之間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生產上可以大放“衛星”——水稻畝產可達十萬斤。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之所以發生,是集體喪失理性的狂熱導致的。這種狂熱源于一種非理性的觀念——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個觀念又源于非理性的政治宣傳需要,而政治宣傳也是一種教育。所以歸根結底是教育理性的被消解。這種情況并非人們沒有基本常識,而是政治對教育的強迫造成教育應有的真理性被偽理性取代了。真理性的缺失,偽理性的泛濫,現實生活中就產生了許多似是而非的滑稽現象:“富民強國”變成了“富國強民”,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官僚利益階層;“小河漲水大河滿”變成“大河有水小河滿”,成為盤剝民眾的理由;公平獲得相應勞動報酬的權利被套上“無私奉獻”的枷鎖,成為勒索民眾的政治道德。
再說實用理性對價值理性的遮蔽。教育的科學理性固然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但不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它還包含更為重要的科學精神,具有價值理性屬性。而人文理性和審美理性實質上就是價值理性,是人的主體性的體現,對于人的修為更重要,正所謂“善比真重要,美比善重要”。中國本來有著偉大的人文和審美傳統,但由于實用理性傳統和現代物質主義的負面影響,教育的價值理性——科學精神、人文精神和審美精神被遮蔽了,只剩下工具理性。教育不再是造就完整的人的自覺活動,而墮落成為把人造就為工具(奴才和經濟人)的工具。教育理性被消解了,實用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先秦時期的善惡之辯本沒有辯出結果,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孔孟之道的“性善論”借助政治給力而占了上風,中國成為了假定“君子國”,導致人們對惡的忽視,沒有深入剖析,只是簡單否定,所以惡得以橫行。假定人人都是君子的國度,結果一定變成小人國,假定人人都是小人的國度,結果反而造就出大批的君子,這是早就被歷史所證明了的“法乎善,取其惡”。只肯定人性之善,不敢正視甚至故意隱瞞人性之惡,喪失對惡的批判能力,不能制定控制惡的制度,惡就會泛濫成災。就如忽視人的貪婪本性,只靠官員自律性的修養而不靠他律的法律制度,反腐敗就不可能成功,腐敗就會越來越泛濫,甚至泛濫到民眾無奈認可的程度——當官不貪才怪。這就是物質的實用理性取代了精神的價值理性,人們喪失價值判斷力的惡果。為善言善,為惡言惡,效果往往不佳。一個對惡一無所知的人怎能很好地理解并接受善呢?沒有科學精神,我們就永遠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層面上,中醫的現代化其實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是時日尚遠,中醫還只能罩上神秘的面紗。人文精神缺失,我們就永遠是冷漠的看客——在觀看農民工跳樓中增強自己的優越感,在別人的苦難中獲得無聊的快意。沒有審美理性,人們只體會到生活的艱難,工作的辛苦,不能領略工作生活的快樂。
總之,在常態生活中,理和法的底線經常被突破,如官場的腐敗萬象,商場的賄賂成風,民眾對求神拜佛的熱衷,江湖義氣對法律制度的肆意踐踏,都是實用理性取代價值理性,理性被消解的非理性現象。具體影響到教育領域,就造成了教育的浮躁甚至墮落:如“學而優則仕”變為“仕而優則學”,官員、商人都成了大學教授、博士;“真的假文憑”和“假的真文憑”大肆泛濫;師生之間的種種不正當交易等等。
三、教育功能的變異
人是萬物的尺度,也是自己的尺度。教育的主體是人,人的主體性通過教育得以顯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實際上是自我教育,人通過教育的控制功能實現對客觀世界以及對自己的控制,使人作為人而存在。但是教育理性的消解必然帶來教育功能的變異。具體表現就是科學理性變異為科學至上和技術中心主義,繼而發展為物質主義。人文理性雖然在苦苦支撐,但掩蓋不了節節敗退的現實,誠信缺失,道德失范的事實誰又能視而不見?而詩意的審美理性則陷入唯美主義泥淖,華而不實,成為回避現實的美麗鴕鳥,或者公開走向媚俗主義,成為丑惡的幫兇或導師。
科學理性使人得以控制自然之惡,讓自然為人所用,為人的發展服務。但在這個過程中,人類也感受到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滿足感,從而產生了科學崇拜和物質崇拜,于是不自覺地陷入了科學至上和技術中心主義的迷途,以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技術可以帶來一切,人的物質欲望被激發了,人成為科學的工具,技術的載體,無限的物質欲望的追求者。科學家發現了核裂變,人類掌握了核技術,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時,也給人類自己制造了核威脅,成為高懸于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醫學只管最大限度地延長個體生命期限,卻不顧自然生命體的生死極限,更不考慮一個垂危生命的尊嚴、價值和意義,有無必要再維持。在沒有做好科學倫理的準備之前,盲目發展克隆技術,大量克隆滅絕物種和人類自己,我們何以應對自然進化規律被破壞之后的混亂。還不清楚轉基因食物是否有害,人們就大量生產和食用轉基因食品,誰知道何時會因此而禍從天降?人類瘋狂消耗地球資源,肆無忌憚破壞自然環境,地球已經面目全非,達到承受極限。以此為代價建立的現代文明,終有一天會突然轟毀,人類終將自食惡果。因為物極必反,人類發展到最強大的時候,離自我毀滅也不遠了。這就是科學理性變異的結果——科學理性應該是控制人類的瘋狂的,但卻反過來促進了這種瘋狂。
人的自我意識使人不僅打開身體的眼睛看世界,進而把握世界,還能閉上“身體的眼睛”,打開“心靈的眼睛”,認識自己,提升自己。[5]23這個過程就是要控制人的動物性和物質性,強化人的高貴的精神性。這是人文理性的價值所在,即以人文精神合理控制人的動物性的物質欲望。“人是有心者,人是用心者” ,[6]3人若“無心”或“用心”失敗(教育的失敗),喪失精神性,就會陷入“創造物質,滿足欲望,創造更多的物質,滿足更大的物質欲望”的怪圈。當下的社會狀況即是:“享受物質財富的現代人實際上也被物質所虜,在擁有物質的同時也被物質所擁有,沉溺于物質,被物質所包圍,患上了嚴重的‘物欲癥’。”[7]3你占有了手機,同時也被手機控制,你成了“手機控”“低頭族”。其實物質已經比較豐富的現代人的焦慮和壓力大都來自于物質欲望的無限膨脹所導致的虛幻的不滿足,以及物質欲望充斥人的心靈,擠占人的精神空間。房子越住越大,車子越換越好,票子越掙越多,永不滿足。正如一個網友所說的——我們正處在“一個不夠”的時代:一部手機不夠、一份薪水不夠、一輛車子不夠、一棟房子不夠……我們對外面的世界過度需求,對每天的自己過度使用。“一”不再是單純的數字,而是一個欲求不滿的代名詞。雖然趨利避害、趨樂避苦是正常的人性,即人們常態的目標和方向,但對財富的過度追求,僅為了人性深處的劣根性導致的炫耀,就是一種病態。因為炫耀性消費始終是虛假性消費,是一種浪費資源的異化消費。虛榮的攀比、時尚的跟風、盲目的服從都是沒有價值理性所導致的人的劣根性的外在表現。“甘于受生命必然性、生命壓力的驅使,安于生命本能,忘記或懶于超越生命現狀,只是瘋狂地追求財富、瘋狂消費,結果是除了將生命的軀殼打扮得光鮮亮麗外,就剩下極度的空虛和無聊的虛榮以及別人無益的羨慕與贊賞。而這些并非生命必然的消費需求竟是偽消費偽需求。”[8]5-96生活中的購物狂就是實例:用不上也購買一大堆,最后變成污染環境的垃圾。此時最需要人們具有價值判斷力,需要人文精神和審美精神發揮作用——人們需要明白什么東西對自己有價值,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樣的生活是自己向往的詩意生活。不明白就無法選擇。但價值理性在哪里呢?西哲說“適度的物質貧困有利于人們思想”,反過來說就是“過度的物質富裕不利于人們思想”,人的價值理性就這樣在過度的物質消費中變異了。人的獨立自由變成了人身依附或“圈子里的人”,愛情變成了青春肉體的待價而沽,生命的尊嚴演變為除夕夜的滅門慘案,財富的獲得靠權力尋租或商場的爾虞我詐。生活的詩意被生活的焦慮和壓力取代,被華而不實的唯美主義所粉飾,被低俗、庸俗、惡俗的媚俗主義所裝扮。不接地氣的唯美和以俗為美,都是以丑為美。這就是價值理性功能變異的結果。
教育理性是以整體理性的方式實現控制功能的。但是由于科學教育、人文教育、審美教育的分離與偏頗,實用理性和物質主義的影響,教育的整體理性一定程度上被消解,教育理性的控制功能發生變異,教育就只是把人變成技能載體的工具。這樣的教育造就了現實中非理性的荒誕存在:在正義的名義下掠奪,在真理的光環下欺騙,在發展的誘惑下破壞,在幸福的追求中異化(喪失自由)。因此,教育理性的回歸,教育功能的恢復,應該是教育改革發展應注意的問題。
[1]高德勝.我們都是自己的陌生人[J].高等教育研究,2013(2):9-19.
[2][蘇]阿·布羅夫.美學:問題和爭論[M].凌繼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3][美]弗洛姆.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M]//西方學者論.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
[4]謝素軍.盛產英雄的國家[J].東方女性,2012(12):46.
[5][美]漢娜·阿倫特.精神生活·思維[M].姜志輝.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6][美]丹尼爾·丹尼特.心靈種種:對意識的探索[M].羅軍.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7][美]約翰·格拉夫.流行性物欲癥[M].閭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8][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前言[M].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