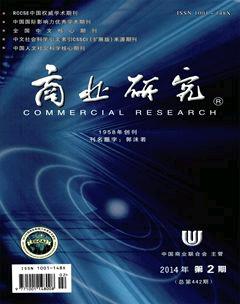種業企業植物品種權申請狀況分析
胡凱
摘要:企業是種業發展的主體。加強育種創新、獲取植物品種權是提升種業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通過對1999-2012年我國種業公司植物品種權申請情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植物品種權申請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良好態勢;種業公司申請占比逐漸增加,企業正日益成為商業化育種、成果轉化與應用的主體。從分地區來看,種業企業品種權申請的地區差異非常大,要充分發揮龍頭種業企業對地區現代種業發展的帶動作用,扶持一批現代農作物種業集團。從分品種來看,不同類別的品種權申請存在很大的差異,與水稻相比,玉米育種的市場化程度更高;蔬菜、花卉作為附加值高、利潤大的經濟作物面臨非常嚴峻的國際競爭,應發揮市場機制的引導作用,鼓勵包括私人資本在內的大型企業進入農作物種業。
關鍵詞:種業企業;植物品種權申請;育種創新;商業化育種
中圖分類號:F27912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中國人多地少、人多水少,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根本出路在科技。農業科技是加快現代農業發展的決定力量。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把農業科技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大幅度增加農業科技投入,推動農業科技跨越發展,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注入強勁動力。
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科技興農,良種先行。在“三化同步”推進的歷史階段,農業持續穩定發展更加依賴種業科技進步,現代農業的新突破也更加依賴科技。長期以來,我國種業發展滯后,突破性品種不多、種子企業創新能力不強、育種資源和高端人才不足等問題是制約我國種業乃至農業發展的重要問題。我國現有種子企業6 296家,整體規模較小且分散,缺乏龍頭型的大公司,與跨國種子企業的差距是幾何數量級的。在種子市場開放以后,跨國種子企業大量涌入,并加緊在我國進行研發布局,嚴重擠壓了國內種子企業的生存空間,對我國的種子資源和種子產業安全構成了威脅。農業部統計數據顯示,除大宗糧棉油等主要農作物育種外,目前我國有50%以上的生豬、蛋肉雞、奶牛良種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種依賴進口。加強育種創新、獲取植物品種權是提升種業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正是基于這樣嚴峻的形勢,中央高度重視種業科技創新和現代種業發展。2012年12月國務院發布了《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規劃》(2012-2020),強調種業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的核心產業,是促進農業長期穩定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明確了企業是種業發展的主體,鼓勵科技資源向企業流動。事實上,2011年國內企業申請植物品種權占比第一次超過了國內科研機構申請占比,反映了企業日益成為我國種業科技創新的主體。
植物新品種是農業科技創新的主要成果,植物品種權保護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和科技興農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調動植物育種者的積極性,發達國家率先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植物品種權保護制度。我國于1999年正式加入了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該條例的實施為促進我國種業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
二、我國植物品種權申請總體狀況
植物新品種是指經過人工培育的或者對發現的野生植物加以開發,具備新穎性、特異性、一致性、穩定性并有適當命名的植物品種。目前,我國植物新品種分為大田作物、蔬菜、花卉、果樹、牧草及其他等6大類。截止到2012年底,農業部植物新品種保護辦公室共受理品種權申請10 556項,已授權3 880項(見表1)。
(一)品種權申請授權總量變化趨勢
從圖1可以看出,總體上我國植物品種權申請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從1999年的115項增加到2012年的1 361項,反映了我國農業科技創新活動不斷增強,科研人員及研究機構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斷強化的良好態勢。品種權授權則表現出較大的起伏,在1999-2009年之間呈上升的趨勢,但在2009年達到峰值后連續三年大幅下降,從2009年的941項減少為2012年的167項。品種權授權數量的大幅波動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品種權申請和授權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且授權時間不確定,使得不同年份數據波動較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近年來我國對植物新品種授權要求越來越嚴格,使得授權數逐年減少。考慮到品種權授權數量的大幅波動,下文主要分析我國植物品種權申請情況。
(二)分單位性質品種權申請總體情況
植物育種者包括國內外研究機構、企業、大學及個人等,因此農業部植物新品種保護辦公室將植物新品種申請主體分成了國內科研機構、國內企業、國內教學機構、國內個人、國外科研機構、國外企業、國外教學機構、國外個人等8種。2002-2012年各單位品種權申請比重如表2所示。
從表2我們發現,國內個人申請所占的比重基本在5%左右,總體變化不大,國外個人、國外科研機構、國外教學機構申請量很少,均在1%以下,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國內科研機構、國內教學單位、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4類申請機構品種權申請的變化情況(見圖2)。
從圖2可以看出,國內科研機構和國內企業植物品種權申請數占全部申請數的80%以上,反映出我國目前農業科研機構和種業企業是我國農業科技創新的主體。其中,國內企業品種權申請數近年來迅速增加,2011年申請量第一次超過國內科研機構申請量,其品種權申請占比也從2002年的238%上升至2012年的425%;相應地,國內科研機構的品種權申請占比則呈下降趨勢,從2002年597%下降至2012年的395%。因此,我國植物品種權申請結構的總體變化趨勢是國內科研機構申請占比逐漸下降、國內企業申請占比逐漸上升,這種結構的變化反映了企業日益成為我國農業科技創新的主體,這與國務院發布的《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中提出的“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從事農作物種業基礎性公益性研究,引導和積極推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業化育種,促進種子企業逐步成為商業化育種的主體”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
在國內企業申請數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外企業申請數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占比從2002年的14%上升到2012年的65%,說明國外企業近年來大幅增加了在我國植物品種領域的研發和保護,我國育種者將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
三、國內種業企業品種權申請狀況分析
(一)種業企業品種權申請量的地區差異
表3統計了到2012年底我國各地區品種權申請數量及種業公司申請數量。不難發現,各地區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其中,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超過300項的僅有2個地區,分別為北京、山東;種業公司申請量為100-300項的有10個地區,分別為吉林、河南、四川、安徽、河北、云南、遼寧、江蘇、湖南、黑龍江;種業公司申請量為50-100項的有6個地區,分布為內蒙古、江西、山西、廣西、山西、湖北;種業公司申請量不足50項的有12個地區,分別為天津、上海、廣東、新疆、甘肅、重慶、浙江、福建、海南、貴州、寧夏、青海。進一步,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前的、超過100項的12個地區共申請品種權2 613項,占種業公司品種權總申請量3 396項的769%,而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后的、不超過50項的12個地區僅申請312項,尚不足北京或山東一地的申請量,僅占種業公司品種權總申請量的92%,這反映了我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在不同的地區存在巨大的差異。
從地域分布上來看,我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居前的省份主要位于東北、華北、中部等地,這些地區大多是我國農作物的主產區;而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居后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北、東部沿海、華南、西南(四川、云南除外)等地,其中既有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浙江、廣東等地,也包括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廣東、浙江、天津等地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均低于50項,這一方面說明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較低,農業生產、研發活動相對較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農作物育種整體水平不高、投資回報率較低,對于資本的吸引力很弱,在這些我國經濟最為發達、人才集中的地區,私人資本進入農作物育種領域的積極性很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全國第一位的北京。北京與上海、廣東、浙江、天津等地都是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北京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全國之首,我們分析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北京農業科技人才聚集,育種能力強,品種權保護意識強;二是北京總部經濟優勢明顯,很多跨國種業企業在北京設立分公司,這些公司的品種權申請增加了北京的申請量,如孟山都科技有限公司、KWS種子股份有限公司、先正達種苗(北京)有限公司等;三是北京培育了一批龍頭種業公司,這些企業發揮了很好的帶動作用。
(二)種業公司申請量占地區品種權申請量的比例分析
公司申請占比是指一個地區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占該地品種權申請量的比例,該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商業化育種機制的完善程度。該指標越高,說明該地區種業公司在種業商業化過程中的作用越顯著,該地區商業化育種程度越高。表3反映了我國不同地區種業公司申請占比的差異。
從表3中可以發現,我國有3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超過60%,分別是江西、山西和海南,其中江西省公司申請占比達到816%,居全國首位;有8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位于40%-60%之間,包括內蒙古、北京、天津、吉林、安徽、甘肅、山東、陜西;有13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位于20%-40%之間,包括河北、云南、新疆、廣西、遼寧、湖南、河南、四川、重慶、寧夏、上海、湖北、江蘇;有6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不到20%,包括廣東、黑龍江、福建、浙江、貴州、青海。
公司申請占比超過60%的3個地區均為我國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說明這些地區農作物育種市場化進程較快,種業公司在商業化育種中的作用顯著,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和這幾個地區品種權總申請量較少有關系。以全國平均公司申請占比425%為限,全國只有9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超過了平均水平,還有21個地區在平均水平以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江蘇、廣東、浙江等幾個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經濟發達地區,其公司申請占比均很低,浙江甚至僅為106%,說明在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農作物商業化育種機制還不完善,種業公司的活躍程度和所發揮的作用還很小。結合前文所論述的這幾個地區公司品種權申請總量少的情況,進一步印證了這些地區農作物育種的滯后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商業化育種機制的不完善。
(三)龍頭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情況
在北京和山東這兩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居前的地區都有重要的龍頭種業企業,它們對促進當地的農作物育種創新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如北京金色農華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請量為192項,居全國種業公司之首,登海種業申請量為155項。在我國其他申請量居前的地區也大多都有實力強、規模大的種業企業帶動,如吉林吉農高新技術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含子公司)及其參股的吉林長融高新種業有限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合計為109項,隆平高科品種權申請量為90項。其他一些種業上市公司或龍頭企業品種權申請量也位居前列,如德農種業申請量50項,豐樂種業31項,神農大豐30項,奧瑞金種業28項,荃銀高科20項等。
不難發現,一個地區種業的發展需要靠一批實力強、規模大的龍頭種業公司帶動。比如,北京盡管農業產值較低,但聚集了一批國內領先的種業公司,如金色農華、德農種業、奧瑞金種業等,同時也吸引了孟山都等一批跨國種業巨頭,使得北京公司品種權申請量位居全國首位。因此,堅持扶優扶強,重點支持一批龍頭種業企業,鼓勵企業兼并重組,吸引社會資本和優秀人才流入企業,是我國種業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應該作為我國其他地區如上海、廣東、浙江等發展農作物種業的重要啟示。
四、國內種業企業分品種類別申請狀況分析
我國植物新品種分為大田作物、蔬菜、花卉、果樹、牧草及其他等6大類。考慮到果樹、牧草及其他品種權申請非常少,本文主要分析種業公司在大田作物、蔬菜、花卉3個類別的品種權申請情況。
(一)大田作物品種權申請狀況
大田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大豆、普通小麥、棉屬、甘藍型油菜、花生、高粱、大麥屬、甘薯、谷子、甘蔗屬、蠶豆、綠豆、芝麻屬、苧麻屬、芥菜型油菜、亞麻等18個類別,種業公司累計申請3 010項,各類別申請項數見表4。
在國內企業申請數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外企業申請數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占比從2002年的14%上升到2012年的65%,說明國外企業近年來大幅增加了在我國植物品種領域的研發和保護,我國育種者將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
三、國內種業企業品種權申請狀況分析
(一)種業企業品種權申請量的地區差異
表3統計了到2012年底我國各地區品種權申請數量及種業公司申請數量。不難發現,各地區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其中,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超過300項的僅有2個地區,分別為北京、山東;種業公司申請量為100-300項的有10個地區,分別為吉林、河南、四川、安徽、河北、云南、遼寧、江蘇、湖南、黑龍江;種業公司申請量為50-100項的有6個地區,分布為內蒙古、江西、山西、廣西、山西、湖北;種業公司申請量不足50項的有12個地區,分別為天津、上海、廣東、新疆、甘肅、重慶、浙江、福建、海南、貴州、寧夏、青海。進一步,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前的、超過100項的12個地區共申請品種權2 613項,占種業公司品種權總申請量3 396項的769%,而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后的、不超過50項的12個地區僅申請312項,尚不足北京或山東一地的申請量,僅占種業公司品種權總申請量的92%,這反映了我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在不同的地區存在巨大的差異。
從地域分布上來看,我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居前的省份主要位于東北、華北、中部等地,這些地區大多是我國農作物的主產區;而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居后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北、東部沿海、華南、西南(四川、云南除外)等地,其中既有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浙江、廣東等地,也包括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廣東、浙江、天津等地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均低于50項,這一方面說明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較低,農業生產、研發活動相對較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農作物育種整體水平不高、投資回報率較低,對于資本的吸引力很弱,在這些我國經濟最為發達、人才集中的地區,私人資本進入農作物育種領域的積極性很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全國第一位的北京。北京與上海、廣東、浙江、天津等地都是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北京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全國之首,我們分析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北京農業科技人才聚集,育種能力強,品種權保護意識強;二是北京總部經濟優勢明顯,很多跨國種業企業在北京設立分公司,這些公司的品種權申請增加了北京的申請量,如孟山都科技有限公司、KWS種子股份有限公司、先正達種苗(北京)有限公司等;三是北京培育了一批龍頭種業公司,這些企業發揮了很好的帶動作用。
(二)種業公司申請量占地區品種權申請量的比例分析
公司申請占比是指一個地區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占該地品種權申請量的比例,該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商業化育種機制的完善程度。該指標越高,說明該地區種業公司在種業商業化過程中的作用越顯著,該地區商業化育種程度越高。表3反映了我國不同地區種業公司申請占比的差異。
從表3中可以發現,我國有3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超過60%,分別是江西、山西和海南,其中江西省公司申請占比達到816%,居全國首位;有8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位于40%-60%之間,包括內蒙古、北京、天津、吉林、安徽、甘肅、山東、陜西;有13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位于20%-40%之間,包括河北、云南、新疆、廣西、遼寧、湖南、河南、四川、重慶、寧夏、上海、湖北、江蘇;有6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不到20%,包括廣東、黑龍江、福建、浙江、貴州、青海。
公司申請占比超過60%的3個地區均為我國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說明這些地區農作物育種市場化進程較快,種業公司在商業化育種中的作用顯著,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和這幾個地區品種權總申請量較少有關系。以全國平均公司申請占比425%為限,全國只有9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超過了平均水平,還有21個地區在平均水平以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江蘇、廣東、浙江等幾個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經濟發達地區,其公司申請占比均很低,浙江甚至僅為106%,說明在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農作物商業化育種機制還不完善,種業公司的活躍程度和所發揮的作用還很小。結合前文所論述的這幾個地區公司品種權申請總量少的情況,進一步印證了這些地區農作物育種的滯后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商業化育種機制的不完善。
(三)龍頭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情況
在北京和山東這兩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居前的地區都有重要的龍頭種業企業,它們對促進當地的農作物育種創新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如北京金色農華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請量為192項,居全國種業公司之首,登海種業申請量為155項。在我國其他申請量居前的地區也大多都有實力強、規模大的種業企業帶動,如吉林吉農高新技術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含子公司)及其參股的吉林長融高新種業有限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合計為109項,隆平高科品種權申請量為90項。其他一些種業上市公司或龍頭企業品種權申請量也位居前列,如德農種業申請量50項,豐樂種業31項,神農大豐30項,奧瑞金種業28項,荃銀高科20項等。
不難發現,一個地區種業的發展需要靠一批實力強、規模大的龍頭種業公司帶動。比如,北京盡管農業產值較低,但聚集了一批國內領先的種業公司,如金色農華、德農種業、奧瑞金種業等,同時也吸引了孟山都等一批跨國種業巨頭,使得北京公司品種權申請量位居全國首位。因此,堅持扶優扶強,重點支持一批龍頭種業企業,鼓勵企業兼并重組,吸引社會資本和優秀人才流入企業,是我國種業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應該作為我國其他地區如上海、廣東、浙江等發展農作物種業的重要啟示。
四、國內種業企業分品種類別申請狀況分析
我國植物新品種分為大田作物、蔬菜、花卉、果樹、牧草及其他等6大類。考慮到果樹、牧草及其他品種權申請非常少,本文主要分析種業公司在大田作物、蔬菜、花卉3個類別的品種權申請情況。
(一)大田作物品種權申請狀況
大田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大豆、普通小麥、棉屬、甘藍型油菜、花生、高粱、大麥屬、甘薯、谷子、甘蔗屬、蠶豆、綠豆、芝麻屬、苧麻屬、芥菜型油菜、亞麻等18個類別,種業公司累計申請3 010項,各類別申請項數見表4。
在國內企業申請數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外企業申請數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占比從2002年的14%上升到2012年的65%,說明國外企業近年來大幅增加了在我國植物品種領域的研發和保護,我國育種者將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
三、國內種業企業品種權申請狀況分析
(一)種業企業品種權申請量的地區差異
表3統計了到2012年底我國各地區品種權申請數量及種業公司申請數量。不難發現,各地區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其中,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超過300項的僅有2個地區,分別為北京、山東;種業公司申請量為100-300項的有10個地區,分別為吉林、河南、四川、安徽、河北、云南、遼寧、江蘇、湖南、黑龍江;種業公司申請量為50-100項的有6個地區,分布為內蒙古、江西、山西、廣西、山西、湖北;種業公司申請量不足50項的有12個地區,分別為天津、上海、廣東、新疆、甘肅、重慶、浙江、福建、海南、貴州、寧夏、青海。進一步,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前的、超過100項的12個地區共申請品種權2 613項,占種業公司品種權總申請量3 396項的769%,而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后的、不超過50項的12個地區僅申請312項,尚不足北京或山東一地的申請量,僅占種業公司品種權總申請量的92%,這反映了我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在不同的地區存在巨大的差異。
從地域分布上來看,我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居前的省份主要位于東北、華北、中部等地,這些地區大多是我國農作物的主產區;而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居后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北、東部沿海、華南、西南(四川、云南除外)等地,其中既有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浙江、廣東等地,也包括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廣東、浙江、天津等地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均低于50項,這一方面說明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較低,農業生產、研發活動相對較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農作物育種整體水平不高、投資回報率較低,對于資本的吸引力很弱,在這些我國經濟最為發達、人才集中的地區,私人資本進入農作物育種領域的積極性很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全國第一位的北京。北京與上海、廣東、浙江、天津等地都是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北京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數居全國之首,我們分析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北京農業科技人才聚集,育種能力強,品種權保護意識強;二是北京總部經濟優勢明顯,很多跨國種業企業在北京設立分公司,這些公司的品種權申請增加了北京的申請量,如孟山都科技有限公司、KWS種子股份有限公司、先正達種苗(北京)有限公司等;三是北京培育了一批龍頭種業公司,這些企業發揮了很好的帶動作用。
(二)種業公司申請量占地區品種權申請量的比例分析
公司申請占比是指一個地區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占該地品種權申請量的比例,該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商業化育種機制的完善程度。該指標越高,說明該地區種業公司在種業商業化過程中的作用越顯著,該地區商業化育種程度越高。表3反映了我國不同地區種業公司申請占比的差異。
從表3中可以發現,我國有3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超過60%,分別是江西、山西和海南,其中江西省公司申請占比達到816%,居全國首位;有8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位于40%-60%之間,包括內蒙古、北京、天津、吉林、安徽、甘肅、山東、陜西;有13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位于20%-40%之間,包括河北、云南、新疆、廣西、遼寧、湖南、河南、四川、重慶、寧夏、上海、湖北、江蘇;有6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不到20%,包括廣東、黑龍江、福建、浙江、貴州、青海。
公司申請占比超過60%的3個地區均為我國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說明這些地區農作物育種市場化進程較快,種業公司在商業化育種中的作用顯著,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和這幾個地區品種權總申請量較少有關系。以全國平均公司申請占比425%為限,全國只有9個地區公司申請占比超過了平均水平,還有21個地區在平均水平以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江蘇、廣東、浙江等幾個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經濟發達地區,其公司申請占比均很低,浙江甚至僅為106%,說明在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農作物商業化育種機制還不完善,種業公司的活躍程度和所發揮的作用還很小。結合前文所論述的這幾個地區公司品種權申請總量少的情況,進一步印證了這些地區農作物育種的滯后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商業化育種機制的不完善。
(三)龍頭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情況
在北京和山東這兩個種業公司品種權申請居前的地區都有重要的龍頭種業企業,它們對促進當地的農作物育種創新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如北京金色農華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請量為192項,居全國種業公司之首,登海種業申請量為155項。在我國其他申請量居前的地區也大多都有實力強、規模大的種業企業帶動,如吉林吉農高新技術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含子公司)及其參股的吉林長融高新種業有限公司品種權申請量合計為109項,隆平高科品種權申請量為90項。其他一些種業上市公司或龍頭企業品種權申請量也位居前列,如德農種業申請量50項,豐樂種業31項,神農大豐30項,奧瑞金種業28項,荃銀高科20項等。
不難發現,一個地區種業的發展需要靠一批實力強、規模大的龍頭種業公司帶動。比如,北京盡管農業產值較低,但聚集了一批國內領先的種業公司,如金色農華、德農種業、奧瑞金種業等,同時也吸引了孟山都等一批跨國種業巨頭,使得北京公司品種權申請量位居全國首位。因此,堅持扶優扶強,重點支持一批龍頭種業企業,鼓勵企業兼并重組,吸引社會資本和優秀人才流入企業,是我國種業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應該作為我國其他地區如上海、廣東、浙江等發展農作物種業的重要啟示。
四、國內種業企業分品種類別申請狀況分析
我國植物新品種分為大田作物、蔬菜、花卉、果樹、牧草及其他等6大類。考慮到果樹、牧草及其他品種權申請非常少,本文主要分析種業公司在大田作物、蔬菜、花卉3個類別的品種權申請情況。
(一)大田作物品種權申請狀況
大田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大豆、普通小麥、棉屬、甘藍型油菜、花生、高粱、大麥屬、甘薯、谷子、甘蔗屬、蠶豆、綠豆、芝麻屬、苧麻屬、芥菜型油菜、亞麻等18個類別,種業公司累計申請3 010項,各類別申請項數見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