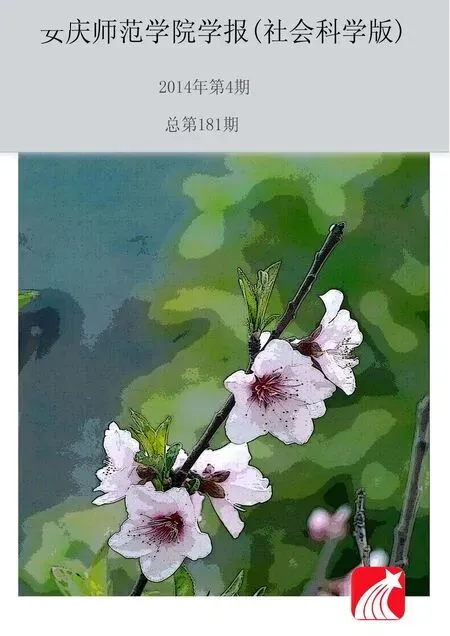“保底”與“跳級”:高收入高福利行業子弟回流就業行為的場域分析
劉 偉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山東 濟南 250100)
“保底”與“跳級”:高收入高福利行業子弟回流就業行為的場域分析
劉 偉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山東 濟南 250100)
石化行業長期存在著員工子女憑借內部優惠政策“回流”至本行業就業的現象,其特征可概括為“保底”和“跳級”,即行業子弟在規避就業風險的前提下努力向更高層級行業流動。作為求職場域斗爭妥協的結果,回流就業受到職業觀念、行業歸屬感、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級別等因素的影響,反映了個人就業模式的變遷以及就業公平問題的復雜性。
高福利行業;子弟回流;就業行為;場域視角
當代中國社會的就業難問題人所共知,大學生就業則是其中的主要難點。國家壟斷比例高、大型企業集中的石化、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憑借其特殊的歸屬身份和經濟地位,幾乎成為高收入高福利的代名詞,受到廣大畢業生的普遍關注。
但是,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這些高收入高福利行業中卻長期存在著一條專為其職工子女服務的就業捷徑,即企業員工子弟可憑借其血緣身份獲得本企業的特殊就業權(如中石油系統)。為此,對這種“子弟回流就業”(本研究所稱“回流就業”,是指依靠行業內部的優惠政策,某一企業員工的子女憑借子弟身份獲得該企業就業權的現象,不包括員工子女到同行業其他企業就職的情況)的行為展開更具體的社會學觀察與分析,將有利于認識并解決當前的就業不平等問題,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一、文獻回顧
目前學術界對這一現象的直接關注更多來自政治學和經濟學語境下的概括性主張。這些學者認為,國企子弟先天優先獲得國企就業權的現象在我國由來已久,其成因在于國企企業性的凸顯和國家性的弱化;并將相關的優先招錄政策與憑借關系安排入職的現象統稱為“職業世襲”,認為應從根本上約束權力、限制尋租機會,從而杜絕此類行為[1-3]。
社會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則主要來自職業代際流動與職業地位獲得等方向。許多研究證明,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經濟收入、職業地位、政治身份等變量為代表的家庭背景因素,對子女的職業地位獲得確有影響,并造成了社會地位差異在代際間的傳遞[4-7]。但是,由于中國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單位、區域等集體機制的影響[8],父代工作單位、父代所處行業等集體性變量可能更需要關注。對此,林南與邊燕杰認為,在當代中國,父代工作單位對子代工作單位的獲得具有直接而顯著的影響,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傳承是通過工作單位而不是職業進行的[9],其具體表現為:與父代務農的情況相比,其他單位向上的職業代際流動的機會都相對較大;父代單位級別越高,越不可能下降流動[10]。更詳細的分析指出,對于優勢階層的子女來說,在只有低教育程度的條件下,有更多的機會避免從事最低的非技術體力的工作(“保底”);在擁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條件下,則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專業技術等非體力階層(“跳級”),很少掉到非技術體力這一城鎮職業地位最低的階層(“保底”)[11]。本文正是在上述文獻的基礎上,選取了“父代工作單位和所在行業”這一重要卻少受關注的集體性因素展開探究。
對于家庭背景影響子女職業地位獲得過程中的限制要素,則以對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級別的研究為主。相關研究指出,青年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是其能否進入精英階層的關鍵所在,研究生學歷是個人成為高級精英(特別是高級技術精英)的重要條件之一;父輩想要幫助子女獲得中等級別的位置,則其本人的行政級別要足夠高[12]。而子女的學業表現則是家庭教育背景對子女初職地位獲得影響的中間變量[6]。
但是,以上絕大多數研究均使用量化的統計分析方法,缺少對個體主觀意識與策略的刻畫,沒有也難以解釋這一影響的過程機制是如何運轉的;一些質性研究雖然指出回流就業作為單位意識的延續給企業和個人都帶來了困擾,甚至指出了就業觀的新變化[13],但并未說明這一趨向的生成機制;另一方面,回流就業始終是在相關企業優惠政策之下產生和運作的,企業對政策關卡的態度將顯著影響著該現象的表征;而上述研究均缺少對這種相對公開的、不斷變化的、結構性的權力的介入考察。為此,本文將打破上述文獻普遍遵循的個人屬性的職業代際流動研究路徑,增加機會阻隔路徑和剝削支配路徑意義上的分析[14],即將職業代際流動和階層再生產視為充滿主體策略性和運作性的過程。由于這涉及結構與運作兩類要素的雜糅交錯,本文借鑒以往文獻[15],承認“關系”與正式渠道兩種入職方式并存的現實,力求建立更明晰的邏輯框架。
二、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場域理論是布迪厄最重要的社會學理論之一,也是其所主張的社會研究基本分析單位。場域可以理解為依附于某種權力(或資本)的各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所構成的網絡或者結構,具有如下性質:場域的效果在其空間內得到發揮,并將影響所有對象的行動;場域中各種位置的占據者利用種種策略來保證或改善其在場域中的位置,在場域中展開斗爭;場域通過一套結構性的預設或邏輯影響其中的對象,并以習慣的形式使影響內化[16]。因此,場域視角可以使分析者較容易地在多重訴求與策略交織的情況下,抽離出各方行動的內在機制。
場域視角下的子弟回流現象發生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關系結構中,期間運行著以行業內部政策為主導的各種邏輯,充斥著形式各異的資本或權力;另一方面,該場域又受到現實世界的深刻影響,被卷挾進入無止境的變遷當中。在這樣復雜的背景下,各主體為保持并增加所掌握的資本(即實現自身訴求)而不斷發生充滿策略意義的斗爭。
三、W公司子弟回流就業現象描述
W公司現為國有特大型煉油化工燃料企業,年原油加工能力為百萬噸級,對W市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城市布局和社會心理均具有重大影響。公司共有在職員工15 000余人(2009年),包括退休員工、員工家屬及相關服務業人員等群體保守估計不少于10萬人,并圍繞生產廠區形成了一個具備經濟、教育、文化娛樂、公共服務等職能的綜合性巨型社區。筆者在W公司員工子弟中采訪了4位2013年應屆本科畢業生A、B、C、D作為具體案例,另外還采訪了一位退休工人E以了解政策沿革情況。
(一)W公司子弟回流就業政策的沿革與現實
石化行業的子弟回流就業優惠政策最早始于上世紀60年代大慶石油會戰時期,隨隊家屬被允許直接入職從事油田后勤工作,后來入職范圍逐漸擴大到職工子弟;至上世紀60-70年代,隨著社會就業壓力增大,這一做法開始在包括W公司在內的石化企業廣泛推行,稱為“學大慶,讓子女上班,解決職工的后顧之憂”。至上世紀90年代,W公司每年新入職員工幾乎全部來自于廠辦學校應屆畢業生當中的職工子弟。但是,在經歷了上世紀末的國企大改革和單位制弱化后,面對不容樂觀的收支態勢與人力資源現實,W公司對子弟回流政策做出了調整:“211工程”高校的理工科子弟全部接納就業,非理工科子弟只接納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一般高校則根據學校情況只招收化工、儲運和裝備制造等個別專業的子弟;三批本科院校畢業的子弟無論任何專業一律不予接納。
(二)“保底”:W公司子弟對回流就業的態度
在上述政策改革的背景下,W公司子弟對于是否回流一般都已有較明確的立場;但是無論最終是否選擇該途徑,他們都試圖將回流作為其他就業選擇未能成功時的“留一手”,以保證最終結果不低于W公司。如就讀于某高校重要工科專業的A君,始終把通過招聘會應聘企業作為求職首要途徑,次之則有可能從事他喜歡的舞臺設計等工作,如果以上計劃全都落空,再考慮以子弟身份回W公司工作。又如已經回流與W公司簽約的D君,她實際上從剛入大學起就有考研的打算,目前的回流簽約只是為了萬一失敗后有一穩定工作,以便明年復考。
不難看出,不選擇回流的W公司子弟其實并未在根本上排斥回流,而是將其作為無工作可聘時的一種應急方案;而已回流的子弟也并未將回流視為工作首選,而是作為保障最終發展目標的跳板。因此,這里不妨借用李煜的“保底”概念[11]來概括。這是為了保證就業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種相對穩妥的選擇策略,在相當程度上為子弟就業規避了風險。
(三)“跳級”:子弟們的近期職業規劃
那么,既然回流到石化行業并非子弟們所熱衷,他們更理想的職業又是何種模樣?對此,調查材料顯示,4位子弟無一例外對工程設計[2]410行業表現出明顯的就業興趣,而且4位子弟均有讀研深造的計劃。以A君為例,除了上述應聘對口職位和憑愛好自主創業等選擇以外,他最理想的工作就是設計,并向筆者詳細講述了設計工作的優越環境;D君則干脆將考研作為進入設計行業的敲門磚,明確提出了“設計院>考研>回流就業”的傾向排序。
(設計院)這是我們這個行業擠破頭最想去的,無論如何,你一旦能進去,是所有人都會羨慕你的行業。工作穩定,事不多,工作條件極其安全,基本上屬于按勞分配的,掙得真的是非常多。(訪談材料A20130131)
可見,盡管上述諸君憑借子弟身份可以較容易地在W公司獲得一份相對不錯的工作,但他們仍將在收入、職業地位、工作生態等方面更優渥的設計行業作為追求的新目標,即“跳級”概念:在能夠獲得確定工作的前提下,勞動者仍然具有向更高層級職業(行業)流動的傾向;“跳級”與“保底”相互配合,“保底”是為了能夠實現“跳級”,“跳級”失敗則可借“保底”實現就業;兩者的實質都是為了獲得就業利益的最大化。
四、場域斗爭的演變——基于場域視角的分析
綜上,W公司子弟的回流入職主要涉及W公司、子弟父母(W公司員工)和子弟本人三方主體,并在以W公司為核心的W社區中獲得了運作空間——此處不妨稱其為W場域,其特征除上文所闡述外還包括如下幾點:第一,W場域結構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這會通過對行動者的習慣形塑而產生強大的歷史慣性。第二,該穩定狀態在最近遭到了明顯破壞,很可能造成場域權力結構的失衡。第三,場域內各方力量對比并不均衡,相較于子弟本人及其父母,W公司的力量明顯強勢。由此,以場域斗爭為分析核心,筆者對“保底-跳級”特征生成的原因作出如下解釋。
(一)場域斗爭的產生:集體與個人的利益沖突
面對W公司的政策改革,子弟家長首先作出了反應,原因如下:第一,中國歷來就有父母影響子女個人選擇的文化傳統。目前,為子女找到合適的工作已經內化為中國父母的典型角色期待。第二,許多子弟父母是經過了若干次職業流動后才最終在收入與穩定性均相對較高的W公司立足的,十分希望將該優勢地位傳承給子女。這體現了來自W場域的形塑作用。第三,W公司曾長期實行的寬松的回流政策使員工普遍認為公司對子弟就業應負有責任。這也是職工對傳統單位制的一種路徑依賴。于是,他們憑借公司職工的身份,借助“鬧事”等輿論力量向W公司施壓:
“為啥是裝備二本肯定要,我們二本不要?上廠長辦公室鬧去唄。”(訪談材料C20130117)
作為回應,W公司一方面不再公開任命組織當年回流招聘工作的工作人員,以防個人尋租;另一方面嚴格保密當年回流招聘的專業要求,并盡可能縮短該政策的傳達時間,一經公布立即執行,給潛在的“鬧事”者以既成事實。于是,W公司與子弟父母形成了僵持對抗的局面。
(二)場域斗爭的發展:代際間的變遷與對立
1.職業觀念的代際變遷
就在此時,子弟本人的就業主張卻逐漸開始異于其父母的想法:一方面,由于他們從小生活在發展水平較高的W社區中,與其長輩相比,向上流動的外界刺激更強,自我期望也更高;另一方面,職業在他們眼中被更多地賦予了豐富人生經歷、體現生活態度的意義,特別是應滿足個人在尊重和自我實現層面上的需求。因此,回流就業雖然能夠獲得較穩定且收入豐厚的工作,但由于上升通道狹窄、工作內容乏味,加之復雜的工作生態,難以得到子弟們的真心青睞。
2.行業歸屬感在代際間的弱化
子弟對石化行業歸屬感的明顯滑坡是導致其對回流就業較低認同的另一重要原因。在緩慢卻不可逆轉的單位制消亡進程中,新一代石化子弟主張應以更強的自我意識來認識自身與這座工廠及整個行業的關系,石化只是“我爸媽的”行業,生活只是在此進行而已,W社區已不是他們的精神與文化依托:
它對于我來說就是這個東西就像街邊大馬路上的存在而已……它頂多說和我父母有點啥關系,和我有什么關系?(訪談材料A20130131)
進一步講,這種歸屬感的消亡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場域內文化資本代際傳承的失效,也就是說,父代在職業生涯中積累的角色定位、行為模式、思維方式、組織認同等文化要素已經很難傳遞給下一代。
(問:你爸媽平時和你聊不聊在單位的事?)我爸:“明兒有時間沒?”“有。”“陪我打麻將去,三缺一。”我媽:“搞對象沒有啊?哪兒的?人咋樣啊?”不怎么嘮工作的事。(訪談材料C20130107)
3.親子角色差異與路徑依賴
但是,文化傳統一方面賦予父母以資源提供者的身份,同時也使其獲得了對子女的天然優勢。這不但體現在倫理和情感上,也體現在理性的計算上;而且由于親子間影響的長期存在,子弟本人對父母長期為自己設計的學業及職業規劃已經形成了路徑依賴,很難予以抗拒:
我爸的決定誰也不能拒絕,你是不知道我爸,絕對全廠第一辯手……他不是強制,他是說服。(訪談材料B20130131)
而且還考石化吧。因為我要是別的專業挺難的,畢竟大學這個學著呢。(訪談材料D20130125)
最終,子弟本人與其父母在根本態度上形成了契合:子弟們并不否認“有飯吃”是就業的首要目的,亦不否認回流后將獲得的正是這碗還算不錯的“飯”。以至于B君就曾這樣自我反思過:“(雖然)自己被安排、被建議,覺得不甘心,其實呢,我爸想的還是比我多,也為了我好,我沒什么好抱怨的。”因此盡管工業設計等更高層級行業早就取代了子弟們心中“原本應該是”石化行業占據的就業首選,但在父母的壓力下,他們終將有意無意地在就業選擇中摻雜進后者的主張,“跳級”從此很難得以順利實施。
(三)場域斗爭的深化:三方主體的交互博弈
不過,此種親子間的博弈又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級別的制約:一方面,W公司的新政策將子代教育水平視為重要的評價標準,成了回流路徑中最“硬”的指標和最“窄”的瓶頸。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客觀世界的影響,W場域在以回流政策為表征的常規邏輯背后,還存在著另一套難以為人所知的隱秘規則,即我們平時所稱的“走關系”、“走后門”、“花錢(就業)”。在這套邏輯中,行政級別越高的行動者,其獲取與調用資本的能力顯然就越強,在公開規則外安排子弟回流的能力也就越強;由于傾向于讓子女回流的員工往往處于行政序列的下層,因此父代行政級別在其中的限制作用實際上表現得相當強烈。其外祖父生前曾任W公司副廠長的C君就表示:“我姥爺要還在職的話,我還考研?!我都不念!興許能費點勁,但肯定能進。”特別地,上述兩個限制性因素的根源均來自W公司!這充分體現了子弟與公司間的隱性互動模式,說明場域作為一個運作空間總是能夠對所有相關對象的行為有一定作用。
(四)場域斗爭的妥協:對“保底”與“跳級”并存局面的解釋
由此,該場域的三方主體既熱衷于通過策略斗爭為自身爭取利益,又在這一過程中被場域的內在邏輯所形塑,被其他主體所影響。W公司的回流政策改革限制了子弟的大規模涌入,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職工的“鬧事”隱患;子弟父母的主張能夠充分影響子弟本人,但不能從根本上反對W公司的政策,同時又受到教育水平等要素的制約;子弟本人在就業觀念與傾向上有著明確的個人偏好,但又難以完全違背父母的主張。
因此作為一種妥協,子弟們一方面考慮按照新政策的要求應聘入廠工作,但同時仍保持指向場域外的其他就業傾向,即形成“保底-跳級”并存局面。
五、結語
綜上,石化子弟的回流就業現象呈現出“保底”與“跳級”并存的特征,即將回流與高層級行業崗位分別置于就業選擇的末尾與首位,一旦機會成熟則放棄回流而向高層級流動。這既是個人實現就業利益最大化的主體策略,又源自維持就業場域斗爭均勢的各方妥協。期間,回流就業將受到職業觀念、行業歸屬感、子代教育水平和父代行政級別等因素的影響,在就業機制上主要體現為:第一,文化資本的代際傳承已經很難成為父代影響子代職業地位獲得的方式;第二,父代的經濟社會資本可能對子代就業觀念的形成具有一定作用,并間接影響后者的職業地位獲得(即“跳級”);第三,“回流入職”等就業優惠政策成為階層再生產最簡便直接的方式之一。三者綜合反映了當今社會職業選擇模式的變遷趨勢:以文化和情感為紐帶的原始職業選擇已基本消亡,以單位和行業為中介的傳統職業選擇正逐漸弱化,但仍發揮一定作用,而突出主體意愿和個性的新式就業正在快速發展,“保底-跳級”的并存局面就是后兩者間沖突的妥協。
從傳統單位制企業的角度看,漸進的、調控的、策略性的改革確實有助于它們在保證穩定的前提下推動人力資源轉型。但是,由于難以完全擺脫職工的文化與情感依賴,現代管理制度發育不良,致使改革后的回流就業仍是一種憑借先賦身份和政策壁壘來擠壓其他勞動者進入該行業的機會空間、最終實現規避就業風險和向更優行業流動的就業策略。可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職業地位差異仍將是個人屬性與單位或行業集體阻隔共同作用的結果。為此,今后在國企轉型和單位制解構進程中,應特別關注集體層面的就業政策改革,以便更有效地打破就業藩籬,推進就業問題的解決。
[1]胥仕元,李慕白.論國有企業職工子弟就業世襲問題——從國企的國家性和企業性矛盾談起[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0(3):121-122.
[2]劉建明,張明根.應用寫作大百科[G].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
[3]梁志全.論職業世襲對青年發展的重大影響——兩代青年就業方式的比較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1(5):21-25.
[4]張翼.家庭背景影響了人們教育和社會階層地位的獲得[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4):82-92.
[5]王立波,馬丹.轉型期遼寧代際職業流動研究[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52-55.
[6]高舒.家庭背景對重點大學畢業生初職地位獲得的影響[D].復旦大學,2009.
[7]張瑞玲.農村居民代際職業流動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調查[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36-41.
[8]謝宇.認識中國的不平等[J].社會,2010(3):1-20.
[9]Bian Y.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M].New York: SUNY Press, 1994.
[10]李晚蓮.社會變遷與職業代際流動差異:社會分層的視角[J].求索,2010(6):62-64.
[11]李煜.家庭背景在初職地位獲得中的作用及變遷[J].江蘇社會科學,2007(5):103-110.
[12]張樂,張翼.精英階層再生產與階層固化程度——以青年的職業地位獲得為例[J].青年研究,2012(1):1-12.
[13]周旋.當代單位意識的延續及困惑[D].吉林大學,2012.
[14]梁巖.職業代際流動研究路徑與最新進展[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12(2):35-40.
[15]吳愈曉.社會關系、初職獲得方式與職業流動[J].社會學研究,2011(5):128-152.
[16]樂國林,張麗.大學排名對高校影響的社會學分析——基于布迪厄場域、資本理論的探析[J].現代教育科學,2005(3):37-39.
責任編校:汪沛
“MinimumGuarantee”and“AdvancedPlacement”:AFieldAnalysisofReverseEmploymentofWorkers’OffspringinHigh-incomeIndustries
LIU 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reverse employment, existing among workers’ offspring with intern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minimum guarantee and advanced placement, which means that the offspring try to move to advanced industries with the minimum employment risk. As a result of compromise over the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employment, reverse employ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employment concept,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offspring and the executive level of their parents. It reflects the change of personal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employment equity.
high-income industries; backflow of the offspring; employment; perspective of field
2014-02-24
劉偉,男,遼寧錦州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
時間:2014-8-28 15:45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04.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04
C913.2
A
1003-4730(2014)04-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