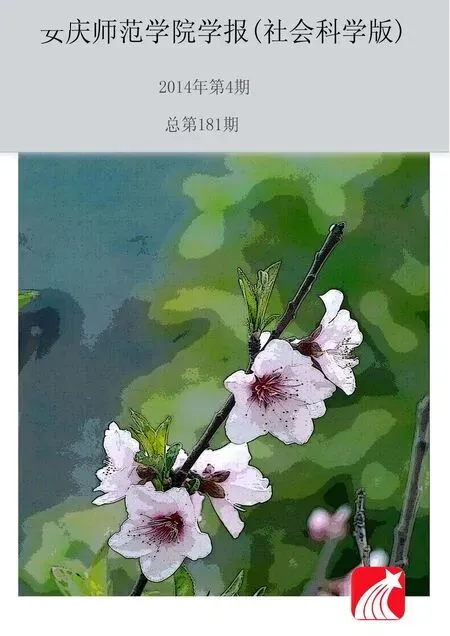郭象對《莊子·齊物論》的自然詮釋
路 高 學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1)
郭象對《莊子·齊物論》的自然詮釋
路 高 學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1)
“自然”一詞在郭象的詮釋體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郭象在《齊物論注》中,通過對“吾喪我”的自然詮釋,展現了物自然其所然的形態;用物的自然之境來觀照人,強調人的自生自是;用自然來詮釋名教,強調人應“各當其分”;用自然來批判社會文化現象,否定社會文化上的是非紛爭;用自然來詮釋“道”,強調“道”之自然“獨化于玄冥”。郭象對《齊物論》的自然詮釋,是其自然哲學體系中的核心環節。
齊物論;物;自然;詮釋;道
郭象的《莊子注》(學界對于《莊子注》的作者是郭象還是向秀存在著爭議,本文無愿去考證其中的糾紛,默認今本《莊子注》為郭象作品)遵循道家“言不盡意”的傳統,采用“寄言以出意”(《莊子注·山木》)的方法,在注解《莊子》的同時,闡發郭象自己的哲學思想。后世有言:“無者云: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卻是莊子注郭象。”(《大正藏·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今人劉笑敢認為,郭象通過對經典的詮釋“提出了許多新的哲學概念和命題”,賦予了經典“新的生命力和時代性”[1]。而《齊物論》作為《莊子》一書中最為艱深晦澀的篇章,自然是郭象詮釋的重點。
一、自然:自然其所然
郭象在詮釋《齊物論》的過程中大量使用“自然”一詞,其思想主旨也被學者稱為“自然的存有論”。[2]163因此,筆者擬以“自然”一詞為切入點,對郭象對《齊物論》的詮釋進行探究。在道家的思想體系中,“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其獨特的含義,與我們今天所使用的“自然”有著非常大的差異。如今我們所使用的“自然”一詞多指與社會領域相對的自然界,具有濃厚的客觀意義。而在中國傳統道家的理論旨趣中,自然是指“精神生活上的觀念”,“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無所依靠”[3]。在魏晉玄學家那里,“自然”是與“名教”相對的一個概念,“是指人物之‘自生、自得、自由、自順其性,而非由外物使其必然如此如此然’”的情態之辭[4]568。
郭象在注解《莊子》中多次使用“自然”一詞,其中內七篇注中有64次,僅《齊物論注》中就有19次之多。而《莊子》內七篇中“自然”一詞共出現2次,分別在《德充符》篇和《應帝王》篇。由此可見,“自然”在郭象《莊子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要理解“自然”一詞,首先應從認識“然”開始。“然”,古同“燃”,是指燃燒的意思,后來又衍生出肯定、合理之意,也可以作為形容詞詞尾表示“……的樣子”[5]。唐君毅根據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記載,認為:“此‘燃’之一字,依說文謂從肉(月)在火上,而犬在其旁,即有然悅、肯可之義;而火之炎上,即有生發之義。故用為‘火之始然’之然。”[4]567因而“自然”,顧名思義,即為自始之然。老子有言:“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這里所講的“自然”應是人與萬物“自順其性”、“自生其所生”、“自由其所由、自得其所得”的“自然其所然”[4]567。而莊子所講的“自然”,強調主體的普遍性、能動性。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調情。吾所調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莊子·德充符》)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氣于漢,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莊子·應帝王》)
莊子注重人的心靈解脫,“恒指點吾人能不安不忍,于成心之茫昧陷溺中超拔出來,調適上遂,以安頓吾人之身心性命,自適其適,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一心之真淳徹達,是重主體實踐的主要內容。”[2]164
“自然”一詞在郭象《齊物論注》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學者根據郭象所詮釋的義理,把他的思想歸為“自然的存有論”,認為他“論自然,除了老、莊所特重的自然之主體義之外,舉凡命遇奇偶、才知之小大,運會之盛衰、事物之形勢逆順、倫常之尊卑分際等,率皆歸屬于自然”,遠遠地超越了前代[2]163。郭象繼承王弼等玄學家關于“自然”的觀點,通過注解《莊子》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強調人與物的特殊性和個性,擺脫了莊子過分強調主體而忽視個體的客體意義的束縛,注重個體各自的“自然其所然”。這種發展使道家的“自然”學說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按錢穆的說法:“必俟有郭象之說,而后道家之言自然,乃始到達一深邃圓密之境界,后之人乃不復能駕出其上而別有所增勝。”[6]
從重心之主體義到重人、物的個體義,從重主體的能動性和普遍性到重個體的特殊性和限制性,道家的“自然”學說發展到郭象這里到達一個更為完滿圓融的境界。郭象也正是以這種圓融的“自然”觀來詮釋《莊子·齊物論》。
二、“重明天籟”:對物的自然詮釋
莊子在《逍遙游》中描繪了一個“游”的極致境界——“逍遙”,并把它歸為自然而然的“道”,鑄就了《莊子》一書的靈魂和基調。《齊物論》上承《逍遙游》之精神主旨,郭象以“吾喪我”的“天籟”之境中的“自然”旨趣為切入點,展開了對《齊物論》的自然詮釋。
在進入郭象對《齊物論》中物的自然詮釋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他對“齊物論”的解釋。郭象言: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7]48
郭象認為萬物都有一種自我的中心主義:“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這里講的“物”應該囊括世間的一切,也包括人在內。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我的放大,人為地賦予了人外之物以人的情感,也是一種人作為主體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表現。可是,郭象又說“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認為萬物雖然有差異但都是一樣的,明顯是要萬物破除“是非”的偏見,認識到它們本質上的一致之處。所以,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如果“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都是萬物都具有的,是不是一種“均”呢?要如何來破除呢?
莊子在《齊物論》中首先通過子綦和子游的對話為我們呈現了一種“天籟”之境。子綦曰: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莊子·齊物論》)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莊子·齊物論》)
莊子形象地描繪了風所產生的不同形態,用來表示萬物產生的根源,指出了各種現象都是產生于物之自身的。馮友蘭認為莊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提出“怒者其誰邪”的問題,而是要取消問題,因為“‘自己’和‘自取’都表示不需要另外一個發動者”[8]。而郭象認為:
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而,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7]55-56
郭象是從存在主義的角度把物的“生”看成是其自然而然的結果,而且把這種現象稱為“天道”。而實際上,“天籟”只不過是人的一種主觀的“吾喪我”之后的精神狀態,是意識的主觀產物,并不能代表事實即為如此。郭象緊緊抓住了莊子講的“天籟”之意,把它從一種個體的主觀體驗擴大到任何一物,認為物的存在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天籟”,他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7]56
郭象所理解的“天籟”和莊子的原意是有差異的。莊子側重于主體主觀上的境界感知;而郭象則側重于個體的存在現象。
綜上所述,《齊物論》是從對“物”的理解開始,把“天籟”之境看作是“物”自然而然的結果——無所生,也無所用。郭象也正從對“天籟”的“重明”進入到對人、社會文化以及“道”的詮釋。
三、“言其自生”:對人的自然詮釋
在郭象看來,莊子所言之“物”是包括世間一切的,當然也包括人及人類社會。這是道家學說一以貫之的觀點。當然,如此之說并不代表道家不言人與社會。道家思想的一個傳統就是以物*此物指與人和社會文化相對之物。之自然主義來觀照人,來批判社會文明,來否定社會文化。
在《齊物論》中,莊子通過對“天籟”之境的論述轉向了對人的理解,莊子曰: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斗。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執,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莊子·齊物論》)
莊子在這一部分對“大”、“小”兩種人不同的心理情態進行了生動的描述,說明人雖有才智、德行等不同,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樣的,都是“莫知其所萌”。馮友蘭認為莊子“是用形象化的語言寫心理現象的千變萬化”,講的是人的主觀世界[8]。而這種人之主觀上表現出的“縵”、“窖”、“密”等精神情態,都必然會表現出差異性的恐懼之心、是非之心。這樣的人就像自然之物到了秋冬季節就會衰敗一樣,最后都會衰亡;他們沉溺于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能回復如初;他們“厭沒于欲,老而愈恤”;他們有“耽滯之心”,心靈閉塞受到束縛而不能得到解脫。[7]59在莊子看來,這些“喜怒哀樂,慮嘆變執,姚佚啟態”的各種心理情態,就好像“樂出虛,蒸成菌”,而那些“大知”、“小知”之人卻沒有認識到他們為什么會是這樣的。
郭象基本上同意上述莊子對人的心理情態的描述,但是在如何破除這些情態的困擾方面兩人的觀點略有不同。郭象通過承認個體的差異性,強調個體的不同,正如其言:
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7]60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7]60
郭象把人之個性、情態的不同,也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是謂“言其自生”[7]60。
郭象從莊子主觀的否定態度轉向了對個體存在的肯定態度,以“無方之自然”實現了對人之“形雖彌異,其然彌同”的自然詮釋。郭象把世間的人與物都歸為“自然”,同時也否定了個體的主觀意志,就如其在對《德充符》注解中所說的:
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7]205
郭象把生命中的一切都歸為自然的結果,包括人的出生以及存在在內,都不是人的意志所能管控的。這是不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呢?
從表面上看,郭象的自然哲學在論述人的時候去除了人的主觀意志,或者說把人的各種存在形態也看成是自然而生的結果,具有宿命論的傾向,但是他的根本旨趣是通過強調自然無為的工夫來達到某種玄冥的境界,是一種除卻人之歡樂憂愁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不僅表現在對人事現象的認識上,而且更為突出地反映在對社會名教的詮釋方面,而這才是郭象自然哲學的最終導向。
四、“各當其分”:對名教的自然詮釋
在道家思想里,物性和人性是沒有分別的,都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郭象和莊子一樣,從“吾喪我”的“天籟”之境來理解人的存在樣態,把人看成是與物一樣完全稟受自然之理的存在物,從而否定了個體的主體性。但所不同的是,莊子對名教也采取了完全否定的立場。而郭象卻通過承認個體的特殊性對名教的存在進行了合理性論證,提出了“各當其分”的主張。
在《齊物論》中,莊子對是非彼我和現實的禮法關系持有一種批判態度,提出一種無是無非和無君的主張,其言曰: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莊子·齊物論》)
郭象認為,莊子所講的“彼”為“自然”,而“自然生我,我自然生”,由自然而生的“我”完全稟受自然之理,并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因此,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目的[7]62。正如成玄英所說:“信己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7]62然而,人的這種“信己”而行是看不到的,所表現出來的只是“情智”。在莊子看來,人終生稟受自然之理,但是一旦有了是非之心而“與物相刃相床靡”就會“終身役役不見其成功”,就會“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這是非常可悲可哀的,這樣的人活著和死了沒有什么區別。而郭象則認為:“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7]63郭象也正是在這種“自然”狀態下采取了肯定的態度,他說:“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而他所反對的是臣妾不各安其才而“上下相冒”[7]63。
從郭象對名教的態度來看,他一方面承認自然的名教,并維護名教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又批判異化的名教,反對名教的“上下相冒”,主張“各當其分”。郭象言:
皆說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7]63
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7]63
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7]64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于當而必自當也。[7]64
在郭象看來,君臣、妻妾各有其位,各有等級的差別,都是天理自然的,是不能僭越的。然而,郭象不是對現實名教一味地肯定,而是主張“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主張在人與人之間有一種才性之分,人人應各安于其性,而這種性是自然自生的。因此,從整體上來看,郭象所支持的是“賢者為君”;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不賢者就不能為君。從理論上看,這是郭象對名教的一種理想主義態度;而從魏晉時期的政治生態來看,郭象的名教思想又有強烈的現實指向。可以說,郭象的自然哲學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種集中反映,是以道家的自然主義精神對現實政治形態進行了一種合理性的證明,正如其言: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7]303
郭象一方面強調“明王之功”,另一方面又強調“無為”、“自任”,但是最終還是著重強調道家的“無為”。
綜合前述,郭象的名教觀和他的自然哲學是密切相關的。郭象的自然哲學一方面繼承了莊子對現實禮法的批判精神,對現實名教中的不合理現象進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通過強調個體存在的特殊性而把名教中的倫常制度、禮節秩序看成是天理之自然,強調各依其才、各安其位,“無為”而“自得”,又為魏晉時期的政治生態提供了合理性的證明,已和莊子的旨趣十分不同。
五、“無是無非”:對文化現象的自然詮釋
郭象在《齊物論注》中除了論述社會倫常的名教之外,對文化現象也進行了詮釋。莊子在《齊物論》中把人看成是與物一樣完全稟受自然之理的存在物,否定個體的主體性,并進而對文化現象也采取了否定的態度。按照勞思光的觀點,莊子是從“情意我”的角度對“認知我”進行了否定,認為知識的存在是無意義的[9]。而郭象則通過 “彼我”之“反覆相喻”、“相明”,論證了萬物皆“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強調“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無非”[7]75,并由此指向了莊子“道通為一”的境界。
莊子把“言”與“吹”相比,認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莊子·齊物論》)。莊子是把文化現象與自然現象相比,用自然現象中物的“自然其所然”來觀照社會文化。他認為社會上的各家各派都是以自家之說為“是”而以他派學說為“非”,如其言曰:“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他不但把儒墨各家的言論都看成是“浮辯之辭”,而且認為他們是違背“道”的結果,因此主張泯滅“是非”,對文化現象持有否定態度。而郭象沒有持明確的否定態度,而是主張通過儒墨之“反覆相明”來宣揚“無是無非”,其言曰: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7]70-71
在郭象看來,是非之言皆是“彼我之情偏”的結果;有“彼我之情偏”,則有“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7]68。如此,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一個統一的言論。然而儒墨之士又據己之言以為有。郭象言:
夫小成榮華,自隱于道,而道不可隱也。則真偽是非者,行于榮華而止于實當,見于小成而滅于大全也。[7]70
郭象一方面肯定了儒墨之言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是“隱于道”的,不是真正的 “道”。如此,郭象就超越了社會文化的是非紛爭,主張一種“無是無非”的文化觀。
郭象所持有的文化觀是對莊子文化觀的一種詮釋,是其自然哲學邏輯演進的自然結果,與莊子本人的觀點有一定的差異。莊子曰: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莊子·齊物論》)
莊子認為物本來是沒有是非之分的,但是人卻往往各持己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不能認識到各自只是偏安一隅、各執一詞,由此也不能真正地理解“道”。在莊子看來,真正的“道”是沒有是非紛爭的,只有圣人才能真正準確理解和把握“道”,才能“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對此成玄英認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于天下”,才可以“得道樞要”而“會其玄極”[7]73。而郭象則認為:“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7]74在郭象看來,是非之爭即為“環”,而作為“道”之“樞”的“環中”即是“無是無非”。郭象與莊子在文化觀上的差別主要表現在其特別強調“物”之“自是”,其言曰:
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7]72
郭象把“物”之自是、自性普遍化、絕對化,強調個體存在的普遍意義,主張一種“無是無非”的“玄同”狀態。從根本旨趣上看,郭象和莊子的文化觀是一致的,都主張去除是非紛爭,到達“道通為一”、“玄同彼我”之境。
由此,郭象的自然哲學從物的自然主義起,完成了對《齊物論》所論及的文化現象的自然詮釋,進入到“道”的詮釋。
六、“獨化于玄冥”:對“道”的自然詮釋
“道”是道家學說中最為核心的概念,代表了終極真理。與郭象重視個體自然的特殊性不同,莊子重主體普遍的能動性。莊子在《齊物論》中經過對物、人、名教和社會文化的論述之后,指向了對“道”的理解,主張“道通為一”。
莊子“道”的境界集中體現在“自得”一詞。“自得”與“自然”意思相近,代表了莊子的逍遙之心:“逍遙游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莊子·讓王》)。莊子曰: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莊子·齊物論》)
從中可以看出,莊子所講的“道”是“已而不知其然”,即強調主體的主觀感覺,通過主觀破除“成”、“毀”之心,使主體從成心執著中超拔出來,認識到“物無成與毀”,也就是“道通為一”,也就是莊子《齊物論》的主要意旨。而在郭象看來,“道”是“不知所以因而自因”的[7]78,也是自然其所然的,其言曰:
夫莛橫而楹縱,厲丑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丑、恢詭譎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7]76
由“理雖萬殊而性同得”可知,郭象是從自然之性分來說齊一的。郭象認為,萬物之“縱橫好丑、恢詭譎怪”,都是自得的。因此,所謂“齊”或“道”之一,指的都是物物各是其所是,自然其所然。由此可知郭象與莊子二人對“道”理解的巨大差異:莊子“由心上做工夫,欲由成心之執超拔出來,無執無滯,則物論可齊”[2]174,強調的是主觀上去除分別之心的“齊”,是一種“道通為一”的精神境界;而郭象則主張物性皆自然自得之“齊”,強調個體自然而然之“道”。
郭象對自然而然的“道”的理解,最突出地表現在“獨化”一詞。何為“獨化”?萬物“自然其所然”,即為“獨化”。 郭象言: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后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于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也。[7]117-118
“獨化”在此處說得非常明白:第一,“物各自造”,沒有一個造物者的存在;第二,物“無所待”,是共生共成的;第三,物是自然“獨化”的,“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這也就是說,郭象否定了萬事萬物背后有一個創造他們的主宰之物,把物看成是自生的,而且萬物之間也不存在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是共生共在的。猶如海德格爾把“存在者”看成是“涌現著的在場”的自然“存在者整體”,“讓存在者是其所是”[10]。如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郭象的態度:他是把萬物之間的關系看作是自然的關系,強調個體的存在意義,以個體的論述為核心,認為應“各反所宗于體中而不待乎外”,也就是“獨化于玄冥”。
“道”在郭象的思想里不是一個“造物主”的形象,也不是一個空無的概念,而是指一種無能無為的存在樣態。而“獨化”,正是對這種存在樣態的生動詮釋。而對于“獨化”與“道”的關系,郭象在《大宗師》中說的更為確切,其言曰:
道,無能也。此言得之于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于道,內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7]252
郭象把“道”看成是一個無能、無為的存在,但不是不存在,是存在的無;把物之“自得”稱之為“道”的體現,但又不依賴于“道”,而是由“自得”而“獨化”的。
郭象從“獨化”的角度詮釋了自己對“道”的理解,強調萬物個體的自然之道。“獨化于玄冥”所指向的即是萬物自我實現的最高境界;同時否定了事物外部有一個“造物主”的存在,也否定了事物自身可以有肆意妄為的情識之偏。
郭象在《齊物論注》中所詮釋的哲學思想,是其自然哲學體系的核心環節。這也充分說明,郭象的哲學思想具有十分突出的個人特色,不能將它只視作簡單的注解。
通觀郭象的《齊物論注》,“自然”是其哲學思想中的核心概念。郭象的“自然”觀與其對物、人、名教、文化、道的理解密切相關,彼此交融,貫穿了郭象思想的始終。而且在“自然”觀的引領下,萬事萬物融為一體,最終走向了道之“獨化于玄冥”的最高境界。
郭象由自然論齊物,就不可避免地強調個體的特殊性;同時,它也否定了個體具主體性的可能性。郭象一方面重主體之能動的普遍性而否定個體存在的主體性,是對莊子思想的一種繼承;另一方面又承認個體存在的特殊性,強調個體存在的自然意義,是對莊子思想的一種發展。
[1]劉笑敢.經典詮釋與體系建構——中國哲學詮釋傳統的成熟與特點芻議[J].中國哲學史,2002(1) :32-40.
[2]莊耀郎.郭象《莊子注》的性分論[C]//洪漢鼎,傅永軍.中國詮釋學(第五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3]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3.
[4]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M].北京:中國社會科出版社,2006.
[5]王力,岑麟祥,林濤.古漢語常用字字典 [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22.
[6]錢穆.莊老通辨[M].北京:三聯書店,2005:426.
[7]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2.
[8]馮友蘭.三論莊子[J].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1(4):21-26.
[9]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97.
[10]海德格爾.路標[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18-219.
責任編校:汪沛
2014-02-24
路高學,男,河南新鄭人,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時間:2014-8-28 15:45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18.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18
B235.6
A
1003-4730(2014)04-00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