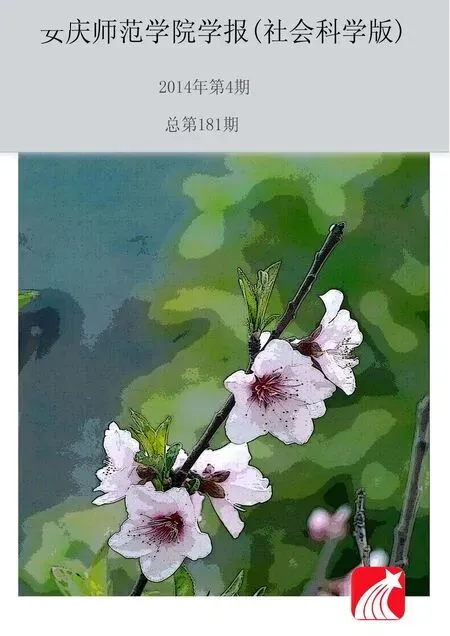方文“嵞山體”及其對清初詩壇的影響
宋 豪 飛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方文“嵞山體”及其對清初詩壇的影響
宋 豪 飛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方文是明末清初桐城著名詩人,明遺民詩人的杰出代表,在詩壇享有極高的聲譽。其詩自成一家,被稱作“嵞山體”,創作內容豐富,突出表現在抒發強烈的遺民情懷、反映現實、感時紀事等方面;在藝術上表現為語言通俗流暢、淺顯如話,所抒發的情感真誠直率等特色。“嵞山體”在清初詩壇多受褒揚,占有一席之地。
方文;嵞山體;遺民詩人;清初詩壇
清初詩壇呈現較為繁榮的局面,緣于由明入清詩人之創作,其中就包括人數眾多不仕新朝甘當遺民之詩人群體,他們成為清初詩壇的創作主體,代表著清初詩歌的最高成就[1]。明遺民的詩歌作品真實反映出鼎革變亂時代的社會現實和人生際遇,為研究明遺民文學提供重要文本。明遺民的詩歌創作與成就,關乎對清初詩壇之影響和在清代詩歌史上的地位等重要問題的評價,頗具探討之意義。今學界對明遺民之相關重要人物的行藏出處、心態變化及其文學成就等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于其生存狀況和清初文學生態等考察亦較為深入。但筆者以為,還有一位明清之際振羽詩壇的著名詩人方文值得重視,他理所當然可以視為明遺民之典型代表之一,其詩歌創作數量極其可觀,內容豐富,獨具特色,被稱作“嵞山體”,于清初詩壇影響頗大,然后世竟至湮沒無聞。今李圣華編訂《方文年譜》,對其生平行實考訂翔實,為研究方文生平及其詩歌提供了莫大的便利。謝正光寫有《讀方文〈嵞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實小議》[2],對方文生平及方氏家族家風予以考述,可以參考。至于其詩歌創作之研究,則見諸嚴迪昌所著《清詩史》。此書列有專節,從遺民詩界的視角分析了方文反映時事的一些作品,為認識和研究這位明清之際創作成就卓著的詩人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并肯定方文于清初詩壇理當擁有一席之地。但與其詩歌成就相較而言,學界的研究明顯不足,“嵞山體”的藝術特色及其在清初詩壇的地位和影響尚需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
一、“嵞山體”之得名
方文(1612-1669),初名方孔文,字爾識,后更名文,字爾止,明亡后,更名一耒,號嵞山、明農、忍冬、淮西山人,諸生,江南安慶府桐城人。方文于明末清初詩名顯赫,“以詩名家者三十年”[3]902,“聲震天下”[3]897,《康熙桐城縣志》稱其“性豪宕不羈,聰穎過人,幼工文詞,所交多天下俊彥。以棘闈數奇,博覽名勝,詠吟不輟,后學推為宗匠”[4],然后世聲名埋沒,不免令人嘆惜。
方文一生刻意為詩,所作不下六千首,詩文合集五十卷,惜未傳世。其婿王概(字安節)搜其詩作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刻《嵞山集》及《嵞山續集再續集》,錄詩二十一卷計二千三百多首傳世。今有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本《方嵞山詩集》由黃山書社于2010年出版,為深入研究方文詩歌提供方便。
其詩體裁多樣,詩集依年編訂,詩人紀事紀游,抒情寫景,可視之為人生寫照,行藏出處的真實記錄。方文以詩歌見長,抒真情寫實事,語句淺俚易懂,“其為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為纟希章繪句之工”[5],所作皆嘔心瀝血所得,自成一家,被稱為“嵞山體”。今略加探究“嵞山體”得名之由來。
方文同邑同時代之著名詩人潘江最為稱賞方文之詩歌,他寫有《王子安節以〈嵞山續集〉見貽,即效“嵞山體”賦以志感》[3]916一詩,詩題中即直接稱之。雖然此詩是潘江贊嘆王概傾力搜集刊刻其岳丈方文詩歌,以唐代李漢于韓愈去世后為之刻集事相類比,而非評價其詩。潘江于《跋〈嵞山續集〉后》還有詩一首:“有明著作最權奇,熙甫文章爾止詩(自注:予嘗謂太仆古文、嵞山詩皆淡不可及)。淡處盡教耐思索,太羹元酒少人知。”[3]915他認為歸有光之文與方文之詩最為突出的特點皆在于“淡不可及”,為有明一代文學之奇觀。當然,潘江對方文詩歌的總體評價較高,于其詩歌創作特色的認識也較為客觀。由此可知,在潘江看來,方文詩歌已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個性,有其特殊的審美意蘊和價值,可以自成一體,在詩壇上擁有一席之地。
除潘江所稱“嵞山體”之外,還有“爾止體”之說。李雅《程松皋、方東來餉金刻集,猶吳錦雯之捐俸刻方爾止詩也,作此謝之,即仿“爾止體”》(《龍眠風雅續集》卷十五),于詩題中即直接言明“爾止體”,與潘江所稱“嵞山體”意思應是相同。
今筆者所見文獻明確以“嵞山體”或“爾止體”指稱方文詩歌者僅此數例,或不能由此證明“嵞山體”之名廣為流傳,且未必為詩壇普遍認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清初詩壇雖未徑直稱“嵞山體”,但均意識到方文詩歌獨具風格和個性特征,則是不爭的事實。潘江寫道:“一時詞坫耆宿若錢牧齋、林茂之、施愚山、孫豹人、宋玉叔、王涓來、顧與治、王阮亭、紀伯紫諸公盛相推許,以為必傳。”[3]894與方文同時代的這些著名詩人都與方文交游密切,情誼深厚,彼此詩酒唱和、往來酬答,或為其詩集作序,皆盛贊其詩,都認為方文詩歌“必傳”,正是對方文詩歌創作特色及其價值的認識和贊同。其以詩存史,以詩寫心,真實地展現了明清之際的時代風云變幻、詩壇面貌和遺民心態,語言平易曉暢,別具一格。
與其同時,詩壇上亦各體紛呈,如吳偉業“梅村體”、王士禛“神韻體”、施閏章“宣城體”等,各具面貌,顯名詩壇。“嵞山體”與之各有所長,足相匹敵,卻未能與之并傳于世,可謂不幸。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六月,《嵞山集》為安徽巡撫裴宗錫奏繳禁毀,二年后《嵞山續集》為浙江巡撫三寶奏繳禁毀。其后厄運不斷,各地均紛紛奏毀詩集,致湮沒二百余年,詩名不傳,迄今未能為人所廣知。
二、“嵞山體”創作之內容
方文詩歌創作題材豐富,內容相當廣泛,舉凡贈別、紀游、敘事、詠史、詠物、感懷等均記之以詩,尤以紀游贈答詩為數最多。這類詩歌真實記錄了詩人的行藏出處和交游圖景,為讀者了解明末清初文人群體的生存狀況及心態提供了重要的文本。限于篇幅,本文對此類詩暫不展開探討。除此之外,方文“嵞山體”創作內容還突出表現在,其詩抒發強烈的遺民情懷、反映現實等方面,茲略加論述。
(一)詩歌抒發遺民情懷。桐城桂林方氏自宋末元初遷居桐城,至明初科第起家,歷代簪纓不絕,漸至門第興盛,成為江南著名望族。方氏世受國恩,對朱明王朝有著深厚的眷戀,“吾家十世主恩深,父祖嘗懸報國心”(方文《送三兄仁植先生開府武昌》),所以一旦明朝滅亡,方文悲痛不已,絕不出仕新朝,甘當遺民。作為一個遺民詩人,方文最為典型的心理,即哀思故國,其遺民情結至深至誠,至死未改,發之于詩,哀切悲戚。
方文此種哀思故明情結,突出表現在每年三月十九日即崇禎自縊、明朝滅亡之日,必哭祭且歌之以詩,傾訴其憤慨悲痛之情。乙酉年(1645)他在鎮江與幾位友人登北固山哭悼而寫下《三月十九日作》,眼前所見景物是“烈風吹黃沙,白日黯無光。江水聲震蕩,草木零芬芳。莫春景物佳,何為倏悲涼”,對大明滅亡悲痛不已,“小臣本微細,憤懣結中腸。陟彼西山顛,涕泗瞻北荒。奄忽歲已周,哀情若新喪”[3]25。
康熙八年(1669),即其病逝之年是日遇錢馭少,寫下《三月十九日作》:“野老難忘故國恩,年年慟哭向江門。南徐郭外三停棹,北固山頭獨愴魂。流水滔滔何日返?遺民落落幾人存?錢生未死重相見,雙袖龍鐘盡血痕。”[3]831方文自明亡至辭世,凡二十五年,見諸《嵞山集》中題為三月十九日所作存有八首,如“年年此日淚沾纓,況是今年寓北平。……猶有野夫肝膽在,空山相對暗吞聲。”(《三月十九日》)“啼鵑又過一年春,每到今朝倍愴神。南詔也歸新負版,西山誰問舊遺民。”(《三月十九日巨野道中》)確是年年“縱使海枯還石爛,不教此恨化寒煙”(《三月十九日作》)。這種郁積內心近乎凄厲的故國哀思,濃烈而又沉痛,終其一生,不曾改變。
甲申明亡之年除夕,方文作有《除夕詠懷》四首,其第一首:“除夕年年不忍除,今年除夕痛何如。先皇玉歷五更盡,文祖金城九月虛。江左重瞻新氣象,墻東無改舊門閭。藏書遍寫崇禎字,每歲開函淚滿裾。”即抒發亡國之哀痛。亦是此年,他寫有《宋遺民詠》十五首,歌詠宋遺民十五人,以表明自己“甘心隱遁,不復萌仕進之念”,使人知“予志之所在”[3]17,就已經抱定隱遁之志,遺民終老,不仕清朝,態度極其堅決。他甚至想仿照徐渭作《四聲猿》雜劇,取宋末遺臣六事,演為雜劇成《六聲猿》“以泄其胸中不平”,但因“音律未諳”而作罷,只記以詩。方文“胸中不平”或許即是他在《舟中有感》詩中所控訴的:“舊京宮闕已成塵,寶馬雕鞍日日新。萬劫不燒唯富貴,五倫最假是君臣。詩書無恙種先絕,仁義何知利獨親。三百年來空養士,野人痛哭大江濱。”將此詩與他在甲申之年除夕所作《除夕詠懷》(其二)參照理解則意思更加明了:“降志但知夸衛律,渡江誰復慕劉琨。乘軒急乞新朝寵,對酒都忘故主恩。獨有野夫籬落外,長號不敢暗聲吞。”他極其鄙視那些紛紛邀寵仕清乞恩的明朝士大夫們,自己唯有仰天長號,痛哭不已。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戊申(1668)正月初四,正是三百年前朱元璋登基之日,方文又再次來到孝陵哭祭,伏地大哭,“拜罷不能起,泛瀾淚沾袂”(《戊申正月初四日恭謁孝陵感懷六百字》),竟至哀傷過度站立不起,許久方才離去。他的一腔忠心至死不泯,其遺民血淚死而后已。
他對歸降之臣、仕清之士,多有憤慨之言,對族中歸順、出仕新朝者亦有所不滿,于自己則絕意不仕,其《水崖哭明圃子留》(之四)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里門裘馬日紛紛,鸞鶴寧同雞鶩群。如以衣冠坐涂炭,不徒富貴等浮云。家人愚暗還相勸,異類腥臊孰忍聞?十世國恩蒙者眾,獨將破衲報明君。”他對異族的仇視,根本原因還在于方氏“十世國恩蒙者眾”,蒙受大明王朝恩典至深至厚,所以要為之盡節盡忠。他更不愿“試禮闈”,而且蔑視“輦下新朝服”。正如其《自題小像》一詩所作:“山人一耒字明農,別號淮西又忍冬。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后凋松。藏身自合醫兼卜,溷世誰知魚與龍。課板藥囊君莫笑,賦詩行酒尚從容。”其遺民之志非常堅定。
(二)反映現實之作。方文的詩歌感時而發,憂慮時事,記錄下時代的變幻風云,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為后人認識那段歷史提供了解讀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說,這類詩歌亦是“詩史”,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作,更具認識意義。
方文一生游歷四方,他用詩歌真實記錄下所親歷的動蕩戰亂的社會現實、民生凋敝的凄涼情景。如《泊蕪湖》:“蕪陰衰柳掛斜暉,亂后人家萬事非。官稅紛紜商賈斷,戈船絡繹市廛稀。”《泊魯港》、《泊紫沙洲》等詩亦如此。隨著滿清入主中原,在不斷向南推進過程中,清軍不斷掠奪百姓財物,圈占漢人土地,《遷安》即反映這種現象:“莫言邊令好催科,縣小民稀奈若何。一自投充與圈占,漢人田地剩無多。”《南潯嘆》則是對清軍于百姓財富赤裸裸掠奪的控訴:“南潯一村當一縣,財貨云屯商賈便。中間巨富者誰子,擁貲百萬人所羨。百萬金錢是禍胎,片時飛滅如浮埃。匹夫無罪懷璧罪,盡室誅夷亦可哀。”
方文的這類詩歌,不僅揭露了清軍的殘暴與掠奪,而且還反映了清初由于兵禍戰亂給百姓所造成的苦難,如《捉船行》:“吳閶一路兵捉船,榜人奔竄蘆葦邊。三日五日不敢出,夜夜驚呼那得眠。歸客蹉跎情自苦,況復秋風亂秋雨。荒洲無處覓飲食,紫芋紅姜噉少許。”作于順治十六年的《太湖避兵》(其一):“將近楓橋路,惟聞人語喧。北來兵肆掠,東去艇皆奔。震澤煙波迥,高秋風雨繁。此時期免患,艱苦復何論。”真實描寫了百姓為逃避戰亂或清兵“肆掠”抓捕而驚恐躲藏的情形。
作為一位優秀的詩人,方文還憂時憫農,關心農事關注民間疾苦。他因數月不雨而憂,寫下《憂旱》詩,而《喜雨》則是對天降大雨的滿腹喜悅之情。《谷賤》:“頻年苦旱今年稔,百事支分盡在田。豈料秋成農更苦,一擔新谷糶三錢。”描寫農民因糧食豐收卻遭受更大的貧窮。其詩集中也不乏對自然災害的記錄和描寫,如《大水嘆》就記敘了癸卯(1663)九月,金陵大水淹沒整座城池,百姓遭難的悲慘情景,詩人想到百姓今年冬天將不得不忍受饑寒,禁不住“嗟嘆為之久”。《紀災》則是對戊申(1668)六月江浙等地發生地震,暴雨如注,房屋傾倒的記載,對百姓遭受深重的災難深表同情。
三、“嵞山體”之特色及其成因
方文詩歌創作獨具風格,自成一家,被視作“嵞山體”,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語言通俗流暢、淺顯如話;二是所抒發的情感真誠直率。稱之為“真詩”,自是合乎其實。
其詩歌藝術特色之形成,蓋由于他對陶潛、杜甫和白居易三位大詩人詩歌創作風格的汲取與融合。其詩歌抒寫亂離悲憤憂慮時事,則傾向于效法杜甫沉郁頓挫的風格,多蒼老之作;自然渾樸,有陶詩真趣;天真爛漫,觸手成妙,近于白詩。事實上,他的詩歌合三家之長融于一體,于清初詩壇矯然不群,自具面目。
方文少年聰慧,尤擅長寫詩,明季即以工詩而顯名。他對陶淵明、杜甫、白居易三位大詩人心懷仰慕,故詩歌創作受之影響較深。他因自己與三人同屬壬子年生辰,故請武林畫師戴葭湄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一幅《四壬子圖》。圖中,陶淵明居中高坐,杜甫、白居易分坐兩旁,方文則手捧詩箋傴僂呈詩于前,俯首求教,此為文壇佳話。方文將此畫懸于室內,以此自勵,表明自己將承襲三子詩風,上邁先哲,直追大家。他不但以與三位大詩人同生壬子年而自豪,而且一再宣稱自己以之為師,如他在《初度書懷》(九首之二)詩中寫道:“昔聞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后香山翁,生年亦復爾。相去六十載,英名千古峙。我生幸同庚,性情復相似。酷嗜二公詩,詩成差可擬。杜猶拜拾遺,白直躋卿士。我老窮且賤,曷由繼芳趾。”《崔李行》詩:“有唐詩人累千百,我獨師承杜與白。……古今風雅有神契,況復俱生壬子歲。”他終生酷愛他們的詩作,研讀不倦,如《舟中漫興》寫道:“平生癖好惟三種,左馬文章老杜詩。”《夜讀白詩》:“門巷秋陰斷往來,階除晚霽獨徘徊。消愁唯有《香山集》,夜夜燈前當酒杯。”還有《元旦讀陶詩》等,皆明確表明自己對三位大詩人的偏愛。當然,方文也頗為自信,其詩可以與杜、白二人相比,“酷嗜二公詩,詩成差可擬”,不但得其形似,而且得其“神契”,“古今風雅有神契”,即貫注了詩歌的寫實原則和內在精髓。朱麗霞認為方文詩歌是“作為他反觀自我固守自我及與外界社會進行調適的忠實記錄,較之陶、杜、白則更具有現實性和真實性”[6]143,這樣的評價大體上是符合方文詩歌創作特點的。
錢湘靈題《嵞山續集》云:“壬子同年作者同,陶公杜公與白公。若修歲譜兼詩譜,又記嵞山江以東。”指出其詩風深受三家影響之實,且成就亦卓然可觀。朱則杰寫有《方文〈四壬子圖〉考論》[7],考論《四壬子圖》畫作者、為之題詞的詩人、畫作主題等具體情況,這將有助于深入探討方文的詩歌創作淵源。
“嵞山體”最為突出的藝術成就,正在于其效仿白居易詩歌語言,甚或以俚俗口語等入詩,“其詩任性靈,雖民謠里諺,涂巷瑣事,皆以入詩”[8],他將詩歌創作與民間語言形式相結合,吸納民間語言養料,淺顯易懂,真摯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跡。
現略舉幾首如下,以此感知他的詩歌語言淺顯易懂、明白如話之特點。如他的贈別詩《送沈治先歸皖》:“秋江同作客,春水又同歸。何事棲遲久?仍嗟生計微。對床聽夜雨,把酒問漁磯。坐惜沙邊鳥,乘風忽背飛。”《旅夜》詩,記事感懷:“客舍已凄苦,況聞風雨聲。一杯消永夜,孤燭坐深更。饑鼠分行出,寒雞失次鳴。此時心眼靜,歷歷悟浮生。”登山而寫有《攝山絕頂》:“下方惟見石,不信有柴荊。仄徑盤空上,危峰到頂平。夕陽千嶺秀,春水一江明。愁絕浮云外,蒼茫舊帝京。”其實,一部《嵞山集》詩歌的語言大體皆如此,可讀可解,從中亦可感知詩人誠摯淳樸自然純真之情。
方文詩歌善抒性情,樸素無華,讀來明白如話,于其時曾受譏評,以為淺俚可笑。其實不能由此視作粗俗膚淺,任意貶低其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價值。紀映鐘《徐杭游草題詞》中則準確把握了方文詩的特點:“以自然為妙,一切纖巧華靡、破裂字句,從不泚其筆端。垂三十年,守其學不變,而日造堅老純熟,沖口而道,如父老話桑麻,不離平實,卻自精微。”[3]918其詩歌看似“平實”,實出于苦吟,是一種“堅老純熟”后對詩歌語言的錘煉,內含“精微”之義。
方文作詩出自真率,看似淺顯,實在是得來不易。孫靜庵于《明遺民錄》寫道:“其為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為絺章繪句之工,間有徑率句,頗為讀者口實。然方文實苦吟,含咀宮商,日鍛月煉,凡人所輕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腑而出之者也。”[5]即道出了方文詩歌創作“苦吟”之實情。
方文極自信也極自豪地宣稱他的詩是“布衣語”,絕不憚人譏為俚俗,“有客慈仁古寺中,蒼龍鱗畔泣春風。布衣自有布衣語,不與簪紳朝士同”(《都下竹枝詞》第二十首)。這位布衣詩人遠續白居易詩歌創作手法,自我標榜“布衣語”之創作特色,自成一格,于明末清初詩壇占有一席之地。當代學者嚴迪昌總括方文詩歌為“詩語明白如話,詩心深摯蒼涼,詩境清樸純真”[9],應是比較客觀全面地把握了方文詩歌的藝術特點。
四、“嵞山體”對清初詩壇的影響
方文詩歌當時即流傳較廣,詩坫耆宿如錢謙益、施閏章、孫枝蔚、王士禛、陳維崧、朱彝尊等著名詩人都盛相推許其詩,以為必傳,于其詩多有精到的評價。如施閏章評價他的詩:“爾止為詩,雖民謠里諺,涂巷瑣事,皆可引用。興會所屬,沖口成篇,款曲如話,真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痕。”[10]所論中肯。
孫枝蔚題《嵞山續集》詩曰:“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嵞山詩合荊公語,輕薄兒曹莫浪彈。”他在《京口遇方爾止》詩中寫二人相逢飲酒賦詩,方文吟詩“驚人”的情形,“君髯雖白氣猶壯,樓上吟詩樓下驚。醫學旁搜未肯已,六書辨論何其精。”(《清詩匯》卷十二孫枝蔚詩)鄒祗謨題詩“平淡盡從攻苦得,時賢未許斗清新”二句也能得方文詩歌要旨。陳維崧《題嵞山丙午詩卷首二絕句》其一:“字字精工費剪裁,篇篇陶冶極悲哀。白家老嫗休輕誦,曾見元和稿本來。”盛贊方文作詩字字精工,精心剪裁,堪與白詩相比。其二:“春雨春陰又幾朝,他鄉寒食總無聊。把君丙午詩三卷,吟過城南丁卯橋。”[3]919由此詩可以看出,方文詩歌當時即已流傳開來。他對自己的詩歌創作也頗為自信,正如他在《賣卜潤州鄔沂公談長益潘江如錢馭少玉汝秦臣溥李木仙各有詩見贈賦此答之》詩中所寫:“一生得意是詩成”之告白,絕不是簡單的自負,而是包含著對自己詩歌的認識以及“四海同人”于其詩歌的客觀評價。其詩多記親歷聞見,樸老真至,渾脫有杜陵之風;又好學香山,堅老純熟,清真如話,不離平實,卻自精微。發自真情,堪稱真詩。
方文之“嵞山體”于其時亦有批評指責的聲音,最突出者莫過于王士禛。上面也提到,見諸一些文獻所記,王士禛是贊許方文的詩歌創作的,但何以又批評呢?其實他較為稱許方文的為人,“方爾止瀟灑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為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揜覆其短。予以此重之”[11]。但他指斥其詩“流為俚鄙淺俗”,于此有所不滿。《漁洋詩話》云:“嵞山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之語,為世口實。”[12]208他在《古夫于亭雜錄》中記有一則與方亨咸的對話:“桐城方嵞山文,少有才華,后學白樂天,遂流為俚鄙淺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予常問其族子邵村亨咸曰:‘君家嵞山詩,果是樂天否?’邵村笑曰:‘未敢具結狀,須再行查。’”[13]雖或是戲言,但亦反映其對方文詩作的態度,或語含輕視之意。他為《四壬子圖》題詞,卻又加以調笑一番:“余為題罷,語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嵞山不免吃藤條耳。’一座絕倒。”[12]209《詩觀》亦持此說:“爾止詩專學長慶,仆昔與之論詩蕭寺,頗有箴規,爾止弗善也。要去其俚率,存其蒼老,斯爾止為足傳矣。”[10]都規勸方文作詩當摒棄淺俗粗陋之語,突出蒼涼渾厚的風格,這樣的詩歌才能更廣泛的流傳。
但王士禛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方文的一些詩歌確有佳句。他在《分甘余話》中就列舉其佳句大加稱賞:“方嵞山文《冬日林茂之前輩見過》云:‘積雪初晴鳥曬毛,閑攜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缊袍。’嵞山又有詩云:‘烏衣巷口多芳草,明日重過是早春。’亦佳句。”[14]因王士禛作詩主張“神韻說”,因此他對方文詩歌的“俚鄙淺俗”之語自然也就有所非議,然方文的某些詩篇還是契合他的詩學之旨的。
朱彝尊則折中兩端之說,持論公允,他說:“爾止間作可笑詩句,頗為時論揶揄。然如嘉谷登場,或舂或揉,秕糠終少于粒米。”[15]他認為方文的詩歌總體上還是值得肯定的,并且舉出數首詩歌為例來肯定他的詩歌創作成就。李楷為《嵞山集》作序,顯然是針對“時論揶揄”有感而發的。他對當時詩壇排斥異己而“必律天下之人皆歸于己一軌”的做法表示憤慨,大加鞭撻,主張詩歌“自成一家”,大可不必獨尊一家,歸宗一派,更不可黨同伐異;又批判那種“不排人無以自見”之舉。他指出方文詩歌淵源有自,踐行自己所倡導的“樸老真至”的詩歌創作原則,因而能“自成一家”,形成較為成熟的獨特風格。他還專門拈出方文所言“樸老真至”一語來概括其詩歌的風格特征。他為方文詩歌創作學習白氏而辯解,有的放矢,論述有力,是很有見地的。
五、結 語
方文理所當然可以看做是清初遺民詩人的典型人物。他有著強烈的遺民情結,忠于朱明王朝,堅守民族氣節,絕不仕清,為明亡而深哀巨痛,至死未泯。
方文明季即以工詩著稱,三十年間以詩名家。作詩已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甚或是生命的組成要素,可以說他是無事不可詩,無時不為詩,無地不寫詩。他一生不事生產,家人窮餓亦不理會,以執著于作詩為業,致力于做一位專業詩人且為之自豪,“妻孥莫恨無生產,千首詩傳抵萬金。”(《熙城漫興》)“平生酷好在聲詩。”(《姚若侯暑中見訪并有所饋賦此答之》之二)“富貴功名非所望,惟祈書種種書田。”(《元旦》)而且他還自信所作詩歌將得以流傳不朽,這是詩人最大的心愿。
同時,他大半生漫游,廣泛結交詩壇故友新朋,其詩真實記錄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時代變幻,堪稱詩史,由其詩可考其時,因其時可窺其志,閻爾梅《白耷山人詩集》卷四《桃花城秋夜贈方爾止處士》:“尚論古今作詩史。”[16]張其淦《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二:“嵞山亦詩史。”[17]皆認識到其詩歌的價值。胡金望將方文詩歌創作概括為“遺民情結鑄詩魂”和“性命所寄成詩風”[18],認為其詩歌風格正是明清之際時代風云與詩人特殊生活經歷感受相互作用的藝術顯現。朱麗霞對方文則有著極高的評價,她認為“無論對于清初遺民還是整個文學史,方文的作品都有著無可爭議的重要意義,因為他代表了一個文學時代的新起點”[6]142。我們姑且不論方文于文學史上究竟處在怎樣的地位,但他的詩歌“嵞山體”自成一家,應該予以肯定,其詩對于認識明清之交的社會歷史和文人心態及交游頗具意義,其詩的藝術特色及其于清詩的發展與影響等諸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1]李圣華.方文年譜[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1.
[2]謝正光.讀方文《嵞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實小議[M]// 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109-181.
[3]方文.方嵞山詩集[M].胡金望,張則桐,校點.合肥:黃山書社,2010.
[4]胡必選.康熙桐城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169.
[5]孫靜庵.明遺民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59.
[6]朱麗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與文學生態——以徐渭、方文、朱彝尊為個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朱則杰.方文《四壬子圖》考論[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
[8]馬其昶.桐城耆舊傳[M].合肥:黃山書社,1990:266.
[9]嚴迪昌.清詩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197.
[10]施閏章.學余堂文集[M]//文淵閣四庫書集部第1313冊.臺北:臺灣商務書館,1986:51.
[11]王士禛.池北偶談[M].北京:中華書局,1982:369.
[12]王士禛.漁洋詩話//清詩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8:97.
[14]王士禛.分甘余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9:24.
[15]朱彝尊.靜志居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707.
[16]閻爾梅.白耷山人詩集[M]//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3 .
[17]周駿富.清代傳記叢刊·遺逸類(一)[M].臺北:明文書局,1985:118.
[18]胡金望.論方文的遺民情結與詩風[J].東南學術,2008(5).
責任編校:汪孔豐
FANGWen’s“TushanStyle”andItsImpactontheEarlyQingPoetry
SONG Hao-f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FANG Wen, a famous poet in Tongcheng count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circle pf poetry. His poems have a style of his own called “Tushan Style”, rich in contents ranging from expressing strong feelings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to reflecting and recording social reality. Artistically, FANG Wen’s poems are smooth in language,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and sincere and straightforward in emotion. His “Tushan Style” poems were spoken highly in the early Qing poetic circle and had a place of its own.
FANG Wen; Tushan Style; adherent poet; early Qing poetic circle
2014-03-20
安徽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桐城方氏三詩人研究”(2011sk782)。
宋豪飛,男,安徽安慶人,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時間:2014-8-28 15:45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20.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20
I207.22
A
1003-4730(2014)04-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