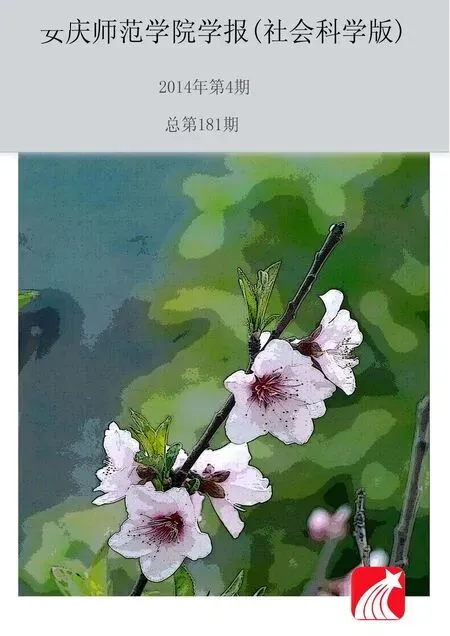北齊士人間交游酬唱的文學意義
劉 飛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安徽 蕪湖 241000)
北齊士人間交游酬唱的文學意義
劉 飛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安徽 蕪湖 241000)
北齊時,南北文士間進行了頻繁的文學酬唱。在以軍國文章為主流,詩歌為支流的北齊文學發展的背景下,士人間交游酬唱的文學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北齊軍國文章對江左文風的選擇接受;二是北齊詩歌對江左文風的接受與抵制;三是北齊士人對南北文風觀念的彼此認同。而由此引發的北齊文學的勃興,也于側面反映出北朝文學與南朝文學分庭抗禮時期的到來。
北齊士人;交游酬唱;文學意義
北齊文學由文章和詩歌兩部分組成,其中文章尤以軍國詔書為重。北齊文學呈現為以軍國文章為主流,詩歌為支流的同步發展。如此同步發展的態勢,同樣體現在北齊士人的入仕途徑上。據《北齊書·文苑傳》載,擅長以軍國文章命世的北方士人,多因“參掌綸誥”、“參知詔刺”、“關涉軍國文翰”而被征召入館。所以,軍國文章作為北齊文學發展的主流,有其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反觀詩歌,因南來士人深受江左詩風浸染,故其文學作品或多或少帶有齊梁詩風的痕跡。江左士人的入北,為北齊士人直接學習南朝詩風打開了方便之門。同時,他們所帶來的江左文風,也為北齊文章盛世下的詩歌勃興提供了有益借鑒。北齊的軍國文章及詩歌能與江左文風有如此深刻地互動關系,這和北齊士人間頻繁的文學酬唱不無關聯。
一
侯景之亂,江陵陷沒,深受齊梁詩風浸染的南朝士人,順利攜江左文風進入鄴下。他們的到來,對于北齊文學而言,可謂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諸如“辭情典麗”的顏之推、“工于詩詠”的蕭愨、文辭“清辯”的諸葛潁等江左士人的入北,直接促成了北齊文士間文學酬唱的形成,繼而推動北齊文學的發展,尤其是促使了鄴下軍國文章與江左詩歌的相互借鑒。此實為北齊士人對南北文風的選擇性接受。北齊本土士人因長期同處北地,故其間多有不同形式的文學交流。其中最為普遍的是由同事之誼形成的文學交流,此交流多集中于國史文章的撰寫。以軍功出身的北齊統治者,不喜經世文章偏于江左文風,擔心文風盛行而引起軍隊的戰斗力下降,故而在朝堂之上,重視以軍國文章選才,非以詩賦取士。文襄帝時,曾大贊魏收為“國之光采”。魏收能得此殊榮并非其文詞高于溫子升、邢邵,而是緣于他的文章“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更為關鍵的是他有周悉文襄帝“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的神妙。可見,軍國文章被北齊統治者所重實乃是因其表達的政治意義,而非文辭上的玩賞。魏收,其人也正因文襄帝賞識其軍國文章的文采,不僅被召為主客郎,負責接待南來梁使謝珽、徐陵,還在齊受禪時,被收置于別館中,“撰禪代詔冊諸文”[1]2030。其中《為孝靜帝下詔禪位》一文,便是當時之作。文曰:
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圣重光,暨于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于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系,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克翦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埽除,國由再造,鴻勛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己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睿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于萬物,被大道于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還,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跡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
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藉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于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之望?今便遜于別宮,歸帝位于齊國,推圣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2] 44-45
此為魏孝靜帝下詔禪位北齊之詔。全詔書唯有“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最后一節為真正的禪代內容,約占篇幅的五分之一,而其余的五分之四均為北齊承運命世、祥和晏如、終為大業的宏大描述。在文辭方面,該文雖無江左的駢儷之美,但它深富北朝文學所特有的“貞剛之氣”。軍國詔書能有如此剛健質樸之語,也正是魏收文章為北齊統治者所青睞的緣故,所以“自武定二年以后,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1]2035。
同樣以軍國文章得名的李德林,其幼年時便與魏收結下不解之緣,據《北史·李德林傳》載:
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嘆異之,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余車馬不絕。……善屬文,詞核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升。”[1]2504
李德林因其文學作品的“詞核而理暢”被魏收評為“終當繼溫子升”,這實為北齊文章所重之思想性的體現。此番李德林雖未與魏收見面,但他之后參典文翰,借共事之際,與魏收多有文學交流,如《北史·李德林傳》云:“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1]2505魏收與李德林有過頻繁的書信往來。該據雖未明確魏收與陽休之會議的具體內容,但通過往來書信基于“論《齊書》起元事”的事實,我們亦可略知其所談之事。據《與李德林書論齊書起元事》所載:
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2]49
魏收將關于“《齊書》起元事”所論的內容告知李德林,便于與其討論相關史學問題。又李德林回以《復魏收議齊書起元事書》,他提出“即位之元”與“受終之元”兩種說法及各自反例,以答魏收。后李德林與魏收再次于《重遺李德林書》、《答魏收書》中,將上述問題深入探討。以上皆是李德林與魏收頻繁的史學交流,這對李德林軍國文章思想境界的提升,頗有裨益。
同時,與擅長“雕蟲小技”的魏收的長期交流,亦對李德林文章的文辭有潛移默化地影響。如魏收文章剛健質樸的風格就為李德林有所吸收。李文《為周靜帝誅尉遲迥大赦詔》:“朕祗承洪業,二載于茲。籍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奸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思。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眾,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兇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縈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群丑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為治,圣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謀,執迷不悟,及迥子侄,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2]4115敘事明晰,略無滯澀,且有北方士人中鮮有的事典之功力。與同時期的關中軍國文書用典不多,多直敘而較少文采不同的是,李德林文章中既有北方質樸的思想內涵,又不失駢儷的華美文辭。再將李德林與江左文人所作的文章相比,江左文章的駢儷之美又有過之。因此,李德林文章的風格恰于江左的艷麗與北齊的質樸之間,很好地體現出南北文風在軍國文章這一文學形式上融合的痕跡。于此,李德林因其軍國文翰之才而被周武帝驚為“天上人”[1]2505,周代文書基本由他一人主筆,也就不足為奇。
李德林文辭上除受到魏收影響外,恐怕和其多與士人共事交流的經歷密不可分。如李德林被敕與“美于詞令”的李孝貞,“別掌宣傳詔敕”;又與江左士人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1]2505。除同事之誼外,“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宴集”[3]2571,共同研讀徐陵之文。如此廣泛的交流,客觀上為李德林文章兼具思理與藻飾提供了有益幫助。
總之,北齊士人在同事之誼式的交流中,使北齊文章,尤其是軍國文章在保持北朝質樸文風,亦對江左文風中的清麗藻飾有所接受。
二
因北方士人生長在“唯以章表碑志自許”的文學土壤之上,故他們在崇尚江左文風的同時,亦能保留北朝剛健質樸的風格。對借鑒江左文風而言,北齊的文章僅取其詞采華美,而北齊的詩歌卻呈現出其接受的復雜性,即抵制與接收的兩面。
對詩歌接受江左文風復雜性的考察,可從北方士人間常見的游宴交流入手。
不同于同事之誼間國史文章的探討,北齊的游宴交流多集中于詩歌評點,且較多地反映出北齊本土士人對江左文風的抵制,如《顏氏家訓·文章》中所云: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于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邪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4]275
顏之推甚為贊賞蕭詩,稱其詩風蕭散,所寫之境宛然在目。同為南來士人的荀仲舉與諸葛潁(字漢)亦持顏氏評價,而盧思道對此詩卻“雅所不愜”。盧思道并非不愛江左的華美文風。反之,他對崔贍的“文詞之美”頗為稱道,又素與“文章綺艷,體調清華”的辛德源“時相往來”。故盧思道對蕭詩“雅所不愜”,或許是地域對峙而帶來的文風偏見,抑或“各有朋黨”所引發朋黨間的“更相訾毀”。而后更有甚者,抵制南風的舉動逐漸演變為加害江左士人。據《北史·顏之推傳》載:
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于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于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勛要者所嫉,常欲害之。[1]2795
顏之推入文林館后,一切文書皆由其封署,且其監校處事極為勤敏,故后主對其禮遇甚厚。時當朝之勛貴,一方面嫉妒其被后主恩寵,一方面不滿其奏立文林館時“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的主張,故“常欲害之”,索性沒有得逞。
縱使北齊士人對南風有所抵制,但他們之間的文學交流卻從未停滯。即使是在行“公事”時,王晞、陽休之仍“數與諸人游宴”;又“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勵、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1]946。北齊南北士人間文學酬唱的頻繁,使北齊詩歌漸脫輕艷柔靡,并融合了北齊文章的質直。其中蕭愨與北方士人陽辟疆唱和的《和司徒鎧曹陽辟疆秋晚詩》:“葉疏知樹落,香盡覺荷衰。山藪良多思,田園聊復歸。”[5]2279該詩在句式上,皆為工對,頗為整飭。于語言方面,若說前兩句中,落葉稀疏與香荷盡衰是南朝文風中特有意象的殘留,那么后兩句“山藪良多思,田園聊復歸”則是以平淡質樸的田園語說出。此詩正是質直義理與清麗藻飾的完美結合,亦是北朝文風與江左文風融合的有益嘗試。
除江左士人的詩歌漸漸褪去艷麗而融合質樸之外,北方士人亦積極模擬江左文風,吸納其擅長清麗辭藻之風。據《北齊書》云,古道子“自袁奭等俱涉學有文詞”[6]628。又“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瑯邪王儼大將軍咨議,入館”[6]626。可知,古道子與飽受江左文風熏陶的袁奭,有直接涉學文詞,模擬江左文風的經歷。而從袁奭現存的《從駕游山詩》:“天游響仙蹕,春望動神衷。澗水含初溜,山花發早叢。玉輿明淑景,珠旗轉瑞風。平原與上路,佳氣遠蔥蔥。”[5] 2267來看,袁奭對從駕時春光明媚的景色描寫,不乏江左的清麗明快。雖現已無古道子的詩歌留存,但不難想見,江左文風卻為其所崇尚。
袁奭崇尚江左文風有其涉學文辭的確證,而大部分北齊士人模擬南風已無史料可考,其中盧思道便是一例。盧思道雖對蕭愨的《秋思詩》“雅所不愜”,但他卻有頗似江左文辭清麗的文學作品出現,《從軍行》便是這樣的典型之作。
它將傳統的五言短詩變為七言長篇之作,“語言清麗流暢,句法多用對偶,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7]。他以七言歌行把塞外肅殺的氣氛、征人懷鄉和思婦閨怨的情思巧妙地融為一體。既不同于南朝寫作閨怨的輕艷綺靡,又異于北朝寫作邊塞的尚理重質,而是將二者融合,內質不殊于北方的剛健俊逸而詞采又兼有齊梁的柔婉清麗,實屬當時融南北文風之佳作。
通過對北齊南北士人間游宴的考察,可知北齊詩歌的復雜性是體現在抵制與接受江左文風上。而文學交流又無疑是消解了文學觀念上的分歧,它對北齊詩歌融合南北文風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
前述蕭愨《秋思詩》所引發對江左文風接受與否的爭論,實質上是他們各自固有文學觀念存在分歧。對南北文風觀念上的差異,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多有論述。他對南北文風持中和態度。之所以顏之推的文學作品中有北方質樸和南朝清麗的融合,這與他“世善《周官》、《左氏》”的家學淵源和“虛談非其所好”的個性主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持中和態度的他才能對南北文學觀念的優勢與不足,作客觀分析。
據《顏氏家訓·風操》云: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谷。自茲以降,雖孔子圣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后雖有臣、仆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4]86。
顏之推對北朝文風積極贊賞的同時,亦指出其不足。他力求在分析導致南北文風差異的因素時,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如《顏氏家訓·文章》所載: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4]259
蓋上述兩處材料并不意味著顏之推對南北朝一方有所傾斜,相反他正是從南北朝文化的優勢來闡述其文風差異的。
在了解南北朝文風差異的基礎上,顏之推從地域論及南北音辭,如《顏氏家訓·音辭》云: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4]473-474
他從水土論及到音辭,全面細致地考察了南北文風相互漸染的原因與“深弊”,這意味著南北士人不再認為南北文風是難以調和,他們轉而慢慢地接受彼此文風的差異。如此,北齊士人對文風差異的觀念認同,在文學創作的接受上已初見端倪。據《北史·李德林傳》所載“武平初……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1]1337云,從文學實踐的角度來看,南北稱美詩作的出現,說明當時對南北文風觀念認同已然存在。此外,“南北稱美”不僅可以理解為“道衡和之”之詩被南北士人稱道,而且可被視為南北士人對“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唱和舉動的稱賞。若作后者理解,這一“南北稱美”的唱和舉動,無疑反映出文學酬唱對南北文風融合的推動作用。
此外,對南北文風的認識,北方士人亦持顏氏觀點,如《顏氏家訓·文章》所載:
齊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4]247
“既有寒木,又發春華”是指文章的深沉內質與華翰辭藻要統一起來。劉逖在此所要表明的是其南北文風融合的文學觀念:一方面要求吸收北朝的清剛貞烈的內質;一方面要用南朝的詞采文華來作潤飾,“兩須并存,不可偏棄”。同時,顏之推也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具體闡述了如何在文學創作中,實現南北文風的融合,如《顏氏家訓·文章》云:
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本棄末,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樸,未為密致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并須兩存,不可偏棄也。[4]248-250
“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無疑是實現文章“既有寒木,又有春華”的具體途徑。如此,南北文風融合便從觀念上的認同,轉而走向實踐的認同。
綜上,北齊文士間頻繁的文學酬唱,使南北文士在同共事、共游宴的交流中,促成了南北文風碰撞的發生。而其碰撞出的文學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北齊軍國文章對江左文風的選擇接受;二是北齊詩歌對江左文風的抵制與接受;三是北齊士人對南北文風觀念的彼此認同。其中北齊軍國文章與詩歌對江左文風的借鑒,既表明了北齊文人對文學創作的自覺追求,又直接促發了“北地三杰”對“北地三才”文學轉接的形成,為周隋培養并輸送了大批文壇巨子。同時,北齊士人對南北文風融合也上升到文學觀念上的認同。由此,北齊士人間廣泛而深刻的交游酬唱,在文學創作與文學觀念的雙重向度上所引發的北齊文學的勃興,也正預示著北朝文學與南朝文學分庭抗禮時期的到來。
[1]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2.
[2]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8.
[3]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M].北京:中華書局,1983.
[6]李百藥.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2.
[7]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19.
責任編校:汪孔豐
2013-10-25
劉飛,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時間:2014-8-28 15:45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23.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23
I207.2
A
1003-4730(2014)04-01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