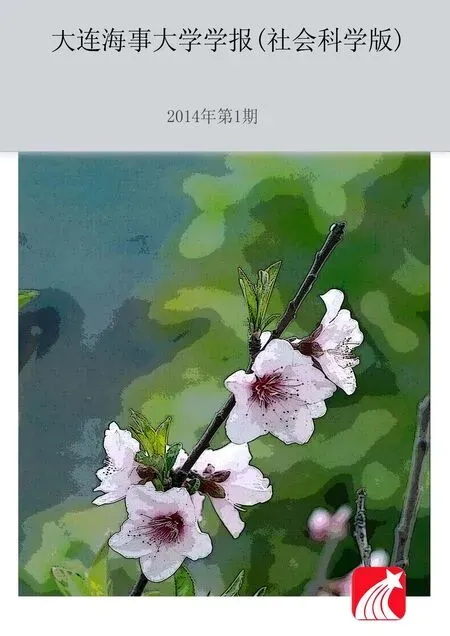凋零的美國南方文化
——論《欲望號街車》中的南北方文化沖突
馬喜文,呂春媚
(1.東北財經大學 國際商務外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2.大連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44)
一、引 言
在所有的文學體裁中,美國戲劇的發展歷史是最短的。直到20世紀早期,一些美國的本土劇作家才相繼出現。1920年到1960年期間,美國集中出現了一批國內外知名的劇作家,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其中一些作家開始關注當時最為熱門的社會問題——南北方文化沖突。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戰爭對美國的政治和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方最終的失敗造成了南方傳統生活方式的毀滅和傳統價值觀念的淪喪,貴族淪為平民,工廠取代了農田,曾經一度繁榮的南方文化逐漸走向衰敗。戰前,南方人富庶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優越感,優雅的生活方式已經在他們的記憶中根深蒂固。戰后,他們不能接受失敗,也不能應對生活中出現的新困難,只能一味地沉浸在對昔日榮耀的回憶中。這時,美國文壇上出現了很多現實主義作家,他們關注平民百姓的現實生活,如何走出南方戰后的困境成為這些現代作家的話題。他們將作品中的人物置身于南北兩種文化中,就像是田納西·威廉姆斯《欲望號街車》中的布蘭奇和米契一樣,在不斷探索中找尋擺脫困境的出路。
田納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戰后作家之一。由于在南方長期生活,他已將南方的文化印記深深地植入了心間,可以說他是南方文化的最佳代言人。在南方目睹了過多的貧窮困苦,他一直致力于描寫南方人在美國內戰戰敗后所面臨的困境。《欲望號街車》(AStreetcarNamedDesire)是他的杰作,是南方種植園文化在北方工業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人文悲劇。[1]女主角布蘭奇是美國文學創造的眾多醒目的女性形象之一。她對南方文化的堅持,她對真愛的執著追求,她自相矛盾的性格和一度放蕩的舉止都是評論家鐘愛的話題。本文將重點分析布蘭奇和米契兩個在夾縫中生存的人物,試圖將南方人在戰后的沖突與困難中艱難前行的生活圖景展示在讀者面前。
二、布蘭奇——“南方神話”中的淑女
南方文化的產生和形成與其種植園體系有著直接的關系。17世紀早期,與北方惡劣的自然環境相比,南方優越的自然環境使殖民者輕松地創建了南方種植園產業,并將歐洲的貴族傳統移植過來。這種以農業為主的生活方式初步構建了南方文化。然而,南北戰爭的失敗使南方在政治、經濟上處于不利的地位,他們開始逃避現實,追憶往昔種植園生活的點點滴滴。在緬懷過去的過程中,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隨之產生,這就是“南方神話”。“南方神話”描繪的是“一幅栩栩如生、如詩如畫的田園生活的水彩畫:殘存于想象的古老南方是一片擁有繁茂莊園和快樂黑奴的熱土,大片裝有玻璃窗的白色房屋里居住著高貴的精通詩文音樂的紳士們和淑女們;以棉花為主要產品的南方經濟穩定繁榮;幸福和睦、其樂融融的完美家庭則是這幅美景的中心”[2]。事實上,“南方神話”是南方人對其舊生活方式和社會體制的一種美化。《欲望號街車》中的女主人公布蘭奇也是這樣一位心懷“南方神話”的戀舊者。她帶著重新編織的夢想來到了北方化的城市新奧爾良,以期尋找庇護,然而迎接她的卻是冰冷的工業化社會。
布蘭奇是“南方神話”中南方淑女的典范。她純潔優雅,文雅善良。對于她來說,美貌是她唯一可以依賴的事情,她堅信只有容顏永駐才有可能實現夢想。然而真正摧毀她的并不是逝去的青春,而是南北方的文化沖突。一方面,她不能背叛南方祖先們遺留下來的傳統;另一方面,她承受不了來自北方的咄咄逼人的壓力。當這兩種文化強烈碰撞之時,她很難在新文化中找到立錐之地,也不能在心理上保持獨立生存的空間。
布蘭奇身上有著與生俱來的南方人的特質。她柔弱、敏感、驕傲、優雅的特征均體現了她對南方文化的理解。布蘭奇的柔弱在劇本一開始就有所交代。當她出現在天堂路時,有一段關于她羸弱身姿的描寫:“她柔弱的美麗必須躲避強光的照射。她那游移不定的舉止和白色衣服讓人聯想到飛蛾。”[3]103*本文此處及后文所有《欲望號街車》的引文均為筆者譯。布蘭奇懼怕強光是因為她有著太多不可見人的秘密。當剛遇見妹妹斯蒂拉時,她立即要求關掉燈,好像是在陽光下會立即融化掉的雪人一樣。隨著劇情的不斷發展,讀者和觀眾發現布蘭奇害怕所有的光線,甚至連白熾燈的光線都令她坐立不安。
布蘭奇經常身著白衣,劇作家威廉姆斯把她比作一只白蛾而非一只天鵝或一片雪花。原因在于白蛾比起后兩者在顏色上更加蒼白,在含義上更加悲壯。蛾子經常能夠讓人們聯想到不幸或者軟弱。布蘭奇在失去了南方家園的家產后決定離開家園,到新奧爾良去投奔自己的妹妹,然而她卻沒有意識到這座已經北方化的城市的威脅性。而她試圖從新興北方工業階級的代表斯坦利身邊奪回妹妹的行為更無異于飛蛾撲火。
布蘭奇的敏感是她柔弱性格的副產品。一到斯蒂拉的家,她就開始擔心自己是否是一個不速之客。當她注意到妹妹的沉默后,便開始懷疑斯蒂拉并不歡迎她:
布蘭奇: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而你卻不歡迎我的到來!
斯蒂拉:布蘭奇,你怎么這么說?你知道不是這樣的。
布蘭奇:不是嗎?——我已經忘了你曾經是多么安靜的一個人。
斯蒂拉:你從未給我說話的機會,布蘭奇。所以我已經習慣了在你周圍保持安靜。[3]111
布蘭奇之所以如此敏感多疑是因為她身處異地,擔心自己的命運。如果斯蒂拉不接受她,她就會走投無路。這也就是為什么當發現斯坦利對她懷有敵意時,她竭力拉攏斯蒂拉,希望她能夠站在自己的一方。布蘭奇的敏感并不能夠拯救她的未來,她無法躲避已經預知到的危險,無法釋放已經感受到的壓力。事實上,她的敏感讓她更加迅速地走向了崩潰的邊緣。
布蘭奇來自于有法國血統的南方貴族家族,受過良好的教育,懂得文學和法語。當她向米契介紹自己家族的時候,她自豪地說:“我們是法國裔。我們最早的美國祖先是法國胡格諾教徒。”[3]157這種貴族的傲慢已經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無論現在多么潦倒,她始終試圖在穿著上與眾不同。當她第一次出現在新奧爾良的街頭,她的裝束與周圍的環境是如此格格不入:
她的樣子與周圍的環境是不相稱的。她身著一件質地柔軟的緊身胸衣和講究的白色西裝外套,戴著珍珠項鏈和耳環,白色的手套和帽子,看起來好像是要參加在郊外花園舉行的夏日茶話會或雞尾酒會一樣。[3]103
事實上布蘭奇所有的羽毛、裘皮、鉆石都是仿制品。她用這些贗品把自己包裹在高傲的優越感里,用虛偽的貴族式的生活方式來反襯北方人的平庸和卑賤。布蘭奇南方淑女的驕傲感也讓她鄙視斯坦利的出身。斯坦利身上每一個北方人的品質都成為她攻擊的對象。她稱斯坦利為“波蘭佬”(這是侮辱從波蘭來的人的一種方式),嘲笑他濃重的北方口音,指責他粗魯、原始的生活方式。布蘭奇在劇中是這樣形容斯坦利的:
……他太平庸了!……他毫無紳士風度!……他就像動物一樣,有著動物的習性!吃飯像是只動物,走路像是只動物,說話也像是動物!……成千上萬年過去了——斯坦利·科瓦爾斯基——石器時代的幸存者!在叢林里狩獵,然后將生肉帶回家!你不要退化與野獸為伍了![3]180-181
布蘭奇的驕傲和自信讓她不能接受自己親愛的妹妹竟然已經習慣于目前這種平庸的生活。她幻想能夠將斯蒂拉拉攏到自己的一邊,但這是斯坦利所不能夠容忍的。兩人的沖突也就由此而產生。
和布蘭奇南方女性的特質不同,生活在工業化的新奧爾良人具有北方人的特點。北方化的城市是建立在工業的基礎上,城市骯臟、擁擠,人們揮汗如雨地工作在工廠的車間里。而南方人生活在廣闊無垠的莊園,以他們土地上的產品為生,過著恬靜的鄉村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性格的人們。像劇中的斯坦利一樣,北方人彪悍粗魯、為所欲為。斯坦利的世界非對即錯。當他懷疑布蘭奇對他們有所隱瞞時,就告訴她要直截了當、光明正大。他的生活毫無掩飾。
隨著南北戰爭的結束,北方新興工業階級逐漸占據了社會的統治地位。他們是十分現實的一群人,追求物質主義,珍視真實、實際的事物,而幻想并非他們生活中的要素。當布蘭奇將要被帶往精神病院時,除了米契之外,所有在場的人都表現得無動于衷。斯坦利竟然站起來擋住布蘭奇的逃路。在布蘭奇被帶走之后,男人們的撲克游戲繼續進行著。斯蒂拉為發生在姐姐身上的事情不停地哭泣,她的鄰居安慰她說:不要相信那件事(斯坦利強奸布蘭奇),生活還要繼續。北方人的麻木和冷漠在這一場戲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
布蘭奇鄙視斯坦利,同樣,斯坦利把布蘭奇看作小偷和蕩婦。他不能接受布蘭奇的生活哲理,諷刺她記憶里的崇拜者,質疑她所描述的百萬富翁男友。當他知道了布蘭奇在家鄉不光彩的過去后,他不失時機地羞辱她。斯坦利刻薄的話語讓布蘭奇所剩無幾的南方淑女的尊嚴和優雅蕩然無存。
布蘭奇一直相信如果她能夠找到可以依附的人,她就會找到自己的棲息之所。事實上,她沒有意識到只要她生活在新奧爾良——這個北方化的工業城市,她就不會找到自己最終的歸宿。她的柔弱在殘酷的北方變得更加不堪一擊,她的敏感在冷漠的北方顯得格格不入,她的傲慢在現實的北方成為眾矢之的。“斯坦利戰勝布蘭奇標志著美國新興的野蠻勢力完全地摧毀并顛覆了美國舊南方所固有的文明禮教,取而代之的是以粗野、放肆、追求肉欲和物質主義為特征的新型的現代工業社會。”[4]真正摧毀布蘭奇人生的并不是斯坦利,而是南北方不可調和的文化沖突。“南方神話”在強大北方的威懾下終究會破滅。
三、米契——南北文化的綜合體
米契在第三場“撲克游戲”時第一次出場。和其他三位粗暴無禮、令人厭惡的牌友相比,米契看起來的確有些與眾不同。隨著劇情的不斷展開,米契成為布蘭奇期望托付余生的人。這并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英俊瀟灑、才智過人的男人,恰恰相反,米契此時是個碌碌無為、窮困潦倒的推銷員。但是他的敏感氣質吸引了布蘭奇,使他看起來比起周圍的人更加優秀,更具有紳士風度。米契的這種氣質來自于他的個人經歷。他和布蘭奇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他也是一個寂寞孤獨的人,在遇見布蘭奇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母親的呵護之下,沒有什么和其他女人交往的經歷;他也曾經受過失去愛人的痛苦,當他傾聽布蘭奇講述她年輕愛人的故事時,他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布蘭奇內心的寂寞和苦楚;和布蘭奇一樣,他也不敢直面殘酷的現實,寧愿在現實和虛幻之間游走。米契的溫柔和感性讓布蘭奇感受到了久違的南方紳士風采,也讓她重溫了昔日的美好時光。她幻想在米契的呵護下,有機會能夠再次成為南方嬌嫩的花朵,純潔、柔弱。
米契雖然有著南方紳士的特點,但是他卻離“南方神話”中南方紳士的標準相差甚遠。他身材魁梧,笨手笨腳,說話時帶著生硬的南方口音。他的思考、辦事方式完全和北方男人一樣。當發現布蘭奇有著不光彩的過去時,他暴露出與斯坦利一樣的冷漠和殘忍。如果不是他懦弱的個性,他完全可以成為另一個斯坦利。他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對詩歌和文學的理解。當布蘭奇談到某些詩句時,他總是感到困惑不解。藝術和文學對他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物,他所需要的是生活的必需品。和所有的北方男人一樣,他缺少浪漫的思想和精神,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虛的。米契秉承了南方紳士的氣質,但因身處劇烈變化的南北沖突,終日為家庭生計所累,面對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的社會現實,他美好的想象無處棲身,米契在不知不覺中經歷著南方紳士的演變過程。[5]
如果說布蘭奇是作為南方的代表在和北方的工業文明進行著抗爭,那么米契則是一直在和自己進行著斗爭。他身上的南方的特質和北方的品性使他成為一個矛盾特征的綜合體。他獨特的敏感吸引著布蘭奇,但他軟弱的性格使他既拯救不了布蘭奇,也令自己身處困境。一旦他的敏感氣質遭遇到阻礙,他就會將真實感受隱藏起來。最終,他得以存活下來,但卻終日飽受良心的折磨。
四、衰敗的南方文化
南方文化走向衰亡可以從布蘭奇和米契兩位主人公的命運窺見一斑。他們都生活在自我的沖突中。他們的相似點讓彼此相互靠近,卻又相隔萬里。最終,兩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布蘭奇遭遇暴力而走向瘋狂,米契屈服于強權并推開了布蘭奇。兩人都不得不放棄心中的南方而委屈求存。
布蘭奇最終瘋了,當“Blue Piano”再一次在她的耳畔響起時,她的神經徹底崩潰了。斯坦利、殘酷的現實和過去的虛幻把這個昔日南方的淑女逼瘋了。斯坦利想要把她逐出自己的領地,殘酷的北方現實試圖約束這個南方女子,她的過去逼迫她永久地生活在幻覺之中。布蘭奇最終只能逃到她虛幻的世界里,在那里她能夠感受到一絲安撫和歡愉,一個昔日輝煌的南方世界。她愿意在那里找尋她逝去的青春。在這個虛幻的世界里,她能夠堅守自己的南方生活方式,能夠驕傲、優雅、美麗地生活下去。
在《欲望號街車》這場殘酷的南北方文化沖突中,南方經受了慘痛的失敗。南方家族隨著土地的喪失而滅亡了。而南方文化的兩位繼承者(布蘭奇和斯蒂拉)也消失了。一位早已忘記了自己南方的特質,期待著和愛人在北方的環境中開始嶄新的生活;而另一位,只能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回憶著南方的家園。
米契是本劇中最令人失望的人物。當孤獨寂寞的時候,他渴求獲得布蘭奇的愛戀,然而他卻承受不了來自現實的壓力。他的溫和與感傷都是虛假、偽善的。他的懦弱和最終的妥協斷送了他的前程、希望和機遇。當他最終決定站在斯坦利一方時,他放棄了重新開始生活的權力。他的放棄使最后一粒南方文化的種子枯朽在冰冷的北方土壤中。
五、結 語
美國的南北戰爭徹底地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戰前,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著。在北方,人們在工廠工作謀生。沒有富庶祖先的他們絲毫不在意自己的儀表和風度。他們堅信自己的力量。而在南方,土地所有者們生活在他們的土地上,享受著奴隸們帶來的服務。他們絲毫不為生活而擔心,藝術和娛樂是他們生活的重心。戰后,南北方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在北方,戰爭激發了人們追求權利和財富的熱情。北方不僅在機械文明方面而且在現代精神文化方面成了先驅和主角。[6]他們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謀求更好的生活。同時,北方人也變得更加現實。而在南方,戰爭摧毀了農業的基礎,摧毀了蓄奴制,中斷了南方戰前短暫的經濟繁榮,使南方大大地落后于美國其他地區。南方業主開始失去他們的財富和社會地位,開始質疑這個社會和他們曾經擁有的信念。他們的當務之急是如何另找出路來應對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南北戰爭的失敗不僅進一步增強了南方的封閉保守狀況,而且使南方成為美國唯一具有向后看的歷史意識和深沉的悲劇感的地區。”[7]
《欲望號街車》中主人公們悲劇式的命運恰恰呈現出了南北方在戰后發生的變化。布蘭奇沉溺于舊日的美好時光。每當生活中出現危機,她就會把自己藏匿于昔日的影子里,用南方貴族的尊嚴將自己包裹起來。米契害怕母親有一天會離他而去,他將會孑然一身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喜歡布蘭奇,但是他的生活經驗讓他無法理解布蘭奇的苦痛。南北方文化的差異讓他感到彷徨,最終他選擇了放棄和逃匿。本劇的結尾預示著南方種植文化的終結以及南方文化的衰敗。在南方的舊文明逐漸被工業化所取代的過程中,南方人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都經受了重大的變革。南方人的精神家園隨著物質家園的喪失而喪失。《欲望號街車》反映了劇作家威廉姆斯對南方文化價值觀念在現實中的境遇的反思。
參考文獻:
[1]徐錫祥,吾文泉.論《欲望號街車》中的象征主義和表現主義[J].外國文學研究,1999(3):95-98.
[2]陳曦.“南方神話”的幻滅——試論《欲望號街車》南方傳統價值觀的解構[J].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0):154.
[3]WILLIAMS T.Tennessee Williams[M].New York: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1994.
[4]趙冬梅.《欲望號街車》——一部聚焦多元社會文化沖突的縮影[J].當代戲劇,2010(3):26.
[5]肖瀟.《欲望號街車》中南方紳士的進化論解讀[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7(8):120.
[6]張禹九.南北戰爭后的美國南方文化[J].美國研究,1992(2):54.
[7]肖明翰.美國南方文藝復興的動因[J].美國研究,199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