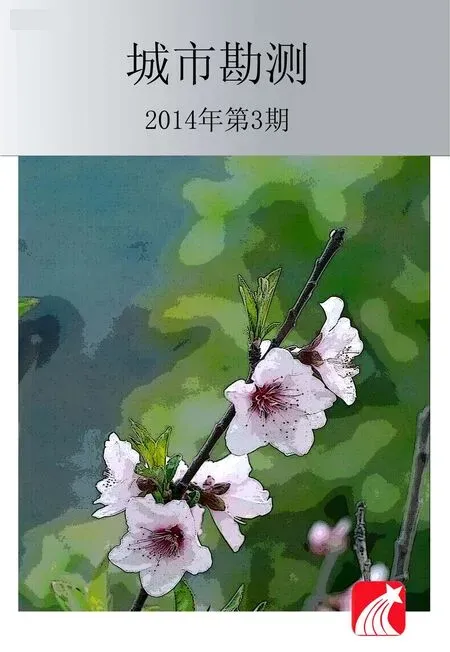基于GIS的城市公交換乘模型與實現
簡志偉,馮軍鋒
(上海市測繪院,上海 200129)
1 引言
城市規模的擴張以及城市人口的增長使得人們在城市中的出行愈發困難,同時也對城市智能交通的信息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加快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的優化是解決城市人口出行困難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隨著城市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城市公共交通不再僅僅由單一的公交車構成,而是集合了公交車、軌道交通、輪渡、索道等眾多交通手段的公共交通系統。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乘客的出行效率和選擇性,但是,出行手段的多樣化使得公共交通系統的復雜性也大大的增加,往往導致公共交通資源的浪費和出行人群在時間、財產上的損失。因此,如何高效的分配公共交通資源是提升城市人群出行效率的關鍵。
乘客在出行時會主要考慮“換乘次數”、“出行距離”和“出行耗時”這三個方面的因素[1]。傳統的公交換乘模型多采用基于數據庫的模式[2~4],通過數據庫對公交路線、公交站點及其相關關系進行有效地數據組織,并在此基礎上完成公交線路的檢索和查詢。然而該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上述三個影響因素,使得換乘模型與實際出行情況差異較為明顯,例如:基于數據庫的換乘模型往往忽視了人們能夠步行一段距離進行換乘來減少換乘次數的情況,并且無法靈活和準確的計算出出行距離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出行耗時。而基于GIS的公交換乘模型與傳統模型相比,利用GIS在智能交通領域的優勢[5],對公交網絡系統和交通網絡系統進行GIS數據組織和處理,將屬性數據和空間數據有機的結合到一起,不僅可以獲取更加符合城市人群實際出行情況的出行線路,還能夠在GIS的圖形可視化顯示這一特點的基礎上對選取的線路進行顯示,使出行人群對線路的解讀更為直觀和明了。
公路網絡與公交網絡的差異[6]決定了解算城市道路網絡最短路徑的方法并不適用于解算公交網絡中的最短路徑或最優路徑[7,8],但是道路網絡最短路徑適用于城市人群在出行時進行站點間換乘的線路選擇。因此,本文分別對城市道路網絡和城市公交網絡進行了GIS抽象,結合圖論理論[9]對網絡中的各個要素進行了拓撲結構、空間關系、屬性關系的表述。在道路網絡結構關系完善的基礎上采用最短路徑算法[10,11]計算城市中任意兩站點在城市道路網絡中的最短路徑,設定彈性的閾值以確定不同的步行換乘距離所對應的換乘路線并將其作為乘客步行換乘時的最優路徑。在公交網絡結構關系完善的基礎上制定公交最優路線選擇模型,選擇最優的公交線路,并將公交線路與步行換乘線路結合生成最優的出行線路。本文最后結合杭州市的路網和公交等數據進行了試運算,并對結果進行了分析和說明。
2 交通路網與公交網絡的GIS數據組織
2.1 公共交通系統要素的GIS表達
城市公共交通系統良好運作的前提是高效的公共交通數據組織和表達。本文對公共交通系統中的各個要素進行了GIS表達,將其抽象為GIS中的“點”要素和“線”要素,并對各要素進行詳細描述。
道路的GIS表達主要包括道路節點和道路路段。節點是道路網絡中非常重要的一種要素,它是不同路段的相接處,在現實中往往屬于城市道路網絡中的特征地點[12]。根據需要本文對節點的屬性進行組織表達,道路節點的屬性主要包括節點編號和節點X、Y坐標,節點編號為該節點唯一標識編號,通過編號可對相應節點進行索引查詢;節點X、Y坐標用來標識該節點的絕對位置。路段是對城市中道路的抽象,是城市路網中的“骨架”。單純采用路段的幾何特性對現實道路進行描述并不足以完全表達其特性,更不能滿足公交換乘計算的需求,比如計算行車距離需要對乘車路線經過的路段的長度進行求和,因此本文對道路路段的主要屬性進行了表述,道路路段的屬性主要包括路段編號、路段名稱、路段起始節點和終止節點、路段長度等,路段編號為該路段位移標識編號,通過該編號可對相應路段進行索引查詢;路段名稱為路段所在道路中文名稱;路段長度表示該路段實際長度,據此計算線路距離和換乘距離;路段起始節點編號和路段終止節點編號表示連接路段兩側節點的編號,為路段和節點建立索引關系;路段長度標識該路段空間長度。
公交線路的GIS要素包括公交線路、公交站點和公交換乘區。公交線路是公共交通工具在城市道路網絡中行駛的路線,它的屬性決定了乘客乘車的耗時、距離、花費,如表1公交路線屬性中所示,公交線路編號標識公交線路唯一標識,且區分同名線路的不同方向;票價標識乘客乘坐該路公交路線的花費;首班時間和末班時間標識公交線路運行時段,以便為乘客提供準確的公共交通信息。公交站點是公共交通工具在公交線路上行駛的時候停靠的固定點,以滿足乘客上、下公共交通工具的需求,如表1公交站點屬性中所示,公交站點編號是該公交站點的唯一標識,可以通過編號對站點進行索引查詢;公交站點名稱表示該站點的中文名稱,并不具有唯一性,如相鄰反向的一對站點一般均為同名;站點X坐標和站點Y坐標標識公交站點的絕對位置。公交換乘區是乘客進行換乘時在可忍受最大步行距離內能夠到達站點的集合。
公共交通網絡中的各要素間具有密切的關系,公交換乘區內包含的站點數量主要由乘客所能忍受的最大步行換乘距離以及換乘站點附近的公共交通網絡情況決定。如圖1所示,該區域中共有3條公交線路,A為某線路中的一個站點,根據設置的最大步行換乘閾值求解站點A的公交換乘區,由圖可知,隨著最大步行換乘閾值的增大,公交換乘區內包含的站點數量也隨之增加,同時,在站點A處可供換乘的公交線路也增加了。

公交路線與公交站點部分屬性表 表1

圖1 公共交通網絡關系圖
通過上述過程對城市道路和公交線路的空間數據和屬性數據進行組織,為基于GIS的公交換乘模型做好數據準備。
2.2 道路網絡與公交網絡的表達
城市交通網絡作為城市運行的“大動脈”,在城市的發展和建設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交通網絡并不是簡單的規則網絡,而是一個典型的由道路物理網絡與交通需求網絡結合而形成點-邊結構網絡,其中道路可以抽象為連線,道路特征點抽象為節點,大量的點和線組成了交通網絡構架[13]。城市交通網絡主要分為道路網絡、公共交通網絡、物流網絡等,根據基于GIS的公交換乘模型需求,這里只對道路網絡和公共交通網絡進行表述。
道路網絡主要由道路路段和道路節點構成。節點是引起實際道路中斷的分界點,表示城市道路屬性或交通流在該點發生變化;而路段是由節點截斷的城市道路,因此路段與節點的復雜程度決定了道路網絡的復雜程度。而城市道路網絡作為空間網絡具有不同于抽象網絡的特性,這些特性決定了城市交通網絡的拓撲性質[14]和屬性性質。首先,城市道路網絡是具有實際意義的網絡,并不是抽象出的,路網中的路段都存在與之相對應的現實道路,節點都具有明確的位置,可在現實中找到,如圖2(b)所示為某市部分道路網絡,其中的路段均具有唯一性且可在現實中圖2(a)找到對應的道路;其次,道路節點與路段的連接受到現實道路情況的約束,每個節點連接的路段數是與現實路況相符的,而每條路段的起始位置和終止位置由兩個節點確定;再次,現實道路的運行情況決定道路網絡的屬性,現實道路中存在禁止左行、禁止右行、禁止直行、禁止掉頭等情況,這些道路性質決定了道路網絡的屬性,如圖2(a)中的現實道路中存在單行道,則在其道路網絡中以禁行標志體現圖2(b)。

圖2 現實道路及屬性表達示意圖
公交網絡是由公交線路、公交站點以及公交換乘區構成的。首先,不同于道路網絡,公交網絡中的“線”是抽象出的要素,并不能夠在現實中明確的找到,而公交站點則是實際存在的地物特征;其次,公交線路具有重合的特點,即不同的公交線路在某個路段內可能發生重合,因此在該路段中的公交線路不具有唯一性;最后,公交站點不存在于公交線路上,并且他們是多對多的關系。
綜上所述,城市道路網絡與公交網絡具有其各自特點,因此,為他們進行高效的邏輯關系組織是實現本文目標的關鍵。
2.3 公共交通系統要素邏輯關系表達
公共交通系統包括了城市道路網絡與城市公交網絡以及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如圖3所示,城市道路網絡中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包括:①道路節點標識符具有唯一性,因此可以通過路段的起始節點標識符和終止節點標識符索引到對應節點;②路段具有唯一的起始節點和終止節點,因此通過確定起始節點與終止節點可以鎖定唯一路段。城市公交網絡中要素的邏輯關系包括:①公交線路的行駛路線決定了經過站點和道路節點的次序;②公交線路與公交站點是多對多的關系;③公交站點與公交換乘區是一對多的關系,換乘區內站點數量與換乘站點位置及其周邊路網狀況相關,一個站點的換乘區至少包含其自身。本文中公交線路與節點、站點通過公交線路-站點-節點索引建立邏輯關系。公交線路-站點-節點索引中設置公交線路標識符以檢索公交線路,設置換乘矩陣檢索換乘站點的公交換乘區,設置站點、節點出現在指定公交線路中的次序索引以確定公交線路運行方向,設置節點標識符和站點標識符檢索道路節點與公交站點。

圖3 道路網絡與公交網絡邏輯關系圖
通過上述的邏輯關系組織建立公交線路與站點、公交線路與節點、公交線路與路段等不同要素間的相關關系,基于上述相關關系在換乘模型中通過已知要素檢索其他要素的空間信息和詳細屬性信息。
3 基于GIS的公交換乘模型
基于GIS的公交換乘模型包括換乘矩陣模型和公交線路查詢模型。通過換乘矩陣模型求解站點在指定閾值內的公交換乘區,同時在道路網絡數據、公交網絡數據以及求解得到的公交換乘區的基礎上通過公交線路查詢模型求解公交線路。
3.1 換乘矩陣模型
本文通過換乘矩陣記錄各站點的公交換乘區。定義換乘矩陣的行名和列名均為公交站點的編號,矩陣的元素為0或1。如表2所示,若兩站點間存在換乘關系則其對應元素設為1,反之則設為0。顯然,因為同站與其自身必定具備換乘關系,所以換乘矩陣對角元素均為1,且換乘矩陣是一個對稱陣,所以將其存儲結構設定為半角矩陣。
換乘矩陣是由兩個要素確定的:
(1)兩站點間的距離:
城市中兩站點的距離可分為空間距離和道路網中的最短路徑。兩站點的空間距離可認為是兩點間的直線距離;兩站點間的最短路徑可由Dijkstra算法[15]求解得到。
本文采用兩站點在城市路網中的最短路徑來計算換乘矩陣。很多情況下,人們步行換乘的路線并不是直線,因而采用兩站點空間距離計算換乘矩陣會產生數據不精確甚至數據錯誤的可能性,例如:某兩站點空間距離小于乘客可忍受的步行換乘距離,但是因為兩站點間有障礙物阻擋,乘客換乘必須繞行較遠距離,此時若設定這兩個站點存在換乘關系則會誤導乘客,給乘客的出行帶來不便。而城市路網中兩點間的最短路徑則是道路網絡中由出發點到目標點實際存在的線路,且換乘矩陣所標識的具有換乘關系的兩個站點必定存在小于乘客可忍受步行換乘距離的路線,所以采用最短路徑計算明顯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2)乘客可以忍受最大步行換乘距離dmax:
不同乘客可以忍受的最大步行換乘距離一般是不同的,因而對于不同的乘客換乘矩陣是不同的。本文通過設定 300 m、500 m、800 m三種不同的閾值dmax計算了得到了 300 m換乘矩陣、500 m換乘矩陣和800 m換乘矩陣來滿足不同乘客的出行需求。
根據上述兩要素最終可由下列公式確定換乘矩陣:

其中hij為換乘矩陣中第i行第j列的元素,dij為編號為i的站點和編號為j的站點間的最短路徑,dmax為計算換乘矩陣設定的閾值,n為城市路網中公交站點數。
3.2 換乘時間模型
公交路線的確定離不開時間這個重要的參數,往往大型城市的公共交通網絡中存在上百條公交線路,不同公交線路的始發和結束時間,時間間隔都不一定相同。因此,時間因素需要作為一個重要參數放入換乘模型中進行考慮。
本文通過在公交線路數據中設置首班車時間、末班車時間以及發車間隔,使換乘模型更為準確和符合實際。乘客在查詢路線時可以選擇將乘坐時間輸入,模型將乘客乘坐時間作為可選參數在數據庫中進行選擇,保留符合乘客乘坐時間的線路。
3.3 公交線路查詢模型
本文針對復雜的軌道交通網絡、豐富的公交資料結合基礎地理信息重新設計更為合理的公交換乘算法模型,使其同時為最優推薦,即直達車優先考慮,其他方案根據經驗公式綜合評估步行距離、總里程、換乘次數、公交類型等因素進行篩選的原則提供查詢結果。如何設計模型、測算經驗公式使其更合理、高效提供方案是關系到本系統實用性的最主要因素。
公交換乘模型建立在城市道路網絡的GIS表達、城市公共交通網絡的GIS表達以及公交換乘矩陣上,模型算法思路是:根據城市道路網絡的GIS表達和城市公交站點的GIS表達解算出不同閾值下的換乘矩陣并將其錄入數據庫;根據起始站點和終止站點檢索公交站點的GIS表達,尋找站點唯一編號后結合公交路線的GIS表達和公交換乘矩陣依次進行直達路線檢索、一次換乘路線檢索和兩次換乘路線檢索,考慮到計算效率和實際乘車情況,3次及3次以上換乘路線被視為不可到達。
公交路線查詢模型具體分為:
(1)直達線路查詢模型如圖4所示。

圖4 直達線路查詢模型圖
(2)一次換乘線路和兩次換乘路線查詢模型,如圖5、圖6所示。

圖5 一次換乘線路查詢模型圖

圖6 兩次換乘線路查詢模型
4 城市公交換乘實例分析
為了驗證算法的可靠性以及效率,本文采用杭州市的城市道路網絡數據和城市公共交通網絡數據進行驗證。實例選取杭州市區西北側的“大關山站”為起始站點,杭州市區東南側的“新街站”為目的地站點,換乘時間設定為夜間10時,換乘閾值設定為 500 m進行測試。該實例的選取跨越杭州市區,屬于遠距離的公交線路查詢,具有典型性。

圖7 公交路線查詢實例圖
查詢結果如圖7所示,路網中的點表示公交站點,加粗實線表示查詢得到的公交線路,圖右側為乘客在中轉站進行步行換乘的線路,虛線表示乘客步行換乘的路線。結果表明全程共需要進行兩次換乘到達目的地,總行程長度約為 32.3 km,具體路線為:
(1)從大關山站乘坐K348路公交車,行駛55站約 22.9 km到武林門北站下車;
(2)從武林門北站步行約 358 m到武林門湖墅路口站;
(3)從武林門湖墅路口站乘坐K106路公交車,行駛14站約 7.1 km到總管塘站下車;
(4)從總管塘站換乘K520路公交車,行駛15站約 2.3 km到終點站新街站下車。
根據上述結果可以發現,通過設定步行換乘的最大閾值,乘客在出行過程中需要步行換乘的最大距離為 358 m,經過兩次換乘后到達目的地,完全符合乘客設定的需求。
5 結論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作為區域經濟中心的城市擴張是在所難免的,而伴隨而來的問題也與日俱增,包括城市居民出行在內的所有問題都面臨著新的挑戰。因此,不斷探索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是城市居民正常生產生活的保障。本文結合地理信息系統在解決空間數據方面的優勢和傳統的基于數據庫的公交換乘模型在解決屬性數據方面的優勢,提出了基于GIS的公交換乘模型,經過測試顯示,換乘模型能夠滿足對步行換乘距離有要求的乘客的需求,并對查詢結果采用可視化顯示和文字說明結合的方式,使公交路線更為直觀和明了。
[1] 楊新苗,王煒,馬文騰等.基于GIS的公交乘客出行路徑選擇模型[J].東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0,30(6): 87~91.
[2] 王建林.基于換乘次數最少的城市公交網絡最優路徑算法[J].經濟地理,2009,25(5):673~676.
[3] 王慶平,張興芳,宋穎等.城市公交換乘的數學模型及其算法實現[J].計算機工程與應用,2008,24(7):246~248.
[4] 張林峰,范炳全,呂智林.公交網絡換乘矩陣的分析與算法[J].系統工程,2003,21(6):92~96.
[5] 李曙光,蘇彥民.基于GIS的城市公交路網的最優路線算法研究[J].中國公路學報,2003,16(3):83~86.
[6] 趙月,杜文,陳爽.復雜網絡理論在城市交通網絡分析中的應用[J].城市交通,2009,7(1):57~65.
[7] W SC,T CO.Estimation of time-dependent origin-destinationmatrices for transitnetwork[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1998,32(1):35~48.
[8] 何迪,嚴余松,郭守儆等.基于矩陣分析的公共交通網絡最優路徑算法[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7,42(3):315~319.
[9] 王杰臣,毛海城,楊得志.圖的節點-弧段聯合結構表示法及其在GIS最優路徑選取中的應用[J].測繪學報,2000,29(1):1~5.
[10] 嚴寒冰,劉迎春.基于GIS的城市道路網最短路徑算法探討[J].計算機學報,2000,23(2):210~215.
[11] 張福浩,劉紀平.一種基于Dijkstra的海量空間數據最短路徑算法[J].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28(4):554~557.
[12] 鄔倫,劉瑜,張晶等.地理信息系統-原理,方法和應用[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134~176.
[13] 吳建軍,李樹彬.基于復雜網絡的城市交通系統復雜性概述[J].山東科學,2009,22(4):68~73.
[14] 徐建華.現代地理學中的數學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59~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