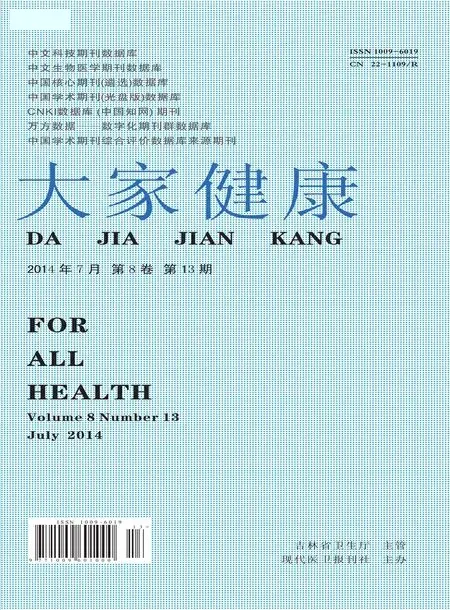淺析艾滋病患者的自我護理原則
李冬梅
(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疾控中心 甘肅酒泉 736100)
淺析艾滋病患者的自我護理原則
李冬梅
(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疾控中心 甘肅酒泉 736100)
艾滋病帶原是一種慢性傳染病的生物學狀態(tài),需要透過長期的自我護理來維持身體健康與舒適感,在傳染病防治上更有風險管理的意義。目前醫(yī)護公衛(wèi)知識典范強調(diào)艾滋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模型,以行為作為研究變量和介入目標,自我護理被簡化為個人的效能與責任問題,感染者的自身經(jīng)驗在專業(yè)知識中被邊緣化,很難真正從感染者的日常生活脈絡中看到他們自我護理上付出的努力和面臨的困境。本研究經(jīng)由文獻分析法,針對艾滋病患者的自我護理原則進行分析,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
艾滋病,自我護理,原則
一、艾滋病及其特征
艾滋病(HIV)一旦感染,終身帶原;作為一種慢性傳染病,它有別于一般慢性病,也不同于一般傳染病或性病。HIV會侵犯并破壞人體免疫系統(tǒng),引發(fā)伺機性感染或其他免疫低落相關疾病,而有致命的可能;而一般性病在經(jīng)過治療后,或許仍有病原的帶原,卻鮮少有致命的情況。雖然HIV帶原現(xiàn)已有HAART藥物延長病程,然而在漫長的帶原生涯中,感染者可能經(jīng)歷各種因免疫機能低落而引發(fā)的健康狀況,需要長期的治療(即服藥)與自我護理來維持身體健康與舒適感。因此HIV不只是一般的傳染病,它同時具有慢性病的特性,而慢性病的病情控制、管理與照顧,主要是在以個人為中心的生活場域中實作,與醫(yī)院間的關系并不見得非常密切,尤其HIV感染者通常只有在剛驗出陽性、或是剛開始服藥時,與醫(yī)院與個人管理系統(tǒng)的互動會頻繁些,后來只要三到六個月回診一次,因此在感染者的日常生活中,醫(yī)院與個人管理系統(tǒng)并不密集地發(fā)揮作用。[1]
HIV帶原同時也具有傳染病的特性,除了避免將病毒傳染給他人外,也要避免自己再度感染其他病毒株、或是得到其他性病,在自我護理上更多了一層風險管理的意義。由于HIV傳染途徑的特性(在此特別指性行為與靜脈注射)主要在以自身與他人間的微觀互動場域中被處理,并非遠離生活場域的國家機器所能完全掌控。總之,HIV帶原作為一種慢性傳染病,并不像急性傳染病那樣由國家在短時間內(nèi)高度密集介入,而是仰賴個案對于身體狀況與生活習慣的自我管理。
二、艾滋病患者的護理
實證典范研究將HIV感染者的健康議題界定為生理癥候或心理適應問題,常見的身心問題包括疲倦、燥熱、神經(jīng)痛、惡心反胃或嘔吐、食欲不振、焦慮、憂郁和恐懼等,并且探討病者的適應策略。這是一種醫(yī)療的病理化-介入邏輯,將感染者的病苦操作化為需要經(jīng)由特定身體策略而解決的病理問題,也較少關注到病者的生活處境。這是就一種健康科學的眼光來檢視病人的行為與生活型態(tài),界定出不健康的定義,將不健康歸因于個人特質(zhì)、行為、能力或信念問題,并將維持自身健康的責任歸于個人,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采行理性的方式-即專家認可的方式-照顧好自己。這種為自己的健康負責的觀點,不只出現(xiàn)在慢性病人是否有做好自我護理的判準上,也存在于傳染病的預防層面,不論是已感染者必須改變不安全性行為、還是未感染者必須保護自己避免感染,都是理性人必須遵從的倫理原則。[2]
在公共衛(wèi)生上,HIV感染者的健康意味著一種生活型態(tài)上的調(diào)整。慢性病生涯中的健康議題,跨越了公共衛(wèi)生上的三段五級,從預防自己再度感染其他疾病、定期回診追蹤、到服藥治療或醫(yī)療照護,自我護理不只是疾病控制,同時也涵蓋了健康促進。目前的健康促進研究,多著重于關心一般大眾的健康;然而健康促進對于帶病者來說,有更為特別的意義:是一種避免自己進入發(fā)病狀態(tài)的作為,是一種有別于醫(yī)療介入的自我技術。
三、艾滋病患者的自我護理原則
本研究以社會及文化的視角,重新理解傳統(tǒng)上被歸為醫(yī)學、護理、公共衛(wèi)生領域的研究議題。在生物學與行為科學的知識脈絡中,病者的自我護理被認為個人行為或效能問題;在當今新自由主義滲透的生活世界中,自我護理被視為個人的責任。而本研究希望呈現(xiàn)的是:病者的疾病經(jīng)驗與自我護理可以有不同的認識途徑。如果我們將疾病問題還原為倫理問題,疾病事件則開啟了一段對生命重新認識與反思的過程,而病者的自我護理實作則反映了一種關照自我的倫理,是帶病主體對自身生命的治理。因此,經(jīng)由探討自我護理這個看似技術性的經(jīng)驗,我更核心的關懷其實在于:病者如何面對帶病狀態(tài)中自身的生命處境。[3]
將疾病浮現(xiàn)的生活場景:就醫(yī)、服藥、病苦感的出現(xiàn)、養(yǎng)生法、性實作等感染者切身體會到疾病存在的時刻,作為探究的起點。[4]在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動作中,感染者隨時要面對可能發(fā)病的焦慮、維持CD4與身體狀況的焦慮、以及跨越人我界線的焦慮。感染者對于生病這個醫(yī)學上的事實,有著某種心理深層的抗拒感。這種感覺是隱晦的,但經(jīng)由一些具體事件而表露出來:抗拒吃藥、不安全性行為、積極的養(yǎng)生法、規(guī)律的生活等等。[5]
每個人表現(xiàn)這種焦慮的方式不盡相同,自我護理的方式也異質(zhì)而多樣,這與感染者的患病處境、生活情境與社會脈絡有關。如果我們回到感染者的生活經(jīng)驗來看,可以發(fā)現(xiàn)常民的自我護理實作是在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在動態(tài)過程中權宜而做,盡管不完全符合專業(yè)知識與體制涵納的范疇,然而卻也并非反體制、反社會的極端者。感染者以種種行得通方式,重新編排、重新使用,并再現(xiàn)出各種異質(zhì)的技法,而這一切都依靠環(huán)境所能提供的可能性。因此感染者并非逃離這個強加于他身上的體系,而是在它的法則中建立起一個有創(chuàng)造力的不同可能性。這是一種實作而生的自我護理知識,做了后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做,同時也是在帶原生涯中面對各種不確知而試試看的自身知識與實作感。
[1]朱海林,陳雅雪.我國艾滋病防治模式的倫理思考[J].醫(yī)學與社會.2012(02)
[2]張明利,魏俊英,吳毓敏,郭選賢,程延安,屈冰.HIV/AIDS生存質(zhì)量量表(HIV/AIDSQOL-46)[J].中醫(yī)學報.2010(04)
[3]陳曉,陳小英,卓藝玲.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抑郁狀況分析與護理對策[J].解放軍護理雜志.2008(19)
[4]李蕤,徐玉娥,武俊亞.家庭干預在艾滋病患者中的應用體會[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0(11)
[5]周巧玲.艾滋病患者心理調(diào)查及護理對策[J].醫(yī)藥世界.2009 (06)
R473.5
B
1009-6019(2014)01-0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