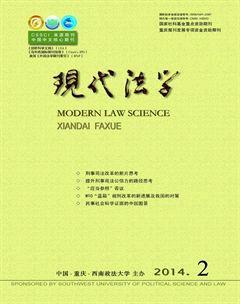WTO“藍箱”規則改革的新進展及我國的對策


摘要:“藍箱”不僅是大國間貿易利益博弈的產物,而且由于其免于削減承諾,事實上已成為某些發達國家固有的特權,對農產品貿易的扭曲作用不可忽視。多哈回合“藍箱”規則談判的近期成果——2008年的“模式草案”雖嚴格限定了“藍箱”使用紀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若干特殊與差別的待遇,但卻從另一方面擴大了“藍箱”的作用空間,使慣以使用“藍箱”的發達國家繼續從中獲利。作為一個從未使用過“藍箱”的農產品貿易大國,我國將會因之面臨更加不利的競爭局面。故在即將重啟的多哈回合農業談判中,我國宏觀上應繼續恪守發展中國家的原則與立場,提高發達國家的“藍箱”使用標準;微觀上則應把握改革時機,采取更為靈活的談判策略,促使發達國家對“藍箱”支持進行實質性削減。與此同時,我國也應當對現行的國內農業補貼制度進行適時的調整與優化,以里外配合,形成合力,為我國未來農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內外部規則環境。
關鍵詞:國內支持;“藍箱”;《框架協議》;模式草案
中圖分類號:DF961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4.02.13
農產品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農業是解決人類生存的生產部門,無論對于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基于農業在國內產業中的基礎性、弱質性、敏感性和外部性,各國都對農業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護。具體到農產品貿易領域,發達國家慣以使用的各種國內支持(domestic support)措施就是典型例證“國內支持”作為一個固定的提法源于WTO《農業協定》,然WTO規則體系迄今并沒有對之做出明確的定義。從《農業協定》及其附件相關規范內容看,“國內支持”可理解為一國政府在境內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農業和農民為扶持資助對象所進行的各種直接或間接財政支持措施的總稱。這些支持措施不需要計入農業的生產成本,但會不同程度造成農產品國際貿易價格的扭曲。就此而言,“國內支持”與“農業補貼”(agricultural subsidy)的內涵并不一致。后者包括“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是前者的上位概念,而在我國入世承諾放棄出口補貼的情形下,當前可使用的農業補貼只剩下國內支持,即人們通俗所說的“三箱”補貼。(參見:王軍杰.論我國農業國內支持法律制度的完善與重構[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2,(2):120.),特別是其中具有貿易扭曲作用的“藍箱”支持措施因其被免于削減承諾而備受爭議,并逐漸成為晚近多邊農業自由化的一大障礙。因此,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對發達國家既有的“藍箱”支持進行有效的限制。截至2012年底,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阿根廷、泰國等成員方和凱恩斯、G20、G33等談判集團向WTO提交了109個農業提案,而其中就有49個涉及“藍箱”問題。凱恩斯集團主要是由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巴西、南非等19個農業出口國組成的聯合體,主張撤銷貿易壁壘并穩定削減影響農業貿易的補貼;G20集團主要是以巴西、印度、中國、阿根廷、泰國等20個發展中農業貿易大國組成,主張實質性消除發達國家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等貿易扭曲措施,推動發達國家開放市場;G33集團則由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烏干達、坦桑尼亞等一些中美洲和非洲地區的發展中成員組成,主張在農產品進口自由化時設立自我決定的“特殊產品”類別以免除減讓和爭取發達國家給予“特殊與差別”的待遇。這些國家和談判集團的提案都可以在WTO官網(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rulesneg-e/rulesneg-e.htm)查到。此外,提案的數目系筆者自行統計,而非來自WTO的官方統計(WTO沒有相關的統計數據)。那么,“藍箱”緣何成為各方談判關注的焦點?目前WTO在此取得了哪些進展?后續談判前景如何?這些進展今后會對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帶來哪些潛在的利弊影響?對這些問題,目前國內尚無系統深入的研究。以下筆者嘗試做一全面的梳理與剖析,從中探尋我國未來參與后續農業談判的應對之策,以期對破解當前多哈回合農業談判僵局和更好地調整國內農業補貼制度有所裨益。
現代法學陳斌彬:WTO“藍箱”規則改革的新進展及我國的對策一、美歐貿易角逐的產物:WTO“藍箱”規則的形成與缺陷1995年烏拉圭回合達成的WTO《農業協定》以“政府執行的國內農業政策是否對農業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為標準,將成員方現有的各種農業國內支持措施分為“要求削減承諾”與“免于削減承諾”兩類。為認識與理解上的方便,人們習慣于用“綠箱”(green box)、“黃箱”(amber box)與“藍箱”(blue box)三種交通信號燈的顏色對之進行形象化的描述和區分。其中,“綠箱”屬于免于削減承諾的國內支持措施,諸如政府一般服務、糧食的安全儲備補貼、自然災害救濟及區域援助補貼等。參見:《農業協定》附件2的規定。這些措施因其通過政府的服務計劃提供,不構成對生產者的直接支付,對生產和貿易沒有影響,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故免于被削減。相反,“黃箱”指的是政府通過貨幣或特定產品形式給予農產品生產者的直接支持,像價格補貼、營銷貸款、按產品種植面積或牲畜數量給予的補貼以及種子、肥料、灌溉等投入的補貼等。這些支持因其會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和降低農產品的生產成本,會給農業生產和貿易帶來扭曲作用及影響,故屬于被要求削減承諾的范疇。根據《農業協定》第6條(b)款和第6條(d)款,“黃箱”被削減并非絕對,其還存在著“發展性支持”和“微量支持”兩種削減例外。“藍箱”則指那些本應削減,但因限產而無須削減的直接支付措施,依《農業協定》之界定,這些直接支付包括:按固定面積和產量的補貼;按基期生產水平的85%或85%以下的補貼及按固定牲畜頭數給予的補貼三種。參見:《農業協定》第6條(e)款。
為什么同為扭曲和影響農業生產和貿易的直接支付措施,“黃箱”被納入綜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以下簡稱AMS)中加以削減“綜合支持量”(AMS)是指以貨幣形式表示的,有利于基本農產品生產者的對某一個農產品提供的年度支持水平,或指有利于一般農業生產的非特定產品的年度支持水平。與之相對稱,“綜合支持總量”(Total AMS)是指所有的基本農產品和非特定產品的綜合支持量的總和。各成員方承擔國內支持的削減義務以基期的綜合支持總量為基準,主要針對超過微量支持水平的“黃箱”支持。相關內容參見:《農業協定》第1條(a)款和(h)款之規定。,而“藍箱”卻可以免于削減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須從“藍箱”規則的形成過程談起。
眾所周知,在美歐主導的GATT時期,農業談判同其他領域的談判一樣,其進程和結果完全掣肘于兩締約方的政治意志與經濟實力之較量。其中,纏繞于美歐之間近30年的“油籽補貼”爭端案就是這種較量的集中反映。從1960年GATT狄龍回合談判開始,當時的歐共體為換取美國不將其谷物的關稅列入約束稅率,一方面承諾給予從美國進口的大豆(主要是油籽)以零關稅待遇,而另一方面,為了保護本地區的油料作物,從1962年開始,其又把原來對大豆的補貼改成對榨油商的補貼,即凡用歐產大豆榨油者均給予收入補貼。此一舉措造成美國大豆在歐洲市場中的銷售份額急劇下降,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在多次與歐共體協商未果的情形下,美國于1990年向GATT指控歐共體違反國民待遇原則,扭曲了歐產大豆與美國大豆的競爭關系。GATT專家組經審理裁定美國勝訴。歐共體被迫從1991年起對上述政策做了調整,將原先給榨油工人的補貼改為按種植面積直接給農民或生產者的收入補貼。美國對此依然強烈反對,認為這種調整雖然避開了國民待遇原則,但同樣會起到刺激歐共體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效果,致其生產出超量和過剩的油籽以迫使政府給予出口補貼,仍會扭曲貿易,損及歐共體先前承諾給予美國大豆零關稅的預期利益。歐共體不服,認為對油籽生產者的收入補貼與扭曲貿易無關,不應受到GATT規則的約束。雙方互不相讓,為此再次訴諸GATT專家組二度裁決。雖然美國在裁決中再次勝訴,但因歐共體的反對,該裁決在GATT理事會中最終未獲通過,農業談判因此不歡而散。此后,美國便宣布從1992年12月5日開始對歐共體價值3億美元的進口農產品加征200%的懲罰性關稅,雙方旋即陷入了一場報復與反報復的貿易戰。
與此同時,當時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也到了最關鍵、最艱難的時期。各方已無力影響談判進程,只能寄希望于“油籽補貼”案爭執不下的美歐。為此,雙方又進行了多輪磋商和密談,直至1992年11月21日,形勢才得以扭轉。雙方在華盛頓的布萊爾莊園(Blair House)達成《布萊爾莊園協議》。在該協議中,歐共體同意美國提出的削減其油籽種植面積的要求,但美國以承認其“補償支付”(compensation payments)的合法性為前提。歐共體于1992年通過了“麥克希瑞改革計劃”(Macshacarry Plan),提出“補償支付”,對農業生產者從價格支持轉為直接收入支持。美國也正想借此為其國內的“差價補貼”(deficiency payments)尋求合法性支持。“差價補貼”是美國1973年《農業法》確立的一項制度,其要求政府對主要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間的差額給予農場主補貼,并規定享受補貼者必須參加政府的減耕計劃。于是,兩相交換,各取所需,雙方很快就達成共識,認為對農民的“收入補貼”雖有扭曲貿易的作用,但在限產的條件下危害不大,可被允許,無需同“黃箱”一樣被納入AMS削減。為了將此與以往那些無限產要求而理應被削減的“收入補貼”區別開來,雙方就將這種限產條件下的“收入補貼”用“藍色”標簽罩住,以作油籽貿易紛爭的最終了結[1],這就是后來WTO《農業協定》“藍箱”規則的前身。那么,在這么多信號顏色中,美歐雙方當時何以唯獨青睞“藍色”標簽呢?在筆者看來,其遮人耳目的意圖非常明顯:因為藍色顏色較深,用該色罩住會使人們看不清分入該箱的東西究竟為何物,這樣就容易將那些扭曲農產品貿易和生產的支付措施無害化,以求蒙混過關。可見,“藍箱”純粹是美歐在“油籽”貿易戰中為互給對方臺階可下而達成的一項利益交易,是雙方為維護自己固有的補貼特權進行角逐和妥協的產物。
比較WTO《農業協定》中的“三箱”支持規則,不難發現,“綠箱”免于削減是“理直氣壯”的,這是因為其對農業貿易沒有或只有極小的扭曲作用,對農業生產沒有或只有極小的影響。相反,“黃箱”被要求削減也是“理所當然”的,這是源自于直接支付對農業生產和貿易的明顯扭曲作用。但反觀“藍箱”,作為直接支付,本與“黃箱”無異,然其僅憑限產條件的要求就逃避了本屬于自己應承擔的削減義務,則似乎有點“理屈詞窮”。以筆者觀之,《農業協定》對“藍箱”的這種限產要求充其量也只是將其危害限制在一定范圍內而已,并不能抹殺其本為“黃箱”的貿易扭曲效應。并且,《農業協定》的這種限制也僅是對“藍箱”總量的限制,而不關涉對特定產品的“藍箱”支持量。這就意味著,只要“藍箱”支持所涉及的產量不超過農業基期生產水平的85%,成員方就可以在基期內的任何時期把《農業協定》允許的“藍箱”額度集中用于某一特定農產品。由此可見,在某些特定的農產品生產貿易中,“藍箱”仍有可能會同“黃箱”一樣造成嚴重的扭曲效應,其危害性不可小覷。WTO歷史上第一次針對國內支持政策的爭端案——2003年巴西訴美國陸地棉案就極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該案中,巴西向WTO提出了關于美國對棉花提供的國內支持和出口補貼違反WTO規則的4項指控,其中就有一項認為美國對棉花的國內支持措施違反了《農業協定》第6條,即美國1996年至2002年間實施的生產靈活性合同支付(Production Flexibility Contract Payments,簡稱PFC)和2002年后正在實施的直接支付(Direct Payments, 簡稱DP)不應計入“綠箱”或“藍箱”中而被合法化。其余三項指控包括:美國對棉花的國內支持不符合《農業協定》第13條b款;美國對棉花提供的出口補貼不符合《農業協定》第13條c款及《SCM協定》第5條和第6條;美國的使用者銷售支付、出口信貸擔保和ETI法案下的補貼違反了《農業協定》、《SCM協定》和GATT1994第16條等出口補貼紀律。有關本案詳情,請參見:WTO.United States-Subsidies on Upland Cotton[EB/OL].[2013-09-21].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267_e.htm.因為這些看似“藍箱”的支付措施都將支持量在上述時間段內集中用于7種特定農產品,特別是棉花身上,致使美國棉花生產者可基于基期內任何時期的種植面積和產量持續獲得補貼,這顯然不是“藍箱”限產的初衷,而是利用“藍箱”規避削減義務的違法行為。巴西提供的數據表明,從1999年8月至2003年7月間,美國為棉農提供了約125億美元的巨額補貼,棉花種植面積增加了100萬公頃,國際市場上棉花價格跌到64美分/公斤,為近20年來平均價格的40%,嚴重損害了巴西作為傳統產棉國的利益,致其棉農損失近4.78億美元。2004年9月8日,專家組雖裁決美國敗訴,認為美國對陸地棉的國內支持不符合“和平條款”的豁免條件,但卻未對美國上述兩種直接支付措施何以違背國內支持紀律予以正面評價和說明。與之不同的是,在本案中,專家組對巴西指控美國的其余三種國內支持措施(營銷貸款、反周期支付、市場損失援助)和三種出口補貼(出口信貸擔保、使用者銷售支付和出口支付)的違法性均做了正面的定性和解釋,并建議美國取消。
巴西與美國的陸地棉爭端案表明,WTO《農業協定》雖然規定了“藍箱”的三種支持手段必須與限產計劃相結合,但很容易出現以下情況:只要成員方的國內農業支持政策在形式上符合限產的要求,即使給其他成員方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在WTO既有的補貼框架內卻似乎很難給予違法性的評價。在烏拉圭回合的實施期間,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是充分利用了WTO國內支持規則的不周延性,向其國內的大宗敏感農產品的生產者提供持續、巨額的補貼,嚴重扭曲了國際農產品的正常貿易。是故,自多哈回合談判啟動以來,受此影響的WTO成員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就一直強烈呼吁WTO改革“藍箱”規則,削減“藍箱”支持水平以及對特定農產品的“藍箱”支持進行封頂[2]。
二、北多南少:WTO成員方對“藍箱”規則的使用 “藍箱”規則雖為美歐之間利益沖突與妥協的產物,但其作為WTO《農業協定》的組成部分,無疑具備合法性外衣,仍是WTO各成員方除了“綠箱”之外應用國內支持措施的又一國際法依據。表1顯示,1995年至2004年間,WTO中僅有9個成員方使用或曾經使用過該支持政策。其中,歐盟最為頻繁,其不僅保持連續10年使用“藍箱”的記錄,而且額度逐年增長。特別是2004年,隨著捷克、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愛沙尼亞的相繼加入,歐盟“藍箱”支持在2006年就達到280億歐元的最高位。統計下來,歐盟10年間的“藍箱”使用量累計逾2400億歐元,位居WTO成員方之首。
作為農業補貼制度發源地的美國,在“藍箱”支持的使用上與歐盟則有所不同。為使本國農業“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美國于1996年頒布了《聯邦農業完善和改革法》,主動廢止了以往長期使用的差價補貼這一“藍箱”措施。但好景不長,迫于國內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下跌,農民增收的困難以及歐盟、日本等高水平農業補貼因素的倒逼,美國于2002年出臺了《鄉村發展與投資保障法》(以下簡稱《2002年農業法》)。該法確立了“貸款差價補貼、固定直接補貼和反周期補貼”三種嶄新的“藍箱”支持措施,對種植小麥、飼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高粱、燕麥、大豆的農民構建“三級收入安全網”。因此,雖然從1996年到2001年間,美國“藍箱”使用量為零,但2002年后又死灰復燃,而且增長勢頭迅猛。由表1統計可知,截至2004年,僅3年的時間,美國“藍箱”支持總量就突破了235億美元[3]。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原定于2007年到期的《2002年農業法》,由于各方分歧,直至2008年6月17日才被《2008年食物、保護與能源法案》(以下簡稱《2008年農業法》)所取代。不過,《2008年農業法》不但沿襲了《2002年農業法》的三種“藍箱”措施,而且還將干燥豌豆、小扁豆、兩種埃及大豆共4種豆類產品追加到補貼范圍。同時,新法又竭力倡導“收入保障直接補貼計劃”(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Program,簡稱ACRE),即所謂的“新反周期補貼”(counter-cyclical payments)。該補貼實施期從2009年至2012年,允許農戶自愿選擇適用反周期補貼或收入保障直接補貼,從而有效地彌補了反周期補貼根據價格補貼給予補償的漏洞,確保美國農戶原有的“收入安全網”更為安全。可以肯定的是,伴隨著《2008年農業法》的施行,美國的“藍箱”補貼額度到2012年必將又有一個大幅度的增長。迄今為止,WTO官網并沒有提供各成員方2005年后向WTO秘書處通報的最近幾年的“藍箱”使用量,故筆者在此只能對美國“藍箱”的使用趨勢做一個大致的研判。
其他成員方在“藍箱”使用上雖不及美歐頻繁,但從表1提供的數據同樣可以發現,其支持總量也呈逐年上升趨勢。以日本為例,其1998年開始推行“稻作收入穩定計劃”(Rice Farming Income Stabilization Programme, 簡稱JRIS)這一“藍箱”補貼政策之初,使用量僅為500億日元,然2004年就飆升到984億日元,在額度上增加了近1倍。
可見,在現有的《農業協定》框架下,WTO成員方在“藍箱”支持的使用上形成了“北多南少”的一邊倒局面從地理位置上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處在幾個主要發達國家南面,所以國際上通常把全球的發展中國家統稱為“南方國家”,把發達國家統稱為“北方國家”,并將這兩類國家泛稱為“南北國家”。所以筆者借此義將這種狀況概括為“北多南少”。有關“南北國家”指稱的由來,請參見:陳安.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第一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39.:北方國家即發達成員方特別是美歐不僅通過國內立法對“藍箱”關愛有加,而且在使用量上有增無減,節節攀升。南方的發展中國家則將其束之高閣,無人問津。其原因在于:發達國家農業產能長期過剩,借助“藍箱”的限產要求不僅可以有效對之加以抑制,而且又可以緩解本國“黃箱”在AMS中的削減壓力,以間接推動農產品出口,起到同出口補貼相同的效果。反觀發展中國家,這種“一石二鳥”的效果根本無法實現。原因有二:首先,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普遍面臨生產不足的問題,尚未達到限產的地步,難以滿足“藍箱”的使用條件;其次,“藍箱”作為一種直接支付,由政府公共財政負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財力貧弱,欲對此持續支出,可能無力為繼。兩相比較,發達國家長期以來都是“藍箱”規則不折不扣的受益者,實乃不言而喻。三、前進中的隱患:WTO“藍箱”規則改革進展述評2001年11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WTO第四次部長會議通過了《多哈部長宣言》(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決定啟動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即多哈回合談判。根據《多哈部長宣言》第45段的規定,多哈回合談判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結束。(參見:WTO. 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WT/MIN(01)/DEC/1[EB/OL].(2001-11-20)[2013-01-21].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da_e/dda_e.htm.)由于談判各方分歧較大,加之期間遭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談判幾度中止,目前尚無法預計何時完成。作為WTO成立以來的首輪多邊貿易談判,多哈回合旨在繼續推進貿易自由化,內容涉及貨物、服務、知識產權、氣候變化等廣泛領域。在這其中,農業問題最攸關成員方的切身利益,被公認為談判的重中之重[4]。《多哈部長宣言》第13條為此專門明確了各方在農業談判中的主基調,即實質性削減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在此基調下,“藍箱”自然成為各方談判首當關注的焦點。雖然多哈回合啟動至今12年,談判一波三折,屢陷困境,但客觀地說,已有的談判并非一無所獲。至少從“藍箱”規則改革的成果看,這個問題的談判已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特別是2008年“模式草案”的達成就是一個可喜的突破。概言之,迄今為止,多哈回合在“藍箱”規則上取得的談判成果包括:
(一)2004年的《框架協議》
《框架協議》全稱為《農業談判框架協議》(Framework for Establishing Modalities in Agriculture),由成員方于2004年8月1日在日內瓦達成。該協議對《農業協定》中的“藍箱”規則做了如下調整:
1.擴大“藍箱”支持的種類
《框架協議》增加了“與產量無關的直接支付”這一“新藍箱”,并且,在“新藍箱”下,“按基期水平的85%或85%以下給予”的直接支付能同時被賦予種植業和畜牧業,這使得“藍箱”可不再限于限產條件下使用。
2.厘清“藍箱”使用條件
《框架協議》明確了作為“藍箱”限定條件的面積和產量、基期生產水平、牲畜頭數是“固定”和“不變的”,從而避免了各國在解讀“藍箱”時的隨意性。
3.限制“藍箱”支持總量
這包括兩個方面:(1)規定“藍箱”支持總量不得超過某一基期(如1995-2000年)農業平均總產值的5%,此上限將適用于所有實際或潛在的“藍箱”使用者。(2)提出“總體性貿易扭曲支持”(Overall Trade-Distorting Support, 以下簡稱OTDS)的概念,并將“藍箱”納入其中進行分層削減。OTDS由AMS、微量支持(deminimis)與“藍箱”支持三部分組成。這使得“藍箱”支持不僅要受5%的上限約束,還要受到OTDS削減量的限制。
(二)2008年的“模式草案”有關該草案的詳細內容,請參見:WTO.Revised Draft Modalities for Agriculture(TN/AG/W/4/Rev.4)[EB/OL].[2012-01-02].http://www. wto.org/ english/tratop_e/ agric_e/ agchairtxt_dec08_a_e. pdf.
《框架協議》達成后,自2007年始,時任WTO農業談判主席的克勞福德·福克納(Crawford Falconer)就綜合各方小組談判的成果陸續發布了一系列工作案文(working documents),以期對包括“新藍箱”的協議內容進行更為詳細的修訂。從2007年11月至2008年1月,福克納發布了16個案文,其中有4個案文涉及“藍箱”規則的改革問題。(參見:WTO. Chairpersons Working Documents November 2007-January 2008[EB/OL].[2013-01-2].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gric_e/chair_workdoc_nov07_e.htm.)迄今為止,最新和最全的修訂要數福克納于2008年12月6日公布的“修訂模式草案”(revised draft modalities,以下簡稱“草案”)。該草案涉及“藍箱”規則改革與調整的內容有:
1.維持“新藍箱”不變
草案在承襲“新藍箱”的基礎上,明確成員方只能選擇新舊“藍箱”中的任一種,并且一經選定就不可變更,除非得到其他成員方的一致同意,否則不能隨意增加其他“藍箱”的使用。
2.降低“藍箱”支持總量
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爭取下,草案要求發達國家“藍箱”支持總量的上限從基期農業平均生產總值的5%下調到2.5%,但仍有不少于兩年的過渡期。
3.限制特定產品的“藍箱”支持
這包括:(1)對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特定產品的“藍箱”限額,為烏拉圭回合實施期間(1995-2000年)特定產品“藍箱”支持量的平均值。(2)對美國特定產品的“藍箱”限額為:1995-2000年農業平均產量的2.5%×在《2002年農業法》規定下對該特定產品的支持量占總量的比例×110%或120%(具體比例待定)。(3)所有特定產品限制不能超過上述限制,除非在該特定產品AMS限制中存在相應的和不可撤銷的一對一(棉花除外,必須是二對一)減讓時方被允許。(4)對于使用限產計劃下“藍箱”的發達成員方來說,盡管該成員方對其國內某一特定產品沒有提供過“藍箱”支持并且在基期內也沒有對該產品提供過“黃葙”支持,則對該產品的“藍箱”限制也應當寫進減讓表中,除非沒有超過2.5%的“藍箱”總量限制。4.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特殊與差別待遇
這包括:(1)發展中國家的“藍箱”總水平最大可為基期平均產量的5%,并且,可以選擇1995-2000年與1995-2004年中的任一個時間段作為基期。(2)如果某個產品同時超過基期農產品平均總產值的25%和平均綜合支持總量的80%,那么發展中國家可以選擇將“黃箱”措施轉入“藍箱”支持,即使這樣做會超過上述“藍箱”總量的限制。(3)成員方對每一特定產品的“藍箱”支持不能超過“藍箱”總量的10%,但對糧食凈進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可以放寬到25%。
5.細化OTDS削減方式
具體包括:(1)納入OTDS削減的“藍箱”總量應當為1995-2000年基期內向WTO通報的“藍箱”支持平均水平和這5年基期內平均農業生產總值的5%之間的較高者。(2)制定分層削減公式,分別為:第一層次為基期內OTDS>600億美元的,削減80%,如歐盟;第二層次為基期內100億美元<基期內OTDS≦600億美元的,削減70%,如美國;其余為第三層次,削減55%。(3)設定實施期限。對于發達國家,削減將在5年內完成。其中,第一、二層次在實施期的第一天就須削減1/3;第三層次在實施期的第一天須削減25%;對于發展中國家,其削減幅度為同層次發達國家削減水平的2/3,且可以在8年內完成,但若其AMS為零,則可免于任何的削減義務。
(三)對“藍箱”規則改革進展之評析
1.草案對“藍箱”使用的限制較以往更為嚴格與詳盡
較之烏拉圭回合的《農業協定》,《框架協議》不僅在內容上增加了對“藍箱”總量水平的控制,而且還確立了用分層公式將“藍箱”納入OTDS進行總量削減的原則。這就表明,即使“藍箱”免于AMS削減,也不能免于OTDS的削減。進一步地,為彌補各成員方通過避重就輕、酌盈注虛方式對某些關鍵農產品設置過高保護這一漏洞,草案在對“藍箱”總量封頂的基礎上對一些特定農產品的“藍箱”進行封頂,同時又結合各國基期內OTDS水平的差異與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形,從削減比例與實施期兩個方面對《框架協議》的削減原則做了細化,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有西方權威學者做過測算,如果草案成為正式協定,則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現行OTDS水平可望分別削減70%、80%與75%,而以基期的最終約束水平AMS算,歐盟和日本則至少要削減70%,美國至少要削減60%,其他發達成員至少要削減40%[5]。由此可見,從《框架協議》到草案,多哈回合對“藍箱”支持的限制都較烏拉圭回合時代嚴格與詳盡得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2.草案變相擴大了“藍箱”的作用空間,對發展中國家弊多利少
首先,草案承襲了《框架協議》確立的新“藍箱”標準,使“藍箱”支持不再與限產計劃相連,這無疑使得一些“黃箱”措施可以名正言順地借此轉化為“藍箱”而逃避削減,發達國家依舊可以從中受益。典型如美國現行的帶有“黃箱”特征的反周期補貼,就是因其可以被納入“新藍箱”而使美國得以大大緩解使用“黃箱”所面臨的AMS削減壓力。其次,草案雖然對特定農產品的“藍箱”使用進行封頂,但只要成員方在該特定農產品AMS限制中存在相應的和不可撤銷的一對一減讓,也同樣有允許成員方超額使用的例外。換言之,這其實是允許一國在其特定農產品的“藍箱”限制有余額時,可以將該產品的“黃箱”支持轉移到“藍箱”中,從而變相增加了“藍箱”的使用空間。再次,單從條文表面上看,草案在“藍箱”使用方面給予發展中國家很多特殊待遇,但如前所析,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連“藍箱”都無力使用的情形下,這種特殊待遇無異于畫餅充饑、形同虛設。故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真正的優惠并不在于被賦予多大的國內補貼機會,而在于發達國家的削減誠意以及實際削減的幅度。就此而言,縱然草案對“藍箱”規則的限制較以往更為嚴格,但在筆者看來,“新藍箱”的承襲和各種例外條款的存在都使得“藍箱”與“黃箱”的界限變得更為模糊,這可能是任何后續條款修補都無法挽回的農業自由化的倒退。
3.草案的法律效力與關鍵內容有待確定,對個別發達國家的約束有心無力
雖然草案為最終農業承諾的達成擬出了大致的輪廓,而且其起草與發布是建立在WTO主要成員方一系列密集談判所取共識的基礎上,被外界普遍認為是最有可能達成農業減讓協議的文本,但就當下而言,其畢竟不是WTO全體成員大會正式表決的“硬法”文件,充其量還僅是一個“成長中”的國際法,其法律約束力有待各方的承認與增強。這就導致很多發達成員方在國內“藍箱”政策的調整、跟進上出現了“靜觀其變、能拖就拖”的投機心態。再者,草案專門針對美國特定農產品的“藍箱”設計方案,允許其可以根據國內農業法的規定,選擇農業補貼程度最高的實施期(如2002-2007年度)來決定對某一特定敏感產品采取高額的支持水平加以保護。在美國國內農業法案通常5年一變的立法慣例背景下從1933年農業立法開始,美國基本上形成了每隔5年左右就進行農業法修改的立法規律,以保證其農業支持政策和相關措施與農業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相適應。,這一方案必使美國“藍箱”削減的起點充滿變數,無法真正做到公正與穩定,故而成為草案的一大硬傷和隱患。此外,縱觀草案全文及其附件,還留有很多用方括號(square brackets)和注釋(notes)標明的成員方仍存分歧或有待確定的關鍵內容。諸如大家較為關心的美國特定農產品“藍箱”支持的“上頭空間”(headroom)比例問題2010年3月22日,當時的WTO農業談判主席大衛·沃爾克(David Walker)在向WTO貿易談判委員會所做的全面盤點多哈回合農業談判的報告中指出,美國特定農產品的“新藍箱”上頭空間問題仍是“藍箱”后續談判的關鍵內容之一。(參見:WTO.Chairpersons Report to TNC[EB/OL].(2012-03-22)[2013-06-21].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gric_e/negoti_tnc_22march10_e.htm.),如上面的表2所示,究竟是110%抑或120%的方案,草案至今仍懸而未決,彰顯出其對美國“藍箱”約束的有心無力。參見:WTO.Negotiators Complete First Round on Agriculture “Templates” and Data[EB/OL].[2013-01-21].http://www.wto.org/english/ news_e/news09_e/agng_25sep09_e.htm.
4.草案的后續談判進展緩慢,美國的消極應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草案的發布對彼時陷入困境的多哈回合農業談判而言固然是一大利好,然其離正式減讓協議文本的達成還有很長距離,特別是草案遺留的一些有待確定的實體問題和相關數據編纂報備的程序性問題都亟待各成員方的通力配合。然而,在危機后國內經濟低迷、失業率持續走高的雙重壓力下,原本作為“藍箱”談判主要推手的美國,卻在草案正式發布后一改先前積極改革的自由化立場。在草案發布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首席農業談判代表喬治·格勞貝爾(Joe Glauber)在2008年7月的日內瓦談判會議上多次強調,如果其他國家同意主席有關削減農產品關稅的計劃,美國愿意將包括“藍箱”在內的農業補貼降低到建議的范圍內。當時的福克納主席稱贊美國的這一表態非常積極和具有建設性。(參見:WTO. Farms Talks Chair Reports on “Walks in Woods” and Prepares New Draft[EB/OL].[2013-01-21].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8_e/agric_7july08_e.htm.)喊著“變革”口號的奧巴馬政府一上臺就對多邊貿易談判采取消極抵制的態度,不但沒有積極從WTO多邊貿易體制下尋找談判轉機,反而將注意力的重心轉向區域貿易合作,特別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TTIP)的談判上,顯示出一種要“架空”WTO、重訂世界貿易規則的不良苗頭。參見:子默.美國或構建經濟北約,WTO將會被架空[N].人民日報,2013-07-02(海外版).是故,草案至今在一些遺留的實質問題的解決上仍躑躅不前,不見進展。不僅如此,在草案業已確定的部分“藍箱”規則技術性工作的執行方面,美國的表現也是乏善可陳,迄今仍停留在數據的收集與組織階段。2009年7月20日,WTO農業談判針對草案內容開始進入技術性的編纂工作(technical work)階段。這一工作要求成員方分五個階段進行:表格制定(template)、數據組織(data)、模式確立(modalities)、減讓表制作(scheduling)、相互核實(verify each other)和正式承諾(commitments)。這些工作是多哈回合談判形成法律文件的必經階段,屬于程序性內容。(參見:WTO.Farm Talks Head for Autumn of Forms and Content[EB/OL].[2013-01-21].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9_e/agng_20jul09_e.htm.)無疑,作為發達成員方的“領頭羊”,美國的這種消極和拖延已從另一方面弱化了草案原本的積極效應,增加了后續談判的難度。難怪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與法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2012年2月10日在倫敦的《金融時報》撰文,以“奧巴馬毀了多哈回合”為題公開批評奧巴馬在授意美駐WTO代表作一名“說不的”消極談判者,以這種不光彩的手段扼殺2011年12月的多哈回合多邊談判,對現行的多邊貿易體系造成了重創。參見:Jagdish Bhagwati.Shame on You,Mr Obama, for Pandering on Trade[EB/OL].[2013-06-21].http://www.ft.com/home/uk.
四、內外兼濟:我國參與后續“藍箱”規則談判之應對盡管自2008年7月27日日內瓦小型部長級會議以來,WTO多哈回合正式談判因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和美國在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上的對立分歧而被迫再次中止,但以此斷言多哈回合“死了”或WTO正喪失談判功能并不客觀。如美國前貿易代表蘇珊·斯瓦布(Susan Schwab)于2011年12月27日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就公開撰文宣揚“多哈回合死了”,WTO已喪失談判功能,并建議各國放棄多哈回合以另起爐灶。事實上,包括農業在內的WTO成員方非正式談判的步伐始終在緊鑼密鼓地向前邁進。以農業談判為例,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WTO農業委員會共組織成員方召開了36次非正式談判(informal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meeting)。相關數據由筆者根據WTO官方網站(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archive_e/agng_arc_e.htm)公布的數據統計而來。雖然當前全球貿易前景不容樂觀,與危機相伴而生的貿易保護傾向遠未消退,但各成員方仍在繼續努力尋求一切機會為多哈回合談判注入新的動力,以便在政治、經濟時機成熟時,為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奠定基礎[6]。令人欣喜的是,2013年1月18日,WTO新任農業談判主席約翰·阿當克(John Adank)決定啟動2013年作為農業談判的“調查年”(year of the questionnaire),要求成員方編纂好已有的談判數據、區分談判中的技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以及呈遞新的議案以盡早確定巴厘島第九次部長級會議上的談判計劃。WTO.2013 Kicks off as “Year of the Questionnaire” for WTO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EB/OL].[2013-01-21].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3_e/agng_18jan13_e.htm.2013年10月7日,亞太經貿合作組織(APEC)在巴厘島的部長級會議上聯合發表了題為《促進WTO第九次部長會議取得平衡與可信的一攬子成果》的聲明,敦促各方拿出政治意愿,重新展開多哈談判。在隨后的10月11日,與各方經過三次非正式協商會議后,WTO談判委員會正式將“關稅稅率的配額管理”、“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儲備”與“農業補貼”三個問題確定為2013年底巴厘島會議農業談判的重點。WTO.Farm Talks Chair Outlines Shape of What Might Be Possible for Bali Meetings[EB/OL].[2013-10-28].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3_e/agng_11oct13_e.htm.2013年10月25日,WTO新任總干事羅伯托·阿澤維多(Roberto Azevêdo)也發表了題為“巴厘談判終點線清晰可見”(The Bali Finish Line Is Clear and in Sight)的聲明,呼吁各方付出努力,確保在巴厘島會議上能達成小范圍的一攬子協定,以推動多哈回合談判走出僵局。WTO.The Bali Finish Line Is Clear and in Sight[EB/OL].[2013-10-28].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3_e/tnc_infstat_25oct13_e.htm.由此可見,多哈回合談判的重啟已近在咫尺,這對晚近陷入低谷的多邊貿易體制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利好。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創作完畢后不久,WTO第九次部長級會議于2013年12月7日在印尼巴厘島成功達成了WTO歷史上首份多邊性貿易協定即《巴厘一攬子協定》,實現了其成立18年來多邊談判的“零突破”。雖然該協定仍屬框架性文件,尚未對本文論及的“藍箱”規則的改革做出明確規定,但其在關鍵時刻挽救了WTO,標志著多哈回合后續談判的完全重啟,再次讓人們看到了多邊貿易體制未來前進的曙光。不過,鑒于“藍箱”規則在內的農業談判在整個多哈回合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談判恐怕難以在幾天的巴厘島會議上做到畢其功于一役。因此,作為正在蓬勃發展中的農產品貿易大國,我國理應在談判中結合自身實況進行周密的謀劃和應對:既要顧全大局,探索更為審慎和靈活的方式來完成“藍箱”規則的后續改革,又要未雨綢繆,盡快調整和優化國內農業補貼制度,從而內外兼施,形成合力。具體而言,相關的對策建議如下:
(一)捍衛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堅持“藍箱”總量削減和特定農產品使用封頂的原則
或許是在吸取2004年《框架協議》達成時的教訓如在2004年《框架協議》談判中,美國雖讓步同意對“藍箱”支持封頂,但卻以取消“藍箱”限產為前提。這一政策調整使之成功地把具有扭曲性質的反周期補貼納入“新藍箱”,從而實現了“箱體轉移”,讓很多發展中國家始料不及。,在2010年1月21日WTO非正式農業談判會議上,凱恩斯集團、G33等發展中成員不僅仍對草案內容不盡滿意,而且仍堅持主張廢除“新藍箱”或將之移入“黃箱”,以防發達國家(如美國)在“新藍箱”掩護下進行“箱體轉移”。在2010年1月21日WTO非正式農業談判會議上,凱恩斯集團在“藍箱”問題的態度上表現強硬:要求廢除“新藍箱”,以使“藍箱”支持水平小于“黃箱”。雖然此觀點較為激進,但其力促發達國家實質性削減“藍箱”支持措施的思路則值得我國加以恪守。原因有三:一是國內支持是出口補貼的根源,其和出口補貼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相互替代性。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若不堅持實質性減少發達國家的國內支持特別是其中的“藍箱”措施,則同樣無法防杜發達國家將其在國內受到支持的農產品用于出口,從而導致先前爭取到的發達國家承諾不進行出口補貼的積極效應大打折扣。在2005年12月18日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達成的香港《部長宣言》中,發達國家已向發展中國家承諾2006年之前取消棉花出口補貼,2013年前取消所有產品的出口補貼。二是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在“綠箱”支持還未用足,“黃箱”尚有很大空間可用的情形下,我國目前用“藍箱”規則對2億多農戶進行持續的直接收入補貼并不合算。因而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新藍箱”的存在必將進一步降低國際農產品的價格,對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貿易發展構成威脅。三是在加入WTO之初,我國在農業領域已做出了超前的讓步,包括承諾微量免除水平例外不超過相關農業年份農產品總值的8.5%,不對農產品維持或采取任何出口補貼等。相關內容參見:《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8,第152號減讓表中的第四部分第1節。這些承諾的約束水平遠高于發展中國家,有的甚至高過當時的發達國家。根據《農業協定》第6條第4款的規定,微量支持例外是指成員方對農產品“黃箱”支持量與該產品相關年度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在未超過法律規定的一定標準之內可免于削減。對此,《農業協定》允許發展中國家最高可不超過農產品總值的10%;又如,在放棄出口補貼方面,發達國家也只有到了2005年的香港《部長宣言》才正式做出此承諾。如果說我國做此承諾是彼時為盡快“入世”所需,那么在當前的情境之下,我國就要鎖定既有的承諾水平,拒絕承擔額外的義務,提防發達國家“藍箱”使用擴大化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沖擊。
是故,從宏觀上講,我國應繼續捍衛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在談判中堅持“藍箱”總量削減的原則。不過,慮及適度的國內支持是各國農業發展之所需,倘對“藍箱”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容易觸犯發達國家的“紅線”,引發談判的再次破裂。因此,在當前多邊貿易體制發展處于低谷和美國談判較為消極的情境下,我國要充分發揮自己作為南北國家“橋梁”的特有作用關于中國在WTO談判中充當南北國家“橋梁”這一獨特角色的論述,詳見:徐崇利.中國的國家定位與應對WTO的基本策略[J].現代法學,2006,(2):3-8.,既要積極通過類似“金磚”國家經貿部長會議等平臺協調和促成發展中國家統一談判口徑,又要通過類似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等機制與發達國家展開積極有效的協商,努力找到南北雙方談判的協調點和平衡點,以尋求有效約束“新藍箱”政策的可行性。
在微觀的談判策略上,從我國的現實情境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出發,筆者認為,我國可通過確立逐步削減的時間表和采取“分層削減模式”使發達國家的補貼量同削減量掛鉤,力爭使其封頂值真正降到2.5%以下。同時,對于特定產品的限制,我國要謹防美國反周期補貼等手段的變相“逃離”,對諸如棉花、大豆、小麥、油菜籽等我國對外依存度較高且發達國家保護程度也高的敏感農產品的“藍箱”使用比例予以從嚴限制。此外,我國也應建議成員方完善《框架協議》的通報制度,使發達國家實施的任何可能影響既有“藍箱”使用紀律的國內支持政策及時向WTO通報,以保障其他成員特別是發展中成員的權利得到切實維護。《框架協議》第48條規定了各成員方的通報制度:“第18條將予以修改,以期加強監控,從而有效保證透明度,包括通過關于市場準入、國內支持和出口競爭承諾的及時和完整通報。發展中國家在此方面的特別關注將予以處理。”
(二)把握改革時機,靈活適時地尋求談判的突破口
在已發生的多哈回合農業談判中,盡管以中國、巴西、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使得發展中國家力量顯著加強,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其影響力主要還體現在防止不利結果而非談判方向的主導上。因此,如上所析,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與其主張否定“新藍箱”,還不如“心平氣和”地承認不掛鉤的直接補貼是多哈回合發展的大勢所趨,然后在此基礎上密切把握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與發達國家展開積極的對話,靈活應變,適時尋找“藍箱”乃至整個多哈回合農業談判的突破口。
依筆者之見,這種突破口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并無不可能。在經受2008年的危機重創后,美歐很可能無力維持以往高額的“藍箱”支持水平。以歐盟為例,其2010年財政預算為1415億歐元,但在2008-2010年歐元區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2.93%的情況下,歐盟還是為“藍箱”支付了640億歐元,連同研發、教育和創新等其他領域的花銷,整個歐元區2010年預算赤字達到GDP的6.6%,大大超過《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的上限。歐盟內部的成員國于1997年6月17日達成《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公共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不得突破3%的上限。如果違規,成員國將受到警告、限期改正甚至罰款等處罰。歐盟近期為此成立了專責工作組,尋求如何收緊財政預算特別是削減農業補貼。看來,在債務危機仍在歐洲發酵的現實背景下,歐盟農業保護集團的利益肯定要讓位于上述的調整。無獨有偶,2011年上半年,美國也陷入類似歐元區的債務危機之中。2011財年美國政府財政赤字為1.299萬億美元,比2010年增加500億美元。截至2011年底,美國累計債務高達14.8萬億美元。(參見:佚名.美國政府2011財政赤字近1.3萬億美元[EB/OL].[2012-11-21].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10-15/3390759.shtml.)雖然國會于2011年8月2日通過了提高債務上限的議案,從法律上避免了危機的進一步惡化,但同時也啟動了控制政府預算的法案,規定“兩黨”若無替代方案,則從2013年開始,政府開支10年內須自動削減1.2萬億美元。隨后,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底也被迫公開表示,政府將在未來12年力爭削減4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其中,農業補貼到2023年將減少3600億美元。參見:信蓮.奧巴馬呼吁12年減赤4萬億美元,抨擊共和黨阻撓改革[EB/OL].[2013-01-21].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11-04/15/content_12329268.htm.2013年3月1日,由于民主、共和兩黨未能達成延緩執行或找到替代減支的其他方案,美國聯邦政府的上述開支自動削減計劃正式生效。參見:諶莊流,胡國泰.美兩黨談崩,被迫削減政府開支高達1.2萬億美元[N].環球時報,2013-03-02(01).可以預見,在此財政減支計劃的硬約束下,美國政府未來削減各部門支出包括農業補貼支出已如箭在弦上,不容不發。事實上,美國已就農業支出的削減計劃提前做了布局。根據國會2012年6月21日通過的《農業改革、食品與就業法》即新《農業法》,政府被明確要求在未來10年削減236億美元農業開支。
綜上可見,在當前歐美存有強烈削減農業補貼內生意愿的基礎上,推動發達國家對“新藍箱”進行改革,可謂正當其時。我國倘能聯合發展中國家采取靈活變通的對策,結合其他議題的必要讓步(如發達國家當前最為關心的貿易便利化問題等),從外因上順水推舟,對其予以“勸誘”,則促使發達國家實質性削減“藍箱”的阻力就會小很多。至于如何做到靈活變通,發展中國家則需要做足功夫,在仔細研究草案內容和權衡利弊的基礎上通盤考慮。假以一例,如草案雖然賦予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特殊與差別待遇”,但這些待遇往往“口惠而實不至”,發展中國家在當前較少使用“藍箱”支持,根本無法享受到好處。因此,與其得到這些紙面上的優惠,還不如將這些“優惠”作為與發達國家后續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換取發達國家在“新藍箱”削減方面的真正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