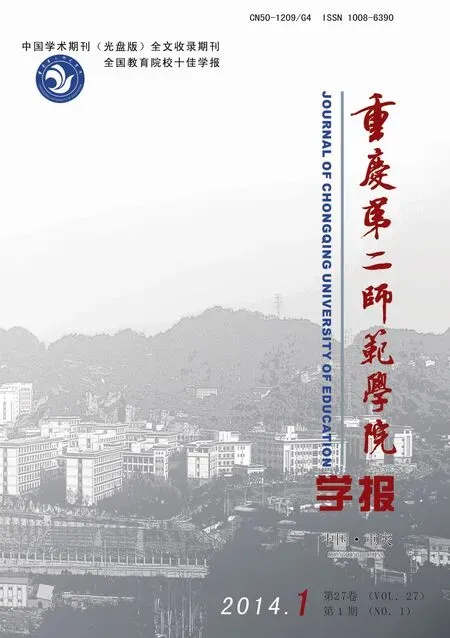《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口頭敘事策略和“虛擬聽眾”
翟艷霞
(河南農業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2)
《麥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國作家J.D.塞林格唯一的長篇小說,從1951年出版以來給全世界無數彷徨的年輕人以心靈的慰藉。塞林格將故事的起止局限于16歲的中學生霍頓·考爾菲德從離開學校到曼哈頓游蕩的三天時間內,小說用第一人稱的手法,從一個中學生的角度,用中學生的口吻和措辭來敘述,既真實可信,有“如聞其聲”之功效,又成功地體現了小說憤怒與焦慮的主題。小說使用了大量的俗語和粗話,直接體現了其反傳統的特點。
盡管《麥田里的守望者》是寫作文本,霍頓的敘事卻以口頭敘述來表達。正如Donald Costello和許多評論家所說,小說在發音法和句法中提供給我們霍頓講話的“聲音”和愛好。在小說的開頭,霍頓似乎很不愿意過多談一些事情,“我他媽不打算口述整個一部自傳還是怎么樣”,然而從頭至尾他談話沒有停頓,甚至沒有請求讀者(聽者)給他點時間喘口氣。他現在的表現與敘事中過去的表現很連貫:他故事中的人物無論與環境是否合適,他總能為他們找到該用的詞。無論與室友、老教師在一起,還是有時與女朋友、妹妹甚至陌生人在一起,他似乎總有話說,即使有時找不到自己的詞,他也會像一個技術嫻熟的滑稽演員一樣重復回到他交談對象的詞匯,語氣變化或尊敬或諷刺,或者就直接重復自己的話。盡管他說他討厭別人如斯賓塞先生重復自己的話,他可以想象裝得“又聾又啞,那樣……我下半輩子就不用說什么話了” ,但顯然他難以抵擋與他敘事中虛擬聽眾進行長談的欲望,盡管這種談話是單向的,正如他說的:“我要的就是有人看,我是個人來瘋。”
他談話的一個重要形式,除了無休止的使用格言警句似的概括來對敘事加以渲染外,就是講故事,至少是故事片段。他對“去年十二月份”在曼哈頓游蕩三天的敘述無疑是最詳盡的,但也包含著其他故事。霍頓是他敘事里的人物,在火車上跟莫羅太太坐在一起,胡謅杜撰她兒子拒絕當選潘西中學班長的故事;在Rocketfeller中心滑冰場與莎莉交談時,暢想與她到新英格蘭樹林中的生活。但他作為那三天經歷的敘述者,講述了奧森伯格的潘西中學之行,講了Edgar Marsalla 這個“極讓人討厭的家伙”,講了Jimmy Castle的自殺等。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說,他在敘事中告訴我們關于霍頓的內容遠比他意識到的多,但他這些敘事本身就是我們了解他性格和憂慮的重要線索。
霍頓講話并不僅僅是交流或策略。在他的敘事中,他似乎從講話行為本身得到很多快樂和力量,一種真正“有活力”的感覺。事實上,有時講話的興趣不在說明意思,而在經歷。霍頓似乎很喜歡自己說話的節奏和韻律,甚至有點自我陶醉,他有時甚至從自己粗野的喊叫中發現難以言表的快樂,把每個面前的場合當作練習喊叫的機會,包括敘述他三天經歷的場合(他經常被告知說話聲音太大)。如果他這樣做部分是出于本能來應對體內燃燒的“過多的荷爾蒙”,是性沖動和侵略性的升華,那么,這里同樣含有一種含蓄的審美情節,這反映在霍頓如何對待那個跟家人一起出來的小男孩:
那個小男孩太可愛了,他不在人行道上,而是在緊挨馬路牙子的馬路上走。他裝作在一條筆直的線條上走,像小孩子會做的那樣,還一直在哼唱。我走得離他近了些,好像聽到他在唱什么,他在唱一首歌:“如果有人抓到別人在穿越麥田。”他的聲音很小,看得出,他唱歌只是他媽的自得其樂而已。街上汽車呼嘯而過,尖利的剎車聲到處響個不停,他爹媽對他不管不問,他還是靠著馬路牙子走,唱著“如果有人抓到別人在穿越麥田。”那讓我感覺好了點,不是很沮喪了。
盡管唱歌的小孩成為激勵霍頓后來設想自己成為“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動力,但孩子本身似乎并不需要抓住什么。也許他只要沿著他走的那條直線就可以遠離危險,而霍頓的愛偏離主題卻總是讓他陷入麻煩,成為那個需要被抓住的人。孩子的聲音吸引了霍頓的注意力,振奮了他的精神,霍頓承認自己“不怎么讀詩”,但他卻對富有詩意的聲音有反應,并且他自己的聲音有時也會被時代沖動所驅使。也許這種沖動有助于理解他與題在艾利棒球手套上的詩的關系,拿著那手套不僅拉近了他與艾利的距離,而且“抓住”了艾利的敏感,包括一個詩人對語言的敏感。
霍頓講話給他帶來的不管是審美的抑或自慰的快樂,都成為使他在這個迷茫、憤怒甚至極度痛苦的世界里幸存的工具,盡管這工具不那么完美且常常很脆弱。雖然在十二月那三天里他手上似乎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沿著馬路牙子散步、唱歌給自己,但他說話的聲音多數情況下處于警惕的緊張中,常常是逃避的,永遠準備著戰斗。有時他的喋喋不休正好表明了他在特定環境下的不自在或緊張,如他面對妓女Sunny時。如果說經常的自我攻擊能使他獲得駕馭將要失控的局面的力量的話,這有時就像是一種本能,如當他與Stradlater 爭論Jane Gallagher,或努力控制自己來反抗門衛時。有時這就像是用難以控制的舉動來填補可怕的安靜,一種留下自己去舔舐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孤獨,例如想到自己在賓館房間里大聲跟艾利交談。
這些片段表明霍頓出于本能常常靠擁有一個傾聽者來尋求感情的宣泄或控制,無論談的是什么,傾聽者多么糟糕,也無論最終他要交流的努力多么不成功。不管他與別人的交談是真誠的還是“虛偽”的,給我們的感覺是喜劇的還是悲慘的,也不管這種交談是暫時的撫慰還是進一步暴露他脆弱的神經,在了解霍頓和這部小說時不能忽略這些有意無意的策略因素。當我們考慮到霍頓與他的“虛擬聽眾”之間的模糊關系時,這些策略因素就變得更加復雜了—一個感興趣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人物),既對講故事本身帶來的快樂感興趣,又對所講的故事的結果感興趣。
“虛擬聽眾”不是指實際讀小說的讀者,是霍頓自己所說的“你”——“你要是真的想聽我聊”——是他敘事的聽眾。很少有批評家對這一虛擬聽眾感興趣,也許里面有霍頓自己以及他的塑造者也不確定的東西。霍頓關于聽眾的性質的線索為我們了解他的性格提供了啟示,不僅作為敘事中的代表人物,而且作為當下敘述者。比如,霍頓關于聽眾需要知道他的世界以便理解這一世界做了肯定的假設——某處他曾說,“如果你碰巧不住在紐約”。同時,他假設他的聽眾非常了解他正在做敘述的地方,在小說的開頭和最后一節,他只簡單地稱之為“這兒”、“這個破地方”,他很隨意地說“我整個人都垮掉了,不得不到這兒放松一下”,“我差點得了肺結核,所以要來這兒做些破檢查什么的”,“這兒一個搞精神分析的家伙”,這些都會使我們想到他在描述他的聽眾已經了解的東西,或者說霍頓在跟一個人面對面坐著交談,這個人是一個來訪者或另一個和他一樣的人。而且,霍頓與相對較少的人直接交談——肯定不超過二三人,很可能只有一個。霍頓作為他敘述的事件中的一個人物,從來沒有同時跟三個以上的人交談(如Lavender Room里的三個女人),很少同時跟兩個以上的人交談(如Maurice和Sunny,兩個修女,大都市藝術博物館中的兩兄弟),常常只跟一個人長談(如與Stradlater, Sally Hayes, Mr. Antolini, Phoebe),與單個人交談似乎使他特別舒服健談。
霍頓還給他的聽眾賦予了一些特質。他不自覺地大量使用青少年詞匯,而對正式的“成年人”措辭使用相對較少,比如他與斯賓塞先生和莫羅夫人所用的詞匯,據此表明聽眾與他的年齡相仿,和他們在一起他感覺舒服,沒有特別的疏離感。他暗指他已經告訴聽眾他的哥哥D.B“所有那些事情”,至少是大部分,而且他推定的聽眾似乎肯定是男性。作為他敘事中的一個人物,他幾乎完全避免與女人直接談性事,無論這女人比他年長、年幼還是同齡。即使與Sunny談這個話題他也很明顯會張口結舌,但同時他又告訴他的聽眾Lilian Simmons“有一對大奶子”,描述他薰衣草舞廳的舞伴“屁股很小”,他對性事的全神貫注在他整個敘事中穿進穿出。但他的“男性”談話卻與陽剛氣概相去甚遠。霍頓能夠向他的聽眾承認他還是個“童男”,而且談論與女人接近性事時的尷尬和無措,對Ackley, Stradlater, Carl Luce卻不愿意承認這些,這表明了他的虛擬聽眾的另一個特質,那就是敏感。
可以說霍頓含蓄地賦予了他的聽眾幾個重要特質。從他開始談話那一刻到結束,他都很明顯指望“你”認真地、充滿敬意地聽他敘述。小說真正的讀者只要想就可以放下書,但他的虛擬聽眾卻愿意連續的聽他東拉西扯地講故事,他可以指望聽眾從來不會像他的潘西同學曾對Richard Kinlla做的那樣“大喊‘跑題了!’”。同樣,他可以相信聽眾的智慧,大多數人可能“從來不注意任何東西”,“總是為一些錯誤的時期鼓掌”,但他假設“你”會喜歡他的妹妹,“如果你跟菲比丫頭說什么事,她總是能準確領會你的意思”,也就是說,他根本不認為他在跟一個“冒失鬼”或“虛偽的人”談話,他相信“你”在聽他講自己過去的尷尬、錯誤、謊言、困惑、孤獨、受傷及現在的看法和迷茫時理解他、同情他。
簡言之,霍頓似乎在對著一些(個)非常理想的聽眾講故事。暫且不說霍頓的談話表明或掩飾了一個“內心的我”,也不必假設他這樣一個迷茫的青少年有那樣的智慧、洞察力給他的理想聽眾講述他們想知道的關于他自己以及他經歷的一切,就霍頓本身來看,他身上明顯表現出他的不連貫的看法、他壓抑的價值觀與行為之間的鴻溝、他的不穩定的對自己動機的洞察力,并且可以說,霍頓的言語表現至少在意識水平上顯示出了他要與“你”“建立真正關系”的急切。盡管他說“我是你一生中見過的最可怕的說謊者”,但這種說謊主要發生在他敘述的過去。現在說話,他承認這些謊言使它們顯得透明。他似乎非常相信現在的“你”可以表達出他真正的困惑、恐懼、傷害以及許多他最看重的東西。
霍頓在跟一群認真的有智慧的值得信任的聽眾述說不是要探討過去,從中學到什么,而是要儲存起來以備將來使用。很明顯,他在保存保全生命中的許多東西時并不順利,不管是劍,給菲比的唱片還是他的弟弟艾利。他對這些東西的遺失反應基本理性——“我有個毛病,就是對丟東西這種事從來不是很上心” 。但有一樣東西他非常在意地去保護,那就是他自己的經歷。他的記憶像一塊布,上面有“秘密藥物”,包裹著他的“木乃伊”——他愛過的人和時刻,甚至是曾經使他困惑或傷害過他的。同時他對這些記憶當中的經歷的敘述又像是要把它們放在一個安全的玻璃箱中展覽,想到自然歷史博物館中的展品,他說:“有些東西應該保持現狀,應該把它們粘在玻璃箱子里就別動了。我知道不可能,反正我認為不這樣就太糟糕了。”霍頓含蓄地把另外一組材料放進那個箱子:他對死的錯綜復雜的感情。他似乎對艾利的死感到痛苦和內疚。這種負疚部分來自霍頓被慣壞了,而那個更乖的弟弟卻死了。在那些內疚的情感中也許有另一成分:一個十二歲的霍頓在他的弟弟死時不可能有的情感,而當霍頓看著D.B、他自己、其他人從無邪的童年墮落了,成為“虛偽的人”時,這種感情現在浮出水面。艾利因為死了,所以從沒承受這種墮落的痛苦,所以霍頓對艾利的死還有一種矛盾的難以言說的興趣,為了保護艾利在他腦子里的形象不受變化的侵襲,霍頓在敘述中把艾利奉為神圣或“木乃伊”。
霍頓敘述他的記憶不僅幫助他應對死亡,更廣義的,應對失去和缺席。死亡畢竟只是失去的一個最震撼人的事情,盡管他宣稱“對丟東西這種事我從來不是很上心……好像從來沒什么東西能讓我覺得丟了就會很在意”。但很顯然他過去沒有什么經歷或個人讓他擔心會失去,即使他幻想逃往西部或樹林里也想著和“某人”一起。對他來說,孤獨和沮喪如影隨形,缺席是他最害怕的。他跟“你”的當前的交談就相當于他抓著簡的手:
我們會在看一場破電影或者干嘛時,很快就拉起手,直到電影放完,一直沒動,也不大做文章。跟簡在一起,你根本不用擔心手出不出汗,知道的就是你自己很快樂,真的。
在許多方面,那個“你”成為他丟失的聽眾的替代品。不論是簡還是死去的弟弟,在他的圣誕節冒險經歷中,當他孤獨和沮喪時,會求助于想象中的聽者,即他的弟弟艾利。八個月后,在與他敘述的聽眾建立起一種深信不疑的關系時,他給自己創造新的兄弟姊妹,把聽眾當作家庭成員,以應對艾利和菲比的缺席。
冒著把自己放在一個值得信賴的聽眾面前展覽的風險與聽眾這一理想家庭成員交談,并不只是填補由于失去自己家庭成員和他們的缺席產生的空隙的一種方法,也是應對自己想象中的缺席的一種方法。他在沿著第五大街走的時候并沒有向他弟弟祈求來救他,而是不斷重復求他,“艾利,不要讓我消失” 。對霍頓來說,世上最糟糕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被遺忘。這種只與自己交談的唯我論行為不足以確定他的存在和身份。借用塞林格在他的《九故事》前言中引用的著名的Zen Koan的一句話,它就像一個手拍手的聲音,用一個聽者的出現來確定自己的存在。這個聽者可能在他不再說話的時候記得他,把他的敘述轉達給其他的聽者。
因此,霍頓花費大約七小時來大聲講述他的故事,他并沒有故意去“教育”自己以達到教育聽者的目的,他不在乎這些。但盡管他沒有明白地承認,他也是在努力“抓住”聽眾的注意力以達到陪伴和見證他存在的目的,他太需要這些了。如果說他不是把他的經歷及他自己展示出來以抓住他們的興趣,他也是含蓄的把他們和自己一起放入展箱。但沒有一個人能永遠講個不停,交談最終必須結束,伴侶要分開,失去和缺席會再度出現。當他的聲音停止,他作為不被打斷的敘述者的控制結束時,霍頓將消失,除非其他人太“想”他了,感覺必須去代表他,因此在最后一章,霍頓努力控制關系,他來說再見,正如離開潘西中學時他說的,“我不管那種離別是傷感的還是糟糕的,但是在離開一個地方時,我希望我明白我正在離開它。如果不明白,我甚至會更加難受”。他想最后帶著那種難以忘懷的離別之情離開聽眾。他要說最后一句話來努力做到這一點,像一個敘述中的演員,他常常盡可能說最后一句話,即使莎莉掛斷他的電話,他還是不停地跟她講話。離開潘西時,他停了很長時間,然后“用他媽的最大的嗓門喊了一聲:‘好好睡吧,你們這幫蠢蛋!’”即使在他想象的死亡中,他也要留下空間控制自己的墓志銘——關于自己的最后的語言:
我甚至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掉,他們會把我塞進一個墳墓,還立個碑,上面刻著“霍頓·考爾菲德”,還有我哪年出生,哪年死的,然后就在下面,會有“操你”這兩個字。說實話,我對這件事有把握。
在霍頓想象中的墓志銘里有個很模糊的字“你”,如果“你”指霍頓,那么“操你”代表了這個社會或世界給不變的經歷、無辜的孩子和他最看重的東西以最后的侮辱,如果是他自己的聲音的分別瞬間,就像他最后向潘西中學喊的那樣,它表明了一個敘述者發出的最鏗鏘有力的聲音。
霍頓也許希望在那個既快樂又痛苦的歌曲中,他的聽眾能“想”他并“告訴”他。也許在霍頓以及他的塑造者身上有一些頑皮的甚至很有競爭力的東西。我們知道他喜歡“胡鬧”,甚至與他最關心的人一起胡鬧,如簡和菲比。因此要記住霍頓更早的一些論調,那是聽眾記憶中的霍頓的一部分:“你只用說些誰也聽不懂的話,就幾乎想讓他們干什么,他們就會干什么。”
參考文獻:
[1]J.D.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Z].孫仲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2]J.D. Salinger: The Catcher in the Ry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1.
[3]Jack Salzman. New Essays on The Catcher in the Rye[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J.D. Salinger: 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 An Introduction[M].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