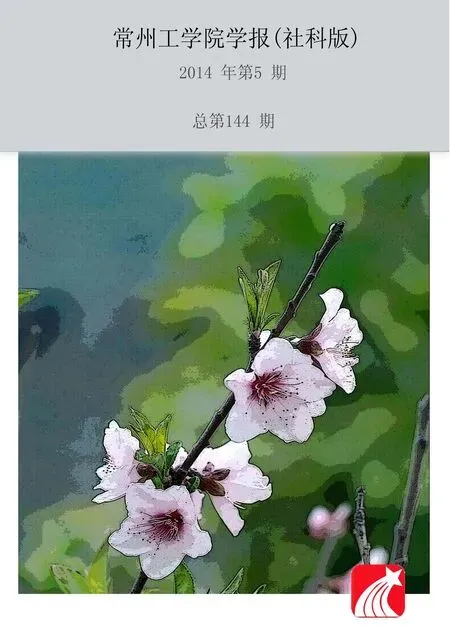高曉聲文學年譜(續1)
張春紅
(宿遷學院教師教育系,江蘇 宿遷 223800)
(續前——本刊2014年第2期)
1972年,44歲
該年,高曉聲被借調到公社細菌肥料廠當技術員,成了一名科學實驗的能手。大概他對藝術的那點愛好,使他無論做什么都要精益求精。此時,高曉聲不僅自己是農民,而且還組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化家庭,和所有的農民家庭一樣參加生產隊勞動,他研究沼氣,培植銀耳,試驗菌肥、農藥,在農村普及科學知識,嫻熟地掌握了各種農活。在長期的勞動改造中,高曉聲感慨是農民給了他體察社會的機會,讓他深思人生,也豐富了他的農村生活經驗,這些都為他新時期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很實在的基礎。
1978年,50歲
5月,高曉聲確認自己不久會回到文學隊伍里,他思緒激蕩,夜不能寐,開始信心十足地重新點燃起文學夢。“‘四人幫’一粉碎,我那創作的念頭忽然又升起來,這念頭隨著撥亂反正工作的進度越來越強烈。這時我才發覺,少年時代在心底點著的火種并未熄滅,現在它得到了燃料和氧,愈燃愈猛烈了。”①
6月,高曉聲“一頭鉆到創作里去了”。21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成為他創作的泉源。他在散文《曲折的路》中回憶到:“這一年的夏天特別熱,而且熱的時間特別長,我每天寫作十八個小時左右。身體本來就瘦弱,后來就瘦得不成樣子了。……天見可憐,蚊子那么多,也慈悲地不大來打擾我,因為我身上血太少。我什么也不管,家里的事不問不聞,旁人來同我講話,我嘴里唯唯諾諾,實際上一點也沒有聽進去。家里人從來沒有見過我寫作,更沒有見過這種樣子,愛人以為我在發瘋,有時搶走我的筆,責問我‘開什么玩笑’!我也沒法跟她說清楚。就這樣,在三個月的時間里,我寫成了18萬字的一部小說,自己則像患過了一場九死一生的大病。這以后,我又陸陸續續寫了些短篇小說,總算替重返文學隊伍準備好了一份薄薄的見面禮。”②
1979年,51歲
3月,“探求者”錯案得到糾正,高曉聲被平反。3月23日晨7時,高曉聲返回南京參加工作,家亦遷至常州市內的桃園新村小區。帶著新近創作的幾部短篇小說和一部18萬字的小說,高曉聲終于可以揚眉吐氣地回到文學隊伍里來了。
5月,短篇小說《“漏斗戶”主》在《鐘山》雜志發表。這是高曉聲非常喜歡的一篇小說,因為“寫出了《‘漏斗戶、主》之后,我才對自己有了信心,認為只有像我這樣在農村幾十年,和農民同甘苦的人才寫得出,我看到了那種生活在作品里放出的光彩了。那真是我自己特有的東西哪!”③。但由于《鐘山》剛創刊,印數不到一萬,讀到《“漏斗戶”主》的人不多,高曉聲為此感到十分惋惜。以后,就寫了續篇《陳奐生上城》,想通過這篇小說引起讀者對《“漏斗戶”主》的關注。“讀者如果對《陳奐生上城》感到興趣,就一定會去看一看《‘漏斗戶’主》,這樣,《‘漏斗戶’主》就被救活了。后來,事實證明我的預計不錯。”④
6月20日至26日,高曉聲在揚州參加《雨花》編輯部召開的文藝理論工作座談會。會上,大家就當前的文藝形勢、文藝的功能、人性、創作方法等問題進行交流,解放了思想。
7月,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發表在《雨花》第7期,后獲得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創作一等獎。
9月11日,作協江蘇分會召開座談會,就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方之的《內奸》、陸文夫的《特別法庭》、顧爾鐔的《在深處》展開討論。與會者認為高曉聲在李順大獨特的經歷中概括了絕大多數農民的共同命運,具有和阿Q、梁生寶同等的典型意義。同月,短篇小說集《李順大造屋》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李順大造屋》《“漏斗戶”主》兩篇小說,葉至誠撰寫了《遲開的薔薇》代前言,高曉聲寫了《我寫小說,不過如此》代后記。
10月28日,高曉聲參加了方之同志的追悼會,與陳椿年、葉至誠、陸文夫、梅汝愷共獻挽聯:“蠟炬燒將燼,春蠶吐正稠。何期永世杰,覓君天盡頭。”作為“探求者”的主要干將,方之在最需要堅持探索的時刻離開了大家。
11月,赴蘇州、無錫參加《鐘山》《譯林》編輯部召開的作家、翻譯家座談會。座談會緊緊圍繞解放思想、繁榮創作這個中心,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明確文學創作要進一步恢復和發揚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不搞“瞞騙文學”“虛假文學”,高曉聲聽后很受鼓舞。
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央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和關心群眾疾苦的傳統,高曉聲深受感動。多年的農村生活讓他接觸到了太多的苦難事實,他急于為農民嘆嘆苦經,把他們的苦處說一說。因此,他的這些寫農民的小說一發表,便好評如潮。有的說“高曉聲近作的最可貴之處,就是‘這里有他自己的東西’”⑤。有的說“他的作品是獨樹一幟的”,“在描寫農村生活的作者中,他登上了新的階梯”⑥。但“兩篇小說用了同一種手法,總是讓農民在極端困難中幾起幾落:希望已經燃起,只要正常發展就能毫不費力地實現愿望,但是總有突然伸出的龐大黑手將希望輕易地砸個粉碎,讓他們重回無邊的黑暗之中”⑦。李順大一家屢經周折,造屋的理想始終無法實現;“漏斗戶”主陳奐生年年虧糧,而且越虧越多,口糧分下來后,還清債,連做年夜飯的米都不會有。小說既揭示了“左”的錯誤對農民命運的深刻影響,又揭示了農民本身的某種“劣根性”。
寫這類小說,對高曉聲來說是很自然的。“眼睛一霎,我在農村里不知不覺過了二十二年,別無所得,交了幾個患難朋友。我同造屋的李順大,‘漏斗戶’主陳奐生,命運相同,呼吸與共;我寫他們,是寫我的心。”⑧他與農民有著相同的感受,他不必有意識去體驗他們的生活,相反倒無意識地把他們的生活變成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寫出了以新面目裝扮了的、茍延殘喘已達數千年的‘未死’者,固執地戀棧不去;他寫出了從舊的胎盤中培育出來的‘方生’者,由于先天不足,又是那樣的荏弱”⑨。這種敘述人和敘述對象的“混合重唱”⑩,造成高曉聲小說文本的敘事成為較典型的“自由轉述體”?。
這一年,高曉聲發表的作品還有短篇小說《特別標記》(《雨花》第2期)、《雪地花》(《紫瑯》第3、4期)、《一支唱不完的歌》(《鐘山》第4期)、《流水汩汩》(《雨花》第6期)、《漫長的一天》(《人民文學》第8期)、《揀珍珠》(《北京文藝》第9期)、《柳塘鎮豬市》(《雨花》第 10期)、《系心帶》(《上海文學》第11期)、《周華英求職》(《安徽文學》第11期);散文《善跳者亦可以休矣》(《雨花》第9期)等;創作談《擺渡》(《青春》第2期)、《也算“經驗”》(《青春》第2期)等。
該年,高曉聲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創作組組長。
1980年,52歲
6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曉聲《七九小說集》,內收《李順大造屋》《“漏斗戶”主》《揀珍珠》《系心帶》《柳塘鎮豬市》《周華英求職》《漫長的一天》《特別標記》《雪地花》《流水汩汩》《一支唱不完的歌》共11篇小說,另有《擺渡》一篇(代前言)。用“七九小說集”作名號,體現了高曉聲的創作“野心”,他想一年出一本小說集,以追回那段被特殊歷史所遮蔽的青春歲月。
同月,高曉聲帶領省內外20多位農村題材短篇小說作家訪問金壇農村,目睹了農村改革開放以后所發生的巨變,訪問了由“窮神”變為“財神”的“萬元戶”,聽到了“光棍村”的“老光棍”3年來儲了谷子、存了票子、蓋了房子、討了娘子、生了孩子“五子登科”的現場介紹……面對改革開放以后農村中出現的新問題,高曉聲長久以來關注農民的目光變得更加深邃起來,他思考著李順大、陳奐生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現實生活的這些變化呢?
10月5日至15日,高曉聲在無錫參加省作協專業作家會議的同時,為前來參加江蘇省第一屆青年文學創作會議的年輕作者們作了一場關于文藝創作問題的報告,并對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提出具體修改意見,關心扶植青年寫作者的成長。
本年,高曉聲發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說《我的兩位鄰居》(《雨花》第1期)、《陳奐生上城》(《人民文學》第2期)、《定風珠》(《鐘山》第3期)、《錢包》(《延河》第5期)、《山中》(《安徽文學》第11期)、《尸功記》(《鴨綠江》第 11期)、《魚釣》(《雨花》第11期)等;散文《痛悼方之》(《北京文藝》第1期)等;創作談《關于〈周華英求職〉的通信》(《安徽文學》第5期)、《希望努力為農民寫作》(《文藝報》第5期)、《且說陳奐生》(《人民文學》第6期)、《爭取更大勝利》(《雨花》第6期)、《生活和“天堂”》(《人民日報》7月23日)、《解放思想和文學創作》(《群眾》第7期)、《〈李順大造屋〉始末》(《雨花》第7期)、《曲折的路》(《四川文學》第9期,收入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第26期)、《在〈雨花〉編委學習“七一”社論座談會上的發言》(《雨花》第9期)、《談談文學創作——給青年作者小說講習班的講課》(《長江文藝》第10期)、《生活、目的和技巧》(《星火》第10期)、《談談文學創作》(《長江文藝》第10期)、《注意反映農村生活的復雜性》(《作家雜志》第10期)、《文藝管理體制要改革:寫自己熟悉的人》(《文匯報》11月21日)等。
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采用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描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發生的深刻變化,通過塑造一位正直、勤懇的農民渴望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質量,展現了廣大農民積極進取的意愿,與此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初農民的真實精神狀態與存在的不足”?。高曉聲也因塑造了陳奐生這一繼阿Q之后的典型農民形象而獲得文壇高度評價。董健的《論高曉聲小說的思想和藝術》、時漢人的《高曉聲和“魯迅風”》(《文學評論》,1984年第4期)、諶宗恕的《對三十年農村生活的再認識——評高曉聲描寫農民的短篇小說》(《湖北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等文章都論述到了陳奐生與阿Q的承繼關系。“陳奐生是一個人,又是一個群體,一個階層,一種現象。他的存在,表明農民遠沒有從因襲的封建思想意識的重負中解脫出來,缺乏一種清醒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的喪失,從根源上說,無疑是長期物質生活的貧困、主流意識形態的‘鏡像’意識以及傳統文化的因襲所造成的;從結果上講,是陳奐生們的精神生活極度貧乏,而且他們無從尋找精神的充實。”?這種認識和評價是十分中肯的。
隨后,《陳奐生上城》獲得1980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連續兩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項,由此引發了文壇上的“高曉聲熱”。
在新時期文學中,高曉聲一直以“擺渡人”自勉,他要用自己的文學作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他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有一個終身奮斗的目標,有一個總的主題,就是促使人們的靈魂完美起來”?。陳奐生形象的塑造成功,使得高曉聲創作的農民小說及本色農民形象在讀者中產生極大影響。高曉聲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面對著人的靈魂,面對著自己的靈魂。我認為我的工作,無論如何只能是人類靈魂的工作。我認為,就是要把人的靈魂塑造得更美麗。”?本著這條創作原則,高曉聲通過系列小說的形式來完成自己的文學夢想。
該年,高曉聲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81年,53歲
2月,在《文藝研究》第1期上發表創作談《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最初發表在1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強調作家創作離不開生活,而作家對生活的看法,即觀點又在創作上起很重要的作用。“生活是源泉,觀點是主導……作家有了觀點,才能發現生活的含義,而發現了的生活含義,又會豐富和發展作家的觀點。”?高曉聲長期生活在農村,自然對農民的生活和情感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寫農民成為他實現文學夢想的本錢,也讓他成為繼魯迅之后的從人文、人性層面切入農民題材的又一位大家。
4月21日,高曉聲應寧波市文聯的邀請,給文學愛好者介紹自己寫作《陳奐生上城》時的創作經驗。會上,作家陸文夫也介紹了《小販世家》(與《陳奐生上城》一起獲1980年度全國短篇小說獎)的創作經驗。
6月7日,高曉聲與連云港業余作者和教師進修學院學員談創作。7月,連云港教師進修學院編寫、出版了《高曉聲研究資料》,內容包括2篇作家小傳、11篇創作談(包括節錄文字)、27篇創作專論(包括節錄文字),以及高曉聲著作目錄索引、高曉聲研究專文目錄索引,是國內較早、較系統地關于高曉聲創作研究的資料專集。
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高曉聲一九八〇年小說集》,內收短篇小說《我的兩位鄰居》《陳奐生上城》《“漏斗戶”主》《錢包》《定風珠》《山中》《尸功記》《魚釣》《寧靜的早晨》《陳家村趣事》和中篇小說《極其簡單的故事》。
《錢包》《山中》《魚釣》,以及后來的《飛磨》《繩子》《劉宇寫書》等作品,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意境深邃,人情哲理兼備,近似寓言小品的雋永耐讀。這些揮發性靈之作,傳達出高曉聲對現實生活難以詳言的感受和體驗,是其小說創作中的精品。高曉聲曾說:“我們現在搞的現實主義,太拘泥了,放不開,很多地方不及傳統。”?所以他的這類作品一經發表,就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有人認為高曉聲這類小說主要偏于一種心理稟性的揭示,是一種持續不變的農民的心理稟性,既屬于農民,又非農民所專屬。小說“恰恰以它的不確定給予我們許多想象的空白,當我們從中填塞各人的見解時,小說的內涵就異常豐富起來,而這一切都是極富啟發性的”?。也有人直接稱其為象征性小說,認為高曉聲“將象征性小說和現實主義緊密、充分地結合起來而獨具意蘊、獨具魅力,從現實主義角度講,顯示了現實主義強大的吸附性和粘合力”?。欒梅健則將此類小說稱之為“諷喻性作品”。“在爆發期過后,當高曉聲竭力主張文學的哲學思辨性與潛移默化的藝術功能時,這類他極其熟悉并喜受的小說品種便極其自然地成為他自覺追求的對象,成為他借以進行‘挑戰’的心愛武器。”?簡而言之,這些頗富哲理性與諷喻性的作品,從形式上看,表明了高曉聲對《聊齋志異》這類傳統筆記小說的特殊偏愛;從內容上來說,作家“先前追隨時代脈動的特點已經逐漸淡化,但作家‘忠于生活、干預靈魂’的創作原則始終沒有改變”[21]。作品依然貫穿著高曉聲對農民生存現狀了解之后,對于農民命運和精神生活的憂患和焦慮。
再聯系高曉聲的創作經歷和創作心態來看,這一時期出現這些新形式的小說也很自然。“文革”結束后,高曉聲離開農村來到城市,城市生活是他不熟悉的,“探求者”的理想又使他不愿重復過去寫過的內容,所以,他感到“寫作不是越寫越容易,而是感覺越寫越困難”,認為“小說只能潛移默化影響讀者,假使作家都是把自己的意圖講得非常清楚,那就沒有意思了”[22]。于是,高曉聲只能在創作上另辟蹊徑,這顯示了作家可貴的進取精神。
10月,短篇小說集《水東流》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21日,高曉聲參加中國翻譯家、作家代表團赴美訪問,這是中美文化協定的一個既定項目。同行人員有語言學家陳原,文學評論家許覺民,翻譯家沈蓁、吳均燮、湯永寬等。11月12日下午,高曉聲乘機回國,隨后寫下了一系列散文隨筆,于12月12日開始在《常州報》上連載。
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創作談》,收高曉聲1979—1981年談創作的文章15篇。
同月,高曉聲發表《讀古典文學的一點體會》(《文藝研究》第6期),指出:“正確地認識農民,是我國最大的一件大事。以農民為對象的作家,不但要讓農民正確認識自己,而且要讓社會各階層正確認識農民,這個任務是繁重的,這個責任是重大的。”[23]文章希望創作者能夠從中國古典名著中學習到表現人物復雜性的寫作技巧,反映出高曉聲對中國社會、歷史冷靜的思考,以及對文學家責任的承擔意識。
該年,高曉聲發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說《寧靜的早晨》(《新觀察》第1期)、《陳家村趣事》(《長城》第1期)、《水東流》(《人民日報》2月21日,《新華文摘》第4期轉載)、《陳奐生轉業》(《雨花》第3期)、《大好人江坤大》(《花城》第3期,高曉聲個人認為這篇小說寫得比《陳奐生上城》還要好,還要深刻)、《水底障礙》(《雨花》第7期)、《崔全成》(《上海文學》第10期)等;中篇小說《極其簡單的故事》(《收獲》第2期);創作談《創作思想隨談》(《上海文藝》第1期)、《為“十有八九”服務》(《墾春泥》第2期)、《船艄夢》(《文藝月刊》第7期)、《江南筆會:文學語言淺談》(《江南》第3期);散文《我們都上去了》(《采石》第2期)、《改革和創作》(《隨筆》第 17期)、《“青春獎”得獎小說簡評》(《青春》第3期)、《短篇小說創作談片——在“青春獎”授獎大會后和青年作者的談話》(《青春》第11期)等。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說集《陳奐生上城》,收集了1978年以來高曉聲創作的農民生活和命運的作品,這些作品以深沉的思考、幽默的筆調刻畫了中國農民的各種形象和心態。
1982年,54歲
1月,小說《陳奐生上城》被瀟湘電影制片廠和北京青年電影廠聯合改編成電影,導演王心語,主演村里、宋春林、田英。
3月,江蘇作家協會委派高曉聲(時任中國作協理事、江蘇作協副主席)帶領省內外部分知名作家,如陸文夫、汪曾祺、林斤瀾、葉至誠、黃裳和葉兆言等,到常州采風。大家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常柴廠、燈芯絨廠、無線電總廠、兩當軒(黃仲則故居)、蘇東坡終老地——藤花舊館、惲南田墓……,共同感受常州武進厚重的文化內蘊和人文精神。
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高曉聲一九八一年小說集》,內收《崔金成》《水東流》《水底障礙》《心獄》《陳奐生轉業》《大好人江坤大》《劉宇寫書》《飛磨》《繩子》共9篇小說。這些小說,有的反映處于變革中的蘇南農村生活;有的刻畫富有嶄新氣質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有的謳歌老一輩農民的政治覺悟和斗爭智慧;有的對農民性格中的傳統因素和精神負擔進行挖掘、剖析。小說既折射出高曉聲對新時代農民生活的熟悉程度,又體現了他在藝術上的不斷創新。
這一年,高曉聲發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說《劉宇寫書》(《小說界》第1期)、《陳奐生包產》(《人民文學》第3期)、《繩子》(《雨花》第2期)、《書外春秋》(《花城》第3期)、《磨牙》(《鐘山》第6期)、《心獄》(《文匯月刊》第 3期)、《陌生人》(《海鷗》第10期)、《大山里的故事》(《人民文學》第10期)、《老友相會》(《上海文學》第11期)等;散文《訪美雜談》(《鐘山》第2期)、《訪美雜談二》(《鐘山》第3期)、《自勉的話》(《青春》第5期)、《也給豆腐唱頌歌》(《上海文學》第5期)、《美國的農莊和農民》(《新觀察》第5期)、《魚的故事》(《芳草》第8期)、《我的第一篇小說》(《山西文學》第 9期)、《讀〈墻〉小記》(《青春》第10期);創作談《短篇小說創作漫談》(《江海學刊》第1期)、《談談有關陳奐生的幾篇小說》(《文藝理論研究》第3期)、《在〈青春〉常熟小說改稿講習班上的講話》(《青春》第4期)、《且說文學的講評》(《北京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水東流,不回頭》(《小說林》第6期)等。在這些創作談中,高曉聲“對自己的創作追求和作品作了一定的闡述,他的一些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評論者對其作品的評析,而這些評論意見對高曉聲調整以后的創作手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4]。
1983年,55歲
1月,短篇小說集《高曉聲小說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月,短篇小說《泥腳》發表在《收獲》第1期。小說著重發掘了努力致富的“當家人”的一種值得警惕的傾向:他們往往只顧帶領全家苦干,而忽視了家庭成員,特別是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文化知識的學習。反映出高曉聲對改革開放時期蘇南地區農民生活敏銳的觀察力和思考力。
4月,由梁清濂根據高曉聲小說《陳奐生上城》改編的小型京劇《買帽子》發表在《江蘇戲劇叢刊》(第4期)。
同月,短篇小說集《陳奐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除《前言》外,收《“漏斗戶”主》《柳塘鎮豬市》《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書外春秋》共6篇小說。
4月5日,應《漓江》《桂林文學》《桂林藝術》三家雜志社的邀請,高曉聲在杉湖畔的曲藝廳演講,談他幾篇得獎小說從生活到成品的制作過程。并就小說的主題思想、小說的構思、小說的語言,以及文學的創新、突破等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出“文學應該從形象上感動讀者,而不是從概念上打動讀者”;“小說的風格應該是每篇都不相同的,你至少不能跟自己重復”;“寫小說不要受拘束,也不要過分去考慮結構,寫的過程中總是要突破原有的一些想法”;“寫作要有良好的環境”[25]等意見,給青年寫作者以極大的啟發。6日上午,桂林市、地40位作者又在桂林市人民禮堂與高曉聲座談;9日,高曉聲離桂去邕。
5月,高曉聲在南京參加《雨花》筆會,為時1個月。會間,以“作家的個性和文學的發展”為題作了主題發言,指出“不同的作家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不同的環境對作家和他的作品產生不同的影響。這無法分開,作家總在作品中表現自己。作品也總在表現作家”[26]。高曉聲長期生活在農村,“成了農民弦上的一個分子,每一觸動都會響起同一音調”[27]。所以在他的小說中,表現農民也就是表現他自己。
自1979年以后,高曉聲除進行文學創作外,經常在國內外參加一些學術交流活動,如參加廬山三省青年創作會議、廈門四省文學創作會議等,另外還在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大、蘇州大學作學術性報告,他認為“時代生活是有主流的。為了推進和繁榮我們的文學事業,我們應該深入生活,忠于生活,并且讓絕大部分作家能夠在時代的主流中建立長久而牢固的生活基地”[28]。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使高曉聲80年代的創作大多以農民為主角,即便是描寫知識分子,也常常會在他們的身上發現農民的心理和性格。
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曉聲一九八二年小說集》,內收《魚的故事》《陳奐生包產》《書外春秋》《大山里的故事》《老友相會》《磨牙》《丟在哪兒》《泥腳》《陌生人》《買賣》共10篇小說。
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高曉聲小說選》,內收高曉聲1979年至1981年間寫的14篇小說,包括《系心帶》《李順大造屋》《周華英求職》《柳塘鎮豬市》《陳奐生上城》《極其簡單的故事》《大好人江坤大》《水東流》等。作者在《序》中說:“我的小說其實并不都是寫農村,格調也不一樣。這里選的,都屬農村題材,風格上也大體相似。只有《系心帶》不同,所以會選它,是因為它有資格作這本選集的序。”[29]《系心帶》寫于1978年12月,是高曉聲復出后較早寫出的一篇小說。它以“文革”劫難過后中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為背景,描寫一位在農民群眾中扎了根的知識分子李稼夫,“之所以能夠忍受了‘比他事前能夠想象到的要惡毒百倍’的侮辱而堅強地活了下來,并決心與惡勢力斗下去,就是因為他在事實的教訓中看清了:在十年浩劫中殘酷侮辱人的尊嚴的,并不是什么共產黨,而是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一群野蠻、一批法西斯惡棍、一批窮兇極惡的封建惡霸’”[30]。可見,李稼夫的想法反映的正是作者高曉聲的心聲。
該年,高曉聲發表的作品還有:中篇小說《蜂花》(《收獲》第5期)、《糊涂》(《花城》第4期)等;短篇小說《丟在哪兒》(《雨花》第1期)、《買賣》(《滇池》第2期)、《一諾萬里》(《小說界》第4期)、《開拓眼界》(《小說林》第 7期)、《“聰明人”》(《上海文學》第11期)、《太平無事》(《福建文學》第 9期)等;散文《想起了樵夫拾柴……——〈告別校園的時候〉讀后》(《青春叢刊》第2期)、《秦蜀行隨拾》(《隨筆》第3、4期)、《大佛小佛小小佛》(《漓江》第3期)、《三江都安我心寬》(《湛江文藝》第3期)、《旅途拾零》(《花城》第5期)等;創作談《在〈青春〉常熟小說改稿講習班上的講話(上、下)》(《青春》第3、4 期)、《作品總在表現作家》(《雨花》第8期)、《漫談小說創作——在四省小說創作講習班上的講話》(《福建文學》第9期)、《注意反映農村生活的復雜性》(《作家》第10期)等。
(待續)
注釋:
①②高曉聲:《曲折的路》,《四川文學》,1980年第9期,第72-77頁。
③④高曉聲:《陳奐生·前言》,《陳奐生》,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3頁,第5頁。
⑤陳遼、劉靜生:《這里有他自己的東西——評高曉聲的四篇近作》,《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0年第3期,第53-59頁。
⑥謝永旺:《獨樹一幟——評高曉聲的小說》,《文藝報》(1978年7月復刊,為月刊),1980年第2期,第5-11頁。
⑦劉旭:《底層敘述:現代性話語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0頁。
⑧高曉聲:《也算“經驗”》,《青春》,1979年第11期,第8頁。
⑨章品鎮:《關于高曉聲》,《人物》,1981年第1期,第121-128頁。
⑩王曉明:《在俯瞰陳家村之前》,《文學評論》,1986年第4期,第57-65頁。
?自由轉述體,一般認為是從法國作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開始正式使用的小說敘事方式,看似第三人稱客觀敘事,實際上是敘述人轉換到角色的視點,模仿角色的語氣描述事物或描寫心理。參見劉禾:《跨語際書寫》,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金海波:《九點峰翠·解讀高曉聲“隱在的痛”》,賀誠主編:《九點峰翠》,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497頁。
?王啟凡:《新時期以來重要文學現象及其文化基因論》,遼寧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1頁。
?高曉聲:《生活、目的和技巧》,《星火》,1980年第10期,第15-20頁。
?高曉聲:《且說陳奐生》,《人民文學》,1980年第 6期,第110-112頁。
?高曉聲:《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第11-17頁。
?轉引自范伯群:《高曉聲論》,《文藝報》,1982年第10期,第39-46頁。
?吳亮:《并非難解之謎——評高曉聲晚近的小說》,《雨花》,1983年第11期,第75-80頁。該文后收入吳亮的《文學的選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
?唐再興、李昌華:《試論高曉聲的象征性小說》,《揚州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第86-92頁。
?欒梅健:《高曉聲近作漫議》,《當代作家評論》,1988年第3期,第88-95頁。
[21]趙黎波:《高曉聲論——“他”的時代已經過去?》,《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第132-136頁。
[22]高曉聲:《高曉聲一九八一年小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頁。
[23]高曉聲:《讀古典文學的一點體會》,《文藝研究》,1981年第6期,第78-82頁。
[24]劉蓓:《新時期高曉聲小說研究綜述》,《彭城職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第52-54頁。
[25]轉引自李侃:《藝苑漫步·高曉聲在桂林談創作》,漓江出版社,2008年,第182頁。
[26][27]高曉聲:《作品總在表現作家》,《雨花》,1983年第8期,第73-75頁。
[28]高曉聲:《生活和“天堂”》,《人民日報》,1980年7月23日。
[29]高曉聲:《高曉聲小說選·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頁。
[30]董健:《論高曉聲小說的思想和藝術》,《文學評論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專號》第十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69-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