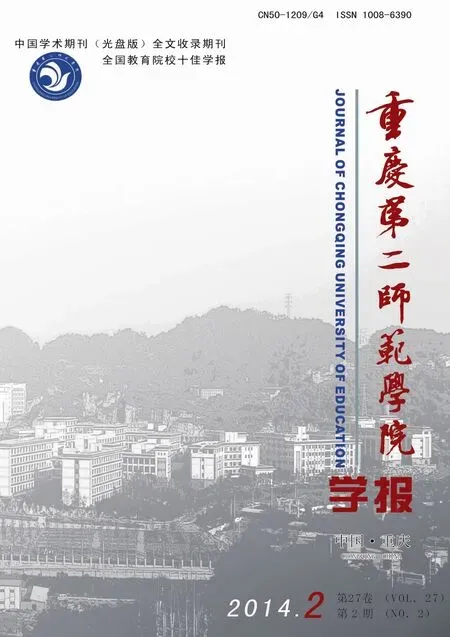批判與超越: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主—奴辯證法”
李貞元,程和祥
(1.南京大學 哲學系,南京 210023;2.西南政法大學 行政法學院,重慶401120)
《精神現象學》是理解黑格爾哲學的關鍵和秘密,而這個關鍵和秘密就是“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這種“否定性的辯證法”表現在貫穿整部《精神現象學》的“異化”或“自我意識的異化”這一概念上,而這又集中體現于《精神現象學》的第四章第一節——在這一節,黑格爾提出了“主—奴辯證法”。在對黑格爾的這一思想的解讀過程中,顯現出一些淺薄的、似是而非的觀點,在這些觀點的包裝下,“主—奴辯證法”成了俞吾金所說的“哲學神話”,即“主人成了奴隸,而奴隸則成了主人”。[1]66基于唯物史觀,從感性活動的視角對“奴隸”和“主人”的處境進行分析,以及對“主—奴辯證法”的歷史審視,將表明奴隸對主人的顛覆具有偶然性;并且所謂的“主人變成奴隸,奴隸變成主人”,也不符合黑格爾的原意。
一、“主—奴辯證法”的神話
按黑格爾的原意,在爭取承認的生死斗爭中,一方冒著生命危險,獲勝后成為主人;另一方因對死亡的恐懼而把自身的命運交由對方決定,被對方蓄為奴隸。在主人的權力支配下,奴隸投入到陶冶事物的勞動之中。在勞動中,他摧毀了曾經令他發抖的異己的存在物,“開始意識到他本身是自在自為地存在著的”;[2]131而主人只是盡情享受,在享受中他成為一個“非獨立的意識”。對這種“獨立性”和“非獨立的意識”的理解,學者們莫衷一是。在肯定“恐懼”和“勞動”的積極意義的基礎上,有學者指出,當奴隸獲得獨立性而主人成為非獨立的意識時,主—奴關系開始反轉:“主人成了奴隸,而奴隸則成了主人。”[3]117
然而,這種理解過于主觀,它肯定了“奴隸通過自己再重新發現自己的過程”中,恐懼和陶冶事物的勞動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但對于奴隸的恐懼和勞動,缺乏科學客觀的分析。
首先,它沒有看到恐懼的負面意義。奴隸之所以成為奴隸,在于他恐懼死亡,即他寧可放棄超越自然層次的自由,選擇作為物而活著。因為恐懼,奴隸在一切異己的存在面前都害怕得發抖,從而不能將一切事物都看作滿足其欲望的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對象,他與事物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欲望與其對象之間的自然關系。他在恐懼中開始否定自身的自然存在,潛在地意識到自己是一種自為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這種使得奴隸成為奴隸的恐懼感,也開啟了奴隸的自我確證之路。但是,奴隸對死亡的恐懼除了具有黑格爾所說的正面意義外,還有嚴重的負面后果。這種“曾經浸透進他的內在靈魂,曾經震撼過他整個軀體”[2]130的恐懼會導致奴隸處于焦慮狀態,長期的焦慮會禁錮奴隸的思維,使奴隸變得麻木和神經質,他“目瞪口呆,而意識也得不到提高與發展”。[2]131
其次,它忽略了現實勞動的消極方面。在黑格爾看來,在恐懼中奴隸所達到的對自為存在的潛在的自覺只不過是智慧的開始,而真正地完成這種智慧,還需要由勞動來實現。對于奴隸而言,“一切‘現狀’都不‘符合’‘自己’的‘本質’,都是要‘改變’的”。[5]20勞動不僅改變了奴隸的依賴意識,而且還是對恐懼的否定——通過勞動,呈現在他面前的令他恐懼的異己的存在都被他改造了。但是,黑格爾雖然“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勞動的結果”,[6]101理解為人在勞動中的對象化和異化,并且揚棄這種外化的自我生成。但他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沒有把勞動看作是“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動”。受其哲學體系的制約,黑格爾把“勞動”桎梏在絕對觀念的牢籠之中,忽視了勞動與現實生活的關聯。因而,他在《精神現象學》中只看到精神勞動的積極意義,而沒有看到現實勞動的消極方面。在奴隸社會或存在奴役的地方,主人驅使奴隸從事的都是最臟、最累、最危險的勞動。一方面,對于這些強制性的、重復且乏味的勞動,奴隸不僅毫無興趣,還常常通過消極怠工、破壞生產工具和逃亡等方式與主人進行抗爭。對于此類勞動,談何“陶冶與教化”?所謂的勞動美學只不過是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的幻想。另一方面,繁重的、屈辱性的、危險性的勞動嚴重威脅著奴隸的身心健康和生命。不少奴隸常常在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的情況下悲慘地死去,又如何意識到自己的獨立性,如何對主人的地位進行挑戰?
最后,恐懼和勞動這兩個環節是相互關聯的。對奴隸而言,“在恐懼中他感覺到自為存在只是潛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勞動中則自為存在成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開始意識到他本身是自在自為地存在著的”。[2]131“沒有服務和聽從的訓練則恐懼只停留在外表形式上,不會在現實生活中震撼人的整個身心。沒有陶冶事物的勞動則恐懼只停留在內心里,使人目瞪口呆,而意識也得不到提高與發展” 。[2]131同樣,如果奴隸一直處于恐懼和焦慮的陰影中,那么,奴隸就不能很好地從事改造自然、陶冶事物的勞動,這樣,意識的純粹自為存在就不能“在勞動中外在化自己,進入到持久的狀態”。[2]130因此,那勞動著的意識便難以達到“以獨立存在為自己本身的直觀”。
二、主人和奴隸——基于實踐的視角
對“主—奴辯證法”的認識,不能“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主—奴辯證法”“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 。[7]54因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7]56換句話說,對“主—奴辯證法”的認識,要始終站在現實的基礎上,從實踐出發、從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出發來理解它、把握它。立足于此,可以發現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存有諸多疑問。
一方面,黑格爾對奴隸的處境的理解,有兩點值得懷疑。
首先,黑格爾認為,勞動節制了奴隸的欲望。但是,他沒有深刻地洞察到,現實中奴隸的勞動不僅僅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更多時候被迫壓抑自己的欲望,而極度的壓抑在一定程度上會摧殘奴隸的身體并扭曲奴隸的心理,使奴隸處于接近崩潰的病態和瘋狂之中。
其次,當奴隸在主人的權力支配下投入到勞動中去的時候,其體能、技能和性格都必定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和奴隸的獨立意識的確立并沒有必然關系——奴隸有可能變得麻木不仁,也有可能更加依賴主人。整個人類歷史表明,作為整體的奴隸階級的覺醒和獨立意識的獲得乃是外在的或從內部成長起來的先知先覺者對廣大奴隸自覺地進行教育甚至灌輸的結果。單純的勞動有可能導致某一個奴隸產生獨立意識,并且這種獨立意識會逐步成熟,但是僅僅單純的勞動就導致整個奴隸階層產生獨立意識卻是一種癡心妄想。
另一方面,黑格爾對主人的論述也有失偏頗。黑格爾這樣寫道:“主人把奴隸放在物與他自己之間,這樣一來,他就只把他自己與物的非獨立性相結合,而予以盡情享受;但是他把對物的獨立性一面讓給奴隸,讓奴隸對物予以加工改造。”[2]128在這里,黑格爾把主人僅僅理解為奴隸勞動成果的享受者。實際上,主人在現實活動中扮演著多個角色,遠比一個單純的享受者豐富得多。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主人都沉溺于享受。主人在追求享受的同時,也試圖維持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以使自己在物質上占據絕對優勢。而且,主人把繁重的體力勞動強加給奴隸后,并不是所有的主人都“無所事事”地飽食終日,主人中的精英階層會用從奴隸那里掠奪過來的時間去構建適合于主人利益的意識形態,“以麻痹并消解可能會在奴隸中間慢慢地形成并發展起來的獨立意識和反抗意識”。[1]67換言之,主人不僅僅在物質上支配奴隸,還試圖從精神上給奴隸套上枷鎖,決不會坐以待斃。
第二,主人也會用掠奪來的時間去自由地學習文學、藝術和其他方面的知識,以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陶冶個人的情操,使自己得到全面發展。對于日夜都被繁重的體力勞動所糾纏的奴隸而言,主人這樣的學習方式和發展方式是他們做夢也想象不到的。另外,主人的這種學習和發展策略也可以看作是對奴隸反抗的全面防范和戒備。在談到資本家的財富時,馬克思曾經指出:“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8]218又說:“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8]225把馬克思關于資本家的觀點運用到主人身上,也是適當的。這樣,黑格爾把主人僅僅設想為純粹的消費主義者只不過是一種偏見。
總之,在“主—奴辯證法”的神話中,主人是只知道癡迷于享受而一無是處的白癡。與此同時,奴隸則被精心打扮成了真正的智者和命運的寵兒。通過勞動,奴隸擺脫了對主人的依賴,而主人反過來依賴奴隸。但是,這又如何解釋人類的歷史?
三、對“主奴辯證法”的歷史審視
重新理解“主—奴辯證法”,我們需要對主人和奴隸的關系作一番歷史考察。馬克思的“從后思索法”啟示我們,對“主—奴辯證法”的歷史考察應該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結果”出發。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結果”出發去審視“主—奴辯證法”,完全是由現實的社會實踐所激發和規定的,因為從“事后”開始思考,無非是說明“思維應該在實踐的最高端和發展的最前沿”。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著眼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人類社會總體歷史進程作了一個深刻的劃分與展望。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主奴關系”刻畫了人作為“自然存在物”的特性,存在于“以人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社會之中,當該社會形態終結之后,人成為“生產當事人”,但奴隸并沒有成為主人——奴隸仍然是奴隸,但主人不再是人,而是外在于曾經的主人和奴隸的物——他們所賴以生活和維持生產的物。換句話說,當作為整體的奴隸階級顛覆主人的統治,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之后,又被“物”所奴役。至于馬克思許諾的“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依舊還未到來——即使到來,奴隸也只是“社會自由人”,不是“主人”。由此觀之,立足于現實的歷史,奴隸從來就沒有作為一個整體對主人進行統治。所謂的“奴隸變成主人,主人成為奴隸”沒有歷史依據,根本不具備普遍性。有鑒于此,尼采拒斥“主—奴辯證法”。與馬克思不同,在尼采看來,奴隸的勝利只是一種極其偶然的個別結果,具有主人氣質的超人完全可以再次取勝。尼采認為,奴隸永遠是奴隸,它不可能“升華”為主人,主人也永遠是主人,它不可能淪落到奴隸的自保狀況。“主人和奴隸的關系本身并非辯證的關系。那么誰是辯證法家,誰使這種關系辯證化了呢?是奴隸,是奴隸的視角和屬于奴隸視角的思維方式。[9]14”或者,“辯證法僅僅是那些不具備任何其他武器之人手中的自衛手段”。[10]49
四、回到黑格爾——生死斗爭
實際上,根據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的安排,奴隸并沒有在現實中冒生命危險去實現自己的自由,而是倒向了斯多葛主義、懷疑主義與基督教主義。
在斯多葛主義中,奴隸只是在思想中承認自己的自由,他以口頭議論的方式調和自己的奴隸地位與抽象的思想自由,而口頭自由與現實處境的沖突,驅使著奴隸走向懷疑主義;在懷疑中,奴隸否定一切外在的存在,包括他在現實世界中的奴隸地位,這種懷疑使得奴隸走向虛無主義,其中一些人會選擇自殺,而活下來的虛無主義者選擇了基督教主義;在基督教主義中,對于作為教徒存在的奴隸而言,“自由并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一個簡單的抽象理念,一個無法實現的理念,就像在斯多葛主義和懷疑主義中那樣。自由是真實的,自由真實地存在于超越之中” 。[11]55
但是,歸根結底,斯多葛主義者、懷疑主義者以及基督教主義者都是奴隸。因為他們在死亡面前哆哆嗦嗦,不敢冒著生命危險與主人作斗爭,因而不能改變他們自身的奴役處境,終究只是奴隸。“在生死斗爭中,人成為其對手的奴隸是因為想不惜一切代價保存生命,人成為上帝的奴隸也是因為想避免死亡,想作為教徒在自己身上尋找一個不死的靈魂” 。[12]81但人終究是要死的,“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躪的生活,而是敢于承當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 。[2]21“正是人自愿地接受在為了純榮譽的斗爭中的死亡危險,甘心死亡、并通過語言揭示死亡,人才成為人” 。[12]642畢竟,是死亡形成了植根于自然之中而又憑借人的精神而振拔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死亡令人“走向他自己的最后命運”。也只有這種“朝向死亡的存在”,才能作為一個整體被置入了先有之中。“只有這樣一種存在者,它就其存在來說本質上是將來的,因而能夠自由地面對死而讓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拋回其實際的此之上,亦即,作為將來的存在者就同樣原始地是曾在的,只有這樣一種存在者能夠把繼承下來的可能性承傳給自己本身之際承擔起本已的被拋狀態并在眼下為‘它的時代’存在。只有那同時既是有終的又是本真的時間性才使命運這樣的東西亦即使本真的歷史性成為可能。”[13]435-436
奴隸真正應該做的,是接受死亡的事實,“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4]1483-1490只有冒著生命危險,主動與主人作斗爭,奴隸才能被承認為具有獨立性的人。“一個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場的個人,誠然也可以被承認為一個人,但是他沒有達到他之所以被承認為一個獨立的自我意識的真理性。”[2]126也就是說,僅僅意識到自身的自由是不夠的,充其量只是像一個主人,一個假主人。“但是,真主人殺人:他為了得到承認進行斗爭。”[12]97
五、小結
基于唯物史觀,從感性活動和歷史的角度,對“主—奴辯證法”進行分析,以及立足于原文的解讀,都能夠證明:從“主—奴辯證法”中解讀出“主人成了奴隸,而奴隸則成了主人”,將“主—奴辯證法”制造成哲學神話,純屬誤讀和褻瀆。毋庸置疑,“主—奴辯證法”作為黑格爾青年時期最深刻、最神圣的思想之一,影響深遠:馬克思把“主—奴辯證法”中的承認論題和勞動論題結合起來,并深入思考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承認問題——“對馬克思來說,主奴關系的核心無疑就是階級斗爭,承認問題的關鍵就是無產階級的解放”;[15]90欲望、死亡和承認等概念也被科耶夫發掘,成了他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對“主—奴辯證法”進行透視的重要主題,從而為之后的諸多流派提供了可汲取的思想資源——“欲望主題在薩特、德里達、福柯、拉康、德魯茲等人那里得到了極其絢爛的發揮;死亡主題使海德格爾通向法國成為可能,進而在列維納斯那里得到最強有力的回應”;[16]5至于承認主題,在德國由霍耐特繼承,并在流行于英語世界的后殖民理論思潮中得到了某種異鄉的回響。
參考文獻:
[1]俞吾金.走出“主奴關系”的哲學神話[J].東南學術,2002,(2).
[2]黑格爾.精神現象學[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3]陳偉.片面承認的全面化——論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主奴辯證法[J].理論界,2008,(1).
[4]陳良斌.“主奴辯證法”的揚棄與承認的重建——從黑格爾的“主—奴關系”論到馬克思的承認理論[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9,(10),22(5).
[5]葉秀山.關于“自由”與“必然”——研討黑格爾哲學斷想[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3,(1).
[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吉爾.德勒茲.尼采與哲學[M].周穎,劉玉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0]尼采.偶像的黃昏[M].衛茂平,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1]A. Koje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M].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12]科耶夫.黑格爾導讀[M].姜志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13]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1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張盾.馬克思與黑格爾《精神現象學》[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7),47(4).
[16]張亮.欲望、死亡與承認:科耶夫式黑格爾哲學的三個關鍵詞[J].江蘇社會科學,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