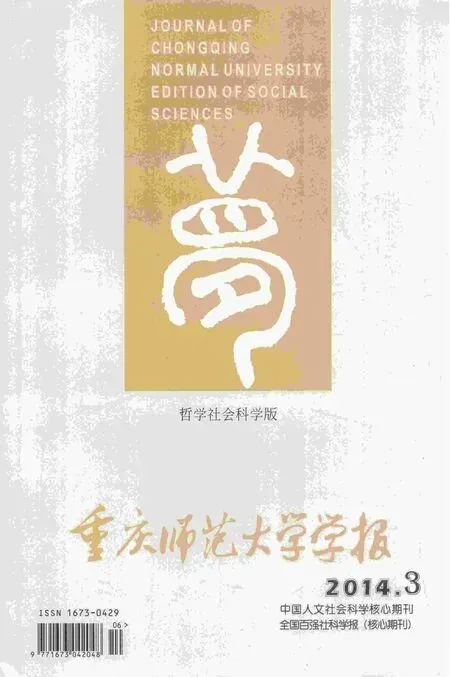杜甫夔州詩與三峽文化關系論說
曾 超
(長江師范學院 學報編輯部,重慶涪陵 408100)
唐代大歷年間,我國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寓居夔州(今重慶奉節),寫下了數量眾多的詠贊三峽特別是夔州的詩歌,是為夔州詩。杜甫夔州詩作為杜甫詩歌創作的第三個高潮和整個杜詩創作的高峰,受到了歷代文人學士、杜詩研究者、三峽文化研究者的高度關注。雖然學界研究涉及杜甫在夔州的方方面面和杜甫夔州詩的豐富內容,但對杜甫夔州詩與三峽文化之間關系的考察仍感薄弱,故陋陳己見,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夔州詩:詩性描述三峽文化
三峽文化是一個總概念、類概念,杜甫及其夔州詩是屬概念,兩者是種屬關系。就此而言,杜甫及其夔州詩總體包容于三峽文化的“大范疇”之中。不僅如此,雖然杜甫夔州詩涉及到三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杜甫是作為“詩人”名世的,因此杜甫及其夔州詩更應歸屬于三峽文學文化的范疇。
杜甫一生詩歌創作“有三個高潮:安史之亂前后為第一個高潮,漂泊秦州、成都時期為第二個高潮,寓居夔州時期為第三個高潮。在最后一個高潮中創作的詩篇,無論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藝術手法之巧妙,思想性之強,都超過了前兩個高潮。”[1]
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春末杜甫來到夔州,大歷三年(768年)正月出峽,寓居夔州一年零十個月,留詩430多首,成為杜甫詩的巔峰之作。杜甫夔州詩,就其文化屬性而言是三峽文學文化,但就詩歌所描述的內容來說,則涉及到三峽文化的各個方面。政治、軍事、民族、民俗、民生等均有所涉及。不僅如此,杜甫更是用詩性的語言,結合實地感受,利用五古、七律、絕句、俳諧體等,充分地記錄、描述、詠贊三峽文化。這里充分利用學界的研究統計成果加以說明。
(一)記錄杜甫夔州生活
大歷元年(766年)暮春杜甫一家從云陽來到夔州,大歷三年(768年)正月離夔東下,前后跨三個年頭,實際寓居夔州一年零十個月。“況乃主客間,古來逼側同”(《贈蘇四徯》)杜甫在夔州先后搬家五次:初到住客堂,遷草閣(江邊閣),再遷西閣,再遷赤甲,再遷瀼西,最后遷東屯。[2]對此,杜甫在《客堂》、《草閣》、《江邊閣》、《入宅》、《赤甲》、《贈蘇四徯》、《峽口二首》、《覽鏡呈柏中丞》、《西閣雨望》、《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西閣二首》、《月》、《卜居》、《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堂五首》、《園官送菜》、《暇日小園散病,江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等詩中進行了記述。
杜甫到夔州后,積極經營生活,樹雞柵,課伐木,管理果園,管理公田,覽勝訪古,課兒勉學,帶病延年,拼命作詩。對此,杜甫有《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堂五首》、《自瀼西移居東屯四首》、《引水》、《示獠奴阿段》、《夜歸》、《太歲日》、《小園》、《贈南卿兄弟瀼西果園四十畝》、《行官張望補稻〔田圭〕水歸》、《茅堂檢校收稻二首》、《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等詩加以說明、記述和描述。
杜甫到夔州后,積極交流溝通,建立人際關系網絡,謀求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據胡煥章統計,杜甫在夔州生活中的“親朋往來”有韋有夏(《寄韋有夏郎中》)、崔公輔(《贈崔十三評事》)、李文嶷(《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贈李十五丈別》)、崔十六(《毒熱寄簡崔評事石流弟》)、柳少府(《貽華陽柳少府》)、元二十一(《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李瑀(《奉漢中王手札》、《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楊某(《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李八(《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十五弟(《送十五弟侍御使蜀》)、杜豐(《第五弟獨在江左》)、韓注(《奇韓諫議注》)、蘇徯(《君不見簡蘇徯》、《贈蘇四徯》、《別蘇徯》)、李潮(《李潮八分小篆歌》)……等等。[3]
(二)感知夔州氣候和自然生態
奉節縣屬中亞熱帶暖濕東南季風氣候,在海撥600米以下的長江河谷兩岸及其階地,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霧日少,晝夜溫差大,無霜期長,屬高溫中濕多日照氣候類型。但奉節受重慶、武漢兩大“火爐”和高山谷地的影響,夏季毒熱,冬季寒冷。杜甫移居夔州后,雖只在夔州住了一年十個月,仍感受到夔州氣候一年四季的變化。諸如毒熱奇寒、風雷雨雪、陰晴燥濕、四季轉換等無不入詩,形容備至,可以說是一部夔州氣象日記。單從篇名來看,就有《雷》、《熱三篇》、《毒熱寄簡崔評事》、《雨》(11首)、《雨晴》、《雨不絕》、《晨雨》、《雨夜》、《云》等。[4]有人統計,杜甫寓居夔州所作 430 多首詩,其中就有31首專寫晴雨天氣。
受氣候影響,夔州亞熱帶常綠果樹和溫帶常綠果樹混交,四季鮮花不斷,水果殊多。茂密的森林,豐厚的植被,是野生動物棲息活動的場所。杜甫詩大量描述夔州森林植被、疏果花草、飛禽走獸的詩篇,是當時夔州自然生態的真實寫照。[5]杜甫有許多韻贊夔州水果的詩篇,如《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寒雨朝行視園樹》、《樹間》、《園》等。還有不少反映夔州飛禽走獸的詩作,而最引人注目的關于虎豹的記述,如《課伐木》、《夜歸》、《晴二首》、《晚晴》等。
(三)記錄夔州物產
夔州土地肥沃,水源便利,物產豐饒。據明正德《夔州府志》卷之三《土產》,奉節物產谷類有黍、稷、稻、粱、麥、豆、菽、粟、蕎、芝麻;貨類有鹽、棕毛、黃蠟、花椒、鹿皮、麂皮、茶;菜類有梅、棗、栗、菱、銀杏、橙、橘、桃、李、梨、柿、柑、枇杷、木瓜;疏類有青、芹、筍、韭、油、芥、木耳、瓜、茄、蔥、蒜、扁豆、蕨、胡蘿卜;藥類有黃連、茱萸、芍藥、大黃、香附、五倍子、麝香、厚樸、楓香、麥門冬;木類有楠、松、麻柳、青岡、櫧、楸、白蠟樹;竹類有筋竹、水竹、斑竹、慈竹;畜類有牛、馬、豬、羊、雞、鵝、鴨;鳥類有杜宇、山雞、白鷴、竹雞、斑鳩、畫眉、黃雀;獸類有麂、熊、鹿、野豬、刺豬、狐貍、猿猴;蟲類有白蠟蟲。[6]據統計,杜甫夔州詩記載了上百種夔州物產,其中,動物50種,植物19種,農產品29種,手工業產品9種,大多為原生態產品。詩中的動物,野生的有猿、狼、虎、豹、熊、羆、鹿、糜、麝、兔、雉、魚、蛇、山雞等,圈養的有牛、羊、豬、雞等。描述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的詩約有70余首,主要涉及畬田、水田、糧食作物以及水果、蔬菜等。記述手工業產品的詩有80余首,主要涉及鹽、船、酒、衣等。如鹽,杜甫夔州詩約有7首述及,包括外地產品。主要詩作有《客居》、《柴門》、《夔州十絕句》、《秋日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負荊行》、《滟預》等。船,大約有48首詩述及各類船只。杜甫夔州詩述及的船有商船、官船、漁船、龍船以及鐵船等。主要詩作有《最能行》、《秋風二首》、《白鹽山》、《夔州十絕句》、《柴門》等。酒,杜甫夔州詩反映了當時夔州酒業興盛,其中看到的夔州酒,有春米酒、巫峽酒、竹葉、柏葉、崖蜜等。主要詩作有《撥悶》、《送十五弟侍御使蜀》、《九月五日》、《人日二首》、《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客堂》、《柴門》等。[7]
豐饒的物產不僅在杜甫夔州詩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唐代夔州對各種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及其水平,體現了唐代夔州的社會生產、生活和富庶。
(四)描述夔州山水
夔州山水天生雄奇險峻,尤以瞿塘峽以及滟預堆、白帝城等最為奇特。杜甫為這些著名景點寫下了不少雄奇絕妙的詩篇。在詩中起興或夾寫夔州山水者,據朱樹群粗略統計竟有350多首,約占全部詩篇的70%。其中專寫瞿塘峽及滟預堆的有10首,寫白帝城有9首,寫西閣、草閣、江邊閣的有12首,寫先主廟、孔明廟、八陣圖的有5首。其中最為有名的如《長江二首》、《峽口二首》、《白帝城樓》、《白帝》、《白帝城最高樓》、《夔州歌十絕句》、《詠懷古跡五首》等。[8]
(五)韻贊夔州三國文化
夔州是三國文化的重要遺跡,這里有白帝城、永安宮、八陣圖、觀星亭、撫軍橋、先主廟、武侯祠、關公廟、張飛廟等,是三國故事“劉備托孤”的發生地,自然成為杜甫夔州詩的一個主要內容。杜甫寫有夔州三國文化的詩作約30篇,僅有關白帝城的就有《上白帝城》、《上白帝城二首》、《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白帝城最高樓》、《白帝》、《白帝樓》、《白帝城樓》等。這些詩有極其豐富的內容。據劉厚政研究,杜甫在《夔州歌十絕句》、《諸葛廟》、《詠懷古跡五首》、《古柏行》、《夔府書懷四十韻》、《謁先主廟》、《武侯廟》、《八陣圖》、《閣夜》、《上白帝城》、《上白帝城二首》、《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贈左仆射鄭國公嚴公武》等詩中憑吊祭祀三國英雄豪杰,贊頌賢君忠臣之間的融洽關系,對劉備任用賢臣給予贊揚,贊頌諸葛亮的忠誠,贊頌諸葛亮的雄才大略,對諸葛亮不能實現大志表示遺憾,對有才之士不能征用表示感嘆,登臨白帝城表現出憂患意識,對國家戰亂表示不滿,對人民苦難表示同情,對天下永安寄予期盼,用諸葛亮的品行勉勵親朋,記錄夔人對諸葛亮的祭祀情況等。[9]
杜甫夔州詩體現的三峽文化并不僅限于上述內容,其他如《示獠奴阿段》、《負薪行》、《最能行》、《戲作俳諧體解悶二首》、《十月一日》、《火》等對夔州異俗的描述,在《詠懷古跡五首》、《諸葛廟》、《謁先主廟》中對三峽歷史文化名人如公孫述、庾信、王昭君、劉備、諸葛亮等的詠嘆,因篇幅關系,就不一一羅列了。
二、夔州詩:影響三峽文化的生成
杜甫夔州詩不僅以詩性化的語言描述了三峽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極大地影響著三峽文化的生成與發展。
(一)杜甫詩整理
杜甫在夔州留下了諸多不朽詩篇,如何將其詩歌文獻加以承傳,使之不朽,受到了后世詩家和夔州政要的高度關注。最早推出并屬意杜甫夔州詩的是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載:他“謫居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丹棱楊素翁“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并由工匠楊鳩工刻石并建“大雅堂”以藏之。治平年間(1064—1067年),夔州知州賈昌言刻杜詩十二石于北園。建中靖國元年夔州轉運判官王遽刻杜詩碑于漕司。[10]
(二)杜甫詠贊
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其詩現實性、思想性、藝術性極高,因此,無論是杜甫本人還是杜甫的詩歌,都備受歷代詩家和研究者的推崇。這些人也以詩歌的形式論贊杜甫,從而影響著三峽文化的生成與發展。如:唐朝詩人元稹《酬孝甫見贈十首》之二云:“杜甫天材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韓愈《調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北宋蘇軾《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之三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南宋王十朋《夔路十賢·少陵先生》云:子美稷契志,空懷竟無用。夔州三百篇,高配風雅頌。并另有《詩史堂》、《杜工部祠二首》詠杜。南宋著名抗元將領文天祥《山中呈聶心遠諸客》云:“黃葉婆娑上釣舟,喚回舊夢到江流。多情政自憐檣燕,兩鬢終當付野鷗。未說離懷向南浦,須知詩意在夔州。朔風昨夜吹沙急,早覺寒聲戰玉樓。”清代著名詩人王士禛有《杜工部祠》七律五首,李調元有《謁杜少陵祠》。夔州知府江權有《杜工部祠落成》七律一首:拾遺垂老客江鄉,處塞秦關入望長。鳥道千盤過隴蜀,鯨波一棹隔荊襄。孤忠展轉惟憂國,白發棲遲只自傷。瀼水東西歌嘯地,定知陟降在斯堂。前任知府李復發、蓮峰書院主講張鳳翥、奉節縣令李作梅等十二人競相奉和,共得同韻詩十三首,為夔州詩壇一段佳話。
(三)杜甫景觀
杜甫寓居夔州,先后五次遷徙,茅屋故居頗多。杜甫雖只在夔州居留一年十個月,但后世治理夔州者均高度關注其文化景觀之建設,還產生不少新的三峽文學作品。北宋慶歷年間(1042-1048年),瀼西建歲寒堂。治平年間(1064-1067年),夔州知州賈昌言刻杜詩十二石于北園。建中靖國元年夔州轉運判官王遽刻杜詩碑于漕司。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夔州通判陸游作《東屯高齋記》。嘉定初年夔州知州費士戣有《漕司高齋記》。慶元三年(1197年),夔州通判于栗作《東屯少陵故居記》。嘉定元年(1208年),夔州知州費士戣重建漕司高齋,作《漕司高齋記》。明萬歷初年,夔州知府郭棐令奉節知縣羅繡藻在關廟沱重修瀼西草堂,四川按察使陳文燭撰有《重修瀼西祠堂記》。萬歷二十九年夔州通判何宇度在關廟沱坎上路北立有《唐杜工部游寓處》碑。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夔州知府江權在魚復就原晉階書院舊址新建杜工部祠,江權有《杜工部祠碑記》,有詩《杜工部祠落成》七律一首。嘉慶二十年(1815年)夔州知府楊世英重修杜工部祠。同治九年(1870年)奉節知縣呂輝改東郊杜公祠為少陵書院,并于其旁新建武侯祠。光緒二十二年(1906年),奉節知縣侯昌(桐初)鎮捐俸在東屯浣花溪畔重建瀼西杜甫草堂,塑杜甫肖像,以草堂部分廂房設學館,延師教育后生。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安徽巡撫馮煦撰有《重建杜工部瀼西草堂記》。20世紀80年代,白帝城博物館建西閣,黃瓦紅墻,飛檐斗拱,閣中貼杜甫巨幅瓷像,庭中塑杜甫大型石像。[10]
(五)杜甫祭祀
杜甫是偉大的詩人,人民性極強,忠君愛民,備受尊崇,夔州人民也不例外,人們總是以各種方式祭祀、憑吊杜甫。北宋慶歷年間(1042-1048年),瀼西建歲寒堂,祀前賢屈原、諸葛亮、嚴挺之、杜甫、陸贄、韋昭范、白居易、柳鎮、寇準、唐介十人,各畫像堂中,外栽修竹。后更名為忠孝堂、十賢堂。明萬歷初年,夔州知府郭棐令奉節知縣羅繡藻在關廟沱重修瀼西草堂,四川按察使陳文燭撰有《重修瀼西祠堂記》,文末有《迎神送神曲》,詞曰:“昔飄零兮流寓,嘆遷次兮朝暮,側身來兮參差其歸路。三年飽兮煙霧,千載驚兮香柱,尚轉蓬兮山靈其呵護!”清乾隆二十一年(1755年)李調元經水路赴浙江過夔州,到東屯草堂遺址憑吊杜甫,有《謁杜少陵祠》,詩云:“漂泊誰為浩蕩游,當年老杜此淹留。一朝詩史為唐作,萬丈文光向蜀留。風雨茅祠仍見撥,云煙瀼宅尚含愁。艱難我亦棲遲久,試問秋懷得似不?。”同治九年(1870年)奉節知縣呂輝改東郊杜公祠為少陵書院,并于其旁新建武侯祠。在白帝廟明良殿兩邊建三楹,其右祀杜甫、李白、范成大、陸游諸詩人。[10]
(六)杜甫研究
杜甫詩歌對后世影響極大。宋代孫僅具體地分析了杜詩藝術對中晚唐詩人的影響:“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筒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爀世烜俗。后人師擬不暇,蚓合之乎?”[11](2238)人們對杜甫極為推崇,對杜甫研究投入了極高的熱情,產生了諸多的杜甫詩歌研究成果。試看:
著名詩人劉禹錫論說:“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12]劉禹錫的七絕就頗類杜詩風調,尤其是他的《竹枝詞》,“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13]
著名散文家、思想家韓愈極為推崇杜甫。清代趙翼指出:“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14]
著名詩人黃庭堅云:“觀子美到夔州后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后文章,皆不煩繩屑而自合矣。”[15]
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論杜甫詩歌內容與風格,說:“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舟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深,觀者茍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16]
詩人劉克莊特別推崇杜甫的《壯游》:“《壯游》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還說:“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里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余謂崔、韓比此詩于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語。”[17]
劉熙載《藝概·詩概》說:“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菡茹到人所不能菡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18]
胡應麟《詩藪》評《登高》詩:“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移,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后無來學,此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真曠代之作也。”贊《閣夜》“氣象雄蓋宇宙,法律細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19]
佚名《杜詩言志》評《秋興八首》云:“唐人七律,以老杜為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為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郁結,與其遭際,暨其傷感,一時薈萃,形為慷慨悲歌,遂為千古之絕調。”[20]
施潤章《李朗仙江淮草序》云:“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人,皆生于蜀者也。杜甫詩入夔州以后,蓋久客于蜀者也。說者皆謂得山川之助也。”[21]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評《秋興八首》云:“懷鄉戀闕,吊古傷今,杜老生平俱于見此。其才氣之大,筆才之高,天鳳海濤,金鐘大鏞,莫能擬其所到。”[22]
今人蕭滌非謂《登高》有九可悲:“他鄉作客,一可悲;離家萬里,二可悲;常年漂泊,三可悲;又當蕭瑟的秋天,四可悲;重陽佳節,無賞心樂事,只是登臺,五可悲;親朋凋謝,獨登無侶,六可悲;扶病強登,七可悲;而且多病,八可悲;百年倏忽,自感年邁無成,九可悲。”[23]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裴斐認為:“杜甫的夔州詩集杜詩之大成。”[24]
杜甫夔州詩是杜甫留給夔州人民的寶貴財富,因之,對杜甫夔州詩的研究,夔州著力甚多。[25]奉節專門成立了夔州杜甫研究會,其宗旨是“立足夔州,研究杜甫。承傳憂患意識,弘揚詩城文化”。夔州杜甫研究會和白帝城博物館聯辦了學術性刊物《秋興》,出版了杜甫夔州詩的研究成果。僅李君鑒主編的《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就收錄有不少本地學者研究杜甫及其夔州詩的文章,如魏靖宇的《不識赤甲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唐田夫人墓記〉發現的意義》、李君鑒的《唐代赤甲山究竟在哪里》、李江的《夔州杜公祠的興廢》、譚光武的《讀杜甫詠諸葛孔明詩札記兩篇》、王大椿的《杜甫〈夔州歌十絕句〉試解》、易衍澄的《鄰里見真情——杜甫與鄰里孟氏兄弟交往詩淺析》、謝雪華與易衍澄的《試說“白帝夔州各異城”》、姚克強的《杜甫〈旅夜書懷〉詩時地質疑》、劉書東的《杜甫夔州柑桔詩的文化解讀》、何定軒的《杜甫詩中的愁及其文化精神》、周祚政的《夏旱秋澇襲夔州——讀杜甫詩探夔州夏秋氣候特點》、劉厚政的《杜甫弘揚了夔州三國文化》、胡煥章的《杜甫夔州生活概況》、朱樹群的《簡談杜甫寓夔時期創作豐碩的原因》、龍占明的《杜詩儒家思想略探》、馮仲祥的《淺談杜甫夔州詩的人民性》、李學清與舒欣的《借古跡詠懷寄意深遠——〈詠懷古跡五首〉淺釋》、彭炳夔的《淺談杜甫〈八陣圖〉的“遺恨”》、劉德武的《也說“遺恨失吞吳”》、廖太素的《讀杜甫〈夔州十絕句〉揣想奉節當年風貌》、余敬之的《關于“日出清江望”之我見》……
總之,杜甫及其夔州詩內涵豐富,影響巨大,這是一筆珍貴的財富,值得我們深入挖掘、整理和傳承。
[1] 馮仲祥.淺談杜甫夔州詩的人民性[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2] 譚光武.讀杜詩札記兩篇[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3] 胡煥章.杜甫夔州生活概況[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4] 劉書東.杜甫與陸游客居夔州詩歌創作之比較[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5] 李江.夔州自然生態古今談——讀杜甫夔州詩一得[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6] [明]吳潛修,傅汝舟纂.土產[A].正德夔州府志(卷之三)[Z].上海古籍書店,1961.
[7] 何定軒.杜甫詩中的夔州物產[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8] 朱樹群.簡談杜甫寓夔時期創作豐碩的原因[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9] 劉厚政.杜甫弘揚了夔州三國文化[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10] 李江.夔州杜公祠的興廢[A].杜甫夔州詩研究文集[C].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11] [宋]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A].仇兆鰲.杜詩詳注(附編)[C].中華書局,1979.
[12]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Z].電子本.
[13] [宋]黃庭堅.跋劉夢得竹枝歌[A].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六)[C].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刻本.
[14] [清]趙翼撰.霍松林,胡主佑點校.甌北詩話(卷三)[M].文學出版社,1963.
[15] [宋]黃庭堅.與王觀復書[A].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C].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刻本.
[16] [宋]何 汶.竹莊詩話(卷五)[M].《四庫全書》本.
[17] [宋]劉克莊.詩話后集[A].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M].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18] [清]劉熙載.藝概·詩概[EB/OL].http://www.xfjw.net/html/wy/rs/13951.html.
[19] [明]胡應麟.詩藪[M].中華書局,1962.
[20] [清]佚名.杜詩言志[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21] [清]施潤章.李朗仙江淮草序[A].學餘堂文集(卷六)[C].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22]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M].岳麓書社,1998.
[23] 蕭滌非.杜甫研究[M].齊魯書社,1980.
[24] 裴斐.杜詩八期論[J].文學遺產,1992,(4).
[25] 羅超華.孫應時蜀中詩論[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3,(4).
[26] 李卉.新時期以來三峽本土文學綜論[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