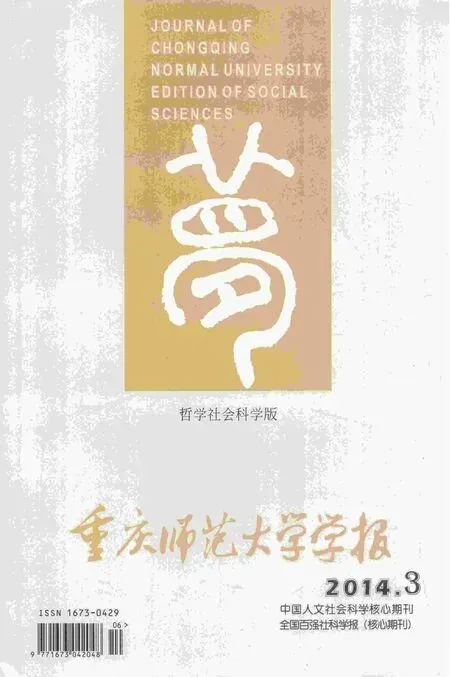紹興五年南宋朝廷“漸圖恢復”下的對金態度
陳 忻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400047)
紹興四年十二月,南宋朝廷挫敗了偽齊與金人的聯兵入侵,扭轉了自建炎以來始終被動奔避的局面,初步改變了南宋在與金齊對峙中的劣勢地位,為南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在這種對外的難得的大好形勢下,如何制定朝廷下一步目標,如何調整對內對外的政策方略,如何規劃措置善后事宜就成為朝廷面臨的新任務。紹興五年正月,高宗與宰相趙鼎于金、齊退遁不久,有這樣一次對話:“上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徳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圣諭。事所可為者,謹當以次條畫奏稟。’”[1](2冊,卷84,紹興五年正月戊申條,1378)可以說,高宗的放棄退避舊策,“大作規模措置”,“漸圖恢復”成為了南宋朝廷紹興五年的根本任務。以此為前提,如何結合現實的、具體的政治、軍事等形勢調整對金的策略,以尋求南宋朝廷在對金與對齊的斗爭中占據主動就成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朝廷屢屢要求朝臣奏上善后之計、攻戰之利、備御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朝臣們以此為主題,圍繞著國家的方略所陳述的各種見解便成為紹興五年政治中特別值得關注之處。本文正是由此入手,結合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梳理涉及到對金關系的相關奏疏,研究其指向及其意義。
一、善后之計當出群策
紹興四年九月,偽齊與金分道南犯,南宋宰相趙鼎促成高宗親征,一時將帥用命,士卒鼓勇。十二月,金齊俱遁,南宋朝廷軍聲大作,取得了自靖康以來對金與偽齊的首次大勝利:“庚子,金人退師。”“金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猊。于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宿州方敢少棲。西北大恐。”[1](2冊,卷83,紹興四年十二月庚子條,1369-1370)這次戰事極大地鼓舞了南宋朝廷上下的人心士氣,自此,退遁避敵、屈辱茍合之策不斷被朝臣質疑。面對宋、金、齊生成的新的對立局面,如何審時度勢,制定對外政策,成為南宋朝廷亟待解決的新問題。紹興五年正月己酉,高宗與宰執大臣討論朝廷的“善后之計”,要求前宰執各陳所見,以備參考:
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圣畫素定。然善后之計當出群策,愿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斷自圣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采眾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倘有可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于是賜呂頤浩、朱勝非、李綱、范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王綯、葉夢得、李邴、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澂、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御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焉。[1](2冊,卷84,紹興五年正月己酉條,1374)
此時,南宋朝廷上下無不以恢復中原、大有作為為最大要務。高宗以此勉勵馳騁疆場的將帥圖報國家:“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其卻敵之功,賜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愿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1](2冊,卷84,紹興五年正月戊辰條,1383)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仆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諸名將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圣未還,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1](2冊,卷84,紹興五年正月壬申條,1384)對于朝廷輔政大臣,高宗也以此相激勵:“上遣中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等奏謝,上曰:‘朕觀《鴻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圣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內修外攘。’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1](2冊,卷94,紹興五年冬十月壬寅條,1552)正是在高宗內修外攘、圖謀恢復的思想主導下,朝臣們奏章頻上,分析金人與偽齊的現狀,結合南宋朝廷的實際情況,提出對金的新方略,探討南宋朝廷在新形勢下的新走向。
二、待釁以乘亂
紹興四年,南宋朝廷克復金、齊聯兵入侵的一大策略就是切割金齊,矛頭直指偽齊劉豫。高宗在其討伐偽齊的手詔中即明確指斥“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于斯”。[1](2冊,卷82,紹興四年十一月壬子條,1346)“間諜和好”,也就是破壞了南宋欲與金議和的意愿,或者說偽齊成為宋金議和的障礙。這樣一來,無論是從和還是從戰兩個方面考慮,劉豫的偽齊都是南宋勢必要鏟除的敵對勢力,這就意味著南宋朝廷必須破壞金人與偽齊的聯盟,分化二者的力量,所謂“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1](2冊,卷87,紹興五年三月癸卯條引秦檜之言,1455)就當時南宋與金、偽齊的實際情況來看,應當說,分化敵人,安慰金人以待時而起的策謀是有其必要性的。
首先,從南宋與金的關系來看,雙方已由各方面的實力懸殊,逐漸具備了抗衡的能力。紹興五年三月,呂頤浩所奏《上邊事善后十策·論彼此形勢》一篇,對此有詳細論述:
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眾,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肆橫。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尼瑪哈(宗翰)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固新貝勒、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斡喇布、扎木、伊都、洛索貝勒、達賚三子、四太子、達賚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強矣。然尼瑪哈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于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巳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其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強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巳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斡喇布、伊都、扎木、國王洛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巳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巳精矣。陛下圣性,精于器械,制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于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金于鎮江,張俊獲捷于明州,陳思恭邀擊于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其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形勢也。[2](141冊,卷3043,249)
呂頤浩以宋金力量的對比為依據,大略分析了雙方力量的發展、變化情況:金方將士“志驕意滿”、“部曲離心”,“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巳甚”,具有“將亡之兆”;我方則與之相對,“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于赴敵”。在這種情況下,練兵待時而乘金之釁并非推諉怯懦之詞。與呂頤浩的見解相類似,端眀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的奏疏也提出了“變亂可待”的觀點,他以自己出使的親身聞見再次證實了金人已是今非昔比:“臣昨在軍前,聞金帥頗有厭兵之意,其眾軍亦思休息。特尼瑪哈、固新、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擕貳,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矣。”[1](2冊,卷87,紹興五年三月癸夘條,1462)與金人的厭兵之意、休息之思相比,南宋一方則“膽氣不怯,勇于赴敵”,具有“待時”乘亂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朝廷集中力量討伐逆賊劉豫,以去除首惡,分化敵人的策略就具備了可能性。
當然,待時乘亂并非無條件的妥協拖延。事實上,南宋朝廷對于金國從無好感。宋金交戰之初,金人無論在政治上、外交上和軍事上都占據絕對優勢,并對南宋朝廷采取絕對敵視的態度。靖康二年,金人廢宋帝時即宣稱“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趙氏宗人不預此議”。[3](卷11,二年二月六日條)建炎二年金太宗指示:“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4](1698)對于南宋派出的使者,金方則一概予以扣押:“凡宋使者,如(王)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遣。”[4](1793)在軍事上,由于南宋“太平日久,民不識兵”[5](370),宋金戰事一開始即處于絕對的弱勢。“自金虜入中原,將帥皆望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6](甲集卷19,《十三處戰功》,449)“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7](卷3,建炎二年夏四月己未條)但是,隨著戰事的發展,南宋朝廷逐漸改變了全然被動的局面。“比年諸將蓄銳練兵,志氣思奮,百倍于前日。”[1](2冊,卷81,紹興四年冬十月辛巳條引魏良臣上書所言,1324)建炎四年,撒離曷及黑峰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彭原店,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8](卷6《太宗文烈皇帝四》,55)至于南攻宋室的主力兀術與撻懶亦并未如預想之順利。和尚原之戰,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6](甲集卷19,《吳玠和尚原之勝》,452)“亟剃其須髯遁歸”。[9](卷361,《張浚傳》,11301)《大金國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記載此戰甚詳:“初,婁室死,兀術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術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余陣,大敗,兀術中流矢,僅以身免。于是,兀術始自河東還燕山。”[8](63)仙人關一役,宗弼“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8](卷8《太宗文烈皇帝五》,127)其后,“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術。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術不得濟,遣使致詞,愿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重。又獲兀術之婿封龍虎大王者舟千余艘。兀術懼不得濟,復遣使致詞,愿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兀術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兀術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為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為趙立所敗”,以至“兀術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州,遣人誚兀術南征無功,可止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術皇恐,推避不肯從之”。[8](卷6,55-56)撻懶的遭遇亦復如此,紹興元年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與南宋張榮相遇于縮頭湖,在張榮的攻擊下,金師“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獲其婿盆輦,撻懶率余兵奔還楚州,遂退師”。“時新為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眾北歸”[8](卷7,《太宗文烈皇帝五》,63-64)……金人一舉滅宋的企圖難以實現,故開始改變對于南宋勢不兩立、一意滅之的態度,于紹興二年八月遣歸扣留已達五年的南宋使臣王倫: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后,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輩皆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在云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貽上書,略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于吝愛,使不成國。”于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偽閤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1](2冊,卷57,紹興二年八月癸卯條,995)
對金人所釋放的和議的信號,南宋朝廷立即予以回應。紹興二年九月,南宋即“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為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為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且附香藥果茗縑帛金銀,進兩宮二后,上皇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圣減三之一,寧德、宣和二后又減半。又遺左副元帥宗維金二百兩、銀千兩,遺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半之,遺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匹,而通問副使朱弁已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1](2冊,卷58,紹興二年九月壬戌條,1004)此后,金人與南宋雙方既互派使者,又戰事不斷,所謂“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1](3冊,卷123,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亥條引秘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秦檜所言,2001)紹興四年十二月,南宋朝廷成功挫敗了偽齊與金的聯兵入犯,這次關鍵性戰事的勝利,扭轉了南宋與偽齊、金對抗中所處的絕對劣勢地位,南宋朝廷也由此擺脫了奔避流亡的命運,金人因此而對偽齊劉豫的作用重新審視,加之其內部矛盾,終于在紹興七年十一月廢掉偽齊,這就使南宋在真正意義上具備了與金對峙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紹興五年南宋朝廷的問策于群臣,以調整新的對敵政策是極為重要的大事件。
其次,從金朝內部的矛盾斗爭來看,南宋朝廷有機可恃,有釁可待。這也使得南宋朝廷有可能暫緩與金人的緊張關系,而得以集中力量解決偽齊的問題。
金人于天會五年(靖康二年)三月七日,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其《冊大楚皇帝文》云:“以璽紱冊命爾為皇帝,以理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5](第163篇,435)然張邦昌于金師北還后,即“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賚書于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但還政趙構后,趙構旋即將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即賜死潭州。[9](卷475,《張邦昌傳》,13793)張邦昌的死并未改變金人的滅宋之心,天會五年(即南宋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金人發布《伐康王曉告諸路文字》,再次重申不承認趙構建立的南宋政權:“趙構雖系亡宋之余,是亦匹夫,非眾人共迷,無由自立。”“如張氏已遭鴆毒,則別擇賢人,使斯民有主。”[5](第187篇,494-495)在金人絕對敵視趙宋的前提下,劉豫于建炎四年由金人冊封為皇帝,建立了偽齊政權。但是,圍繞著扶立劉豫偽齊政權,金朝內部的矛盾也逐漸表面化且愈發激烈,而這也為南宋朝廷的恃機待釁創造了條件。
建炎初年,金人一意滅宋,宗翰、宗望、撻懶、宗弼皆為伐宋之主力,而達懶則與劉豫的關系最為“密切”:“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時為知濟南府的劉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沖要,以鎮撫之。”[4](卷77,《劉豫傳》,1759)可以說,達懶與劉豫隱然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主從關系,所以,在選任偽政權繼任代理人時,達懶力薦劉豫:
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達懶力舉劉豫。[4](卷77,《撻懶傳》,1764)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引張匯《金虜節要》云:“金人之陷山東,多達懶之力也。達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基于這樣的背景,撻懶于公于私都愿意由自己來扶持劉豫,所以,及至南宋高宗“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指偽政權代理人)。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為豫求封”[4](卷77,《劉豫傳》,1760)。然而,撻懶意欲由自己推劉豫為帝,以收恩于己的圖謀卻被權臣宗翰先一步搶奪而去,這就直接影響了劉豫日后判別與金中權貴遠近親疏的標準與態度,也加劇了金重臣宗翰與撻懶的矛盾。對此,《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十二之建炎四年三月條記載甚詳:
初,敵陷山東,左監軍完顏昌(即撻懶)密有許封劉豫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既而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三穗同本,其黨指言以為豫受命之符,乃使豫子偽知濟南府麟賚重寶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維心腹也,恐為昌所先,乃說宗維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后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盍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宗維乃令希尹馳白金主晟,晟許之。宗維遂遣慶裔自河陽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官吏軍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皆莫敢言,曰:“愿聽所舉。”慶裔徐露意以屬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進士張浹等遂共舉之。慶裔至德、博、大名,一如景州之故。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愿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推戴之意,宗維許之。(1冊,628)
建炎四年秋七月丁卯冊封劉豫為偽帝,就是由宗翰的心腹高慶裔親自參與的:“金主晟遣西京留守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仆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高慶裔,金紫崇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韓昉,冊命中奉大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1](1冊,卷35,建炎四年秋七月丁卯條,680)宗翰既然搶先扶立了劉豫,劉豫自然投桃報李,“豫之立也,高慶裔推之,粘罕(即宗翰)主之,虜主吳乞買(金太宗完顏晟)從之。豫知恩悉出三人,又三人虜之最用事者,豫每歲厚有饋獻,蔑視其他酋長。”[10](卷182,引張匯《金虜節要》)至于先前曾經“密有許封劉豫之意”的達懶,劉豫則不再俯首,當達懶“自宿遷北歸,路由東北,劉豫不之出迎,更遣人議于達懶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禮,”。達懶“怒責之”,“大憾而去”[10](卷182引張匯《金虜節要》)。劉豫固然勢利小人,然撻懶之恨亦未嘗不由此而及彼,“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于金太宗晟,以為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1](3冊,卷105,紹興六年九月庚寅條,1711)由于宗翰一意庇護劉豫,撻懶與宗翰的矛盾也因之愈發深刻:“左監軍達蘭(達懶)請尼雅滿(宗翰),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贍,而東路無之,乞割齊境滄州鹽場以贍其用。蓋達蘭怒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尼雅滿方專權庇豫,故不之許。然達蘭自此憾豫愈深矣。”[7](卷11)
如果說,圍繞著扶立劉豫的事件所引發的金上層矛盾,其涉及面尚且有限的話,那么,當金太宗完顏晟去世,以大金國繼承人為矛盾焦點所展開的權臣斗爭則更加尖銳和激烈,其涉及面也更加廣泛。
金太宗時,“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4](卷3《太宗》,66)紹興五年正月,金太宗完顏晟卒,圍繞著皇位繼承人,金廷重臣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其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
初,太宗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即完顏亶)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喇(即完顏亶)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于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于是,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4](卷74,《宗翰傳》,1699)
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杲既薨,太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諳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喇,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于太宗者再三,乃從之……(三月)甲午,以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十一月,以尚書令宋國王宗磐為太師……己卯,以元帥左監軍完顏希尹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慶裔為左丞,平陽尹蕭慶為右丞。[4](卷4《熙宗傳》,70)
初,(金)太祖昱有約,兄終弟及,復歸其子。及晟病,其長子宗磐自以人主之元子,欲為儲嗣。昱之子宗幹言己乃武元長子,當立。宗維言己于兄弟,年長功高,當繼其位。晟不能決者累日。宗室完顏勖者,受師于本廟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粗通文藝,奏曰:“臣請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卻令太祖子孫為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果早卒,有孫稱阿木班貝勒,以為儲嗣,今年十有五矣。”宗維乃止。監軍希尹利其幼弱易制。宗幹,亶伯父,且妻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洪皓《松漠記聞》:“長子宗磐與固倫尼瑪哈爭立,尼瑪哈以今主為嫡,遂立之)……封左副元帥宗維為晉國王,皇伯宗幹為秦國王,宗磐為宋國王,皆領二省事。封右監軍希尹為陳王,除尚書右丞相。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山南西路兵馬都部署高慶裔為尚書左丞,河南東路兵馬都部署蕭慶為尚書右丞。宗維、希尹既罷兵,亶以慶裔與慶本二人腹心,故解其外任。又封右副元帥宗輔為冀王,遷左副元帥。右監軍宗昌為魯王,遷右副元帥。右監軍宗弼為沈王,遷左監軍。陜西經略使薩里干為右監軍。[1](卷84,紹興五年正月癸酉條,1387-1389)
“諳班勃極烈杲既薨,太宗意久未決”,這就給宗磐、宗幹、宗翰等懷有稱帝野心的權臣留下了爭斗的空間:“(太宗)長子宗磐自以人主之元子,欲為儲嗣。昱之子宗幹言己乃武元長子,當立。宗維言己于兄弟,年長功高,當繼其位。”對此,太宗亦難以定奪。本來“太宗亦無立熙宗意”,但一是有太祖的約定:“元謀弟兄輪足,卻令太祖子孫為君”,那么“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果早卒,有孫稱阿木班貝勒,以為儲嗣”,也就成了尊奉祖宗遺命的選擇;二是完顏亶“今年十有五矣”,尚且年少,“監軍希尹利其幼弱易制。宗幹,亶伯父,且妻其母,如己子也”。在各方權衡自己的利益之后,完顏亶便成了各方勢力達成平衡的最佳人選,“遂共贊成其事”。這才有了“‘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于太宗,請之再三”的事實。而太宗雖本無立熙宗意,但無奈“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故當諸人“相與請于太宗者再三,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從此種下了朝廷重臣相互敵視斗爭的惡果。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十四,紹興七年九月末所引《金中雜書》記載:“邁烏奇(即太宗完顏晟)幼年曾出繼達賚之父,故與達賚(即達懶)情好親厚。達賚深欲宋王(即宗磐)之立,而尼瑪哈(即宗翰)廢之,故達賚與宋王共惡尼瑪哈,常有身滅數國之語。”[1](1854)又《大金國志》卷之九《熙宗孝成皇帝一》載:熙宗即位后,“封太宗長子宗磐為宋國王、領三省事……故宗磐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畔,蓋始于此也。”[8](79)
金廷權臣的激烈斗爭一方面削弱了其內部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必然影響到對外策略的制定,這就為南宋朝廷爭取主動,重新權衡對金與對偽齊的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也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才有“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這一方略的提出。
三、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
就南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高宗對金的深恨,所謂“二圣久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為人子弟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1](卷95,紹興五年十一月癸巳,1576)“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猶在,朕敢忘此憂乎”[1](卷84,紹興五年正月壬戍,1380);另一方面,“劉豫介然處于其(南宋與金)中,勢不兩立,必求援于金”[1](2冊,卷74,紹興四年三月丁卯條,1227),“劉豫之害大于金人”[1](卷95,紹興五年十一月辛未條引劉長源之語,1568)。劉豫自稱帝偽齊,就積極與金人相應援,與南宋朝廷對抗到底,“偽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鄧、郢州,又遣重兵歸川口”[1](2冊,卷75,紹興四年四月丙午條,1244),對南宋朝廷的安全形成了極大的威脅。建炎四年十月,南宋“直秘閣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馮長寧以王命阻絕,棄城去。是月,以淮寧附于劉豫”。[1](1冊,卷38,建炎四年冬十月己亥條,729)紹興元年,“(李)成北走降劉豫”[9](卷369,張俊傳,11472-11473),“(李)忠奔歸劉豫”[9](卷26,《高宗三》,491),紹興二年,“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9](卷475,劉豫傳,13795-13796)。紹興三年,“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余人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9](卷475,劉豫傳,13797)紹興四年,“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偽齊”,[1](2冊,卷72,紹興四年正月,1208)“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9](卷475,劉豫傳,13798)可以說,金人于南宋固然有亡國擄帝之恨,但在當時,南宋尚無力量兩手出擊,同時解決金與偽齊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權衡二敵的實際情況,把打擊重點放在偽齊一方,應當說是更符合當時南宋的實際狀況。因為金人“上下猜防,人心攜貳,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矣”。[1](2冊,卷87,紹興五年三月癸夘條引韓肖胄言,1462)且金人與偽齊相較,“金人其來有時,其居不久,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也明矣。且如劉豫以臣竊國,因敵僭君,素無人望,唯多詐謀……今劉豫恃金人之勢,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與我圣宋必不兩立,勢無俱存。彼若以利害痛誘金人進屯淮右,雖不交兵,縱未南渡,無所不修,無所不寡,兩軍相持,積之歲月,必有存亡,將何所逃?臣以謂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11](卷87,《經國》引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伸所言)
正是出于中原未復、二圣未歸的大背景,鑒于金與偽齊各自的實際狀況及其對于南宋的現實威脅,時任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的秦檜提出了“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的對敵之策:
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畫。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為強,亦不必以力弱為怯……今者逆賊劉豫陰導金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釁。今賊豫知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況今勢有未便。臣前奏乞安慰強敵,當用所獲金人,令諸將通其大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為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眾,益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因所獲金人,厚存拊之,彼各識所屬大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為措置之方,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意不得已也,使豫眾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為綏懷之略。[1](2冊,卷87,紹興五年三月癸卯條,1455-1456)
秦檜以“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為強,亦不必以力弱為怯”作為立論的基點,主張當此“勢有未便”之際,對金國則當以“虛張之無益”的態度處之:“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意不得已”,以便分割金與偽齊,破壞其聯合,削弱其對南宋的壓力;對于偽齊劉豫,則“討叛之不必太怯”,“當檄數其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眾”。這一主張的具體實施便是將南宋的軍事打擊目標定位到偽齊,對于金人則采取姑以和議待之的方略。對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在其條上的戰陣守備措置綏懷各五事中,即已明確提及:
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圣在彼,不可遂已。姑以余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1](2冊,卷87,紹興五年三月癸卯條,1460)
李邴此議一方面分析金人自靖康以來的作為,所謂“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1](卷123,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亥條,2001),明言與金之議和“決不可恃”。另一方面又從二帝安危出發,根據當時宋金對峙的實際情況,提出和議“不可遂已。姑以余力行之”的策謀,也就是說,以和議暫時應對金人,以便贏得時間,“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正如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所言:“和議乃權時之宜,以濟艱難。他日國歩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1](2冊,卷66,紹興三年六月丁亥條,1112)應當說,這一建言是務實的,因為南宋朝廷雖然新近取得了擊退金與偽齊的勝利,但尚未具備一舉擊垮金人的實力。紹興四年十二月金人的退師固然有“蕃漢軍皆怨憤”的重要因素,但更與其朝廷內部的上層激烈的爭權斗爭密切相關:
時金師既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簽軍又為飛書擲于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輩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斗志,過江不叛者獨常爾,他未可保也。況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1](2冊,卷83,紹興四年十二月庚子條,1370)
“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是宗弼退師的重要原因,而偽齊的退師則是在得知金兵北去的消息之后:“金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猊。于是麟等棄輜重遁去。”[1](2冊,卷83,紹興四年十二月庚子條,1370)可見,南宋取得的這次決定性勝利不能排除金人一方內部矛盾尖銳激烈的原因。正在基于諸多因素的分析,南宋大舉出擊金人的時機并未成熟,事實上,南宋與金的聯系也并未自此而中斷。所以,呂頤浩于紹興五年五月所奏《上邊事善后十策·論用兵之策》云:
仰惟陛下天性圣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已,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厄,以救生民之命。而敵性貪婪,吞噬不巳,自王倫之回,迄四年矣,歲歲舉兵侵掠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金人巳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箭于國中,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吾賦斂,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圣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2](141冊,卷3043,《忠穆集》卷2,248)
呂頤浩首先分析“敵性貪婪,呑噬不巳”,“歲歲舉兵”,“其志豈小”的實際情況,認為南宋一方的“卑辭屈已,祈請講和”,不可能產生實際效果,所以用兵在所難免,因為“不用兵,則二圣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但是權衡當時南宋朝廷各方面的實力,棄和言戰尚待時日。所以呂頤浩提出了“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的主張,即以和應之,以戰為最終目的,所謂“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值得注意的是,呂頤浩所論北伐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表面上仍然維持“間遣使命”,實際上則“我急為備”。實際上這也是南宋朝臣此期較為重要的一種意見。紹興五年五月,“忠訓郎閤門祗侯何蘚特遷修武郎,赴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圣”[1](2冊,卷89,紹興五年五月辛巳條,1482),就是出于尚書右仆射張浚以“使事兵家機權”為由的奏請:“尚書右仆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胡寅反對與金交通)說,乃遣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蘚偕行。”[1](2冊,卷95,紹興五年十一月戊子條,1574)
當然,南宋朝臣中亦不乏以胡寅為代表的堅決反對和議、一意主戰者。胡寅《斐然集》卷十一中現存有《論遣使劄子》、《再論遣使劄子》,就是直接針對何蘚出使而作:“適睹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系不細,遂具陳奏。”胡寅明白表示了與張浚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2](189冊,卷4162,《再論遣使劄子》,165)“張浚以遣使為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強為之說。”[2](189冊,168)“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2](189冊,165)胡寅以孔子《春秋》的“父子君臣之義”為依據,以魯莊公“釋怨通和”之罪為事例,堅決反對用講和之人,修講和之事:
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于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弒械成于前,慶父無君動于后。卜齮圉人犖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線。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為后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仇也……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2](189冊,162-163)
胡寅將魯莊公釋怨通和之罪和南宋朝廷與金人議和相類比,直斥講和乃“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是“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他要求朝廷“據孔子之論”,“考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2](189冊,164)這里所說的當今之事,便是“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2](189冊,167):
當今之事莫大于夷狄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仇,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女真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后二圣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茍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于仇敵,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2](189冊,164)
胡寅反復強調宋與金的“不共戴天之仇”,認為“欲紓此怨,必殄此仇”。他以《春秋》大義為依歸,堅持“世仇當復,無可通之義”[2](189冊,164),“今以虜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于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2](189冊,167)至于使者北行的行為,胡寅更是直斥其為“謬計”,且以“義”“利”二字判定絕交或通和引發的君臣利害之別:
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舉若通和,則利歸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愿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2](189冊,164)
胡寅認定“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又以昔日富弼出使將口舌之功視為恥辱的事例,對比并判定今日“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
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敵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后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萬一虜人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2](189冊,166)
胡寅援古論今,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出使金國的行為:“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凌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仆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我之弱,增彼之強而已。”[2](189冊,166)
就胡寅所主張的專意復仇來看,確實可以起到從精神上極大鼓舞人們斗志的作用,但從南宋朝廷當時的國力來看,確有實際的困難,且從南宋的實際行為來看,胡寅這一“伸眉吐氣”之策也并未因其激憤而付諸實施。雖然朝廷獎諭了胡寅《論遣使劄子》的“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1](2冊,卷89,紹興五年五月丙戍條,1487),但并未采納其主張,當“尚書右仆射張浚自江上還”,“不用其說,乃遣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蘚偕行”。[1](2冊,卷95,紹興五年十一月戊子條,1574)張浚的遣使主張得以實施,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南宋朝廷的對金態度。針對于此,胡寅又奏上《再論遣使劄子》,言遣使無益者十,且云:“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2](189冊,卷4162,《再論遣使劄子》,168)又因“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侍迎,乞守湖南小郡。”[1](2冊,卷95,紹興五年十一月戊子條,1575)但朝廷也并未因此而改變遣使之行,或阻止胡寅乞守小郡的請求,所以胡寅最后終是知邵州。[1](2冊,卷95,紹興五年十一月戊子條,1575)如果把朝廷對于張浚遣使主張的支持與對胡寅請求小郡的同意聯系起來,在這樣的取舍態度背后已經可以清晰地見出南宋朝廷對金的態度。
以上探討了南宋朝廷在卻退偽齊與金人聯兵入侵之后,朝臣們以漸圖恢復為大前提所提出的善后之計。從南宋朝廷日后所實施的政治軍事策略來看,這一時期提出的乘釁待時、和戰相間的方針無疑具有其可行性。
[1]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中華書局,1988.
[2]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Z].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 靖康要錄[M].四庫全書本.
[4] 金史[M].中華書局,1975.
[5] 佚名編,金少英校補,李慶善整理.大金吊伐錄校補[M].中華書局,2001.
[6]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M].中華書局,2000.
[7] 熊克.中興小紀[M].四庫全書本.
[8] 宇文懋昭撰,李西寧點校.大金國志[M].齊魯書社,2000.
[9] 宋史[M].中華書局,1985.
[1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四庫全書本.
[11] 楊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Z].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