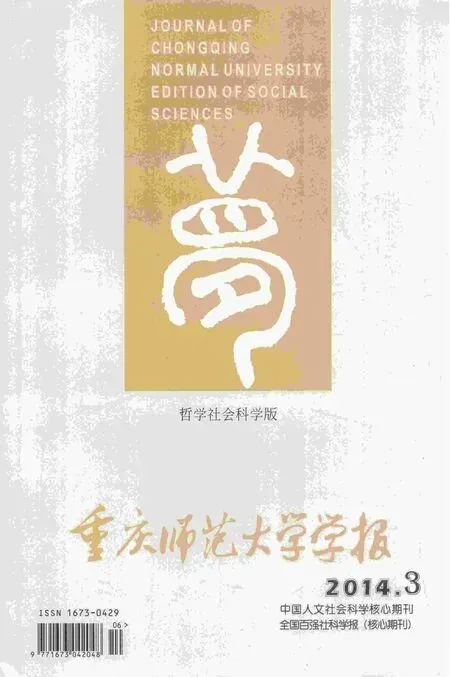哈奇森、休謨、邊沁與哲學功利主義的興起
汶紅濤
(長安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陜西 西安710064)
在近代功利主義的興起和形成中,古希臘的快樂主義、近代洛克的新經驗主義認識論以及英國情感主義道德理論都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尤其是英國情感主義道德哲學將情感作為道德之基礎的思想,為功利主義從功利性角度解釋道德行為與道德現象提供了理論模式。但在這一過程中,休謨作為一個關鍵的過渡性角色,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們所忽略。尤其是從哈奇森到邊沁完備的功利主義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的諸多延續和脈絡,休謨從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因此,對這一過渡性意義的探討是極為必要的。
一、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論
哈奇森作為蘇格蘭啟蒙哲學的開創者,第一個在道德基礎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原創性理論。“道德感”理論是哈奇森哲學的核心理論。“道德感”一詞在蘇格蘭啟蒙哲學語境中譯為“moral sense”,意在強調道德感是一種感覺器官。但這一概念并不是哈奇森首創,而是由莎夫茨伯利于1709年提出。哈奇森這一理論的確立,有兩方面的來源:一是近代洛克的經驗論,二是莎夫茨伯利的道德理論。根據洛克的經驗主義認識論,人類的觀念主要來自對外界事物的感知所獲得的感覺以及人對自身心靈的反思。哈奇森承認洛克的觀點,認為一切觀念都來自感覺與反思,但他認為,我們的每一種簡單觀念都對應著一種感覺器官,除了外部感官之外,還有“內部感官”如“道德感、美感等,而這與我們對洛克所謂的第二性的質的感知十分相似。哈奇森確信這些內部感覺和外部感覺并無二致。因此,在他那里,道德感就是一種與外在感官相對應的內在感官,是人類心靈具有的天然的知覺能力。這樣,哈奇森在人性的生理機能上為道德感找到了合法性依據。
與霍布斯認為“人從根本上是自私的和反社會的”的觀點不同,莎夫茨伯利認為人類有著豐富的情感,這些情感使人類成為天生的群居動物。關于自然情感和道德之間關系問題是莎夫茨伯利道德理論的特色所在。莎夫茨伯利認為,人天生具有趨善避惡的能力。[1](129)人具有一種能感悟道德善惡的內在感官——道德感。人的這種內在道德感如同人的眼睛和耳朵等外部感官對美丑的直接分辨一樣,也能直接感覺出行為善惡的性質。因此,人們對道德善惡的感知不是憑借理性的推理,也不是經驗歸納的結果,而是人的內在感官的直接感悟。但莎夫茨伯利沒有詳細論證道德感究竟是如何分辨善惡的。情感與理性也常常交織在一起,沒有清晰的界定。換言之,莎夫茨伯利并未明確表示道德的基礎究竟是理性還是情感。哈奇森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莎夫茨伯利的觀點。首先,他承認我們對道德善惡的知覺來源于人的道德感。但他認為道德感與外部感官不同,外部感官的職能是感知外物對自己有利或有害,而內在的道德感知覺到的是道德上的善與惡。道德感的本性是見德則愛之,見惡則恨之。從哈奇森對洛克與莎夫茨伯利的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可以確定:第一,道德感是一種判定善惡的內在感覺器官;第二,道德的基礎究竟在于理性還是情感,莎夫茨伯利并未明示,而哈奇森則明確表示,道德感是道德判定的基礎。
那么,道德感究竟具有什么樣的特點?如何進行道德判斷呢?哈奇森強調說:“所謂道德感,只不過是我們心靈在觀察行為時,在我們判斷該行為對我們自己為得為失之前,先具有的一種對行為采取可愛與不可愛意見的作用。”[2](790)既然道德善惡的判定不是依賴于利益考量,那么,如何才能權衡德行,進行道德判定呢?哈奇森認為是“仁愛”。“仁愛”是哈奇森道德哲學中最核心的概念。哈奇森認為,仁愛是一種“本能”,它“先于理性而始于利益”[1](123),但又弱于利己。仁愛普遍存在于激勵人們的各種情感或激情中,驅使我們發現自然之善,并為他人謀取幸福。哈奇森道德哲學的基本觀點是:仁愛是所有德性的基礎。也就是說,在道德評判上,只有完全排除利益考量而出于仁慈動機的行為才是德行。一切有道德價值的行為都應當是出于仁愛的情感,“凡一切被認為出于這樣的感情,對某些人為仁愛,同時又不危害他人,這種行為,在道德上便是善的。”[2](801)因此,在哈奇森的道德哲學中,仁愛是道德感的對象,它不是利己的附屬品,“倘若某種行為可以揭示施動者的善意或仁愛,即為他人謀幸福之愿望,則當這種行為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觀念時,與這些觀念相連的快樂之感便能呈現德行的觀念”。[1](130)以仁愛作為道德感的對象,權衡行為善惡,必然排除理性在感知善惡或判定某種行為是否德行中具有決定權的可能。但哈奇森并不排除理性可以修正我們的道德感和外部感覺,理性在道德評判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不能讓我們感知到善惡。
從哈奇森的論述可以明顯地看出,道德善惡的判斷是一種純粹情感的活動,是一種與自愛、理性無關的情感感知活動,因此,道德感理論實質上是一種以情感為核心的感情主義倫理學。哈奇森不僅確定了道德感是道德判定的基礎,而且進一步明確了道德感的涵義和特點,即道德感是一種以仁愛為對象的情感,這種以仁愛為對象的道德感是道德判斷和道德區分的依據和基礎。相較于莎夫茨伯利,哈奇森第一次明確地將“情感”作為道德判定的基礎,提出并確立了“情感高于理性”的信念,以及情感在人性構成中的基礎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在道德判定中具有決定權的觀點。因此,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論開啟了理性主義道德理論向情感主義道德理論的轉向,同時,為后來更為體系化、明確化的休謨的情感主義道德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休謨的“效用”概念:向功利主義的過渡
休謨贊同并接受了哈奇森關于“道德感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觀點,同樣認為道德感是一種情感,是行為者的行為或品格在我們心中引起的快樂與不快樂的情感,道德評判就是以此為依據。但是,在確定了道德判斷的基礎是情感之后,休謨便與哈奇森分道揚鑣了。
《人性論》第三卷“道德學”(of morals)是休謨第一次系統論述其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部分。在第一章“德與惡總論”中,休謨明確地探討了道德的基礎和區分問題。首先,休謨回應和批判了道德理性論者將理性作為道德基礎的觀點,同時界定了理性的適用范圍、功能及其界限。在“道德學”的第二節中,休謨從正面強調了道德區分的情感基礎:“由德發生的印象是令人愉快的,而由惡發生的印象是令人不快的”[3](510),而這些區別道德善惡的印象,“只是一些特殊的痛苦或快樂(particular pains or pleasures)”[3](498),即特殊的苦樂感。所以,區分道德善惡的機制在于人類的情感,休謨將這一區分道德善惡的情感機制稱為“道德感”。在《道德原則研究》中,休謨提出了四種道德評價的標準:對自己有用;對他人有用;令自己愉快;令他人愉快。概括起來,一種是快樂或痛苦的情感,一種是帶來利益和有用性的傾向,而“有用性是令人愉快的,博得我們的贊許”[4](69),因而,不論是對自己或他人有用還是給自己或他人帶來快樂,都可以引起我們情感上的快樂,并以此對人的行為和品格做出道德評判。
需要強調的是,效用性之所以作為德性評判的標準,并不是因為“效用”本身,而是因為“效用”引起了愉悅的情感,從而給予德的評價。“有用性”作為德性的評判標準,在休謨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中,并不是引起道德贊許的直接原因。“有用性”引起了我們愉悅和贊許的情感,而這一“道德感”才是引起道德贊許的直接原因。那些對社會有用的品質之所以得到贊許,是因為它促進了公共利益。通過同情,我們感受到了因對公共利益的關切而帶來的愉悅感。人們贊許僅對自己有用的品質,是因為它對品質擁有者有用。通過同情,我們感受到了因對他人利益的關切而帶來的愉悅感。因而,不論是對社會有用還是對自己有用,都是因其“效用性”而帶來贊許的情感,因而成為一種德行。
因為同情,我們會關切“效用性”給社會帶來的公共利益;因為同情,我們也會關切“效用性”給他人帶來的個人利益,不論是公共利益還是個人利益,都會引起我們情感上的愉悅和贊許。這種愉悅和贊許的情感是道德評判的直接基礎和依據。
在道德哲學的基礎上,休謨提出了他的正義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正義“乃是由于應付人類的環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為措施或設計”[3](517),即正義是為了應對人性與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實際狀況而采取的一種人為的補救措施和設計。它是出于人類的“需要”和“利益”而產生的。正義的規則和制度對于我們而言是“有用的”,它的“有用性”就在于保障和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對公共利益的同情,是引起我們對正義的道德認同的根本原因。因為,政治社會的成員們基于對公共利益的同情產生了“正義感”。他們感覺到,凡是遵守正義規則的行為就能維護公共利益,凡是違犯和破壞正義規則的行為則會損害公共利益。對公共利益的維護或損害,直接引起人們的快或不快的感受,也即正義感或不正義感。在這一感覺之上,我們對之給予道德或不道德的評判。正義的規則和制度在這種意義上是“有用的”,即它們是作為滿足某一目的的手段,而這一目的就是公共利益。因此,正義是一種人為美德,其實際含義在于,遵守正義規則的行為和品格是一種德行,違反正義規則的行為和品格則是不道德的。
從休謨的道德哲學看來,他和哈奇森一樣,確定道德判斷的基礎在于情感,并提出了和哈奇森相似的概念“道德感”(當然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自此,休謨便與哈奇森分道揚鑣了。第一,休謨認同哈奇森關于出于仁慈動機的行為屬于德行的觀點,但不贊成哈奇森將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排除出道德判定范圍。在休謨看來,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同樣具有道德價值,只要行為者的行為或品格能在我們心中引起快與不快的情感,不論是出于仁慈還是自利,都具有道德價值。在關于“正義作為一種人為德性”中,正義規則的建立以及對正義規則的遵守,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維護,而公共利益是同情感原則聯系起來的個體自利的共識。維護或損害公共利益實際上是維護或損害了自我利益。遵守正義的行為被視為一種德行,破壞正義規則的行為被視為一種惡行。因而,利己是遵守正義之規這一自然義務的基礎,自利動機引發的行為當然具有道德價值。第二,哈奇森認為是上帝賦予了人道德辨認的能力,它是道德感的來源和最終依據,而休謨斷然否定了這一觀點。休謨認為道德感是一種苦樂情感,情感作為反省印象或次生印象,源于人心靈中接受到的經驗知覺,并沒有什么神秘的東西賦予我們情感感受的能力和確保道德辨認的能力。他摒除哈奇森關于道德感源自上帝的思想,也是他與哈奇森的一大區別。
總之,在休謨那里,“有用性”或“效用性”是一種作為手段的效用觀念,休謨對“效用”概念的手段性使用,將“效用”作為一條重要的道德評價的準則,以及從人類的“需要”或“利益”這一歷史經驗的角度出發解釋以正義規則為核心的政治社會的起源,將政治社會視為人類基于“需要”或“利益”而在歷史經驗生活中逐漸人為建構的產物,為后來的功利主義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和理論框架。休謨作為一個關鍵的過渡性人物,在近代功利主義的興起過程中,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三、從休謨到邊沁:哲學功利主義的興起
作為道德哲學中的重要概念,“功利”與“功利主義”的完整觀念是在近代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那里形成的。邊沁并非“功利”一詞的首創者,他對功利概念的發展以及功利原則的提出,不可否認的得自于休謨效用概念的啟發。邊沁就是在讀了休謨的《人性論》和《道德原則研究》之后,明確地把效用歸結為功利。在《政府片論》第一章第三十六節中,邊沁做了一個較為詳盡的注釋,明確地表達了休謨對他“一切善德的基礎蘊藏在功利之中”這一觀點的形成所產生的重要影響。邊沁說:“當我讀了這本著作中有關這個題目(指一切善德的基礎蘊藏在功利之中——譯者)的部分,頓時感到眼睛被擦亮了。從哪個時候起,我第一次學會了把人類的事業叫做善德的事業”。[5](149)對于功利主義原則,邊沁說:“任何行動中導向幸福的趨向性我們稱之為功利;而其中的背離的傾向則稱之為禍害。”[5](115)邊沁將此功利原則定義為:我們對任何一種行為表示贊成或不贊成(或道德判定)取決于這種行為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我們的幸福。因此,功利原則所涉及的內涵,一是個人的利益(個人自身行為的目的是追求快樂和幸福),一是社會的利益、集體的利益,即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僅是判斷個人行為的道德標準,而且是判斷政府一切行政和立法行為的道德標準。邊沁之后,密爾進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功利主義學說。但不論是邊沁還是密爾,他們在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功利”是一切行為道德判定的準則,也是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
那么,功利主義者是如何繼承和發展休謨的“效用性”概念的呢?功利主義者的功利原則和休謨的效用觀念又存在怎樣的區別?在休謨看來,人是一個利益主體,我們對一切行為與品質的道德判斷,都基于利益主體的苦樂感受。“效用性”(Utility)是道德判斷的基礎,也是解釋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我們對社會中人們的個體行為和品質以及政治行為和品質的道德評判,都不能離開其“有用性”,對個體行為和品質的評判依賴于其行為和品質引起的愉悅感,對政治行為和品質的評判依賴于其給公共利益帶來的有用性,有用性引起愉悅性。但是,休謨并不認為追求“效用”或“功利”就是人們的唯一目的,是否符合功利就是判定人類行為正當與否的唯一價值原則。前文已做分析,效用并不是德性判定的唯一基礎,也不直接成為德性判定的基礎,而是因促進公共利益從而引起愉悅感才發生道德認同。因此,效用在休謨這里是達至公共利益的手段,而對公共利益的關切所引起的情感才是德性評判的直接基礎。由此看來,休謨并沒有把效用作為道德評判的唯一價值原則,更沒有將其作為一種規范性原則,而只是說,一些行為和品質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有總比沒有好。也就是說,有用性或功利性在休謨這里,并不是一種規范性的原則。
事實上,作為規范性原則的功利主義是邊沁第一個提出來的,是他發明了哲學上的功利主義。相比于休謨對效用性的解釋和運用,邊沁走得更遠。邊沁認為,休謨把人視為一個利益主體的同時也承認了人有其慷慨和仁愛的一面,那么利益就不是一種完全確定且具有規范性的原則,作為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基礎的人性必須具有堅固的原則。所以,邊沁認為,功利是人的基本天性,人總是趨樂避苦的,這是一個無需證明的事實,它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學辯護和先驗神學論證,它是清楚的、無可爭議的。“趨樂避苦”是人一切行為的根本動機和最終目的,也是道德評判的唯一基礎和根據,快樂與痛苦是倫理原則的根本準則。在邊沁看來,我們衡量一種行為和偏好的準則在于其“功利”,即快樂與痛苦,凡是符合或增進最大快樂的行為就是善的行為,不符合或阻礙快樂的行為就是惡的行為,這便是邊沁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論是邊沁還是密爾,在對功利主義的解釋和運用中,都不僅將“功利”視為人的本性,視為衡量一切人類行為的道德基礎,而且也將其作為人類行為的應然目的。密爾說:“我們最后目的乃是一種盡量免掉痛苦,盡量在質和量兩方面多多享樂的生活,照功用主義的看法,這種生活既然是人類行為的目的,必定也是道德標準。”[6](12-13)他們都從人總是趨樂避苦的事實認定中推斷出人應該追求功利,追求功利是正當的這一價值判斷。“關于‘目的’的問題,換言之,就是關于什么事物是可欲的(或可追求的)問題,功利主義的理論,認為幸福是可欲的,是惟一作為目的而可欲求。一切其他的事物,只是作為致此目的的手段而可欲求任何東西之為可欲的,其唯一可能的證據,就是人們實際欲求它”。[2](263)很明顯,邊沁和密爾等功利主義者相比休謨對“效用”或“功利”的運用和解釋,走得更遠。在這里,“功利”不僅是一切道德判定的基礎,也是人類行為的應然目的。
作為功利主義主要代表的密爾,在其政治哲學中,對政治權力或政府、國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功利性”解釋,不僅展現了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基本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也呈現了這一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的休謨淵源。政治問題以及對政治的評價總是以對人的理解為基礎,也總是與人們的道德判斷息息相關,因而任何一種政治哲學都必然以某種形式的倫理學為基礎,“那些想把政治與道德分開論述的人,于兩者中的任何一種,都將一無所獲”[7](7)。密爾的政治哲學當然也是以其倫理學為基礎的,并在功利主義的基礎和原則之上解釋人類政治生活和政治現象的。在密爾看來,我們應當從人類的實際利益、需要和經驗習慣出發來尋找人類政治社會的根本性原則,解釋人類政治生活和政治現象。政治社會或政府、國家并不是以契約理性的方式建構起來的,而是人類的實際需要和經驗習慣的產物,是人類利益訴求的產物。政治社會中人們對權威的服從,也并非契約論者所說的是基于自己許諾的義務,而是取決于人們的好惡與功利(或利益)需求。也就是說,在密爾看來,政治社會的基礎和來源并非任何形式的先天原則,而是“功利”,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此基礎上,政治社會才具有其合法性和正當性。從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出發,密爾反對契約論者以“權利”作為解釋政治社會的產生與合法性的基礎。他說道:“凡是可以從抽象權利的概念(作為脫離功利而獨立的一個東西)引申出來而有利于我的論據的各點,我都一概棄置未用。”[8](11)他認為,政治社會不能從抽象的權利中推導出來,只能來自于人類的“利益”或“功利”需要,對人類政治社會及其制度框架的解釋和評價只能建立在人類的功利基礎之上。簡言之,政治社會及其制度框架是人類利益和需要的產物。對于人類而言,其合理性在于它是作為滿足人類利益需要的一種手段,這一手段的意義在于,它符合增進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在此意義上,可以看出,“利益”或“功利”不僅是政治社會及其制度框架產生的基礎和目的,也是檢驗政治社會及其制度框架好壞的準則。密爾對政治社會的“功利性”解釋,展現了19世紀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近代契約論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事實上,19世紀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已不滿足于近代契約論以自然法學說、契約論以及理性主義的方式解釋和建構政治社會及其制度框架的思想了。以密爾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家從經驗與事實出發,強調從政治領域以外的經驗世界尋找政治原則的基礎與政治價值的依據,它的實質就是“把經驗論與價值論結合起來,由經驗的內容來規定價值標準”[9]。因而,“利益”或“功利”就成為了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思考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不容忽視的是,休謨作為近代契約論向功利主義轉向中的過渡人物,為功利主義提供了直接性的理論淵源和理論框架,是休謨促成了哲學功利主義的興起與形成。
但是,如前所述,在對“效用”或“功利”概念的使用上,尤其是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家們以“功利”作為道德的基礎、評判準則以及人類的應然目的,則遠遠超出了休謨對“效用”的手段性運用,而發展出一種具有規范性原則的目的—效用理論。邊沁對功利的解釋和密爾在政治哲學中對“功利”原則的運用,在理論上造成了和休謨一致的結論:對近代契約論政治哲學的批判和否定。休謨的經驗論立場使他不可能接受近代自然法和自然權利學說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而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家將功利作為人的目的,事實上也否定了人具有任何先天的目的和本質,也消解了自然權利論者的理論主張。然而,邊沁和密爾對功利概念的運用和發展,依然是基于休謨所反對的理性主義。無論是邊沁還是密爾,他們都相信我們不僅能通過理性的計算區分出行為和偏好帶給我們快樂和痛苦的數量,以此作為道德判定的、唯一的規范性原則,而且也可以通過理性的衡量建構一個正當的政治社會及其制度框架,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致。與邊沁和密爾對理性的信任不同,休謨明確表達了理性在人性構成中相對于情感的次要地位的觀點,并在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中否定理性作為道德與政治根本性原則的基礎性地位,他也反對以任何形式的理性主義基礎與方式建構和論證人類道德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原則、規范和現實框架。而功利主義者對“功利”的事實認定到價值認定的僭越性解釋和運用,更是休謨所反對的。這里實際上涉及到休謨的“是-應當”問題,休謨認為,“是”與“應當”分別是理性和情感發揮作用的領域,兩者的功能和運用領域不能混淆,從理性之所司的事實領域不能直接過渡到情感之所司的價值領域。所以,在“道德學”的第一章第一節最后一段,休謨批評說,以往的道德理論家都是從各種各樣的“是”和“不是”陳述開始,然后“突然”形成一些其系詞是“應當”或“不應當”的陳述,但并未對這一過渡作出解釋和說明。因此,邊沁等功利主義者試圖超越休謨而積極建構的功利原則的根據,正是休謨所批評和反對的從“是”推導出“應該”來的“自然主義的謬誤”。
總之,休謨對效用概念使用,的確為后來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興起和形成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和理論框架,但是,休謨并不屬于任何形式的功利主義者。更重要的是,與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將“功利”作為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理論前提以及理論框架相比,休謨的觀點是有限的。他和功利主義在根本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1] 亞歷山大·布羅迪.蘇格蘭啟蒙運動[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2] 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Z].商務印書館,1987.
[3] 大衛·休謨.人性論[M].商務印書館,1997.
[4] 大衛·休謨.道德原則研究[M].商務印書館,2007.
[5] 杰里米·邊沁.政府片論[M].商務印書館,1997.
[6] 約翰·密爾.功用主義[M].商務印書館,1957.
[7] 盧梭.社會契約論[M].商務印書館,1997.
[8] 約翰·密爾.論自由[M].商務印書館,1996.
[9] 黃偉合.為功利主義辯護[N].文匯報,1989-0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