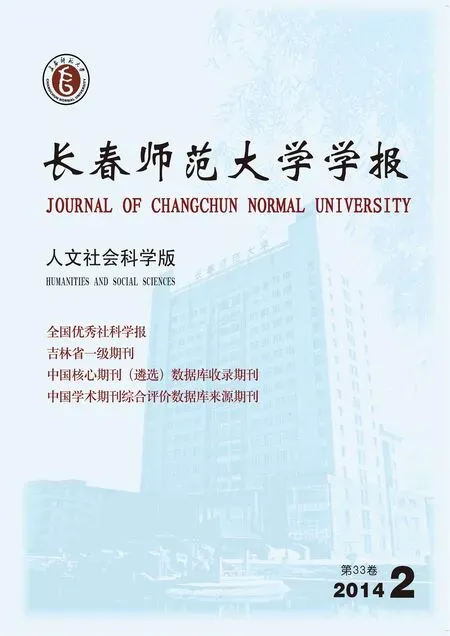大學語文寫作教學動機論
鄭 昀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大學語文寫作教學動機論
鄭 昀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自20世紀80年代大學語文課在高校開始設置至今,研究者多強調教學方法的革新,對寫作教學動機的論述還很不足。論及大學語文寫作教學動機觀的教材編者和學者,多持應需、應試的寫作教學觀,使寫作淪為“訓練”。發展性動機支配下的寫作教學才是大學生實現言語生命價值的最高指向。
動機;大學語文;寫作教學
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學語文教材編者的寫作教學動機
縱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較有影響的大學語文教材,寫作教學多強調應用文的寫作。
其一,在語文教材中未涉及。例如,溫儒敏主編的《高等語文》在編寫目的中強調“必須兼顧語文課必要的工具性, 給學生多一點閱讀和寫作的機會”[1],但教材并未編排有關寫作教學的相關內容。
其二,以附錄形式出現。林紅、張寧主編的《當代大學語文》以附錄的形式收錄了申論寫作的理論知識和國家公務員、福建省公務員的試卷與答案。編者認為,“隨著申論在就業考核中比重的加強,申論寫作也成為大學生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2]顯然,編者是從應付考試的需要確立寫作教學的動機的。
其三,與文選教材并列存在。例如尹少榮主編、中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大學語文》,分為上下兩編:《閱讀鑒賞》與《應用寫作》;又如張銘遠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大學語文》,將教材分為兩部分:《中國文化基本素養》與《漢語應用基本能力》。上述教材應用寫作教學中的應用文類型,主要包括日常事務文書、就業文書、國家機關行政公文與申論等。
其四,滲透進文選閱讀教學部分。2011年版陳洪主編的《大學語文》(第二版)的編寫說明中指出:“通過對各類文章寫作要領及語言表達技巧的體認,提高語言文字的實際應用水平。”[3]此處對“實際應用”的內涵并未予以說明。其后的總序中,則提出大學的語文教育意義之一是提高理解和表述世界的能力。
各類教材主流的觀點認為,大學語文寫作教學是為了讓學生應付學習、生活、工作中的實際需要。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他學者的寫作教學動機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關于大學語文教學中的寫作教學動機建構的觀點,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其一,寫作是應學生學習、工作之需。趙雪梅認為,應當加強應用文寫作教學,主要包括研究報告、學術論文、行政公文、各類文書等。高紅艷認為,寫作能力的培養是為以后的工作服務的,具有很強的實用性。
其二,寫作動機應多元化。有的學者從多種視角出發,試圖建構多層次的大學語文寫作教學動機體系。例如,王向輝認為,寫作教學一方面應從社會、生活需要出發,強調實用性;另一方面,寫作是一種精神生產,寫作能力的培養可以讓學生體味到創造的樂趣。[4]
可見,相對于本時期大學語文教材的編者應付實際需求的寫作教學動機,學者觀點顯得多元化,更加關注從學生的精神培養、建構出發探討寫作教學的重要意義。
三、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剛剛興起的大學語文的教學目標,被定位為針對文革之后大學生較低的語文水平的“補課”。因此,當時的大學語文一度被稱為“高四語文”,并且主要在理工科院校開設。進入90年代之后,大學語文被定位為素質教育課程,在國內普通高校廣泛開設,并且多作為公共基礎必修課。“基礎性”一詞最早出現在了當時的教育部高教司《大學語文教學大綱》(征求意見稿)中。“意見稿”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設置大學語文課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發揮語文學科的人文性和基礎性特點,適應當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日益交叉滲透的發展趨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具有全面素質的高質量人才。”[5]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本文開始部分談到的大學語文教材普遍重視應用文教學的現象。那么,寫作教學重視實用是否合理?寫作教學作為大學語文教學中的重要一環,又應當建構怎樣的動機系統?
四、從“應需”到“應性”
“應需”的寫作教學動機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大學課程實行新制。193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一年級不分系,設置國文為必修課之一。教育部“大學課程整理辦法草案”要求“在發表方面,能做通順而無不合文法之文字。”黎錦熙在1942年發表的《大學國文之統籌與救濟》一文中強調:“國文工具,能否運用?服務辦公,執業施教,‘理財正辭’,以及日常生活,處處需此工具,能否不出岔子?默察現實,忙無把握!”黎錦熙認為,這有待于對中學國文教學進行“根救”,并需要為大一學生補充文藝教材。在“根救”有待、“補救”無人的情況下,提出“搶救”,即通過訂閱報紙,以此作為實用基礎進行訓練。黎錦熙又對寫作教育側重應需動機作了如下補充:“我提這個‘搶救辦法,并不算是教育,乃是一種‘訓練’。訓練與教育,在性質上略有根本的不同。教育史德智體美都要兼顧,任何科目,其取材與修習方術,總須具此教育的意義,固然其中也包含著技能訓練的成分,但單純的‘訓練‘,則只是應某種的需要,懸具體的目標,范圍有定,目不旁瞬,迅速成就,確實有用。在所謂非常狀況下,大一學生,實用國文,岔子百出,危險萬狀,需要迫切,目標不高,允宜限制范圍,力求迅速,亟予‘訓練’,——是之謂‘搶救’。”[6]從以上論述中不難看出,作者清醒地意識到訓練與教育之間存在差別,訓練在“非常狀況”中的運用并不能說明其能夠成為指導教育的原則。
早在1924年,黎錦熙在語文教學法專著《新著國語文法》中,就把聽、說擺在了重要的位置上,認為口語表達與發表文章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社交上的運用”,另一方面還在于“藝術上的建造”。可見,黎錦熙并不認為“應需”是寫作教育的唯一動機[7]。這對于今天的大學語文寫作教學仍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隨著時代的變遷發展,當今大學語文教育立足的現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寫作不只是為了應付日常生活和應付考試,更可以實現交流思想、傾訴苦悶、娛樂內心等方面的目的。
應付考試與應付日常工作、生活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應需”的,并且是應外部的、被動的需求,都是對非應需的文學創作的漠視。由生存需要走向存在的需要,是人的心理發展的必然選擇。
學習應用文的各種規范和格式,可以更好地應試,其激勵作用是較小的,與寫作的客觀實際存在很大差距。學生在規定好的話語空間寫作時,往往很難發揮個人的言語創作熱情和言語表達潛能,長期如此必將壓抑學生的寫作欲望。為激勵學生走向自我言語價值的實現,就要建立多元的寫作教學動機。
大學語文寫作教學在建構動機系統時,應該基于兩種需要之上,一是應生活之需,二是應精神之需。后者是更高級的需要,更符合人的個體生命價值的最大實現。
綜上所述,大學語文寫作教育的動機系統是多個層次的,除了讓學生意識到寫作可以滿足“生存性”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樹立寫作是人的“生存性”需要的認識。教師應當在把握時代特點和大學生認識特點的基礎上,引導學生思考寫作動機,探討言語價值,巧妙地設置教學情境,激發寫作興趣。
[1]趙雪梅.大學語文教改應重視應用文寫作教育[J].江蘇高教,2005(4):139.
[2]林紅,張寧.當代大學語文[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2.
[3]陳洪主編. 第二版.大學語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
[4]王向輝.大學語文教學應該突出寫作能力的培養[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123.
[5]何二元,劉文菊.大學語文研究的歷史、現狀及方向[J].語文教學通訊,2011(2):9.
[6]張鴻苓,李桐華.黎錦熙論語文教育[M].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218-251.
[7]黎澤渝,馬嘯風,李樂毅.黎錦熙語文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9.
2013-12-03
鄭 昀(1986- ),女,山東濰坊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文學閱讀與文學教育研究。
H193
A
2095-7602(2014)02-015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