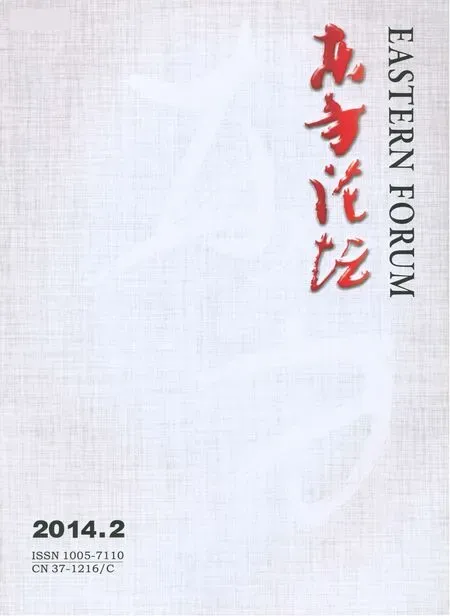威廉斯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
舒 開 智
(黃岡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黃岡 438000;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威廉斯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
舒 開 智
(黃岡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黃岡 438000;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文化是近年來人文學科關注的焦點,也是文學與美學話語論述的對象。馬、恩在創建唯物史觀過程中,既確立了文化問題的唯物主義解釋原則,把經濟和文化區分為基礎和上層建筑,但是也強調文化的相對自主性,揭示了文化與政治、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之間更復雜的關系。威廉斯在20世紀中后期的資本主義歷史語境中,面對工人階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興起,建構出文化唯物主義理論,突出文化生產的社會性、物質性。在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模式之外,提出了大眾文化的建設性維度,豐富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對文化的形態和社會功能的理解。這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啟示與借鑒作用。
文化;唯物史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
文化是20世紀以來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關注的焦點,也是文學與美學話語論述的對象。雷蒙德·威廉斯之于文化理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戰后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不但以自己杰出的理論實踐貢獻出了一大批具有歷史穿透力的著述,而且徹底改變了20世紀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貧乏的局面,對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有著篳路藍縷之功。其門下弟子伊格爾頓說過:威廉斯無疑是英國戰后出現的最有影響的文化思想家和作家,他把文化概念放回到社會和政治的理論探討的核心地位上,而且隨著歷史記載逐漸被人們重審,顯然,威廉斯將被賦予英國20世紀獨有的最重要、最具原創性的文化思想家的地位。如果說,學生的贊譽難免有溢美之詞,那么來自美國的羅伯特·戈爾曼所言——威廉斯的思想地位在許多方面都是無與倫比的,他無疑是戰后英國學識最淵博、最有成就、讀者最廣泛、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作家。無疑是值得信任的最中肯評價之一。本文無意全面論述威廉斯的學術成就,僅從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關系展開。
本文的構思基于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從理論上講,一直以來,學界有一個成見,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文化理論領域是一片空白或語焉不詳。其實,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極大誤解。文化問題在馬、恩創建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并未受到漠視和遮蔽,而要厘清威廉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所作補充與拓展的貢獻和迷誤,首先就要闡明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時代語境、基本觀念和闡釋原則,才能辨明威廉斯文化理論的成就與缺憾。從實踐上講,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泛濫、商品文化的平庸、精神和價值的失落與危機,同樣是擺在每個理論研究者面前的現實。因此,如何看待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系?又如何看待威廉斯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關系?這些都是在理論中需要探索的。
一、文化理論: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與揭示
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論創建與其唯物史觀創建是相伴相生的統一過程。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在其后的著述中,他們“以宗教批判為前提,依次經歷了法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意識形態批判,涵蓋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逐步地實現了對文化史觀的矯正,從而確立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論。唯物史觀亦由此創立。”[1]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又進一步指出:“從前的一些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2](P499)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2](P524)在考察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時始終堅持“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把“現實的個人”“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作為現實的前提,科學地揭示了文化的產生、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并以唯物史觀界定了文化闡釋的基本原則——“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2](P544)馬、恩這里確立了文化分析的現實框架和物質原則。在這個意義上,誠如伊格爾頓所言:“馬克思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人類歷史的理解,這是連馬克思主義最激進的批評者也無法否認的事實。”[3](P2)
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序言中,馬克思更有這樣的論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4](P32)馬克思把經濟和文化區分為基礎和上層建筑,體現了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宏大敘事和唯物主義認識。馬克思之前的社會學理論,過于看重“觀念的”因素及其作用,貶低了經濟力量在歷史和文化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出于對這種反物質主義視角的反抗,強調文化沒有獨立的自主性,上層建筑中的各種觀念和意識形態,都是物質生產的“反映和回聲”。這實際上把對文化現象的揭示從歷史上一切唯心主義的迷霧中解脫出來,不僅為考察和描述人類歷史和文化找到了堅實的物質前提,也確立了文化理論的唯物主義解釋原則。
馬、恩對文化的這種唯物主義闡釋原則,并不表明,他們把文化當做完全依賴于經濟基礎的外部消極因素,在社會變遷中不能發揮任何積極作用。在《神圣家族》中,他們對布魯諾·鮑威爾的批判時就發出過“唯物主義在以后的發展中變得片面了”和“唯物主義變得漠視人了”的提醒。馬克思認為文化離不開人的自由自覺的實踐,人在進行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同時,也在生產著文化的人和人的文化。文化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 “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5](P47)恩格斯晚年在給布洛赫致信中對他和馬克思在早年為什么強調經濟的作用進行了說明:“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6](P695-696)后來的一些機械唯物主義者,片面地認為,文化只能僵化地反映經濟基礎,其內部應有的活力完全被抹煞了。馬克思主義重視經濟基礎對包括文化在內的社會上層建筑諸種形式的根本性決定作用,但是同樣沒有否認文化的重要能動性和自主性。
馬、恩對文化問題的精彩論述還反映在這段話中——“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說明馬、恩實際上看到了文化力量與經濟、政治等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復雜交織關系,文化作為一種積極的社會建構范疇,不只是消極地反映著經濟和政治利益,它與政治、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之間有著更復雜的關系。20世紀的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就表明,經濟和文化被加以“重新統一”,具體措施就是把文化置于經濟之下,“重新組織整個文化的意義和象征意義,使之適應商品的邏輯”。[7](P22)借助復制和傳播等新媒體技術,壟斷資本主義成功地收編吞噬了早先的各種通俗文化形式,并對所有文化進行標準化、組織化和制度化引導和生產,把文化當做社會控制的工具。法蘭克福學派便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大眾文化的這種虛偽性和規訓特點,撕開了文化工業的神秘面紗,給予嚴厲的批判,最終達到拯救資本主義社會、實現解放的目的。
二、補充與改寫:威廉斯文化理論的拓展與貢獻
威廉斯指出:“馬克思本人曾想建構一種文化理論,但沒有完全建成。例如,他對文學所作的即興的議論只是作為那個時期的一位有識之士的感想。很難把它看成是我們今日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有時,他也會憑藉他非凡的社會見識來作一番議論,但人們并不會覺得他是在應用一種理論。他討論這些問題的口氣是變通而無教條獨斷之氣,而且無論是在文學的理論還是實踐上,他都明于自制,限制那種他顯然認為是將他的政治、經濟、歷史的結論過分熱心地、機械地移用到其他領域的做法。恩格斯盡管在習慣上未能如此謹慎,但口氣卻是一致的。這并非說馬克思對這些結論做重大的擴展或對于充實他自己的文化理論的構想缺乏信心。問題在于,他的遠見卓識使他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困難性與復雜性以及他實事求是的立身行事的準則。”[8](P338-339)
威廉斯這段話并非說明馬克思對文化理論毫無建樹,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有生之年沒有寫出一本專門的文化理論著作,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實現了對歷史上唯心主義文化史觀的重大變革,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內解釋文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由于歷史語境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限制,并沒有預計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意識形態的深刻變化和大眾文化的變遷,所以體現出“實事求是的立身行事的準則”。威廉斯有幸目睹了英國社會工人階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出現,歷史給了他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契機。
在較早的《文化與社會》(1958)中,他就考察分析了“工業”“民主”“階級”“藝術”“文化”這五個關鍵詞的歷史變遷,梳理了從浪漫主義以來到奧威爾的文學傳統,并深刻指出:“文化的意義史是我們賦予它的歷史,而且,它只能在我們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中才能被理解和接受。”該書注意發掘詞語背后的社會歷史和意識形態嬗變軌跡,成為后來的《關鍵詞》一書的理論先導和基礎。1961年他在《漫長的革命》中對文化的定義作了三個方面的概括:首先是“理想的”(ideal)文化定義,也就是阿諾德所說的由高雅的文學藝術為代表的“精選”(selective)文化傳統。根據這個定義,就某些絕對或普遍價值而言,文化是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其次是“文獻式”(documentary)文化定義,根據這個定義,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詳細記錄了人類的思想和經驗。最后,是文化的“社會”(social)定義,根據這個定義,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從這樣一種定義出發,文化分析就是闡明一種特殊生活方式、一種特殊文化隱含或外顯的意義和價值。威廉斯同意利維斯關于英國工業文明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弊病,但是他不同意利維斯所主張的文化與生活的新鮮經驗僅僅來自文學作品的觀點。這樣一來,威廉斯所欲建構的文化理論,不同于阿諾德-利維斯式的精英主義傳統,而是人類自己創造自己的社會生活的全部活動方式,因此是唯物主義的。
威廉斯一方面反對將文化視為少數知識分子囊中玩物的英國精英主義傳統,另一方面也極力糾正將文化視為經濟基礎的直接“反映”的某種馬克思主義偏頗。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基礎和上層建筑》一文中他開篇就指出:“任何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現代理解都必須從考察關于決定性的基礎和被決定的上層建筑的命題開始。”[9](P327)因為在當時,從馬克思主義發展來看,一些人沿用了浪漫主義以來的文化概念,然后簡單地套用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公式,將文化歸于上層建筑的位置,把文化看作處于從屬地位、只能機械地“反映”基礎。既忽視了文化的內部復雜性,也抹殺了文化的物質性和能動性。“很清楚,許多在政治上屬于馬克思主義的英國作家,在談論文化的時候,首先關心的是證明它的存在,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以此來反擊眾所周知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確立了一種觀念,以為馬克思主義由于建立了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而削弱了迄今為止人們一直賦予知識創造和想像創造的價值。當然,在那些批評馬克思的人當中存在著對馬克思主義著作驚人的無知”。[8](P349)有鑒于此,威廉斯從他的社會總體性理論出發,將文化界定為普通男女的一種日常生活方式,打破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關系,把這兩個領域的各種相關要素聯系起來。 為此,威廉斯創造出了“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一詞,他認為,研究一個時代一個地域的文化,關鍵就是捕捉它的感覺結構:“我建議用以描述它的術語是感覺結構:如同‘結構’一詞所暗示的那樣,它是穩定和確定的,然而,它在我們的活動最微妙和最不明確的部分中運作。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感覺結構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產生的特殊而鮮活的結果。”[10](P48)“感覺結構”一方面是文化建構的結果,另一方面又是描述文化動態的術語。在威廉斯看來,“感覺結構”的概念優于世界觀、意識形態等凝固的形式,不但可以及時描述反映正在活躍的意義和價值,而且可以彌合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脫裂。為了完整認識過去歷史時期的文化,就必須把握住時人的社會體驗和真實感受。“在研究過去的文化之時,最困難的事情莫過于了解時人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以便領悟到當時人們所特有的各種活動是怎樣組合成為一種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的”。[10](P63)為此,他提出分析一個時期的文化,一定要去分析當時人們的感覺結構。
在后期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威廉斯系統闡述了他的文化唯物主義理論,認為文化可以劃分為主導文化、新興文化和殘余文化,三種文化之間既有對立沖突也有吸收依賴,“實際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生產方式,因此也從來沒有任何一種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或任何一種主導文化可以囊括或窮盡所有的人類實踐、所有的人類能量以及所有的人類目的。”[11](P134)因此,對任何一個社會一個階級所作的文化的分析需要關注其所處時空環境中社會生活方式各種復雜因素間的關系,以及特定時空下人們對自己所身處其中的生活性質和經驗意義的感覺。這種感覺方式既不是弗洛姆的“社會性格”,也不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而是一種更內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覺,“感覺結構”這一概念的提出,為共同文化的理想奠定了基礎。在吸收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的基礎上,威廉斯突出了文化的經驗性、斗爭性和復雜性,克服了阿爾都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悲觀情緒,通過將文化定位為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底層大眾都可以參與文化和意義的創造,這種“民主的共同文化”,有利于促進政治斗爭,推動社會變革。“對激進社會主義者而言,共同文化是這樣一種文化,它全力創造并維護自己的所有形式,包括藝術、政治、道德以及經濟,所有成員都最充分地共同參與這些文化形式。”[12](P140)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有著明確的社會旨歸和目標——實現社會主義、實現男女平等、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以求解放。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理論建構,使得文化概念充分強調了社會的物質過程,避免了抽象的、直線發展的普世論;也防止了文化被狹義地限定為“精神生活”和“藝術”,避免了庸俗經濟決定論,而且徹底消解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二元對立。他的文化理論充分注意到文化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突顯了文化在當代社會變革中的能動作用,在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模式之外,提出了別具一格的大眾文化分析的建設性思路。
三、啟示與反思
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對我們認識中國語境中的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關系有著重要啟示作用。一直以來,我們對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認識陷入糾結和兩難境地,精英知識分子表面上對大眾文化擺出一副居高臨下和鄙夷的態度,但是暗自對大眾文化的廣泛吸引力羨慕不已;大眾文化在無限風光的背后,也渴望得到精英文化所擁有的尊嚴。尤其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普遍化,大眾文化開始不知不覺地影響所有階層的人們,在這種背景下,威廉斯的大眾文化理論更能使我們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的“文化”,不能只是少數政治精英或知識分子倡導的文化,而是平民大眾能親身體驗、創造并樂于分享的文化;也不是用來對抗物質饕餮和機械文明的內在完美,而是具有豐富感召力和具體形式的社會表意實踐。在當前中國,文化產業早已不再是原來法蘭克福學派所聲討的同質化、標準化的工業產物,豐富多彩的通俗化、差異化文化形式為不同階層的社會大眾提供了共享文化、表達自我的途徑。正是在這種日益多樣化的文化實踐和形式中,當代社會環境下人們的感覺結構得以表現。因此,我們當前對大眾文化的評析,不能想當然地借助知識分子精英話語對其作出未經考察的先驗式道德判斷,而是要深入人們的起居生活中,綜合考慮這種文化形式在人們日常生活意義建構中發揮作用的真切機制,以及對普通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實際影響。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不能通過制度化的權力手段采取自上而下的文化整合和文化輸送,而要讓鄉土文化建構起農民的自愿意識和人生意義,滿足他們的精神生活和價值需求。
文化工業的出現是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發生根本變化的結果。20世紀后半葉的西方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恢復和消費主義的興起,出現了新的變化:文化與經濟日益成為一個整體,文化為經濟提供了新的活力、新的發展契機,為利潤和管理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新世界。經濟狀況也不再像從前那樣運行于文化的底層起決定作用,經濟行為與活動也已融入到文化活動本身。面對這種表象,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模式不是失效,而是更深刻地發揮作用。而威廉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拓展與重釋,一方面堅持了從生產方式的變革來解釋文化,誠如他自己曾指出:“我在邊遠鄉村長大所看到的一切使得我相信,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藝術不過是一個社會有機體的組成部分,而這個有機體明顯地要受到經濟變化的影響。”[13](P7)但是也取消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優先作用,弱化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模式的作用,畢竟“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當代理論的批判及其對階級政治的強調和歷來對階級斗爭的重視,所依據的并非僅僅是作出一個又一個的否定。……馬克思主義始終考慮信念、統治地位和社會變革的關系。”[14](P80)
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文化在工人階級斗爭中的重要性并未突顯出來,大眾文化對人的解放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也未出現,馬克思明確地從正面指出“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2](P192)然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福利的發展,馬克思當年視為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內部發生了明顯的分化,有的已被整合進了資本主義體制之中,成為這一體制的維持者和利益分享者。隨之崛起的工人階級文化和大眾文化對于資本主義制度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既有抵抗更有順從和甘心忍受。威廉斯卻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從經濟制度上揭露資本主義的根本弊病來發動工人階級實現社會革命,而是一廂情愿地寄希望于通過工人階級的大眾文化來實現文化革命。威廉斯并沒有完全解決好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和權力之間的復雜沖突與斗爭關系。這反映了威廉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缺憾,在深層次上體現了歐洲左派知識分子理論探索的失敗與困惑。
[1] 胡海波,郭鳳志.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論:一個被遮蔽的唯物史觀的重要視域[J].學術月刊,2010,(1).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M].李楊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美]安德烈亞斯·胡伊森.大分野之后:現代主義、大眾文化、后現代主義[M].周韻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8]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M].吳松江、張文定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9] [英]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基礎和上層建筑[J].傅德根譯,劉綱紀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2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10] 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1961.
[11] [英]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王爾勃、周莉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12] [英]特里·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M].馬海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3] 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London: Verso,1989.
[14] [美]埃倫·梅克辛斯·伍德、[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保衛歷史:馬克思主義與后現代主義[M].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侯德彤
Williams and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SHU Kai-zh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angang 438000, China; Dept of Chines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Culture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also the target of literary and aesthetic discourse. While dividing economy and culture into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Marx and Engels stressed the relative freedom of culture, and disclose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and between economy structure and class relations. Fac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Williams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materialist culture and highlighted the sociality and materiality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mid- and later 20th century. He proposed the constructive dimension of popular culture, thus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 materialist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ultu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lliams; cultural materialism
G122
A
1005-7110(2014)02-0051-05
2014-03-01
黃岡師范學院博士基金項目:“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理論研究”(2012029503)。
舒開智(1979-),男,湖北武穴人,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骨干訪問學者,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