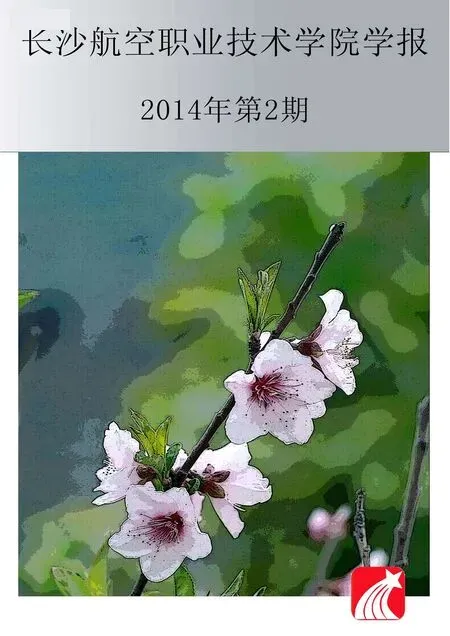中日象征主義詩歌中禪宗因素之比較
李玉婷
(重慶師范大學,重慶 401331)
中日象征主義詩歌一方面承襲了以波德萊爾為首的法國象征主義的影響,以惡為美,追求感官刺激,抒發頹廢情緒等。另一方面,中日象征主義詩歌又受到東方傳統文化影響,尤其是禪宗的影響,呈現出不同于法國象征派的東方特性。佛教傳入中國后又由中國傳到日本,佛教對中日兩國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佛教分支之一的禪宗,從遙遠的古代起就與文學相互滲透,在20世紀初期的中日象征主義詩歌中亦能尋得禪宗浸潤的痕跡。
一、禪對中日象征主義詩歌的浸潤
禪于6世紀起源于印度,印度禪講靜觀,講無我,形式上以坐禪為主。中國禪宗的初祖菩提達摩于梁武帝時期把印度禪宗傳入中國,到六祖慧能時期,他的禪宗脫離了印度厭世的生活態度和苦修的參禪方式,追求的是頓悟,是精神,是個人的體驗和感覺,由此開創了真正的中國式禪宗。佛教傳入中國后又由中國傳到日本,奈良時代,中國禪宗開始傳入日本,但并未產生很大影響。鐮倉時代,榮西傳中國臨濟宗,得到鐮倉幕府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人們對禪的關注和重視。其后,道元傳中國曹洞宗,臨濟宗和曹洞宗形成日本禪宗兩大流派。室町時代,從統治階級的室町幕府到平民百姓,禪宗思想已滲透到日本生活、藝術的各方面中,對繪畫、建筑、劍道、茶道、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對文學方面的影響更為顯著。
中日象征主義詩歌都淵源于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后期的中國象征主義詩歌受日本象征主義和法國象征主義的雙重影響。20世紀初期,詩人們面對現實的荒原決定向內轉,從自己的內心里發掘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這是一種禪所講求的心靈狀態,因此在他們的詩歌中我們能感受到的是一種朦朧暗示的虛無幻滅之感。
中國象征主義詩人多是一邊在外求學,一邊苦苦探索救國之路的“漂泊者”,然而當他們回到故鄉,看到的卻是殘敗的景象,如李金發《懷舊之思》:“泛海歸來,遇見不相識之窗,透來一片哭聲,我破戶入覲時,眼見忠實之乳媼/向蒼天跪著,/及寒暄一二句/她就向我求施了。”[1]游子回到祖國的懷抱,昔日的美好故鄉,熟悉的樂土不翼而飛,如今只剩荒蕪破敗,婦人向蒼天跪著苦苦祈求卻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無人關懷無人問津,甚是凄涼。作者找不到往昔的歡樂美景,看到此番悲慘之景只得發出無奈的感慨,感慨世間一切變化無常,卻無力改變什么。而日本象征主義也受到禪宗無常思想的影響,同樣表現出虛無之感,而希望從夢里,醉里尋求對世俗的暫時絕緣。牧羊神會的成員之一的永井荷風就認為,“夢”“醉”“幻”都是無常的,追逐它們便是像在追逐泡影一般:“夢,醉,幻,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不停地思考戀愛,夢想成功,但是,我們并不希望成功。我們只是追逐現實過程中出現的影子,醉心于預想和預期罷了。”[2]
同時禪宗講求冥想和悟,這為象征主義詩歌增添了神秘感和朦朧感,這也與象征主義詩歌提倡的暗示朦朧是相通的。“詩的世界是潛意識的世界。詩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詩的世界固然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處。詩要有暗示出人的內在生命的深秘。詩是要暗示的詩,最忌說明的。”[3]如李金發《夜之歌》“我們散步在死草上/悲憤糾纏在膝下。/粉紅之記憶,/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你總把靈魂兒/遮住可怖之巖穴,/或一齊老死于溝渠,如落魄之豪士。/但我們之軀體/既遍染硝磺。/枯老之池沼里,/終能得一休息之場所么?”[1]這首詩充滿了神秘和死亡的氣息,“死草”“朽獸”“可怖之巖穴”“落魄之豪士”“枯老之池沼”等意象顯得頹廢而悲觀,詩人沒有直接抒發對現實生活的失望和厭惡,而是通過朦朧暗示的手法變現出來,他希望在肉體的死亡和腐爛之后,靈魂能找到一處休息的場所。讀者能感受到詩人的情感是含蓄克制的,但一首詩讀完后的回響是有力的。而在日本象征主義詩歌中,這種厭世情緒的暗示也是隨處可見的。當時的日本,在追逐西方的過程中,漸漸迷失了自我,人們處于精神的荒漠和饑渴中,再加上天皇政權絕對化的思想壓力,他們產生了極度的絕望感。如在三木露風《幻象田園》中,詩人吟道:“春天出現在天空景色中/在或有或無的淡淡云層里/有苦惱死去的飛蛾的氣息。”[2]春天本來是新生的季節,是生命從冬天的倦怠中重新煥發活力的季節,而詩人在生機勃勃的春天卻敏感地嗅到了死亡的氣息。一前一后是生命和死亡的對應,這正體現出禪中一切變幻無常。
李金發說過:“詩之需要image(形象,象征)猶如人之需要血液。現實中沒有什么了不得的美,美是蘊藏在想象中的,抽象的推敲中。”[5]這正是禪宗所講求的思維方式。
二、入世思想與中國象征主義詩歌
象征主義詩歌強調表現作者復雜的內心世界,追求神秘感和朦朧暗示的效果。中國象征主義詩歌中的禪宗因素體現在受儒家追求文學社會功效思想的影響和道家在“現世”中尋求身心自由的影響,中國象征主義詩人在表現個人感性體驗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對現實的關照,他們心系民族的危亡,無法完全做到與時代保持距離,他們的詩歌呈現出與現實糾纏不清的無奈和苦悶。
如穆木天的《心響》就有別于詩集《旅心》中的其他詩篇的感傷頹廢的情調:“幾時能看見九曲黃河/盤旋天際/滾滾白浪/幾時能看見萬里浮沙/無邊荒涼/滿目蒼茫啊 廣大的故國/人格的廟堂/啊憧憬的故鄉呀/我對你為什么現出了異國的情腸/飄零的幽魂/幾時能含住的乳房/幾時我能擁你懷中/啊禹域我的母親/啊 神州 我的故邦……”[5]九曲黃河,萬里浮沙,是對祖國自然景物的描寫,表現了對祖國的一切的深切思念和渴望回歸故里的迫切。詩人雖然身在異國他鄉,卻仍然心系著家園,坦然面對家園的一切,哪怕是無邊的蒼涼和滿目的蒼茫,卻是游子們最終可以棲身之所,讀來雖有苦澀和憂郁,但更多的是詩人對祖國現狀的關心,讀者能真切感受到詩人那顆滾燙的赤子之心。穆木天在創作中“體現出一種想將象征藝術和現實生活的表現結合起來的愿望,這是緊密地聯系于中國當時的詩歌寫作語境的,想在詩的社會使命與藝術追求間找到某種平衡。”[6]個人的感傷在現代階級的社會革命中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可見在30年代,作者更是表現出了關注現實參與革命的激情。
李金發的詩歌,一直以來都與人民,與政治保持著距離,但他也寫出了像《可憐的青年》這樣的對黑暗社會的揭露和悲憤以及對愛國青年的歌頌。盡管詩歌的基調仍是感傷沉重的,但作者對愛國青年的贊美中,激昂之情溢于言表。逆境并沒有讓他退卻,他在艱苦的環境中頑強地生存著,在他身上有著生命的激情和活力,并且將這種激情與活力帶入到革命之中,詩人對他的歌頌表明詩人并沒有完全沉浸在個人情緒的書寫中,詩歌不能僅僅表現“美”,還要發揮“善”的效果。
究其原因,中國的禪是儒釋道三教合一,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意識形態。受儒家色彩的影響,禪強調對現世人生的關注,體現在文學領域,要求文學作品不僅表現作者個人的感性體驗,還要表現豐富的現實,追求社會效果。禪同時又吸收了道家思想,而道家雖同佛教一樣認為人生是苦難的,但不同于佛教強調的厭棄人生,轉求來世,追求身心的絕對自由,其所追求的曠達放任在“現世”,在每個人的心中,而不是“來生”。所以中國象征主義詩人們被拉回到“現世”和關當下。
三、出世思想與日本象征主義詩歌
與中國的禪宗不同,佛教在日本是主流。受涅槃思想的影響,日本象征主義詩人在現實的荒原上步履維艱,他們希望通過遠離社會,自省自修而達到解脫自在的境界,所以他們的詩歌追求神秘和不可思議的心境,詩歌呈現出閑淡孤寂的特征。
如日本詩人三木露風的詩歌有很強的宗教色彩,他在《去暗處》中低吟到:“我們越海而去,越海而去。依靠不可思議的力量,有時我們憤怒、高興、悲哀。如同影子,我們離去,成群跳過……”[2]人生苦海無邊,在熙攘喧鬧的人群中,人們還是不能擺脫內心的孤獨和焦慮,“我們越海而去”便是作者告訴人們要越過人生的苦海,尋找生命的真諦。而載著人們“越海而去”的小船便是那“不可思議的力量”,這“不可思議的力量”來自于佛祖的智慧和個人的覺悟,那要憑借著自己摒棄一切欲望的虔誠的心才能到達彼岸世界。此岸落英繽紛,彼岸繁花勝放。唯有跟隨步步生蓮花的佛祖才能獲得解脫自在。這首詩歌讀來雖有寂寞之感,但更多的是寧靜與淡泊,那是一顆遠離塵囂的心才會有的心境。如三木露風的另一首詩歌《追憶童謠》也是講述作者向往寂靜神秘的地方,對遠方的世界有無法抹去的憧憬,對陌生地的向往之心,所有冒險的本質,都是企圖脫離自身的生活。拋卻束縛和糾纏,只管沿著寂靜的山路朝前走,那個神秘的聲音一直在前方指引著,如燈火,為黑暗中踽踽獨行的人指引通向光明的路。生命的意義不在人所置身的日常周遭世界里,而在對不可知的命運或神秘莫測的地點的探究中。
日本另一象征主義詩人堀口大學的《椰子樹》:“在那蜃景般的空中寺院,/在金紫色的熱帶黃昏,/在煩惱、燃燒的人類欲望的漩渦中,/椰林挺著身軀,/在那兒變成一座十字架,清心去欲地默禱著的,/是那片椰林還是我的靈魂。”[7]此詩同樣抒發了作者想要擺脫燃燒的人類欲望,像椰林一樣清心寡欲地默禱,使靈魂獲得清凈的愿望,因為這才是滅諸煩惱,到達涅槃之境的唯一途徑。日本象征主義詩人正是借這種禪宗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對喧囂塵世進行無聲的反抗,以淡泊自省的姿態詩意的棲居于大地上。
四、結束語
中日象征主義詩歌都受到禪宗靜觀思想的影響呈現出厭世虛無的特征。同時又由于中日兩國各自不同的宗教文化傳統又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中國象征主義詩歌受中國化禪宗的影響,關注現世人生,而日本象征主義詩歌受日本禪宗的影響,其特征體現為淡泊自省,遠離社會,追求不可知的力量。中日兩國象征主義詩歌特征中的同與不同,體現出了禪宗對詩歌的重要影響。
[1]孫玉石.象征派詩選(修訂版)[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2]肖霞.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與基督教[M].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
[3]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J].創造月刊,1926,(1).
[4]李金發.序林音強的凄涼之街[J].橄欖月刊,1933,(35).
[5]周曉風.新詩的歷程1919-1949[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6]陳太勝.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7]武繼平,沈治鳴譯.日本現代詩選[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