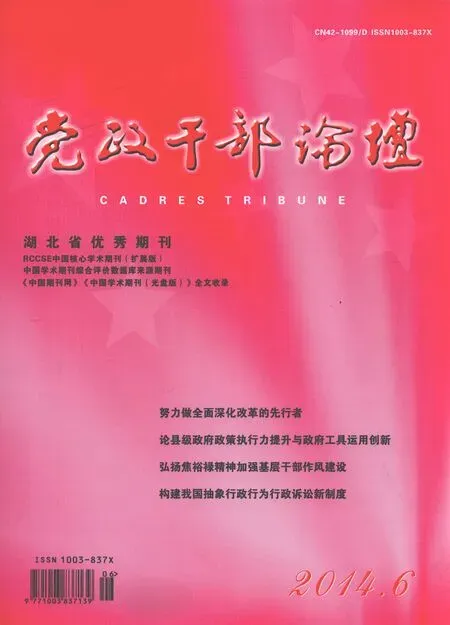公民政治參與的另一種解讀——以理性選擇理論為視角
○ 王發余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在政治生活中就如在經濟生活中一樣,常常為稀有資源而競爭[1]。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民眾更傾向于關注基本的經濟福利,而不是政治權利,那時,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并不強烈。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一方面,人們的政治參與意識比以往強烈,要求獲得更多的民主;另一方面,民眾通過政治參與來保障自身利益,也會成為經濟發展的穩定因素。經濟和政治的關系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些共存現象使得越來越多的政治科學家認識到,經濟學的方法也許可以被用來研究政治。理性選擇理論正是從經濟學理論中派生出來的,它將現代經濟學中的分析方法和技術應用到政治過程,力圖構建一套新的解釋政治現象和解構政治行為過程的分析模式和框架。奧德舒克在一次對現代理性選擇理論全部成就的評價中指出:“理性選擇理論導致了在一種共同范式和推理結構下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的重新整合,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理性選擇理論的產生為分析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個嶄新視角,而本文正是以這一獨特視角重新審視公民的政治參與。
一、理性選擇理論概說
(一)理性人假設
理性選擇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政治學界興起的一個理論流派。理性選擇理論學者認為,政治生活中的當事人,也像經濟生活中的當事人一樣,服從基本的理性人假設,即他們總是在給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約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2]。
1.理性經濟人
所謂理性經濟人,是指個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實現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抽象出了以自利為行為動機的“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們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每個人參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場秩序下,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無意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亞當·斯密以此為基礎構建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體系。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肯定了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進一步把“經濟人”描繪成會算計、有創造性并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明確指出“經濟人理性”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財富最大化的動機,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算計,對所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理性優化選擇,“經濟人”假設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來,進而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公理。
2.延伸到政治科學領域的“理性經濟人”
發端于20世紀50年代的“公共選擇學派”進一步將“公共選擇理論”定義為“對非市場領域的經濟學研究”,他們將經濟學方法運用于政治學領域,認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領域的“經濟人”。政治學領域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在政治學領域“經濟人假說因與人性和社會實際的巨大契合”,從而“避免了一些學科避諱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虛妄無奈的期許之中,并導致說教與現實的無法對接之苦”,進而認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場中的經濟人”。人們在政治生活中與經濟生活中一樣也為一些稀缺資源而進行爭奪,政治生活中的個體也是為了追求和維護自身利益。
(二)理性選擇范式的基本理論假設
其理論假設包含四方面內容。一是行動的目的是功利的最大化,即一個人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也就是說當個體遇到多種選擇時會挑選其中個體認為是最能服務于他目的的選擇。正如奧爾森指出的那樣,當一個人運用他認為“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手段追求其目標時”,他的行為就是理性的[3];二是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為策略可供選擇;三是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選擇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四是人在主觀上對不同的選擇結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可簡單概括為理性人目標最優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動者趨向于采取最優策略,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收益。理性選擇理論家絕不是第一個試圖假設投票人和政治家都是利益或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來解釋政治現象的人,不過,在這方面的早期研究并不是那么的正式,也不是那么的使人印象深刻[4]。
(三)理性選擇理論的分析方法是方法論個人主義
方法論個人主義不是指利己的個人主義,而是從個人行為的角度進行分析研究。“在理性選擇理論中運用最多的分析工具是博弈論。正是博弈論的運用提高了政治科學的科學化的程度,各類的分析模型才得以建立起來”[5]。
二、傳統理論語境下公民的政治參與
(一)公民參與的涵義
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參與思想源自于近代民主理論中有關人民權利的思想。第一個真正論及公民政治參與在實踐和理論方面意義的近代理論家是托克維爾。隨著人們對政治參與研究不斷地深入,不同學者對政治參與涵義的理解和認識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幾種比較主流的觀點:第一,認為政治參與就是影響或試圖影響公益分配的行為,這是最廣泛的理解;第二,認為政治參與旨在影響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行為或有組織的平民的運動;第三,認為政治參與是個人或個人組成的集體有意或無意地反對或支持、改變或維護一個政府的或團體的某些特征的一切行動(或不行動);第四,認為政治參與是在政治體制的各個層次中,意圖直接或間接影響政治抉擇的個別公民的一切自愿活動;第五,認為政治參與是表示社會成員選擇統治者以及直接或間接在公共政策形成等方面的自愿活動;第六,認為政治參與所指涉的是一般平民直接的、或多或少意欲影響政府人事的選擇,以及(或者)他們所采取的行動而做的法律行為。這種看法可以說是最狹隘的理解。政治參與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投票、政治選舉、政治結社、政治表達、政治接觸、政治冷漠等。
(二)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
政治參與主要受四個因素影響。其一,經濟的發展。一個國家的政治參與水平是與其經濟發展程度息息相關的。一般而言,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是正相關的關系。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來社會利益關系不斷變化,使公民不得不訴諸政治行為來維護并進一步實現自身利益。經濟的發展也使得政府的職能不斷地擴大,這也意味著政府擴大了其在社會中的作用,受到政府作用影響的公民為反過來影響政府,就不得不提高政治的參與程度。其二,社會地位。構成社會地位的各種因素在共同發揮對政治參與影響作用的同時,各自又在發揮著自身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其三,政治心理。從行為主義研究的角度看,任何政治行為都是在某種心理動機的驅使下展開的。政治參與行為也離不開它的心理因素的驅動力。政治社會學對于政治參與心理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三點結論,一是發現了與人們參與活動有關的心理品質——個性特征,認為他自己能夠影響政治家和政治秩序的意識。二是與公民政治參與心理有關的心理品質是他們對于政治體制的信賴感和支持程度,包括對政府、政黨及其領袖的支持,也包括對于國家或社區的摯愛等[6]。三是與公民政治參與相關的心理因素是公民關心政治過程的程度與政治責任感。其四,政治機制。政治參與作為一種政治行為,必然要受到政治自身因素的影響。從本質上講,政治制度和政治體系的階級統治性質對政治參與有重大影響作用。但僅就政治運行機制來說,直接政治參與發揮作用的因素主要有選舉制度、政黨制度、監督制度等。
(三)政治參與的作用
政治參與作為公民實現政治權利的主要途徑,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均發揮重要作用。就其政治作用說,首先,政治參與是公民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和資格,通過政治權力最終實現自己利益的主要環節。同時政治參與又與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有著密切關系。其次,政治參與對政治穩定又產生很大影響。究其社會作用來說,政治參與影響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穩定。公民政治參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要根據政治參與的內容及其所處的歷史條件而定。公民參與所做的成本——效益選擇,可以影響到經濟政策中的資源配置與社會效果,決策中的選擇與結果直接掛鉤,這會迫使公職人員的政策行為合乎經濟效益原則。換言之,帶有支持性的政治參與能夠加強政府或執政黨推進經濟增長政策的力量[7]。
三、重新審視公民政治參與
(一)政治參與中的公民是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理性選擇理論家通過假設投票人和政治家都是利益或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來解釋政治現象。人們在政治生活中與經濟生活中一樣也為一些稀缺資源進行爭奪,政治生活中的個體也是為了追求和維護自身利益。公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會遇到一系列的選擇,這是公民無疑會選擇其中他認為最能服務于他自身利益的選擇。在選舉過程中,公民尋求分享候選人的勝利,喜歡一邊倒把選票都投給勝利者,使自己也能從中沐浴到勝利的光芒。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家的觀點,公民在政治參與中帶有功利色彩的個人主義,這也是基于理性選擇理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二)政治參與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博弈
公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會付出相應的成本,即為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的候選人或政黨犧牲公民個人的時間、交通成本和選舉資助等。在這里就出現了公民政治參與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博弈。當公民政治參與成本高于他所能獲得的政治收益時,棄權或者不再參加投票無疑是一個理性選擇。當政治參與的成本低于公民所能獲得的政治收益時,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對于公民來講是維護和獲得利益的一個理性選擇。在筆者看來,還有一種情況是當政治參與無需成本時,公民有兩種選擇:一是參與政治生活,因為參與成本為零,不會給公民自身帶來損失;二是不參與政治生活,當政治參與成本為零時,每個并無差異的公民知道即使他們棄權,選舉也可以照常進行,而政治體制也會照常運轉[8],在這種情況下就導致“搭便車效應”。
(三)理性選擇導致的社會困境——“搭便車效應”
簡單地說,搭便車效應是群體內的責任擴散鼓勵了個體的懶散。當群體結果無法歸因于任何單獨個體時,個人投入與整體產出之間的關系將不明朗。也即是在利益群體內,某個成員為了本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作的努力,集團內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則由個人承擔。雖然理性的公民可能非常關心是誰或哪個政黨贏得選舉,但是選舉的工具性價值分析結果表明,這些公民仍會逃避為集體事業做出犧牲,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選票在改變選舉結果方面的概率是微不足道的,當一個人的選票不能影響結果時為什么還要去投票呢[9]?在缺乏強制或選擇性激勵的情況下,大團體的成員將回避承擔提供集體物品的責任,“每個人都愿意讓其他人承擔所有的成本,自己能夠照常得到所有集體提供的收益不用考慮自己是否承擔了部分的成本[10]。
(四)解決途徑
“搭便車”這一社會困境的本質是個人對利益的追求導致了次優化的集體結果。如何解決這一社會困境?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選擇性激勵機制,公民政治參與的目的是為了在政治生活中獲得最大利益,當選擇性激勵遠遠超過其預期成本時,公民才會努力參與公共政治生活;二是培養公民的政治責任感,提高公民的政治認同感和政治素質,使得公民對其政治參與的行為充滿自豪感,使公民自覺地履行自己的公民職責。
理性選擇理論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其中的經濟色彩較濃,忽視了許多的非經濟因素,其關于人的理性選擇的假設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人類的行為并非都是由理性思考支配的,理論過于強調人的自我意識和控制,忽視了人類行為沖動、無意識和失控的一面,所以理性選擇理論的適用范圍有限[11]。盡管理性理論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將現代經濟學中的分析方法和技術應用到政治過程,是政治科學的一次偉大的嘗試,也為政治科學的發展提供了一條獨特的路徑。
[1][3][8][9][10]格林、沙皮羅著,徐湘林、袁瑞軍譯:《理性選擇理論的病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 1頁、18頁、239頁、64頁、108頁。
[2][美]安東尼·唐斯著,姚洋、邢予青、賴平耀譯:《民主的經濟理論》,上海世紀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4]漢斯·J·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譯,王緝思校:《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頁。
[5]朱德米:《當代西方政治科學最新進展——行為主義、理性選擇主義、新制度主義》,《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6][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162-165、165-168頁。
[11]沙春彥:《科爾曼的理性選擇主義》,《遼寧公安司法干部管理學報》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