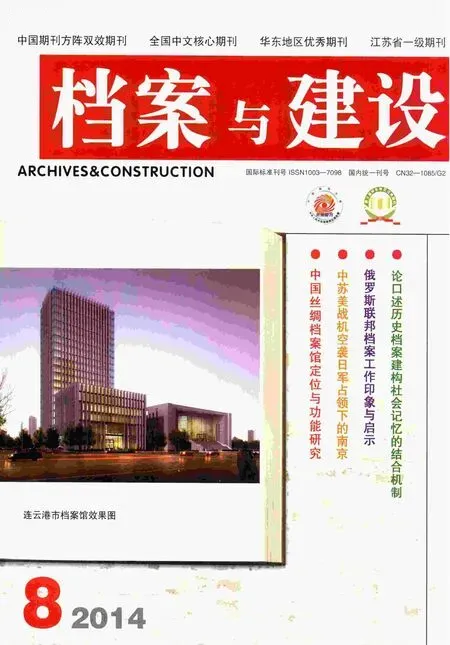論口述歷史檔案建構社會記憶的結合機制
王玉龍 謝蘭玉
(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上海,200444)
自20 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我國口述歷史檔案研究已開展近30年的時間。當前,我國口述檔案研究已經開始興起,并成為檔案界關注的焦點和熱點。簡言之,口述歷史檔案是指為保存社會記憶而采用現代錄音或錄影等新技術對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或目擊者進行采訪,以記錄歷史事件的口述憑證。社會記憶理論認為,社會記憶不是一個復制問題,而是一個建構問題。在口述歷史檔案的形成、收集、保管、管理等過程中,個體經歷與歷史經驗相結合,個體需求與社會發(fā)展相結合,個體回憶與訪談需要相結合,個體記憶與群體認同相互結合。倘若我們把這個過程看作一種社會記憶建構,那么,我們就難以否認口述歷史檔案建構社會記憶中存在著重要的結合機制。
1.個體經歷與歷史經驗的結合
1.1 個體基于歷史經驗回憶過去
施瓦茨認為,過去總是一個持續(xù)與變遷、連續(xù)與更新的復合體[1]。個體記憶雖然極具個體性質,但個體記憶并不是單憑個體的生物官能而保持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經驗基礎上對個體經歷點滴的提取、復活和再現。依據所處的歷史經驗體系,個體將嘗試從過去歲月中提取記憶因子,在現場情境中觸發(fā)、激活和再現。正是歷史經驗的積累沉淀,個體才能更好地提取過去,再現歷史。一般言之,歷史經驗越豐富,經驗體系越完善,個體對過去記憶的提取、復活和再現過程越是順利。這也正是為什么在訪談實踐中我們常常會發(fā)現經驗豐富的受訪者往往更愿意且更善于回憶。正如劉易斯·科瑟所言,盡管現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寫歷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張白紙上來寫的[2]。
受訪者在當前回憶過去,但是必須借助曾經汲取的歷史經驗。就此而言,受訪者的回憶過程可以看作對過去經驗提取的過程。受訪者雖在當前,但是其對過去進行回憶總是基于一定的歷史經驗。更為重要的是,在所有的經驗模式中,其總是把個別經驗置于先前的脈絡中,以確保回憶內容易于理解;同時不難理解的是,受訪者對過去事件進行回憶之前在自身頭腦中已經預置了一個綱要框架和經驗事物的典型形貌。正如康那頓所說,感知一個事物或者對它有所為,就是把它放到預期體系中。感知者的世界以歷史經驗來規(guī)定,是建立在回憶基礎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3]。因此,我們就會理解,人們談起日本人的形象時為什么總會出現“矮小”等類關鍵詞。不過,歷史經驗雖然使受訪者的回憶更加易于理解,但是它也常常會使口述訪談研究遭遇“經驗主義”的危險。因為,受訪者的回憶常常基于歷史經驗,其敘述遵循相應的“經驗模式”,而一旦經驗背離客觀現實,受訪者的回憶便會因“經驗主義”出現失真,從而使口述歷史檔案的真實面臨風險。
1.2 個體經歷的部分回憶積淀為歷史經驗
受訪者的回憶內容中包含著個體對過往歲月的認知、理解和判斷,通過回憶敘述,它們中的部分會逐漸固化凝塑,從而形成一種英國心理學家巴特雷特所認為的“心理構圖”(過去經驗與印象的集結)[4],這種“心理構圖”便是過去歷史經驗的積淀,它將影響個體對未來事物的思考判斷。以張學良口述為例,在張學良多次的訪談中,其回憶內容涉及張作霖、蔣介石、馮玉祥、周恩來等歷史人物,并包含了張學良對這些人物的認識與評價,這些認識與評價通過口述歷史檔案等形式沉淀固定下來,成了后人進一步認識這些歷史人物的重要資料。暫且不論這些認識與評價是否客觀,但其中部分回憶將會積淀形成一種歷史經驗,對后人進一步認識研究相關歷史或將產生一定影響。
1.3 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是個體經歷與歷史經驗結合的結果
在口述訪談中,個體經歷與歷史經驗互相作用影響,并互相結合。口述歷史檔案是口述訪談的結果,其中既包含著個體的過去回憶,又內嵌著某種成分的歷史經驗,是個體過去與歷史的結合,是個體與歷史的統(tǒng)一。
1.3.1 口述歷史檔案基于個體經歷和歷史經驗建構社會記憶
口述歷史檔案包含了個體對歷史事件獨特的體驗、看法、感受,同時彰顯了個體的思想價值觀念。相較于傳統(tǒng)檔案文獻的宏觀的記錄,口述歷史檔案凸顯了人的形象,包含了人的聲音,細微復雜的表情、語氣、面貌,敘述內容常常包含了事件的細節(jié)和獨特的視角。雖然口述歷史檔案不一定總是準確無誤的,但它很容易將人們拉進過去的場景中,將歷史事件相關記憶生動地再現到當今人們的眼前。口述歷史檔案因為包含了個體的記憶,從而使得社會記憶建構顯得富有意義和價值,“正是我的生活所具有那些獨一無二的和無法重復的特點,才使敘述變成一件有價值的事情的[5]。”正因為如此,口述歷史檔案得以建立一種生動豐富的社會記憶。我國大型紀錄片《大魯藝》引用穿插了大量的口述歷史資料,100 多位平均年齡90 歲的親歷者以口述的方式描繪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延安文藝運動的生動情景。通過片中耄耋老人的生動口述,我們仿佛又看到了當年那些進步青年和文藝工作者不畏艱辛、風塵仆仆地從大城市趕赴延安的形象,以及當時延安文藝運動紅紅火火的創(chuàng)作場面和勞動場面。
此外,“我們對現在的體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有關過去的知識。我們在一個與過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聯系的脈絡中體驗現在的世界[6]。”口述歷史檔案中蘊含著許多構成“史料”的“個人經驗的過去事實”,為人們認識歷史規(guī)律提供基礎,為人們的行動提供指導,因此,口述歷史檔案基于歷史經驗建構起來的社會記憶蘊含了歷史、社會發(fā)展的知識和規(guī)律。《大魯藝》中的口述歷史資料量大而繁瑣,每一個口述看似是一個細小而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jié),但正是這些“生活細節(jié)”中蘊含了我國老一輩文藝工作者成長軌跡,體現了文藝運動對中國革命發(fā)展和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性,對我國當下文藝創(chuàng)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3.2 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受個體經歷和歷史經驗的影響
一方面,個體經歷和歷史經驗的變化會影響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個人的經歷和歷史經驗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既然個體回憶是個體基于歷史經驗對個體經歷的回憶,那么個體經歷和歷史經驗的變化也必然對個體的回憶產生影響,即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受個體經歷和歷史經驗變化的影響。如隨著張學良自身經歷與處境的不斷變化,張學良對過去有了不同的認識,在不同的訪談中回憶內容亦有不同,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口述歷史檔案。另一方面,回憶的主體性和“經驗主義”影響口述歷史檔案建構社會記憶的客觀真實性。口述歷史檔案包含著個體對過去的回憶,包含了一定主觀性。同時,口述歷史檔案中蘊含著歷史經驗,可能會使回憶陷入“經驗主義”的誤區(qū),從而妨礙口述歷史檔案內容的客觀真實性。
2.個體需求與社會發(fā)展的結合
2.1 社會發(fā)展為個體需求表達提供支撐
當今社會發(fā)展愈趨多元化、民主化,更加注重個體的發(fā)展與個體需求表達;社會文化的發(fā)展繁榮和城市記憶工程的深入開展,使民眾的文化意識和記憶權利意識逐漸增強,為了搶救即將消失的記憶,我國部分檔案部門已經開始注重收集、保存一些珍貴的“聲音”資料;我們處于一個科學技術迅猛發(fā)展的信息時代,信息技術的發(fā)展日新月異,新技術、新手段、新方式層出不窮,為個體需求的表達提供了技術平臺與手段。諸如錄音機、攝影機、計算機的廣泛使用,為口述歷史檔案的形成和保管提供了前提條件。錄音、錄影等電磁技術設備能夠全面記錄人物的外貌、表情、動作,更直觀地反映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呈現更加生動豐滿的人物形象,彰顯細節(jié)的魅力。可以說,社會觀念的轉變、文化的發(fā)展以及信息技術的迅猛發(fā)展為個體需求表達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支撐。
2.2 個體需求的表達彰顯出時代特征
“事實上,社會上每一個人,都經常在言行上宣稱自己的社會存在;以‘過去’來宣稱自己的社會重要性[7]。”因此,王明珂認為,口述歷史訪談中的個體通過回憶對過去賦予有意義的詮釋,以強化或修正某種社會認同。口述歷史檔案中的分歧則表現了不同社會人群對過去的選擇與詮釋權的競爭。當前社會民主的發(fā)展則要求尊重個體話語權力,以此滿足個體發(fā)展的需求。社會各界的專家學者逐漸體認到一部真正的歷史、一個真實的社會并不只是一些精英人物、社會上層的思想與意識形態(tài),以及典型的文化特征構成。要想避免我們的歷史成為單純的精英人物的歷史、片面的歷史,學者們呼吁重新關注被忽略遺忘的底層人民,讓沉默的人們開口說話,以建構符合當前時代要求的豐富立體的社會記憶。口述訪談與口述歷史檔案恰恰把關注的焦點移向了這部分群體身上,關注他們的表達需求,順應了民主時代發(fā)展的潮流。近年來,史學界和檔案界突破了“精英歷史”研究的傳統(tǒng)史學藩籬,開始把目光投向底層人民,試圖構建立體化的社會記憶。如,常熟市檔案局在紀念抗戰(zhàn)勝利60 周年之際深入當年日軍在沿江登陸的滸浦、徐市、董浜等鄉(xiāng)鎮(zhèn),采訪了親歷日軍進犯常熟的耄耋老人;天津泰達圖書館為了豐富館藏,工作人員走訪了曾經參與過開發(fā)區(qū)起步階段開發(fā)與建設的創(chuàng)業(yè)者們;上海師范大學蘇智良教授為了揭露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士兵對中國婦女的暴行,采訪了依然健在的慰安婦老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曾以“移民史”作為口述歷史的一個課題,訪談了數千戶普通民眾[8]。
2.3 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是社會發(fā)展與個體需求結合的結果
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體現了社會發(fā)展和個體需求的結合。一方面,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要體現當前時代的特征。口述歷史檔案建構社會記憶只有體現當前時代的特征,才具有現實意義,才能滿足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這要求我們在開展口述歷史檔案研究工作時要關注當前社會發(fā)展特點和趨勢,把握好研究主題,為一些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口述歷史檔案資源支撐;另一方面,開展口述歷史檔案工作中只有表達個體的需求,彰顯個體的價值,口述歷史檔案工作才能得到社會和人民的支持。這就要求我們在開展口述歷史檔案資源建設時,要關注個體的需求和發(fā)展,注重收集和保存反映底層人民的記憶。
3.個體回憶與訪談需要的結合
3.1 訪談需要為個體回憶提供框架
口述訪談具有一定的規(guī)劃性、目的性。從眾多口述實踐工作來看,不論是以人物為訪談中心,或是以事件為訪談中心,還是以主題為訪談中心,都暗含著一定的規(guī)劃性、目的性,都是事前安排的。從某種角度而言,訪談者所提的問題實際上包含了對受訪者敘述所做的第一道詮釋。總之,口述訪談絕不是漫無目的的閑談,早在訪談之前,訪問已經通過訪談提綱決定了口述的方向。“口述歷史訪談的實踐證明,受訪者如果沒有訪談者的適當引導可能還會脫離整個訪談的主題,這樣記錄的口述歷史可能僅僅是受訪者的一部零散的‘敘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場嘮叨而已[9]。”從本質看,口述訪談的提綱為個體回憶提供了敘述的框架,為口述劃定了范圍。“正是歷史學家選擇了受訪者并指定了他感興趣的領域[10]。”事實上,我們可以使訪談對象除了注意口述工作者主動的層面(如個人的求知欲、追求社會正義之理想)之外,至少還要考慮到社會認同上的需求如何刺激人們投入某類口述歷史的工作,或者是國家機器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獎勵、資助等措施等,從而形成對特定主題的探索。
3.2 個體回憶豐富訪談內容
邁克爾·弗里施(Michael Frisch)在 其《分享的職權》(A Share Authority,1990)一書中提出,采訪者以問題塑造了對方的回應,抽取存在記憶里的資料,提供學術研究使用。但是,受訪者在回想和描述自己的動機和行為時,也是不斷地在詮釋和分析之中,因此,對訪談的詮釋也不完全落在訪談者這一方的麥克風上。歷史學家埃利·凱杜里(Elie Kedourie)曾指出,人類的活動并不完全是連貫又有目的性的,多半都是錯綜復雜抉擇的組合體,根本無法預測其效應。口述歷史既記載事先有計劃的事,也記錄意外偶發(fā)的事[11]。顯然,訪談框架并不意味著將受訪者關進一個封閉的空間,在口述回憶時,受訪者這一主體仍具有表達和建構社會記憶的諸多空間。很多學者表示,有時我們會從看似“偏離主題”的敘述中獲得意外的驚喜,這些“偏離主題”的敘述可能蘊含著不為人知的過去歷史的事實,因而成為歷史的重大發(fā)現,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豐富原本的訪談內容。對此,唐納德·里奇提醒我們口述歷史總是朝向被忽略的知識領域發(fā)展,最好的發(fā)現往往就是在你原先并不準備提出的問題上,或是在你事先研究時完全沒有注意到的領域里。
3.3 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是個體回憶與訪談需要結合的結果
在整個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和受訪者這兩個主體并不是單獨存在著,而是互動結合的關系。“在這種雙向交流的互動過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建立了一種平等的合作關系,通過積極傾聽與融入對象,并與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產生互動關系,從而深入理解被研究的對象與現象[12]。”口述歷史檔案作為訪談主體雙方互動的結果,既鑲嵌著訪談者的問題框架,又包含著受訪者對過去的回憶敘述。因此,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可以看作是訪談主體雙方互動的過程。訪談者根據一定的目的設計訪談的框架和問題,引導受訪者的回憶,以確保將個體過去的記憶按照一定的形式進行組織、提取、保存和傳承,因此,訪談需要往往決定了口述歷史檔案建構社會記憶的方向,決定了口述歷史檔案的主題和結構;個體通過自身的回憶,使訪談者原本空洞的訪談框架漸漸變得豐滿鮮活起來,為記憶的建構傳承積蓄養(yǎng)分,因此,個體回憶往往決定了口述歷史檔案建構社會記憶的細節(jié)和內容。
4.個體記憶與群體認同的結合
4.1 群體認同塑造個體記憶
認同作為社會心理學研究的范疇,指“一種同化與內化的社會心理過程,它是將他人或群體的價值、標準、期望與社會角色,內化于個人的行為和自我概念之中[13]”。群體認同理論試圖解釋個體所獲得的對自己所在群體成員身份的認識,是如何影響他的社會知覺、社會態(tài)度和社會行為的。在社會交往中,人們總是努力獲得或維持積極的群體認同;同時,群體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體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認知行動。這種群體認同就像一個管道,規(guī)定著個體記憶的方向和內部結構,塑造著個體記憶的樣態(tài)。因此,個體回憶的內容往往是經過群體認同形塑的產物,“個體記憶中相當一部分是從社會生活中獲得,在與他人的社會活動中被共同憶起,并且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中重建,以符合個人的身份認同[14]。”
4.2 個體記憶強化群體認同
回憶敘述不經意間的重復,往往不只是再現過往歲月,更是塑造口述者當前的群體認同。不難發(fā)現,可供集體回憶的一段往事,可以成為一個集體的歷史;倘若重復講述這些故事成為一種傳統(tǒng),便會有助于強化集體成員間的凝聚力。王明珂對此做了解釋:即使在家庭這樣基本的人群單位中,人與人之間的凝聚,都需要借著經常慶祝該人群的起源(結婚紀念日、家庭成員的生日等),并借著述說家庭故事(有時需要靠照片、紀念品之助),來維護及增強集體記憶。隨著家庭的發(fā)展,有些往事不再被提起,有些照片被毀棄,家庭照片簿被重排。這都顯示著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也需要經常以集體記憶來維系,而家庭成員關系的改變也賴重組“過去”來表現[15]。筆者認為,在口述訪談中,受訪者有意或無意地重復、強調、忽略甚至歪曲某段記憶,都是極具目的性的行為。當受訪者不斷重復回憶敘述一段往事,采訪者應該意識到受訪者可能是在有意或潛意識地強化所處群體的認同。
4.3 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是個體記憶與群體認同結合的結果
個體在群體認同的影響下進行回憶敘述,群體認同借個體回憶敘述得以強化,在這一作用關系下形成的口述歷史檔案,不僅呈現了個體的記憶,同時展現了群體認同。因此,口述訪談絕不是一場“你來我往”的隨意的對話,口述歷史檔案也絕不僅是簡單的個人回憶錄,它在無形中建構了個體和群體記憶,塑造了群體認同和觀念,乃至影響著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口述歷史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建構兼具個體性和群體性,是個體記憶與群體認同結合的結果。
筆者認為,依據這一特性,我們不僅可以透過口述歷史檔案去了解個體獨具特性的經歷和歷史細節(jié),同時還可以分析某個群體認同,把握群體認同的特點和規(guī)律,并借此來影響個體的認知和行為。那么,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做出這樣的設想:在建設和諧社會和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檔案部門合理有效地收集、保存和開發(fā)能夠反映中華民族特色和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群體認同的口述歷史檔案資源,對于增強整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具有重要意義。
[1][2][1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2:2;60;69
[7][10]定宜莊、汪潤.口述史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1;77
[3][6][美].保羅·康納頓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
[4] Frederick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199~202
[5][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編,李斌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7
[8]王玉龍.口述歷史檔案建構社會記憶的選擇機制探析[J].檔案學通訊,2013(5):101~104
[9]楊祥銀.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的主流趨勢[J].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1(2):68~80
[11][美]唐納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31
[12]李向平、魏揚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116
[13]李素華.對認同概念的理論述評[J].蘭州學刊,2005(4):201~203
[15]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