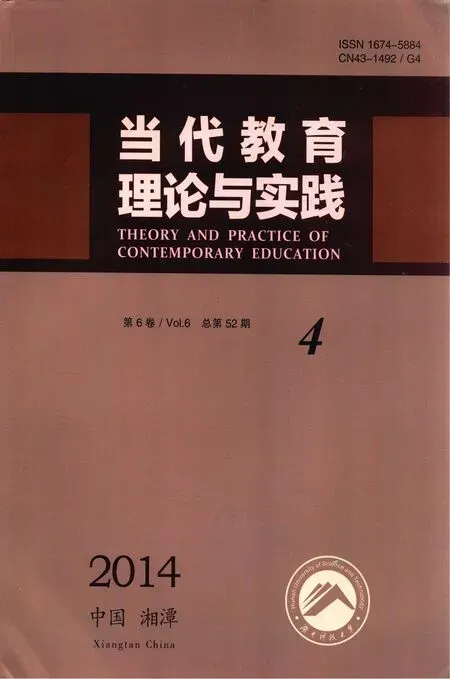不同政治局勢下的中國譯學史發展①
張奕欣,曾曉芳
(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湘潭411201)
談及翻譯的歷史,陳富康的《中國譯學史》是不可不談的一部著作。該著作分別從四個階段詳細地描述了中國譯學的發展過程,即中國古代、晚清民初、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后[1]。這些都有利于我們了解中國譯學發展的曲折歷史以及推動中國譯學蓬勃發展的一些重要因素,進而可以得知促進翻譯發展的因素無外乎是政治、經濟。本文著重分析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政治局勢是如何促進翻譯飛速發展的。
1 中國古代的譯學發展
眾所周知,佛教不是我國的本土宗教。理論上來說,作為外來宗教,它對中國的影響本應弱于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然而,這個由古印度的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傳來的宗教到至今為止都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民,融入于中國燦爛的五千年文化中。而道教在中國的發展卻止步不前。究竟是什么造成如今這樣的局面呢?
毫無疑問,翻譯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功不可沒。但是,為什么古代民眾愿意花費大量的時間鉆研佛經,而不選擇大力推行本土的道教思想呢?這得從佛教和道教的核心思想說起。佛教宣傳的思想是忍耐,號召勞苦大眾要順從,來世就可以富貴,這恰好符合統治者的思想要求。因此相較于道教倡導的無為而治,統治者更樂于舉國推行佛教。于是就有了佛教現今的遍地開花。前有苻堅邀請鳩摩羅來什來華宣講,后有玄奘遠赴西天取經,無一不反映當時統治者對佛教的熱衷程度。
由于統治者想維護自身利益,加強政權統治,佛教如竹筍般飛速發展。與此同時,佛經翻譯也得到了良好的發展。然而,有關佛經的譯著雖然比較多,但是與之相關的譯論卻十分罕見。并且,如果要敘述我國古代譯學理論,需追溯到六朝以后的佛經譯論,而中國早在秦始皇時期就有佛教了。
縱觀我國古代的佛經譯論,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譯經理論大多都是零星的、片斷的譯論,但合而觀之,所涉及的方面較廣,仍具有研究價值。例如:在關于專名的音譯問題上,玄奘提出了“五種不翻”理論,即神秘語,多義詞,中國沒有的無名,久已通行的音譯,以及為宣揚佛教需要的場合,凡遇此類名詞,皆宜不翻。“釋迦牟尼”如果意譯為“能仁”,則其地位便似乎不及孔子與周公,“般若”一詞顯得莊重,意譯為“智慧”就顯得輕淺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其中“五失本”抓住了涉及翻譯的直譯與意譯、質直與文麗、質與量的矛盾和統一;“三不易”涉及了翻譯活動的主體性問題,是系統的、辯證的、先進的中國傳統譯論。“五失本,三不易”涵蓋了翻譯學本體和主體問題,具有全面、系統性。而且,其中的許多觀點非常先進,與現代翻譯理論和語言學觀點有相通之處,對中國傳統譯論進行現代的詮釋具有深遠的意義,是構筑中國當代翻譯學的一塊基石。
二是譯經理論在服務于外來宗教的同時,借鑒了本土文化,并扎根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使之易于中國人民接受。例如,譯經理倫中常常將佛經中的經典故事與中國傳統經典著作《詩經》、《尚書》等。例如支婁迦讖把“真如”譯作“本無”,安世高譯《陰持入經》把“色、受、想、行、識”五類構成人的因素譯作“五陰”,再如支謙譯《般若波羅密經》為《大明度無極經》,把“般入”(智慧)譯作“大明”、“波羅密”(到彼岸)譯作“度無極”,均取自《老子》的“知常曰明”和“復歸于無極”。佛經以翻譯為媒介進行的傳播促進了中國語言、文學、民間藝術、本土信仰、宗教組織、社會風尚等諸多方面的新發展;此外源于本土的哲學思想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這是佛經翻譯所產生的正面影響,而這些思想的傳播逐漸為封建統治者所用,成為長期桎梏人民思想的束縛,佛教的適時而進,佛教的傳入即是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也是一種關于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人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中國的勞動人民的精神訴求。
佛經翻譯到北宋時期基本結束。此后,由于動蕩不安的局面和統治者閉關鎖國的政策等原因,除了少數民族進行了少許翻譯活動外,翻譯活動趨近于無。直至17世紀,西方天主教開始打開中國市場,翻譯活動才開始復蘇[2]。但與佛經翻譯相比,未能產生比較重要的翻譯理論。此外,由于羅馬教廷干涉中國內政,不少傳教士不只能動中國文化禮儀和習俗,18世紀初遭天主教到統治者的驅逐,直接影響到中外交流和翻譯的發展,標志著我國古代第二次翻譯活動又一次停止[3]。
2 晚清民初的譯論
由于清王朝的閉關政策,中國盲目自大,沒有趕上“蒸汽時代”。隨后,在1840的鴉片戰爭中,帝國主義列強憑借火力十足的槍炮打開了中國塵封已久的大門,再加上清政府自身的腐敗,中國淪為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時,在帝國主義如狼似虎似地瓜分中國領土時,各種西方思想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了救國復興,也開始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知識,以尋找強國之路。
在這樣一個復雜的政治背景下,翻譯活動也開始復蘇,日益頻繁,并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此時,有關翻譯的理論也隨之增多,也更加豐富了。翻譯活動也不再局限于宗教翻譯,而涉足于科技翻譯。例如,以嚴復,張之洞為代表的官僚洋務派就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翻譯活動的蓬勃發展,體現了統治者開始意識到翻譯活動的價值,注重培養翻譯人才、組織譯者工會等。但是由于自身的封建思想的桎梏,在翻譯外國著作中,會反對翻譯國外有關“男女平等”等內容的書。
雖然洋務派尋求翻譯內容的突破,但在中國近代對翻譯理論作出最大貢獻的當維新派莫屬。例如,馬建忠、梁啟超、鳳謙等人,最早提倡廣譯,便突破了洋務派及教會人士專譯格致類書的狹隘格局,隨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又提倡快譯和譯日文書。
這一時期,涌現了大批翻譯家,他們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譯論。如嚴復提出了翻譯的“信、達、雅”標準,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林紓強調發展翻譯事業,才能“開民智”,才能讓國人了解列強的兇惡和陰謀,才能抵抗歐洲列強,此外,他認為救國應當靠“實業”,所以他在翻譯過程中注重實業發展;以及魯迅和周作人這對兄弟強調翻譯對于“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引導國人進步意義重大,注重“異域文術新宗”的藝術性,強調翻譯文學作品的怡情和涵養深思作用。并且周氏兄弟不像梁啟超那樣,簡單地以翻譯直接作為改良社會的武器或論證的工具。他們在強調翻譯的社會功利目的之外,同時不忘記文學本身作為藝術的特點和功能。
3 民國時期的譯論
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民國時期主要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中國文化,并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雖然只有短短三十幾年,但在這一時期,文壇上和譯壇上能人輩出。但此時與晚清時候相比,人數雖多,更多不是靠思想、政見來劃分,而是依據社團與流派角度來區分。其中,建樹比較大的社團是文學研究會、創造社、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新月派和論語派等。
其中,文學研究會的朱自清雖然有關翻譯的論述不多,但是其對譯界的影響程度不可小覷。例如,他將歷來譯名的方法概括為五種:一是音譯分譯,即一般音譯,一半意譯;二是音譯兼譯;三是造譯;四是音譯,五是意譯。他對這五種方法逐一作了分析,他認為,“音譯分譯”歷來少用,原是一種嘗試,并不作為正法,其缺點是既不像音,又不像義。“音譯兼譯”則極難,“如要兩全,必然兩失”,吃力不討好。“造譯”除了譯化學書常用外,也很少用,而且這種新詞令人音義茫然。
此外,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是民國時期另外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新文學社團。郭沫若在文化學術很多領域都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貢獻,精通日、德、英等國文字,一生翻譯了大量作品。他在翻譯上理論上也有其獨到的見解。他的譯論也影響到了郁達夫、成仿吾等人。同時,無可諱言,當時他的文藝思想帶有宗派主義和唯心主義色彩,這也影響到他的翻譯理論。他不贊成矛盾、鄭振鐸主張的翻譯介紹“應該審時度勢,分個緩急”的意見,認為這是“阻遏人自由意志”,“是專擅君主的態度”。并且,他強烈翻譯文藝的“功力主義”,認為這是“文藝的墮落”。他還自創了“風韻譯”,強調“詩的生命,全在它那種不可把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于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
民國時期譯論史上的批評、討論和爭辯是很火熱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翻譯理論的發展。例如,新文化運動者,一開始便以林紓,甚至嚴復為批評的靶子。雖然,這些批評未能充分肯定嚴、林兩位對翻譯事業的貢獻,但對于端正新文化運動中的翻譯事業的方向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就涉及翻譯的“外部研究”也在潛移默化的豐富譯論,為我國譯學史上增添了奪目一筆[4]。
4 新中國成立后的譯論
新中國成立后,百業待興,翻譯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新中國翻譯理論史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文革前,翻譯工作隨著新中國的發展而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翻譯理論工作也隨之得到了重視。在此階段,就有《世界知識》社創刊了《翻譯》月刊,其代表編輯有董秋斯、林淡秋、胡仲持等翻譯工作者。除此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出版創刊了《翻譯通報》月刊,該刊適應了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要求,并把加強翻譯工作者之間的聯系,交流翻譯經驗,展開翻譯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翻譯標準為宗旨。當時,由于我國與蘇聯關系密切,大力宣揚共產主義,中共中央宣傳部還設立了斯大林著作翻譯室,全面、系統地開展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
第二個階段是文革期間,由于當時對知識分子的打壓以及閉關鎖國政策,中國文化停滯不前,翻譯研究工作基本停滯。但港臺地區以及旅居海外的翻譯研究者仍在繼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香港的翻譯工作者自發組織了“香港翻譯學會”,經常組織各種學術活動,并出版會刊《譯訊》。學會幾乎每年都舉辦一次較高水平的翻譯研討會,并將這些研討會上的論文編為《翻譯叢論》出版。此外,香港還出版了許多翻譯大家的譯學著作,是當時不可多得的翻譯材料。臺灣地區的翻譯活動也非常活躍,出版了許多翻譯著作,有關翻譯理論的書和論文也出了一些。但是,在當時雖然臺灣地區的翻譯人才眾多,翻譯作品豐富,但卻沒有一個全省的翻譯工作者的統一組織。與香港相比,就落后了一大截。
縱覽中國譯學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翻譯研究,尤其是翻譯理論研究正在不斷的自我完善、日趨成熟。然而翻譯活動要得到健康發展,則需要國家政局穩定的支撐、國家明朗政策的引導,以及對翻譯活動者的開拓創新精神的大力支持與鼓勵。
[1]陳福康.中國譯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廖七一.當代英國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4]許 鈞.翻譯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