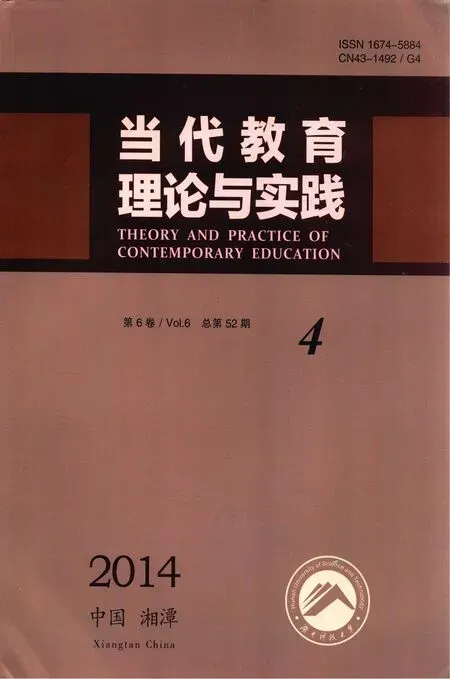略論中國近現代譯家及其譯學思想①
劉一純,伍 攀
(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湘潭411201)
方文華教授將清末民初時期的梁啟超、嚴復及林紓稱為當時的“譯壇三杰”,他們無論在譯作類型或翻譯觀念上都大有建樹,對我國的翻譯事業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五四”時期,魯迅、郭沫若和茅盾不但在文學上熠熠生輝,在翻譯界也成就非凡。該書為再現譯者的風格,在不同章節中提供其譯作片段但不妄加評論由讀者裁定優劣,并且大量錄用翻譯名家的譯學言論,為廣大翻譯理論研究者提供立論的依據,同時反映了我國近100年來翻譯工作者的努力和中國翻譯事業的飛速演進。
1 清末民初時期的翻譯活動
鴉片戰爭之后,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等愛國志士渴望接收新的文化、思想觀念,他們不滿于現狀,挑戰舊的傳統觀念與文化。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形式都在發生了巨大變化,翻譯界也順應潮流大量翻譯了西方的文化知識,強有力的推動了新文化運動,開辟了中國翻譯史上的一個新紀元。梁啟超、嚴復和林紓并稱為譯界“三杰”,改造了當時中國人落后的思想觀念,留下了許多不朽的翻譯作品。這一時期大量外國詩歌、小說和戲劇涌入中國,促進了中國文化內容和形式的發展。同時,由于廣大譯者的不懈努力,中國文化也在西方廣泛傳播。
梁啟超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著名學者和翻譯理論家,他集政治家、文學家、翻譯家于一身,對當時我國的翻譯做出了杰出貢獻[1]。梁啟超在上海南京路創建大同譯書局,宗旨為“本書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來變法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堂各種功課,以便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梁啟超把當時小說的文學價值以及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譯了外國小說《世界末日記》《十五小豪杰》《俄皇宮之人鬼》《佳人奇遇》。梁啟超在翻譯這幾部小說時用得都是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對我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梁啟超對翻譯做大的貢獻就是從一定高度上引導翻譯的潮流。他要求譯者首先必須慎重選擇所譯之書,其次要遵循翻譯的規則,特別是必須統一譯名,再次是要重視翻譯人才的培養。他對我國佛經的翻譯也非常重視,進行過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有許多新的發現。
嚴復曾留學英國,回國后擔任過京師大學堂附設的譯書局總辦及北京大學校長,有著非凡的人生及見識[2]。嚴復對中國翻譯事業上的第一大貢獻就是將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學》翻譯過來,名為《天演論》。他的《天演論》是有選擇、有取舍、有改造地翻譯而并非忠實的譯本。他對外國思想的介紹力求服務于當時中國的需要而并非生搬硬套。《天演論》以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科學性和說服力,激起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使他們走上了革命道路,為后來的救亡運動做了一次社會總動員,在中國現代史上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嚴復對中國翻譯事業的另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信、達、雅”三字翻譯標準。他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明確提出了:“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易》曰:‘修辭立減。’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不僅在當時、而且對以后近百年的翻譯史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后來的譯者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用這一標準來衡量自己的翻譯,無一不受到這一標準的制約。
林紓不懂外文,然而他卻傳奇的走上了翻譯的道路,成為了譯壇泰斗[3]。其譯作數量驚人,碩果累累,如《迦茵小傳》《孝女耐兒傳》(現譯《老古玩店》)《塊肉余生述》(現譯《大衛·科波菲爾》)《賊史》(現譯《霧都孤兒》)等。他以酣暢優美的譯筆開創了我國翻譯事業繁榮的局面,在他的帶動下,翻譯隊伍日益壯大,促進了我國翻譯事業的發展。當時國人讀了林紓的翻譯小說,了解了西方社會的風土人情以及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因此,林譯小說風靡一時。林紓與別人合作譯書,《巴黎茶花女遺事》一經問事,便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讀者將此書譽為外國的《紅樓夢》。它以發展真性情的思想啟發了人們想到婚姻自由,從而覺悟到必須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反封建。《茶花女》給沉悶的封建制中國帶來了新的觀念,激發了世人變革的熱情。《黑奴吁天錄》(現譯《湯姆叔叔的小屋》)是林紓的另一大譯著。此書對美國反對奴隸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被林紓翻譯后對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起到了作用。林紓不僅把我國的翻譯事業推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且也促進了中西比較文學的發展。林紓翻譯的小說讓國人看到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激發了讀者的愛國熱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說當時在中國的地位。
清末民初的科學翻譯形成了我國翻譯史上的“高潮”,給國人帶來了新的觀念,促進了我國各科學門類的發展,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等領域產生了影響。這一時期對外國小說、詩歌和戲劇的翻譯活動開始活躍起來。通過一些翻譯活動,中國文化也在域外得到了傳播。
2 民國時期的翻譯活動
民國時期我國的翻譯活動空前繁榮。“五四”時期是我國近代翻譯史上的分水嶺。“五四”以前,通過梁啟超和嚴復等翻譯家的艱苦努力,介紹先進的西方思想、價值觀念和社會生活,使中國人民意識到了自己的落后。中國的舊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覺醒,同時新的知識分子被孕育出來。“五四”以后,魯迅等一批具有先進思想觀念的知識分子開始翻譯西方書籍,瞿秋白等革命前輩開始介紹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西方各國尤其是俄國和蘇聯的優秀文學作品開始介紹到中國。這一時期的翻譯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變化,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我國翻譯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魯迅創作與翻譯并重,是我國民國時期的大文學家、大翻譯家[4]。他翻譯過許多俄羅斯及蘇聯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捷耶夫的《毀滅》果戈里的《死魂靈》。魯迅在翻譯《死魂靈》時耗費了巨大的心力,但在翻譯過程中對歸化和異化形成了獨特的看法,此后的翻譯家稱贊他這部譯作為“直譯”的典范。魯迅在翻譯時以嚴格的標準約束自己,帶著高度的責任感,一絲不茍的處理譯文。他總是竭盡全力了解清楚了原文的意思才動筆翻譯,從不胡亂發揮。這種嚴肅認真、精益求精的翻譯態度為當時的廣大譯者樹立了榜樣,狠狠打擊了胡譯、亂譯等盛行之風。他對翻譯標準的觀點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面,一當然力求易解,一則保持著原文的風姿。”他針對有人所謂“與其順而不信”提出了“寧信而不順”這一原則,雖有“矯枉必須過正”的意味,但并不是“死譯”。他主張直譯,一是為了使譯文容易理解,二是為了保存原作的風姿。魯迅提出的“硬譯”理論,為翻譯評論家評論譯作提供了新的標準。
郭沫若以優美的譯筆享譽海內外,對中國翻譯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5]。他的重要譯著有:《沫若譯詩集》、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上、下卷,俄國屠格涅夫的《新時代》、英國的《雪萊詩選》等等。郭沫若把翻譯視為向國人傳播知識的途徑,把世界一流的文學作品推薦給中國讀者。與魯迅一樣,他提倡嚴謹的翻譯作風,堅決反對“胡譯”和“濫譯”。郭沫若嚴肅認真的對待翻譯事業,認為譯者在動筆之前,必須把握原文作者的情感,認為譯文和原文必須在意思上一直,但形式上不必拘泥小節。郭沫若強調譯者的責任心,在翻譯之前必須慎重選擇材料,翻譯過程中遵循“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他還說道“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廣泛地參考,多方面賜教,盡量的琢磨。”
民國時期中國對外國文學的譯介中以俄蘇文學的規模最大[6]。“五四”運動以后,中國開始大量翻譯俄蘇文學作品。中國文化也一直吸引著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后,列寧對中國及漢學研究十分重視。俄蘇的漢學家全面研究和翻譯中國的詩作,包括古代詩歌,如詩經、楚辭、漢賦和樂府,以及唐詩和“五四”運動之后的現代詩歌。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文學界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由于明治維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其文學藝術也空前繁榮。中國學者、文學家肯定當時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中國的翻譯家也對日本文學持肯定態度,大量翻譯了日本的文學作品[7]。
“五四”時期,英國文學翻譯隊伍也日益龐大,涌現出一大批如卞之琳、楊憲益、張谷若等的杰出翻譯家。這一時期翻譯的英國文學作品有詩歌、戲劇、小說等,涉及的作家主要有莎士比亞、雪萊、笛福、拜倫、蕭伯納、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等,他們分屬古典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唯美主義、象征派、意識流文學等流派[8]。
3 建國后的翻譯活動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翻譯事業也蓬勃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翻譯隊伍不斷壯大,他們不僅能譯出高質量的作品,而且總結出了全面系統的翻譯理論。但盲目地追求洋理論,忽略我國翻譯理論的優點,只會導致翻譯活動的混亂。因此,羅新璋、劉宓慶和黃龍等人提出了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翻譯理論體系的設想[9]。20世紀末,我國相繼出版了黃龍的《翻譯學》、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劉宓慶的《當代翻譯理論》、陳福康的《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等大部頭成系統的翻譯理論著作。
20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的這一次翻譯高潮,無論在規模、范圍、質量水平還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上都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我國的翻譯工作者所翻譯的領域已不是文學藝術的“一枝獨秀”,而是軍事、外交、科技、社科、法律、貿易、文教、衛生等領域的“百花齊放”。這一次翻譯高潮的出現,首先是由于全球信息時代的來臨,交流知識和信息都離不開翻譯。此外,這次翻譯高潮的出現又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強國之路的結果。中國要在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等領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強與其他國家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合作與交流,而這些合作與交流活動都離不開翻譯。對翻譯標準認識的日趨統一大力推動了我國的翻譯工作,特別是在過去的20年中,我國的翻譯隊伍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通過嚴謹認真的翻譯活動,與西方國家介紹和交流先進科技知識、優秀文藝作品以及民族文化,為我國四個現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斷做出新的貢獻[10]。
[1]孟祥才.梁啟超傳[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2]皮后鋒.嚴復大傳[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3]張俊才.林紓評傳[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
[4]劉緒源.解讀周作人[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5]秦 川.文化巨人郭沫若[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6]李明濱.中國與俄蘇文化交流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王向遠.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8]王宏志.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
[9]羅新璋.翻譯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10]張柏然.面向21世紀的譯學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