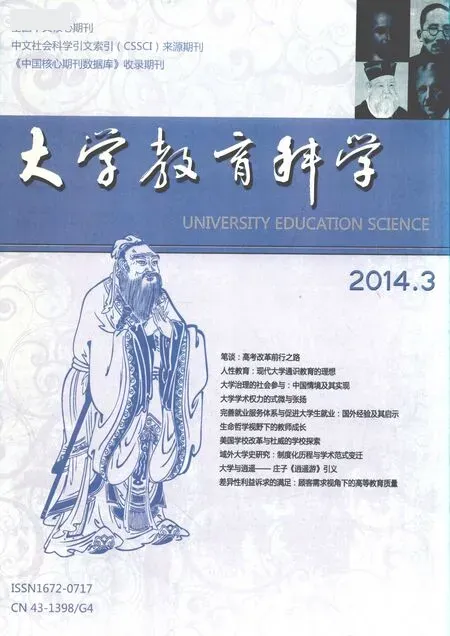人性教育: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理想
□ 龍躍君
現代大學教育面臨著許多困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工具理性的思維下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分離,從而造成所培養的人可能成為失去自然本性的“陌生人”。通識教育作為協調專業教育與自由教育的紐帶,成為現代大學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我國大學當前教育教學改革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影響現代大學開展通識教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觀念與認識方面的梳理是首要的。本文從人性教育的角度對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理想進行了初步探討,希望在認識方面與同行們進行討論。
一、現代大學教育的困境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人類社會總體上仍處于工業社會的時代,同時向后工業時代邁進。就中國社會而言,相關研究認為中國近百多年的變革與發展是急劇的,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一種雙重轉型,既有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同時也在向后工業社會快速跟進。“現代化”成為促進中國強大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困惑。現代工業社會在科學主義背景下,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出現了分離,因此現代社會同時也是危機頻發的時代,如文化沖突、環境污染、能源枯竭、信仰危機等。
現代大學起源于1088年創建的博羅尼亞大學,中國現代大學的歷史也有一百多年。在工業革命前,大學是一個精神培育的場所,主要是人文教育。今天的大學不再是“象牙塔”,已成為各國社會與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如克拉克·克爾所說:紐曼“大學理念”中的大學是一個住著僧侶的村莊;“現代大學理念”中的大學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壟斷的小鎮,這是一個單一產業的城市;“巨型大學理念”下的大學,則是一個充滿無限多樣性的城市。盡管巨型大學的理念有些激進,但大學的這種變化是必然的。大學已廣泛地融入到了社會發展之中,學者們不再只是教書匠,科研與社會服務成為了他們的熱門話題,但大學職能的拓展明顯造成了對“大學之道”的爭議。現代大學發展到近200年,在科學主義的背景下,大學教育明顯地轉向了職業教育或專業教育,對“什么是有教養的人”缺乏深刻的理解。日益細化的專業化一方面使社會整體認識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使不同的專業學科相互隔離,對受教育個體生命構成了壓制,變成了不完整的“單面人”。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式微,使大學變得庸俗而沒有精神,使受教育者完全放棄了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對科學價值的反思。“為了刺激和滿足欲望,人不再區分目的和手段,不再追求崇高和神圣,人性失去了莎士比亞曾描繪過的照人光彩,而演變為一團幽暗的難以自制的欲望”[1]。
我國現代大學產生于我國社會激烈動蕩的年代,是在民族生存危機的關頭,因此其主要改革動力來源于政治的訴求。這樣,其一開始就選擇了激進的、革命式的辦法,先是“改書院淫祠為學堂”、“中體西用”,全面學習和模仿西方現代教育,后來干脆與傳統教育進行了徹底決裂。新中國成立后,為培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急需人才,我國在教育方面采用了前蘇聯的教育模式,更加突出了專業教育。我國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教育和其它方面一樣進行了深入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由于生長在一個奮發圖強、破舊立新、文化革命、實用主義絕對主導的時代,中國現代大學工具理性的思想占據了明顯的優勢。孔子說“君子不器”,我國現代大學人才培養的主要問題正是過“器”,沒有獨立之人格,也沒有自由之思想。
在現代大學發展的歷史中,對大學教育目標的討論一直在進行。歸納起來有三個方面:人文學者們呼吁要培養心智、操守及分析判斷能力,提倡博雅教育;專業教師要求加強專業教育,培養學生的研究開發能力;受市場影響,還有學者提倡要加強學生專業技能的培養,提倡開設實用性、職業性課程。現代大學明顯的趨勢是專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但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薄弱讓人們感到十分擔憂,教育如何在上述三個方面都得到兼顧?于是,我們的教育理念需要認真地梳理,同時要適當改變當前“政治正確性”的價值理性。現代大學在培養沒有自然本性的“陌生人”,這是整個現代大學不得不面對的根本困境。筆者認為,在人才培養中“成人”是根本和基礎的,“成才”則是發展和變化的,現代大學之道應回歸到人性教育的起點。
二、人性教育、自由教育及通識教育
“人性”的概念很早就提出來了。如我國古代告子說:“生之謂性”;荀子對性的定義是:“生之所以然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在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都曾談到過人性。如奧古斯丁認為“人性”就是“內在人”,只有通過“內在人”,教育才能從“符號的游戲”最終指向“事情本身”。在《理想國》第9卷中,蘇格拉底第一次提到了“人里面的人”這個說法。后來,“人里面的人”逐漸變成一個“精神性”的概念,成為人的內在生活的代表。人心“應該思考它自己,按照它的本性活著,也就是說,它應該按照它的本性(在秩序中)得到安置,在它應該服從的下面,在他應該主宰的上面”[2]。但人心的真正處境卻是在“欲望”的作用下忘了自己。按照現代科學的定義,人性是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范疇的概念,人性是指人的本質屬性,包括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由行為、形體、情感、精神、認知、文化等要素組成。
所謂人性教育,就是以人性培養為目標的教育,簡單地說就是關于“如何做人以及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教育。由于歷史的原因,人性教育長期以來不為我國教育所重視。在古代教育中,特別是古希臘、羅馬的自由教育思想中,人性教育是教育的核心。如塞內加(約公元前4年-65)所說,“只要我們還活著,只要我們身為人類的一員,就讓我們來培養人性吧”。后來盧梭以“人的自由”取代“人的理性”,從而對人的本質做出了新的界定。按照盧梭的思想,將人視為自由的存在,就意味著肯定了人的發展的不確定性、開放性和創造性。所以,“教育必須是尊重和維護學生‘自由’、啟迪學生‘自由’的教育”[3]。因此,自由教育始終貫穿著人性教育的宗旨。
自由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在歷史發展上包含古典自由教育和現代自由教育兩個階段。古典自由教育是以“自由學科”為核心的博雅教育。紅衣主教紐曼是古典自由教育思想的偉大倡導者,他在《大學的理想》中指出:自由教育本身僅僅是發展理智,它的目標是獲得杰出的理智。現代自由教育發展成為面向大眾的、科學與人文相結合、“塑造”與“解放”心靈的通識教育。與紐曼不同的是,現代自由教育由關注理性向關注自然轉變。如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觀表現出更加通達的胸懷與開放的心態,由此通識教育的理念及實踐獲得長足發展。赫胥黎認為:“真正的自由教育應該是在自然規律方面的智力訓練,這種訓練不僅包括各種事物以及他們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人類以及它的各個方面”[4]。因此,赫胥黎建議將自然科學、文學、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切教育課程的基礎。而列奧·施特勞斯提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自由教育在于喚醒一個人的心智與卓越,自由教育是從庸俗中解放出來,自由教育在于傾聽最偉大的心靈之間的交談”[5]。
綜上所述,從古典自由教育到現代自由教育,自由教育貫穿的宗旨是人性教育。通識教育是自由教育思想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的集中體現,因此人性教育是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核心。
三、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理想
通識教育的源頭要追溯到蘇格拉底“反省生活”的概念,還有亞里士多德反思公民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古希臘、羅馬時期斯多葛學派“自由”教育的理念。在中世紀,隨著基督教的興起,西方自由教育思想逐步演化為“七藝”教育。到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要求沖破教會束縛、解放人性,自由教育的目標被重新定義為促進個體身心的發展。工業革命后,隨著社會、經濟、科技的迅速發展,知識總量劇增,學科領域和職業分工不斷分化,專業教育在實用主義的催化下開始盛行,并對以古典人文學科為核心的自由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這一矛盾的背景下,在自由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沖突中,通識教育逐漸走進教育的舞臺。因此,通識教育是自由教育理念在現代教育中的體現。
關于通識教育的理想,哈欽斯曾指出通識教育是培養智性的惟一有效途徑,《1978年哈佛報告書》則明確哈佛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是培養20世紀有教養的人。在2004-2006年,哈佛大學重新定義了“受教育的人”,強調課程跨學科的綜合性和靈活性,強調教育國際化和科學技術教育的作用,確定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目標為培養全球公民。在民國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培養“碩學閎材”,要“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主張文理“兼習”。后來,針對過于重視專業培養的思潮,梅貽琦先生提出“通識為本,專識為末”的思想。原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認為,完整的大學教育應以培養現代化的“內圣外王”為目的,而通識教育是達此目的的重要一環。目前,我國高教界對通識教育的理解通行有兩種:一種從知識論的視角,把通識教育理解為知識的全面發展、一般發展或通才教育,因而主張打破專業限制,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另一種觀點則從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考慮,著重在文化傳承、價值取向與社會發展層面,強調人的自由與和諧的發展。
現代大學教育一直存在“通”與“專”兩種人才培養思想,大多數國家是培養專門人才的思路。在科學主義的大背景下,專才教育的選擇是自然而然的,但其弊端也不言而喻。因此,通識教育一直受到現代大學的關注。由于科學主義及實用主義的影響,也由于各國教育“政治正確性”的價值理性,通識教育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即使是在有自由教育傳統的西方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對通識教育理解的多樣性是重要的原因。美國大學對通識教育的理解可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通識教育產生之初,通識教育是指本科教育的一種共同基礎。到20世紀初,科學教育開始對人文教育產生了擠壓,美國大學開展通識教育的理念開始表現為對自由教育價值的回歸,其主要形式是推行分類必修制度,并新設了綜覽概論性科目(the survey course),恢復自由教育那種大綱性質的綜合性、整體性課程,增加學生對社會問題、價值觀、倫理觀等的認識和判斷能力。哈佛大學于1945年發表了《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報告》(即《紅皮書》),科南特提出通識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自由人。這是美國通識教育的第二階段,將自由教育的理念融入到了通識教育之中。在第三階段,美國通識教育開始向公民教育轉向,“自由人”變成了“有教養的人”,后來衍變為培養世界公民。當然,不論是培養“自由人”還是培養“有教養的人”或世界公民,美國大學通識教育十分重視理性培養、批判性思維及普世價值體系的建立,其中人性教育始終是一條不斷的主線,人文教育始終是教育的重點。
從歷史上看,古代中國教育只重文,后來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虧,先進人士大力提倡學習聲、光、電,在這種不斷的追趕過程中全社會重理工輕人文之風逐漸形成。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大學更加突出了專業技術教育,進一步削弱了人文教育。改革開放后,我國曾大力加強了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但多年的實踐并未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過弱的文化陶冶、過窄的專業教育、過重的功利主義導向”的現狀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今日中國的大學,一方面處于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另一方面處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之中,這兩方面交織在一起,形成各種張力,又呈現各種機遇與可能,這就使中國的大學在今天的生存和發展面對新的時代境遇[6]。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中國現代大學應如何開展通識教育?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有很強的包容性與調和性,中國傳統教育蘊涵著追求自由、追求文明、追求進步的強大動力。文化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性教育以“化育成人”為主要途徑。因此,我國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理想應取向于國民性與現代性的融合,要建立世界視野、批判意識和生命意義、人文關懷等觀念,重點是培養當今大學生的文化自覺和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并通過文化自覺致力于現代個體主體性的啟蒙和對生命意義的尋求。在課程層面,不同的大學可以有不同的特色,從人性教育的視角,生命和生態教育、歷史與文化教育、人類學與社會學等課程是必須的。比課程更為重要的是教學方法的轉變,在人的生命的“知”、“情”、“意”中,現代教育只關注了“知”,而對“情”、“意”的教育比較缺乏,新的教學方法應把“事實”與“價值”加以融合,從而促進學生“意義”的生成和心靈的覺醒,從而達到人性教育的目的。
[1]陳云愷.人性教育:全球化時代的教育使命[J].南通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5(3):23-27.
[2]李猛.指向事情本身的教育:奧古斯丁的《論教師》[A].《思想與社會》編委會.教育與現代社會[C].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9:10-12.
[3]吳金華.論教育的人的理念及其構建[J].揚州大學學報,2012(4):3-8.
[4][英]赫胥黎.科學與教育[M].單中惠,等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75-76,59.
[5]劉小楓,陳少明.古典教育與自由教育[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2-8.
[6]熊思東,等.通識教育與大學:中國的探索[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