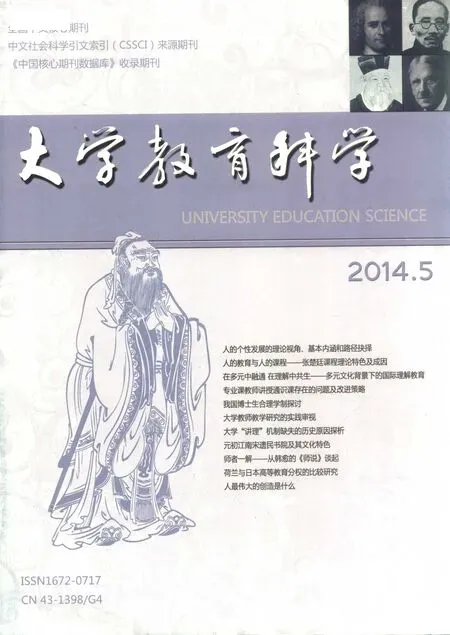書院化的國學教育:問題與改革路徑
□ 田建榮
當前,國學的活躍、書院的興起都是中華文化復興的表現,各地書院建設是“國學熱”的重要組成部分。“書院是弘揚國學的一種形式,國學是書院教育的內容。”[1]書院能夠使國學不停留在一陣風式的暫時熱度上,而為持久的研究、傳承、弘揚搭建起了堅實的平臺,在培育國學人才、養成健全人格、改善社會風尚、傳播民族文化方面,國學與書院的結合使得書院化國學教育的前景更加光明,極易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但濫用書院之名開展國學教育在宗旨、方式和機制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不及時加以糾正、規范和調整,必將會影響國學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國學教育的書院化傾向
從歷史上來看,在中國文化的依附平臺中,“佛家有廟,道家有觀,儒家有書院。”[2]中國的正宗儒學正是從書院中傳承下來的,國學雖然包含儒墨道法等,但主要以儒家思想、四書五經為核心。所以,在“國學熱”逐漸升溫之時,很多民間國學書院便應運而生,它們或扎根山野鄉村,或隱身繁華鬧市,有的是短期興趣班,有的是國學研修班,也有全日制國學教育機構,均面向廣大民眾普及國學知識,解讀中國文化精髓。在這些國學書院里,人們既能看到孩子們身著漢服、手持傳統教材、誦讀國學經典的場景,也能看到成年人正襟危坐、全神貫注、略有所思的神態。
據悉,目前全國以“堂、塾、館、院”命名的民辦國學教育機構達三千多家,開設國學課程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數以萬計,全國有數千萬人學習國學。2010年,教育部等曾發文要求在全國青少年中推廣“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一時很多中小學共推《弟子規》,同讀《三字經》,舉辦經典誦讀比賽。如深圳寶安區中小學采用國學經典誦讀、少兒京劇、國學夏令營等方式吸引了數以萬計中小學生參與,許多學校還開設了每周一節的國學課。同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相繼成立了國學研究院。到目前,我國高校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或相關國學研究機構已近20家。特別是很多國學教育機構都偏愛以“書院”命名。如東有道啟東西的尼山圣源書院、南有深圳梧桐山下的國學書院、西有《白鹿原》中的白鹿書院、北有四海孔子書院。而熒屏里、網絡中、社會上的書院和國學班更是熱鬧非凡,國學和書院“作為古老而新生的社會力量,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推動著中華文化對中國人精神的重新占領。”[3]相比于其他形式,書院可以使國學的內涵得到更好的體現和傳播,使國學教育變得更富正統性和根基深厚。可見,“國學熱”助推了書院的興起,書院的盛行反過來又促進了國學教育的發展。截至2012年底,我國約有591所實體書院,網絡虛擬空間辦的書院有100多所[4],這些基本上都屬于國學書院。國學教育出現了明顯的書院化傾向。
二、書院化的國學教育面臨的問題
1.假國學教育之名,行功利目的之實
國人接受傳統國學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民間熱心人士興辦書院或借書院進行國學教育也是有社會擔當的表現。特別是當前之教育,重智力訓練,輕情商培養;重自然科學,輕人文科學;重分數,輕育人;重外語,輕母語。加之長期的應試教育,偏重學科本位,忽視學生情感品質的發展,導致年輕一代中很多人的道德感、理智感、美感貧乏,理想缺失,價值觀錯位,對長輩不禮貌,人際互動中不負責任,自私自利傾向愈演愈烈等。故重提國學教育,以期矯正現代教育中這種種弊端,不失為一明智之舉,“因為國學自古以來就被看作是人性之學,最講究情感邏輯。”[5]
但民間自發興辦的書院化國學教育機構,由于尚未納入國家教育體制和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的監管范圍,缺乏必要的辦學條件和優良的師資,一些辦學者打著素質教育、人格培養的旗號,撈取利益,使厚重、古樸、深邃的國學變成了他們的斂財工具。這不僅無法保證國學教育奠定傳統做人的規范,甚至連兒童的安全都無法保障,“女德國學班”老師虐打兒童致多處骨折的報道就是典型的案例。而那些動輒收費數萬元的高級國學研修班,更使國學教育變了味。可見,借國學名義誘騙家長、禍害兒童、達致功利目的,不僅給國學教育發展埋下了隱患,還使國學教育聲譽嚴重受損。如果說傳授方式的偏差和師資不足是可以彌補的,那么傳授內容的走偏和目標的嚴重背離則會瓦解國學教育。
2.重國學經典誦讀,輕道德人格訓練
國學的學習是用以改變我們的心性,提升我們的文化素養,這才是國學教育的最終目的。但作為國學教育主陣地的中小學在國學教育內容和學段安排上,如果不遵從教育的基本邏輯,違背教育內部關系基本規律,拋棄循序漸進之原則,將那些連古代教育家也主張暫時緩一緩、等到學生由“蒙館”升入“經館”之后才讀的佶屈聱牙、晦澀難懂的《四書》尤其是《五經》灌輸給兒童,讓孩子從幼兒階段就開始讀經,而且是狹義的儒家經典;同時,不顧兒童個性特點和學習興趣,單純地讓學生死記硬背,使背誦絕對化,這樣過早地讀經,單純地背誦,不僅會導致孩子當下無法把經典學好,只是鸚鵡學舌,沒有入心入腦,而且更可怕的是,會造成學生對經典的恐懼和誤會[6]。當然,中小學生誦讀國學經典時,如果暫時不能理解,沒有太大關系,但我們不能僅僅讓孩子背誦,重要的是讓他們在生活中去踐行。《弟子規》能倒背如流固然好,但得學一句用一句。如“父母呼、應勿緩”,“晨則省、昏則定”,“出必告、反必面”這三句話,孩子們不能只會背,還得去做,這才有國學教育的價值所在[7]。
3.浮于“書院制”模式的吸納,忽視國學教育內容的整合
20世紀80年代重新興起的國學研究也帶動了大學國學教育的開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相繼成立的“國學研究院”還舉辦國學本科試驗班,招收國學方向碩士、博士研究生,為發展高水平、國際化的國學教育研究與人才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書院的名稱與精神在現今我國大學也得到了一定的繼承和體現,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南方科技大學以及眾多的地方院校、民辦高校都相繼成立了本科生書院,實行書院制管理新體系或住宿書院制管理新模式。而國學研究院則專門致力于開展國學課題研究,組織編撰國學叢書或教材,設立國學講座,編輯國學刊物,召開國內、國際學術會議,建設國學網站等。也就是說,在現今大學,書院制和國學教育呈現出二水分流之態勢,一支是研究國學和培養國學專門人才的“國學研究院”,一支是針對大學生進行管理的“書院制”新模式,這兩個系統雖然同時并存,但相互之間卻沒有任何聯系,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現象,有必要將二者在機制上加以有效整合。
三、書院化國學教育的改革路徑
作為一種教育思想,國學教育以優秀傳統文化為核心內容,以培養人的文化素養、人文精神、民族意識以及健全人格為主要目的,這契合了現代教育要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合作、學會生存、學會做人等綜合素質的培養,也是貫徹落實《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增強青少年學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的需要。
首先,應將書院化國學教育融匯到人才培養全過程。據介紹,“臺灣大學不設國學院,傳統文化同文史哲學科聯系緊密,其他學科如經濟系、社會行政系、數學系同國學都有一定聯系。”特別是它們重視“回歸傳統國學情景,回歸書院傳統”[8]。傳統書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書院師生的互相切磋,講學問難,老師的言傳身教和潛移默化,學生在和老師零距離的接觸中,體會、領悟到了那些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真諦。我們希望現代大學的書院制也能進一步完善,開展扎扎實實的國學教育,如同書院制進入學生宿舍一樣,使國學教育深入到大學的課堂,進入到學生的教材,整合進學生的知識體系和結構中去,共同形成一個有機的教育整體,貫穿在大學人才培養的全領域、全過程。中小學的國學教育也應及早滲透在各門學科的教學中。如在語文課堂上誦讀古代經典名著,在數學課中教學生打算盤,在音樂教學中滲透古典民樂,在美術課中增加國畫、書法、篆刻,在體育課中教學生練習中華武術等,并可開設中華飲食、傳統中醫、茶文化、棋類、曲藝等選修課。
其次,國學經典誦讀之外還需踐行書院精神。的確,國學的核心在經典。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是因為它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是真正人文的東西,包括儒家經典、二十五史、諸子百家、詩詞歌賦的名篇佳作。這些經典之作有和諧的音韻、優美的意境、雋永的哲思和優雅的情趣,是真正中國特色的文化。掌握之,有助于提升孩子的情感品質,涵養孩子的文化氣質,幫助中小學生走向成功[9]。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說:“從兒童開始誦讀經典名著,是我們一貫的基本教育方法。”[10]心理學研究表明,兒童記憶儲存的最佳時期是四五歲到十三四歲,此間記憶力旺盛,可塑性強,最宜博記,甚至更適合機械記憶,童蒙時期強調背誦,正好符合了兒童“多記性,少悟性”的年齡特征。但古代“書院把教學與訓育結合起來,提倡教德完善,注重人格教育,形成了一種重視人格陶冶的書院精神。”[11]書院教育家強調踐履既是道德修養的重要方法,又是德育的根本目的,并將其制度化為章程、學規等形式,使書院重視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顯現出來[12]。如此,將書院精神融入到現代學校教育中,就是要在辦學宗旨上注重人格訓練,課程設置上以經典通識課程為主,于課堂講授之外,著重培養學生個人讀書、自我成長的習慣與能力[13]。總之,學習國學,踐履規范,對于實現各級各類學校立德樹人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再次,增加國學教育內容在中考、高考和高校學業考試中的比重。現代國學教育的出現,本是將教育引向個性化、多樣化的積極探索,是值得肯定和應該支持的。所以,作為現代教育體系的一種補充和國學教育的一種形式或者載體,現代私塾、書院、國學研究機構都不應該簡單地被取締,有關部門應盡快出臺相關的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給予社會上的私塾、書院一定的發展空間,并合理引導,有效監管,以滿足學生和家長多樣化的教育需求,促進現代國學教育蓬勃健康發展。然而,受應試教育影響,若不將國學教育納入“應試”的范圍,國學對于中小學生而言終究是“可有可無”,故要增加國學教育內容在中考、高考升學考試中的比重,這樣才能使優秀傳統文化之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真正得到落實。同時,高等學校應探索將書院制與國學研究院整合起來的機制和辦法,通過開設國學通識教育課程、選修課程,在書院制與國學教育之間架起橋梁,做到彼此支援和相互配合,共同促進大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和各自機構職能的充分發揮。對于文史哲學科,特別是理工、師范類專業,還應規定每個大學生必須修滿一定的國學教育科目、考試合格后方能畢業。只有這樣,書院制才會更具內涵且不僅僅起符號的意義,國學研究院也會走出象牙塔,惠及更多學科和師生,促進現代大學的大發展、大繁榮。
最后,書院和國學研究院應合力培育優良國學師資。高校以其自身的優勢,理應成為新時期開展和推廣國學教育最重要的基地和將書院與國學教育結合起來的典范。但當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國學學位,因此,具有專門國學學科背景出身的國學專職教師的職前培養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在這方面,現存的國學書院,如岳麓書院乃人文底蘊最厚重之千年學府,必須為社會上的書院式國學教育機構和中小學國學教育培育優良師資和接受教師職后培訓,而那些建有國學研究院的高校不僅應營造本校書院氣息和國學氛圍,還理應與書院制結合并通過書院擔當起為各級各類國學教育機構提供人才和學術支持,造就數量充足、品德優良、國學功底深厚的國學教師,因為社會上的國學教育亂象主要還是與師資不足、不優有關。當然,國學幾乎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整個領域,可謂博大精深,高校國學教師自身也需要經過相當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實踐,以全面適應國學教育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要求,鞏固高校國學教育重鎮地位。
[1]王璟,張萍.書院:國學復興的顯性路徑[N].精品購物指南,2009-08-17(7).
[2]陳希琳,孫慕遙.私塾化的國學[J].經濟,2011(9):115.
[3]王嚴立玲.千年書院:不能總擋在體制外[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12-08(8).
[4]王薇,葉婧,潘林青.國學書院悄然復興:小眾教育前景如何?[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3-06/21/c_116237641.htm,2013-06-21/2014-07-18.
[5]任民.從《弟子規》看國學教育的情感向度[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51.
[6]徐梓.國學教育的亂象及治理[N].光明日報,2014-07-01(15).
[7]張妮,陳徑舟.少兒國學教育:誦讀之外還需踐行[N].中國文化報,2014-4-7(2).
[8]王紹培.國學教育:熱鬧背后隱憂重重[N].深圳特區報,2013-10-28(B05).
[9]李迎春.論國學教育的文化向度[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59.
[10] 陳杰思.國學復興方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55.
[11] 朱永新.書院精神對于當代大學教育的啟示[J].江蘇高教,1994(2):67.
[12] 李兵,朱漢民.中國古代大學精神的核心——書院精神探析[J].中國大學教學,2005(11):63.
[13] 劉桂秋.“以家塾組織,參書院精神”——梅園豁然洞讀書處辦學特色初探[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4):119.